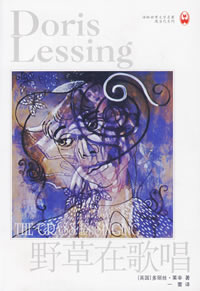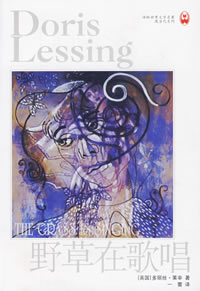 《野草在歌唱》
《野草在歌唱》叢書名:世界文學名著·現當代系列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ISBN:9787806570104
出版時間:2007-1-1
版次:1
印次:2
頁數:231
字數:166000
紙張:膠版紙
包裝:平裝
內容提要
瑪麗是南部非洲土生土長的白人,自幼家境貧困使她本能地渴望擺脫這種與土著黑人相似的生存狀況。工作後,她的生活一度有所改善,但在迫於社會壓力結婚之後,她絕望地發現自己走回了母親的老路。黑人僱工摩西的闖入打破了她麻木混沌的生活,使她有了新的生存力量。然而種族歧視的烙印深深地打在南部非洲每一個人的身上,注定了他們所面臨的必將是一個悲慘的結局。
編輯推薦
多麗絲·萊辛是一位極富創造力的女作家,而最初哺育她、給予她豐厚的生活積累和創作靈感的正是南部非洲那片土地。一九二四年,在她五歲剛剛記事時,就隨全家遷居非洲的南羅得西亞。在父親經營的大農場裡,她經常拉著小弟弟哈里的手,在遼闊無邊的草原上漫遊,那兒的一草一木和風土人情,對她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也培育了她對那片土地和非洲人民的深厚感情。萊辛從小就是一個性格獨立、敏於思索的孩子,幼年時曾在女修道院和女子公立學校讀過書,可是十三歲時因患眼疾被迫輟學回家,從此便開始頑強地自學成長。萊辛父親經營的農場常年歉收,全家人的生活一直在艱難貧困中勉力維持。萊辛十六歲時便去電話公司做接線員,以後又做過打字員和秘書。她在晚年的回憶中把自己在非洲的生活經歷稱做是“一生中最大的幸運”,因為這段經歷為她提供了一般英國中產階級姑娘所無法獲得的生活體驗,也為她日後的創作積累了原始的素材。一九五○年,她的處女作《野草在歌唱》一問世,便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因為小說向西方讀者第一次毫不掩飾地展現了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部非洲的社會現狀,描述了貧窮的白人移民艱難的求生歷程。而在此之前,非洲大陸在西方人的眼中只是一片蒙昧的黑色大陸,難得有旅遊觀光者涉足那塊土地,人們對於它的認識,僅僅局限於抱有種族偏見的白人作家的片面詮釋。
《野草在歌唱》觸及了萊辛創作中一再表現的主題:婦女的生存環境及其社會地位、種族歧視制度和文化歷史背景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書中通過對女主人公瑪麗具有典型意義的悲劇命運的描寫,深刻揭示了殖民統治制度下不同種族、不同階層人與人之間的本質關係,剖析了造成瑪麗悲慘結局的社會根源。
瑪麗的童年生活是在貧困中度過的,落後閉塞的鄉鎮和成天吵鬧的父母在她心中投下難以抹去的陰影,她從小就從大人那兒接受了仇視“黑種窮鬼”的教育,儘管她和全家人同樣在經濟拮据中忍受著煎熬。這種現實與理念相悖的教育,使瑪麗的心理從幼年時期起就未得到健康的發展。不過,作為一個逐漸長大的女孩,無論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上,她都渴望擺脫貧窮和壓抑,過幸福自由的日子。當她跨出寄宿學校的大門,終於在一家公司找到職位後,她甚至對單調刻板的工作感到滿意,因為她自認為在經濟上已經完全獨立,從此可以不受任何干擾地生活下去。由於幼年時目睹家裡的爭吵打鬧和父親的邋遢潦倒,使她對男性和婚姻有一種本能的抗拒,她希望永遠過單身自由的日子。但是到了三十歲,人們的異樣目光和惡意議論使她感到惶恐不安,世俗偏見逼迫她終於意識到:必須找一個丈夫。遇到迪克後,她雖然不愛他,卻迫切地想立刻結婚,因為她心中隱隱約約地把期望寄托在迪克的農場上,認為那兒一定充滿了自然的氣息。
可是殘酷的現實在她渴求獨立遭受失敗後,又給了她沉重的一擊。迪克雖然本性善良卻固執無能,家中一貧如洗,慘澹經營的農場也年年虧損。瑪麗用盡了自己所有的積蓄來改善家中的布置,可是這既改變不了窮困的境況,也擺脫不了精神上的失落感;日復一日,瑪麗在破敗的房子裡打發著沉悶空虛的日子。終於,在極度的痛苦中她決定逃離褊狹的農場回到城裡去,這是她向生活所做的唯一一次抗爭。可是她原先任職的公司拒絕了她,這個城市的其他地方也不接納已婚的女人,在人們眼中,她的社會身份已經從經濟獨立的白領女子轉變為寒傖可憐的鄉下女人。於是,她只能心灰意冷地跟隨尋她而來的迪克回到農場,回到與她母親的命運幾乎毫無差別的生活中。她在生活中第二次被挫敗了,這次打擊幾乎使她變得麻木,但是迪克卻在此時染上瘧疾,現狀迫使她必須面對面地和農場上的黑人僱工打交道。
她先前接受過中等教育,也受過民主平等思想的影響,甚至在初次聽到迪克稱黑人傭工為“老畜生”時,還憤憤不平地覺得他沒有教養;但是“黑人品性頑劣、不可信任”的種族歧視觀念早已牢牢地紮根於她的思想深處,這種觀念使她本能地對黑人充滿了敵意和戒心。當她手 執皮鞭監視黑人幹活時,她心裡竟然感到十分踏實,當她揚起鞭子對準不馴服的摩西臉上抽下去時,雖然心中掠過一陣恐懼,但最終卻體驗到征服者的得意。在瑪麗身上發生的這種現象,在接受過英國文明教育的青年托尼身上也不難見到。先進的民主平等思想對於他們只是空泛的概念,根本不可能在現實中實踐,這是他們在殖民制度下的社會中的奴役地位所決定的,但這也鑄就了瑪麗的悲劇。因為一方面由於社會、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因素,她完全不能自主個人的命運,只是一個可憐的受命運擺布的弱者,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是一個凌辱欺壓黑人的白人僱主。這種人格分裂的狀況,使她的內心體驗和道德判斷一直處於痛苦的矛盾中,每次對黑人濫施淫威後,她總是被更加歇斯底里的絕望所吞沒。與此同時,迪克的精神也日益頹唐,在瑪麗的眼中,他不過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體。窮困潦倒的生活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然而生存的本能使她乞求一種外來的變更,她想生一個孩子陪伴自己,可這一回是迪克冷酷地用貧困的理由否定了她做母親的權利。
生命的支撐點眼看就要傾倒,作為一個女人,儘管她身上帶有鮮明的種族歧視的烙印,可在潛意識裡,她還是渴望著安慰、愛撫和力量。因此,當她忍不住當著摩西的面痛哭失聲後,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這個黑人對她表示的善意安慰。以後,她又被摩西強健的體格和沉靜果斷的舉止所吸引,而摩西似乎也細心地體察到她的苦悶心境,總是在生活上盡力照顧她。在他們倆關係微妙變化的過程中,瑪麗已經在內心對迪克和摩西進行了選擇,儘管她自己並未清醒地意識到這種選擇及其後果。她的思想成天跟隨著摩西的蹤影,可同時她又對自己的感情覺得恐懼,恐懼中還夾雜著對摩西作為黑人的憎恨。排斥與渴望的力量在她內心劇烈地衝突著,這種衝突實際上是還未完全泯滅的良知與被扭曲的人性之間的抗爭。瑪麗最終和摩西發生了曖昧的關係,這種關係在當時的南部非洲是諱莫如深的,萊辛不僅大膽地觸及了這個敏感的問題,而且尖銳地指出了這種關係在本質上無法逃脫階級屬性的事實。一方面,瑪麗在肉體上和某種感情寄託上需要摩西,但另一方面,她決沒有忘記他們之間的種族差別和僱傭關係,依舊時常以女主人的身份對摩西吆三喝四。這種不正常的關係是無法長久維持的,瑪麗和摩西的心中都隱約地感覺到有一個可怕的結果在等待著他們。果然,他們沒有逃過種族歧視社會的道德監視。英國來的青年托尼發現了他們的秘密,震驚之下,他覺得瑪麗簡直是跟野獸發生了關係,雖然他以前對白人統治階級的某些偽善行為很反感,並且一直為自己具有平等的先進思想而驕傲,但他此刻卻憤怒地感到白人的尊嚴受到了玷污,於是他立即以白人衛道士的面目嚴厲呵斥摩西滾開。托尼強烈的種族歧視態度似乎喚醒了瑪麗的白種人意識,她馬上站到了托尼的立場上,冷酷無情地叫摩西快滾。事後她又痛悔地哭泣,這種矛盾的兩面性注定了她的悲劇結局。在她終於認識到那個英國青年無法從精神上拯救自己的同時,她也看透了自己;在生命的最後一個黎明,她無限留戀地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變幻中,她能感受到無數小動物的生命搏動,可她知道自己面臨的只有毀滅。社會制度無疑是造成瑪麗悲劇的主要根源,但是她本人的弱點也是不可否認的因素。瑪麗·特納的性格完全不同於萊辛以後塑造的女性形象。瑪麗在精神上始終被動地接受環境和命運的擺布,她從未真正理解過自由的本質含義,狹隘的種族意識又妨礙了她對社會與自身的關係做深刻的思考,這一切加速了她走向悲劇的進程。
萊辛在小說中不僅描寫了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而且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在南非殖民制度統治下,生活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境況下的白人移民之間,同樣存在著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迪克和查理就是這兩類人的代表。像無數貧窮的白人移民一樣,迪克滿懷美好的願望,期冀在南部非洲創立家業。他老實善良,一心一意地在農場上埋頭苦幹,可是由於缺乏精明的經營管理和盲目施行不切實際的計畫,結果土地只能被查理那種善於巧取豪奪的暴發戶所侵吞。貧富白人移民之間的爭奪兼併是當時南部非洲的一個殘酷現實,萊辛筆鋒犀利地揭掉了蒙在白種人關係上的虛偽面紗。查理在強行買下他稱之為“同種族兄弟”的土地時,竟然還非常動情地說這是“為了使白人兄弟不致敗落到過於悲慘的境地,否則黑鬼們就要自認為和白人沒有區別了”。當他看著迪克痛苦地抓起一把泥土不忍放棄農場時,他心中甚至懷疑自己對迪克是否太拖泥帶水,違背了自己一貫恪守的生意原則。善良懦弱的迪克被查理的“善行”推到了絕境,而查理及其白人掠奪者們在必要的場合下,依舊不忘表現出“維護白人團結”的面目。他們偽善的外表和貪婪的本性被萊辛冷靜的筆觸刻畫得十分逼真,只有對南非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有本質認識的作家,才會有這樣準確的描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萊辛在小說中以充滿人道的理解和同情,把黑人視作和白人一樣具有愛憎感情的人來描寫。而在以前一些以非洲為題材的小說中,黑人大多被醜化成懶惰愚昧、聽任宰割的可憐蟲。摩西的形象在小說中沒有被簡單地面具化,雖然萊辛沒有像描寫瑪麗那樣描寫他的心理活動,但是他的言語舉止使我們從不同的側面比較完整地看到了一個具有個性的黑人。摩西和瑪麗的第一次相遇發生在彼此身份完全對立的場合下,他是出賣勞力的僱工,瑪麗則是心腸冷酷的僱主。當摩西無端被瑪麗狠抽了一鞭子後,仇恨和輕蔑的目光幾乎使瑪麗嚇破膽。但是後來當他到迪克家幫傭,目睹瑪麗在貧困和絕望中度日時,他以寬厚的態度諒解了瑪麗平日對他的苛刻,答應她繼續留下來幫工。在他感覺到瑪麗對他的態度逐漸和緩後,他盡己所能地照料她的生活,甚至從山上采了野花笨拙地插在一起送給瑪麗,希望給她一些安慰。這個小小的細節使人看到一個普通黑人的內心也同樣具有美好細膩的感情。從他和瑪麗不斷發展的關係來看,應該說是他的質樸和寬厚首先觸動了瑪麗內心那點還殘留著的良知。摩西對自己所處的生存環境也沒有顯出渾渾噩噩俯首認命的奴性。他曾問瑪麗:“難道耶穌認為人類互相殘殺是正當的嗎?”這樣尖銳的問題使瑪麗聽了無言以對。除了純樸寬厚的一面,摩西的個性中還有血氣方剛的另一面,當他看見瑪麗殘忍地站在那個沒有心肝的白人一邊,態度堅定地叫他滾開時,屈辱和憤怒在他心中燃起了復仇的火焰,使他舉刀殺死了瑪麗。可是放下刀後,他卻站在雨中等待著人們來追捕他,這一舉止使人感受到他內心經歷著複雜的感情波動。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具有個性特徵的黑人形象,使讀者覺得真實可信。
萊辛一向注重個人對生活的心理體驗,並以心理活動描寫見長,這一特點在《野草在歌唱》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瑪麗在生活變動和感情經歷中的每一絲心理變化都被細緻入微地記錄下來,讀者在跟隨女主角內心體驗的過程中,逐漸加深了對醜惡的殖民制度的認識。此外,用周圍景物和環境氛圍來烘托人物身心崩潰的狀態,是萊辛創作手法的又一特點。瑪麗臨死前頻頻出現的雷聲與閃電,與她對末日來臨的緊張恐懼融合在一起,給人以強烈的印象。西方評論家普遍認為,她的這種手法與英國作家喬治·埃略特和D.H.勞倫斯的風格十分相似。萊辛的傑出才華和不知疲倦的追求精神,使她在以後的創作中不斷變換寫作題材和表現手法,她的想像力在現實世界和宇宙空間任意馳騁,然而貫穿在她所有作品中最鮮明的特點是她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注和嚴肅思考。無論是在人們熟知的《暴力的孩子》、《金色筆記》中,還是在其他數量可觀的中長篇小說以及晚年創作的太空科幻小說中,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始終清晰可見。如今,隨著她的小說被譯成多種文字——尤其是《金色筆記》——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這位當代傑出的女作家已獲得越來越多讀者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