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這個群山環繞的腐朽山洞裡
在淡淡的月光下,野草在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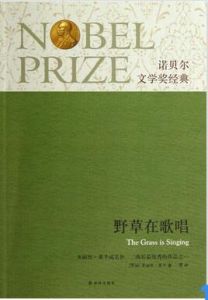 野草在歌唱
野草在歌唱瑪麗是南部非洲土生土長的白人,自幼家境貧困使她本能地渴望擺脫這種與土著黑人相似的生存狀況。瑪麗小時候,她的父親很厭倦自己的工作,並把這種不滿發泄到家裡。瑪麗的母親忍受著貧困和自己丈夫的雙重壓迫。瑪麗在缺少家庭溫暖的環境中長大,對性充滿了恐懼,她認為這是女人必須接受的懲罰。工作後,她的生活一度有所改善,但在迫於社會壓力結婚之後,她絕望地發現自己走回了母親的老路。她的丈夫迪克專心於農村的工作,對瑪麗十分冷漠。他們過著分居的生活。黑人僱工摩西的闖入打破了她麻木混沌的生活,使她有了新的生存力量。她被摩西所吸引並同他發生了關係。然而種族歧視的烙印深深地打在南部非洲每一個人的身上,注定了他們所面臨的必將是一個悲慘的結局。瑪麗和摩西的關係被人發現,瑪麗受社會壓力所迫,拋棄了摩西。摩西盛怒之下殺死了瑪麗,平靜報案等待被捕。
作者簡介
作者:(Doris Lessing)(英國) 中文譯名:多麗絲·萊辛
多麗絲·萊辛1919年10月22日出生於伊朗東北部的一個貧困家庭,原姓泰勒。父母是英國人。
在萊辛5歲時,迫於生計她全家遷往非洲的辛巴威,此後20餘年家境貧困。她15歲(又有說是12或13歲)時因眼疾輟學,在家自修。16歲視力漸漸恢復,便開始工作賺錢養家,先後當過電話接線員、保姆、速記員等等。她青年時期積極投身反對殖民主義的左翼政治運動,曾一度參加共產黨。1939年同Frank Charles Wisdom結婚,生下一兒John,一女Jean。1943年離婚,這段時間後來被萊辛描述為坐牢。2年後萊辛嫁給Gottfried Lessing生有一子Peter。1949年,萊辛離婚攜帶幼子Peter回英國尋找生機。當時她經南非開普敦搭乘客輪前往英國。此時,兩手空空,囊中如洗的她,全部家當只剩背包中的一部反映非洲生活的小說草稿。她拿著這唯一的籌碼去一些出版社碰運氣,結果卻到處碰壁。在半個月裡,她幾乎敲遍了整個倫敦所有出版社的大門。該書終以《野草在歌唱》(1950)為題被一家出版社出版。
然而,這卻使萊辛一舉成名。小說以黑人男僕殺死家境拮据、心態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案件為題材,側重心理刻畫,表現了非洲殖民地的種族壓迫與種族矛盾。
多麗絲·萊辛代表作品為五部曲:《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孩子們》、《簡述下地獄》、《第三、四、五區域間的聯姻》、《簡·薩默斯日記》等。
2007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2007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這位英國女作家。她成為了歷來第三十四位女性諾貝爾獎得主,在文學獎則是第十一位。
這一天,離她88歲生日還有11天,她是目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最高齡者。
頒獎公告這樣說:她用懷疑主義、激情和想像力審視一個分裂的文明,以及她那史詩般的女性經歷。(epicist of the female experience, who with skepticism, fire and visionary power has subjected a divided civilization to scrutiny)
創作背景
《野草在歌唱》的創作以非洲殖民地的種族壓迫與種族矛盾為背景。
20世紀30年代處於英國殖民者統治之下的南非南部草原發生了一起悲劇:一位土生土長的白人婦女瑪麗被一名黑人男僕摩西殺害。作者圍繞悲劇事件展開了小說的創作。
編輯推薦
《野草在歌唱(修訂本)》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文摘
第一章 神秘謀殺案
本報特約記者
恩澤西農場主理察·特納之妻瑪麗·特納,於昨日清晨被發現受害於住宅陽台上。該宅男僕已被逮捕,對謀殺罪供認不諱,唯謀殺動機尚未偵悉,疑涉謀財害命。
這則報導很簡略。全國各地的讀者肯定都看到了這篇標題觸目驚心的報導,都難免感到有些氣憤。氣憤之餘又夾雜著一種幾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種想法得到了證實,某件事正如預期的那樣發生了。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盜竊、謀殺或是強姦罪,白人就會有這種感覺。
接著人們便把報紙翻過去看別的訊息。
但是在“這個地區”里,凡是知道特納夫婦的人,不論是見過他們面的,或是這些年來一直聽到閒言碎語議論他們的,都不急於把這一版翻過去。有許多人必定還會把這則訊息剪下來,和一些舊的信件放在一起,或是夾在書頁里,要將它作為一種警示或一種告誡保存起來,日後好帶著緘默和神秘莫測的表情瞧一瞧這片發黃的紙。人們並不討論這件謀殺案,這是事情最出奇的地方。當時有三個人本可以把事實詳細敘述一番,結果卻一言未發;儘管如此,人們好像都有一種第六感,認為已經把該弄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謀殺案根本就沒有引起人們的議論。要是有人說:“這事很糟糕。”四周的人們都會顯出冷淡而謹慎的神色。然後有人回答:“太糟了!”——話題就此終止。似乎大家都一致默認,特納家的這個案件不該隨隨便便地談開。這是一個農業地區,在這裡,一戶戶的白人家庭彼此相距很遠,他們待在各自的農場上,接連幾個星期只能看到自己家裡人和奴僕們的黑臉;他們難得有機會見面,總是渴望著和同種族的人來往,在見面時高談闊論一陣,爭執一番,七嘴八舌地扯上一會兒,盡情地歡聚幾個小時,然後再回到各自的農場上。在平時,這件謀殺案一定會討論上好幾個月;人們有了談助,一定會興致勃勃才對。
在一個局外人看來,人們這樣默不作聲,大概是那個精力旺盛的查理·斯萊特跑遍了地區所有的農場,關照人們不要聲張的緣故;但是查理絕不會想到這樣做。他所採取的步驟(而且他一個錯誤也沒有犯)顯然是想到哪裡就做到哪裡,並沒有刻意去籌劃安排。整件事中最耐人尋味的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默不作聲。這舉動就像一群似乎在用精神感應的方式互相交流的鳥兒一樣。
遠在這件謀殺案使特納夫婦聲名遠揚以前,人們談到他們時,語氣總是那樣尖刻和隨便,好像是在談什麼怪物、歹徒或自作孽的人一樣。鄰居當中雖然很少有人碰到過特納夫婦,有些只是隔得遠遠地見過他們,但是大家都討厭他們。這對夫婦究竟為何如此惹人討厭呢?就因為他們“落落寡合”,僅此而已。當地的舞會、宴會或是運動會上從來看不到他們的身影。這對夫婦一定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這就是人們的感覺。他們不應當那樣與世隔絕,因為那樣做就等於在每個人臉上打了一記耳光;他們有什麼值得神氣活現的?喔,說真的,過著那樣的日子,有什麼可神氣的呢!那小籠子一般的房子,臨時住住還說得過去,但決不能作為永久的住所。可不是嗎,有些土著黑人的房子也抵得上那種樣子(謝天謝地,這種土著黑人並不多):白人住得這樣簡陋,當然會給人們留下很壞的印象。
那么這就是有些人所謂的“窮苦白人”。於是人言噴嘖。那時候還沒有很大的貧富懸殊(那時也沒有菸草大王),不過種族的劃分當然已經存在。那一小群“南非白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英國人對他們很瞧不起。所謂“窮苦白人”原本指的是南非白人,而決不是英國人。可是把特納夫婦說成是窮苦白人的那些人,一反傳統的說法;自有他們與眾不同的見解。其中究竟有何不同?怎樣才算窮苦白人?這主要由生活方式所決定,也就是生活水平的問題。特納夫婦只需要再有一群兒女,就會成為地道的窮苦白人。
雖然這種見解無可置辯,大多數人卻依舊不願意把特納夫婦看成窮苦白人,否則未免有失體統,因為特納夫婦畢竟還是英國人。
當地人對待特納夫婦的態度,原是以南非社會中的首要準則,即所謂“社團精神”為根據的,可是特納夫婦自己卻沒有理會這種精神。他們顯然沒有體會到“社團精神”的必要性;的確,他們之所以遭忌恨,原因正在此。
你越想就越覺得這樁案件離奇。離奇並不在於謀殺案本身,而在於人們對這樁案件的感受,在於人們同情迪克·特納,卻極其怨恨瑪麗,好像她是什麼令人厭惡的骯髒東西,被人謀殺了正是活該。不過人們並沒有問什麼問題。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野草在歌唱》表現的主題:婦女的生存環境及其社會地位、種族歧視制度和文化歷史背景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書中通過對女主人公瑪麗具有典型意義的悲劇命運的描寫,深刻揭示了殖民統治制度下不同種族、不同階層人與人之間的本質關係,剖析了造成瑪麗悲慘結局的社會根源。
《野草在歌唱》觸及了萊辛創作中一再表現的主題:婦女的生存環境及其社會地位以及種族歧視制度和文化歷史背景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瑪麗一生的悲劇不僅在於她無法擺脫種族歧視和殖民者的心態,更在於婦女深陷無法獨立、無法自主的困境:瑪麗原本憑藉自己的努力在城裡獲得經濟獨立和一定的自由,但迫於“世俗偏見”的壓力嫁給她並不愛的迪克後,婚姻痛苦,她一度從農場逃回城市,但當時的社會並不能為已婚女人在家庭之外提供立足之地,因此,她只能再次回到農場,麻木地繼續無希望的生活。譯者對瑪麗充滿同情,指出“作為一個女人,儘管她身上帶有鮮明的種族歧視的烙印,可在潛意識裡,她還是渴望著安慰、愛撫和力量,因此她發展了和摩西的曖昧關係。瑪麗被 看作種族主義的受害者,認為她“受過民主平等思想的影響”,內心也曾有過對黑人的同情,但無奈種族歧視的種子在她心裡根深蒂固,這最終導致了她的死亡。譯者還將瑪麗與萊辛作品中一以貫之的“自由女性”主題聯繫起來,指出瑪麗“在精神上始終被動地接受環境和命運的擺布,她從未真正理解過自由的本質含義”,這也是造成瑪麗悲劇的“不可否認的因素”。總之,譯者雖並未從女性主義角度解讀小說,但指出了婦女的生存環境這一作品主題,深刻地認識了瑪麗在種族歧視思想和傳統婦女觀念中所面臨的困境。
寫作手法
象徵與暗示
1、野草象徵著摩西為主要代表的南非黑奴
作為殖民統治的犧牲品, 以摩西為代表的南非黑奴像荒原中的野草一樣,“烈日噴炎曬不死, 嚴寒冰雪鬱鬱蔥蔥。”在殖民者的任意宰割、壓榨和摧殘之下,不屈不撓,奮力反抗、吶喊。黑奴摩西第一次出現在讀者面前是在小說的第七章, 瑪麗的丈夫迪克由於虐疾的突然襲擊等原因,迪克病倒了。為了生計瑪麗不得不代替丈夫下地監督黑奴們幹活。小說中有一段震撼人心的場面發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南非土著人受白人虐待的真實寫照, 這樣的血腥場面在南部非洲的殖民地土地上屢見不鮮,摩西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五十年代的非洲處於西方殖民者的統治下, 種族歧視在非洲這塊廣袤的土地上橫行肆虐著, 土著黑人生活在社會的邊緣,他們的處境也非常悲慘。黑人被殖民統治者視為骯髒的、懶惰的、野蠻的、暴力的劣等民族。就像小說主人公瑪麗一樣,會因為黑人“臭”便罵他們“不要臉”;在這塊殖民地上,白人可以隨意像牲口一樣隨意買賣,沒有自己的話語權,也沒有做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禁止黑人在白人的飯館吃飯,不容許黑人和白人同乘一輛公車。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當他被女主人瑪麗鞭打時,“摩西舉起粗壯的大手擦去臉頰流淌的鮮血,他的眼睛裡有一種陰沉和憎恨的神情,而使她難堪的是那種帶有譏嘲的輕蔑的神色。”他用簡單而有力的反抗方式讓瑪麗丟掉了盛氣凌人的武器, 不得不把他當作一個人來對待。也正如小說結尾所講的那樣,在女主人一而再再而三侮辱、壓迫和摧殘之下,摩西再也沒有忍下去,反而拿起鋼刀結束了瑪麗的生命,達到了復仇的目的。由此, 看到題目與內容先悖後的疑惑得到了解釋:黑人摩西正是一株“歌唱的野草”。 摩西殺害了瑪麗,按照常理他是一個殺人惡魔,然而在萊辛的字裡行間根本找不到任何對摩西的譴責, 更多的是對他的讚揚和肯定。萊辛正是通過塑造摩西這一形象來填補標題留給讀者的空白。
2、野草象徵和暗示著荒蕪的非洲自然
小說中萊辛多處揭示了殖民者推行的工業化給非洲這塊美麗的土地所帶來的惡果。在這個“被金融巨子和開礦大王——首創建起來的南部非洲。 ”英國殖民者為了謀取更大的利益, 肆意擴張和掠奪非洲南部的土地資源,根本不顧生態環境的保護,開墾土地,濫採礦石,分割土地,耕種作物。為了牟取暴利,竟然違背自然規律一味地在土地上種植 “邪惡的農作物”——菸草。使得許許多多的良田變成了貧瘠的荒原。正如作者所描述的萊斯特農場一樣,“萊斯特先生的農場上簡直沒有什麼樹,這足以證明他耕作無方;農場上犁出了一條條大溝, 許多畝烏黑肥沃的好地都因為濫用而變得貧瘠。然而他畢竟賺到了錢,這才是最重要的。”“他們一年一年地榨取這些土地, 卻從來沒有考慮過施肥,......即便是像他那樣的肥沃農場,也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最後“他不再每年賺成百上千的錢了,土地荒蕪了。”
3、瑪麗的象徵與暗示
瑪麗這個名字在英文中意味著生活艱難辛苦,反應遲鈍,同時也暗示了她一生注定要受窮受苦,落寞孤獨之苦。她的名字與耶穌基督的母親聖母瑪利亞同名,暗示著她原本有著像聖母瑪麗亞一樣生養子女, 撫育子女的偉大天性。比如在第八章中,當瑪麗意識到她和丈夫迪克的生活沒有生氣、希望渺茫時,要求她的丈夫與她生一個孩子,以此來慰籍空虛的精神世界。然而迪克以生活拮据無力撫養孩子為由拒絕了她的要求。從作品評析及其它而不但生不出拯救人類的救世主, 就連一個普通女人最基本的做母親的權利都被剝奪了。萊辛用含而不露的象徵手法,儘可能地挖掘了作品的深度。在作者看來, 小說的女主角瑪麗是一個既值得同情又值得憎恨的女性。同情的是,她生活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雖然是白人,從小卻家境貧寒、父母不和,早就了瑪麗厭惡男人和婚姻的畸形性格。她逃避家庭,在城裡過著獨立而閒散的單身生活, 本想繼續這種自在的生活,卻迫於社會輿論和世俗偏見,選擇了婚姻。在她嫁給貧窮而懦弱的農場主迪克之後, 發現他們的婚姻是失敗的。這場婚姻一步步把她帶入深淵,直至毀滅。從這個意義上講,她既是一個父權和夫權思想下的受害者,又是種族隔離社會下的犧牲品;憎恨的是,她愚昧而教條式地奉行種族主義,欺壓黑人,從這個意義來講,她的死是咎由自取的,不值得惋惜。
4、摩西的象徵與暗示
“摩西是《聖經》里一個神聖的形象,他是一位先知,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摩西這個人物形象就是以聖經中的摩西為原型來塑造的。” 小說中的摩西是主人公瑪麗的僕人, 這個名字象徵著瑪麗心靈拯救者和反抗種族歧視的黑人領袖。在小說中摩西被塑造成一個誠實、善良、勇敢的,有著獨特個性和人格魅力的黑人。讀者無法從小說中了解到他的身世, 只知道他是千千萬萬個在殖民統治下“一個連狗不如的黑奴”之一,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生存境地。但是,摩西卻完全不同於其他被“愚化”的黑奴,“他倔強自立、勇敢善良、敢愛敢恨”,當女主人瑪麗舉起鞭子無緣無故地抽打他的臉時, 他有力地舉起粗壯的手憤然擦去眼角的血跡,不但沒有害怕退縮,反而用一種陰沉、憎恨、譏諷和輕藐的神情注視著瑪麗,他用這樣一種無聲的方式進行了反抗, 使得瑪麗感到難堪,心驚膽顫,使得瑪麗乖乖地低下了那顆高傲的頭。正如一些評論家所說的:“瑪麗是白人殖民主義種族歧視政策最大的犧牲品和受害者, 他在殖民地成長的過程也是她的人性逐漸被扭曲而最終走向毀滅的。”瑪麗的丈夫迪克是一個懦弱、固執,背運的也不懂生活情調的人,她的生活單調,本身還有一種清高卻又自卑的性格,不願與鄰居和外人交流,和丈夫沒有性生活。他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枯燥無味, 精神處於快要崩潰的邊緣。而摩西的出現,無形中給瑪麗的生活帶來了一抹綠色和希望,也滿足了她心理的需求。摩西的忍耐、還有對女主人的無微不至的關懷使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男人的關懷。雖然在她的內心中對這個黑人有了好感和愛的情愫, 但是由於她像其它種族歧視者一樣對黑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憎恨, 不敢大膽地接受這個黑人。終於, 在白人青年托尼發現了他們之間的不正當的關係後,瑪麗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呵斥責罵摩西。不堪忍受屈辱的摩西終於忍無可忍了, 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結束了瑪麗的生命。”瑪麗的被殺結束了她短暫的人生也同時使她從內心的痛苦中得到了解脫。”,“在她異常痛苦之時, 黑奴摩西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類似拯救者的角色。”
5、房子的象徵和暗示
瑪麗和迪克居住的那個蓋了鐵皮屋頂的房子像一個牢籠,不但囚禁住了她的肉體,而且禁錮住了她的靈魂,讓她的希望之火在這裡逐漸息滅。自瑪麗住進鐵皮房子的那天起, 她就被封閉起來了, 與外界失去了聯繫。“四方形的小屋孤零零地建在荒僻的大草原上,附近沒有人家,從外面看上去,房子是緊閉的、漆黑的、窒息的,到處透著一種陰冷的氣息......裡面又小又低,散發著霉臭味,家徒四壁。”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那寒酸的房子就是對未來要過的窘迫生活的預兆。到了夏天,這個蓋了鐵皮屋頂的房子“熱得使人要發瘋”。在這個完全與世隔絕開來的陋室里,她度過了她的餘生,在這裡她始終感受的是窒息和腐敗,不在沉淪中吶喊,就在沉淪中死亡。
6、天花板的象徵和暗示
從瑪麗住進鐵皮房的那天起, 她就發現房子沒有天花板,她曾多次要求丈夫迪克把天花板裝上,但都由於生活拮据, 裝不起天花板等理由未能實現瑪麗的這個夢想。天花板就像他對迪克的期望,隨著一次次地提出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她對她眼前的這個男人也不抱任何的期望了。她處於一種心灰意懶、破罐子破摔的絕望狀態中。萊辛通過這樣一個意象,不僅深刻地反映了瑪麗一家的生活艱辛的處境, 而且還暗示了瑪麗希望改善生活,改變命運的希望注定要破滅的。這樣的寫作技巧可謂是獨具匠心。
社會評論
萊辛一向注重個人對生活的心理體驗,並以心理活動描寫見長,這一特點在《野草在歌唱》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瑪麗在生活變動和感情經歷中的每一絲心理變化都被細緻入微地記錄下來,讀者在跟隨女主角內心體驗的過程中,逐漸加深了對醜惡的殖民制度的認識。貫穿在她所有作品中最鮮明的特點是她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注和嚴肅思考。
萊辛成為格勞麗亞·斯坦因(Gloria Stienm)和傑曼·格理爾(Germaine Greer)等激進人物所擁護的女權主義的先鋒。
——李志成
《野草在歌唱》中的野草常常被解讀為種族主義壓迫下的黑人。然而,作為白人女性,瑪麗在種族主義和父權文化的物理空間下,不斷體會到物理空間與自身心理空間之間發生的矛盾,徘徊在兩者邊緣無法取捨,始終無法構建起自己的身份,從而導致了最終自己走向毀滅。
——張飛瓏
序言
(一)
10月10日那天,一時心血來潮,就去圖書館借了一大堆多麗絲•萊辛的書回來。因為還有三個多星期就要回上海,想再讀讀她筆下的南部非洲,再體會一下她文字中的遼闊曠野和灼人熱氣,再聽聽非洲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坐在花園裡讀她1994年出版的自傳:原野上的草叢,有入走過時,躲藏在裡面的小鳥們會突然飛出,騰空而去,嘰嘰喳喳唱著;草叢樹叢中還常常有小動物,小鹿、小羚羊、野山貓、豪豬、野兔子。家中房前的菜園子,種著各種香草、小蕃茄、豆角和豌豆,都散發出清新的味道。少年的她在原野上漫步,“我慢慢走著,聽著鳥叫聲,非洲的鳥,特別是鴿子,那種睡意蒙嚨的聲音,讓你做白日夢,讓你充滿渴望。”
萊辛於1919年出生於現今的伊朗,父母都是英國人,五歲時全家遷往南羅得西亞(今辛巴威),父親經營著一個農場,“房子造好了,棲于山坡頂上,房子周圍的樹叢只被清理了三十米都不到……以後的二十年中,真正的原野,活著的,運作著的,滿是動物和鳥類的原野樹叢,一直保留在那裡,一直到二戰期間我父母親離開,我們的房子對這原野幾乎沒有影響……家門口有一棵高大的馬望加樹,淺色的樹身上有雷擊的傷痕。這是棵藏滿了蜜蜂和蜂蜜的古老的大樹。”
以前住在約堡時,常常到北方的鄉下去過周末,有時靠近波札那,有時靠近辛巴威,那裡的景致風物和萊辛所描述的一模一樣。現在住在開普敦,離萊辛所描述的原野有上千公里,但我們租的房子裡有一棵古老、巨大的鱷梨樹,夏秋之交,大風吹起時,要當心硬邦邦的鱷梨掉下來砸在頭上。花園的地下住著一隻執著的鼴鼠,每天都要在草地上拱起一堆堆的泥土。我的兩個孩子最愛把小手伸進鼴鼠的地下通道,感受裡面暖濕的空氣,探索這地道究竟能走多遠,更希望能碰到鼴鼠的尾巴。樹叢中雖然沒有野貓或豪豬,但是常常有幾內亞雞、野鴨和朱鷺來做客,更不用說小松鼠和各種小鳥。想著回到上海後將不再有這樣的樂趣,就情不自禁地開始懷念非洲的空間和大自然。
曾有人說,有一種病毒叫非洲病毒,感染時的症狀是對非洲產生無法克制的熱愛。許多在非洲生活過的人,都會染上這種病毒。我承認自己是這樣,萊辛肯定也是這樣。她的文字就是證明。
1964年萊辛在一次採訪時說,在她家鄉,白人農場主相隔的距離都非常遠,互相之間很孤立,空間很大,不像英國那樣大家擠在一起,需要互相影響互相謙讓互相認同,所以,一些在英國很平常的人,到了南部非洲那樣廣袤的空間裡,能夠放心大膽地讓自己的個性或怪癖伸展擴張。她說,也許是她的記憶在作怪,但是在南羅得西亞,有更多的豐富多彩的人物;英國則沒有,這是住在倫敦的她對非洲的最大懷念。南非也是這樣,這裡能讓人大刀闊斧地做一番事情,這裡讓人盪氣迴腸,這裡出大英雄,這裡時刻有著生與死的較量。從南非看英倫,就覺得北方的那個島國實在很瑣碎,很溫和,那裡的人在乎的事情,實在都很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