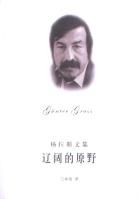內容簡介
《相聚在特爾格特》是作者最成功的小說之一,1979年出版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德國的暢銷書。十七世紀上半葉,德國符宗教派別、德意志皇帝和各諸侯之間矛盾深重,衝突不斷,在經歷了30年戰爭後,一批文人志士相聚在小城特爾格特,他們談占論今,暢所欲言,在探討詩歌、戲劇等嚴肅的學術問題的同時,還痛心疾首哀嘆自身和祖國的命運;他們藉助詩文,共謀祖國統一人業,可在高談闊論的同時,又插科打諢,粗話連篇,葷話迭出,還“不拘小節”同女僕和女店主苟合;最後他們甚至還共同草擬了,一份“和平呼籲書”,但一場意外的大火將聚會場所和“呼籲書”化為灰燼,文人志士們所有的美好願望也隨之煙消雲散。《相聚在特爾格特》中描述的那些詩人、作家等,德國歷史上都確有其人,在作者的筆下,他們的背後分別隱藏著德國當今文壇的一些重要人物。作者以借古喻今的寫作手法,生動地描寫了德國當代最著名的文學團體“四七”社在上世紀60年代的活動,表達了作者憂國憂民的情懷。
前言
《相聚在特爾格特》是當今德國文壇健將格拉斯的一部中篇小說,描寫的是一群德國詩人於1647年夏在小城特爾格特的聚會活動。小說的歷史背景是德國“三十年戰爭”(1618-1648)。這場戰爭由德國各宗教派別、德意志皇帝與德意志各諸侯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而引發,新教聯盟和天主教同盟各自與歐洲外國勢力結盟爭鬥,遂致德國戰禍連綿,田園荒蕪,生靈塗炭。活躍在本書中的一群詩人克服重重困難奔赴特爾格特聚會,時為1647年夏,即三十年戰爭行將以簽訂《威斯伐倫和約》而告終的前夕。
這是一次學術交流,也是對和平的急切期盼和對國家命運的熱切關注。情節雖屬虛構,但卻是以300年後的1947年成立的西德文學社團“四七社”為“克隆”原型。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漢斯·維爾納·里希特”,里希特即“四七社”的領袖人物。很明顯,這是一部以現代人的體驗去溝通歷史的“詠史”之作。這種寫作方式使格拉斯那“思接千代、目通萬里”的藝術想像才華得以充分施展,更重要的,也許是闡發作者的這一理念:“已有之事,後必再有;已行之事,後必再行。”
這“事”即指德國歷史上的分裂、戰亂、被外族占領、民不聊生的悲劇一再重演,又指歷代文人對祖國命運、文化生態和尊嚴的一以貫之的關懷。
精彩書摘
一已有之事,後必再有,已行之事,後必再行。我們當今的許多故事絕非現在發生。本書所講的故事,即肇始於三百多年前。其他故事也大體若是:舉凡在德國發生的故事,無一不是源遠流長。我現在寫下發端於特爾格特的一切,是因為一位朋友要慶祝他的七十大壽。這位朋友曾於本世紀第四十七年將一批志同道合者團結在其周圍。現在他更衰邁,可謂老態龍鍾;而我們——他的當代之友,也個個與之俱老,已是兩鬢染霜。
遙想當年,勞雷姆貝格和格雷弗林從日德蘭半島來到南部高地,再從雷根斯堡徒步下行;另一些人或騎馬,或坐馬車來;如同有些人乘舟順流而下,年老的韋克黑爾林也走水路,取道倫敦至不萊梅航線前來相聚。大家不論遠近,紛紛趕赴目的地。一位視日程安排如同贏虧一樣平常的商人也許會驚詫於他們守時的誠信。要知道這些先生僅僅是口頭應允赴會而已,況且城鄉迭遭破壞,蔓草盈野,滿目荒涼,鼠疫肆虐,民眾流離失所,更兼條條道路極不安全。
從斯特拉斯堡來的莫舍羅施和施諾伊貝二人抵達約定的目的地時已身無分文(只剩下手稿,這東西對攔路搶劫的盜匪毫無價值)。莫舍羅施開懷大笑,笑聲愈增幾分譏諷;施諾伊貝則悲嘆不迭,旅塵甫卸,回程的恐怖就已浮現在眼前了(他的臀部被盜匪的刀劍拍爛了)。
切普科、洛高、霍夫曼斯瓦爾道和其他的西里西亞人身邊攜帶著一封弗蘭格爾的信,一直交替跟隨那些到威斯伐倫徵集糧草集糧草時頻頻發生的恐怖事件——一律不問窮人的宗教派別,他們全都目擊身經。責難和抗議無法阻止弗蘭格爾的騎兵。一個名叫舍弗勒爾的大學生(切普科發現的)在勞西茨差一點被抓獲,原因是他挺身而出,保護了一位農婦。這農婦本該像她丈夫一樣,也要用尖木刺死的,而且要當著她孩子們的面。
約翰·里斯特是從易北河畔的威德爾附近趕來的,途經漢堡。一輛旅行馬車把斯特拉斯堡的出版商米爾本從呂納堡送來。西蒙·達赫來自柯尼斯堡地區的克奈普霍夫,路雖最遠,卻最安全,因為他混跡在其國君的隨從隊伍里——達赫廣邀同道的信函導致這一豪華排場。去年,布蘭登堡的弗里特利希·威廉與奧拉寧的露易絲訂婚,達赫躬逢其盛,在阿姆斯特丹朗誦道賀的韻詩;也就在那時,他寫好了許多邀請函,點明詩人聚會的地點,而且,因為有那位選帝侯的幫助,故信函的投遞就不愁沒人關心。(常常是在各地活動的間諜接收信件,他們喜好搬弄是非。)於是,格呂菲烏斯應他之邀蒞會,儘管他同什切青商人威廉·施雷格爾一年來先在義大利後在法國各地奔波。他是在返鄉途中(在施派爾)接到達赫信件的。他這次準時到達,而且把施雷格爾也一起帶來了。
語文教師奧古斯塔·布赫納從維滕堡來,也很守時。保羅·格哈德雖曾多次表示謝絕,但最終還是踐約來到。一輛郵政馬車在漢堡追上菲利普·策森,他偕同其出版商從阿姆斯特丹前來相聚。無人置身度外,沒有什麼障礙能阻擋他們的腳步。縱然他們中間多數人在學校、國家機關和宮廷任職,公務纏身,但這都未能成為阻力。川資匱缺的人事先尋找贊助者,倘若找不到資助者,像格雷弗林這樣的人就憑頑強意志的引領赴會。搖擺不定者一聽到別人已在途中,便頓生遠遊之念。即便相互敵視的人,比如澤森和里斯特,也願意彼此聚首。洛
高實在無法抑制自己對此次詩翁雅集的好奇心,這比抑制自己對聚會詩人的譏誚更難。這些人在家鄉的活動範圍過於狹窄,既無長久之事、又無短時之愛能把他們聯繫在一起。再者,當和約在暗中商談之際,總起來看,他們騷動的心緒和探求的願望與日俱增,誰也不願孤守一施,施諾伊貝同里斯特計畫打道回府去霍爾斯坦,韋克黑爾林打算乘下一班船回倫敦。大多數人在施壓——對達赫並非沒有怨言,要求取消這次聚會。達赫本人雖則平時鎮定自若,但此刻也開始懷疑起自己的計畫來了。人們提著行李,已經站到馬路上了,正當猶豫不定之際,幾個紐倫堡人不期而至,此時離天黑尚早。他們是:哈爾斯德費爾,他的出版商恩特爾以及青年比爾肯。陪同他們的人名叫克里斯托夫·格仁豪森,此人蓄紅鬍鬚,年約25,一臉麻子,這與他頎長身材洋溢著的青春氣質很不協調。他身著綠色緊身上衣,頭戴羽飾帽,看上去不像是現實中的人。有人說,他是神仙策馬經過時生下的。然而事實表明,格仁豪森比其外表形象要現實一些,連駐紮在周邊的皇家騎兵和用毛瑟槍裝備的步兵,其命令也奈何他不得,只好甘拜下風,因為舉行締結和約的各市,其範圍被宣布為中立區,禁止各方打仗。
達赫對紐倫堡一行人講了詩人們騎虎難下的困境,格仁豪森立馬表示願意效勞,其言滔滔,說得天花亂墜。過了一會兒,哈爾斯德費爾將達赫拽到一邊,道:此人言詞雖然瘋瘋癲癲,像個走江湖的占星者——說什麼他是朱庇特的情人,並以此自薦給這次詩人聚會,說什麼人們看到他在威爾斯蘭對維納斯是有所報答的——,但他性格詼諧,博聞多識,可惜這些都被他的傻氣所掩。這傢伙還是紹恩堡團團部文書哩,該團駐紮在奧芬堡。他們一行從維爾茨堡乘船來科隆,恩特爾未經允許試圖銷售一批“放野的”圖書,教父們懷疑他們搞“異教陰謀活動”,幸虧格仁豪森為其開脫,大力臂助,才使他們擺脫了困境。此人說謊真比撰寫的還要圓滿,口若懸河,教士們只好啞口無言。他把教父,乃至諸神及其星命一併玩於股掌之間。這傢伙很懂世俗人情,而且熟悉各地情況,比如科隆,雷克林豪森和索伊斯特。他可以給他們提供幫助。
格哈德警告說,不要同皇家軍隊的人有什麼瓜葛;而霍夫曼斯瓦爾道頗覺驚異的是,這傢伙剛才還摘引了奧皮茨翻譯的《阿卡狄亞》中的文句哩;莫舍羅施和里斯特一直願意傾聽這位團部文書的建議,特別是當斯特拉斯堡人施諾伊貝探問其團部駐地奧芬堡幾個繁忙的日常活動細節、而文書對答如流、證明所言並非虛妄之後。
格仁豪森可以對這些終於聚集一處、但苦於借宿無門的先生講話了。他的講話頗具說服力,猶如他綠色緊身上衣的雙排鍍金紐扣,粒粒熠熠生輝。他說:他是墨耳庫利烏斯的表弟,所以與他一樣繁忙。他反正要去明斯特,乃受上司的委派——上司即那位綁在馬耳斯戰車上的上校——,任務是給特勞特曼斯多爾夫先生傳遞秘密訊息。特勞特曼斯多爾夫是皇帝的首席和談代表,此君深受性情乖僻的薩杜恩之智慧的哺育,是以滿腹經綸,因他之故,和談終於得以進行。去明斯特的路程不到30里,吃苦是短時的。今夜皓月當空,行進如履平地。
假如先生們不願踏進信奉天主教的明斯特城,我們也可以去特爾格特,這小城親切友好。儘管小城變窮了,但一直保存完好,因為人們擊敗了黑森人,並且始終如一地為科尼希馬克軍團的銀庫提供資金。眾所周知,特爾格特自古以來就是朝聖之地,在此它一定可以為朝拜繆斯的先生們提供寄宿之處。它從青年時代起就學習為各路神明提供住所了。
老韋克黑爾林欲知作為新教教徒的格仁豪森何以深獲皇帝恩寵,竟然由他傳遞天主教黨派的緊急訊息,這位軍團文書說,人們既然容忍了他的教派信仰,宗教就與他無甚關係了。再者,這次為特勞特曼斯多爾夫傳遞的訊息並非絕密,而是人人皆知:在圖倫納元帥的陣營里,魏瑪各軍團為反對外國的控制而舉行譁變,現已分崩離析。這種訊息在他之前已不脛而走,真不值得急急傳送;他寧肯為這些沒有居處的詩人效勞,盡綿薄之力,尤其是他本人——阿波羅可以作證!——也是耍筆桿的,即使僅在紹恩堡上校的團部當文書。
達赫因此同意了格仁豪森的建議,格仁豪森也就不再拐彎抹角,花言巧語,而是對手下的騎兵和步兵下達出發的命令。
二:
自和談開始至今快三年了,這期間,從奧斯納布呂克經特爾格特到明斯特的這條道路可謂車水馬龍,信使絡繹不絕,他們把汗牛充棟的雜亂檔案,諸如請願書,備忘錄,包藏禍心的公函,慶典請柬,有關軍隊不受和談影響的最新調動情況等等,從新教黨派陣營送至天主教黨派陣營,或反向從天主教黨派陣營送至新教黨派陣營。但教派的立場與軍事上敵友的立場,並不完全相符:信仰天主教的法蘭西秉承羅馬教皇的旨意同西班牙、哈布斯堡以及巴伐利亞尋釁爭鬥;信仰新教的薩克森先是一隻腳,後來是雙腳踏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陣營;新教路德教派的瑞典人幾年前襲擊了同教派的丹麥人;巴伐利亞為爭奪普法耳茲而進行骯髒的領土交易。此外,還有軍隊的譁變和倒戈,尼德蘭的矛盾糾紛,西里西亞各階層的哀怨,帝國各都市的軟弱無能,同盟者的興趣雖然有所改變,但覬覦領土的野心依舊。因此,當一年前人們談判將埃爾薩斯割讓給法國,將波莫瑞——首都為什切青——割讓給瑞典時,斯特拉斯堡的代表和位於明斯特與奧斯納布呂克之間的波羅的海各市的代表簡直踏破鐵鞋(絕望而徒勞地),力加阻撓。這條溝通和談各都市間往來的道路,其處境與和談的進程及帝國的狀況是相一致的。
格仁豪森很快就搞到了四輛馬車,與其說是借用還不如說是徵調,以便把這二十幾位寄宿無著的先生送至特爾格特,然而,從托依堡森林的余脈越過特克倫堡地區至特爾格特,其間所需的時間比預想的要長些。(一位教堂司事給他們提供一座空空蕩蕩的女修道院將就做住所——修道院位於奧塞德附近,這教堂司事是瑞典人,棲身於此——,但被眾人婉拒,原因是這座建築年久失修,破舊淒涼,不具備起碼的居住條件;只有洛高和切普科二人贊成這個權宜的落腳處,他們倆不信任格仁豪森。)
當西蒙·達赫為車隊付過橋稅時,夏夜已在他們身後褪去濃重的顏色,東方漸白,晨光熹微。格仁豪森以其特有方式在一家名叫“橋旅店”內安排了住宿。該旅店就在埃姆斯河外河的大橋後面,再往前就是埃姆斯河的內河汊,該河流經埃姆斯城門為止的一段組成了該城的邊界。石頭砌成的旅店被蘆葦掩映,高高的山牆聳立在河岸的荒蕪景色中,乍看上去鮮有戰爭破壞的痕跡。格仁豪森顯然是認識女店主的,他把她拽到一邊,與她竊竊私語,過了一會兒在達赫、里斯特和哈爾斯德費爾面前介紹她,說她是他多年的女友麗布希卡。這位女士貼著疥癬膏,已是徐娘半老,身裹粗羊毛毯,穿軍人長褲,說話忸怩作態,以波希米亞貴族自居,說她的父親一開始就同貝特倫-嘉波爾一起為新教事業奮鬥過,說諸位光臨是她的榮幸,她即使不能立即、但也勿需久等
便可給先生們安排好住宿。
接著,格仁豪森便擺出皇家軍人的派頭,在馬廄前,在旅店前,在過道里,在窄而陡的樓梯上以及所有房門前大肆喧譁,以至於那些被套上鏈子的看門狗幾乎被嚇得窒息而死;格仁豪森一不做二不休,直至把所有的旅客及其車夫從睡夢中鬧醒。這些旅客均為漢薩同盟的商人,是從萊姆戈去不萊梅的。他們在旅店前面一集中,格仁豪森就命令他們快快離開旅店。他指出:誰珍惜自己的生命,誰就應該與病人保持距離。他這樣說是為了強化他的命令。他說,大家都看見馬車上和馬車前面這些疲憊而衰弱的人了,其中有幾個是鼠疫病患者,離期不遠了。他和他的小分隊護送這些倒霉蛋,要把他們隱匿起來,以便不干擾和談。所以,他作為羅馬教皇特使奇格的私人保健醫生,應教皇及瑞典軍方之命,把這些病人送至隔離區去。商人們必須儘快離開,不容抗辯,否則,有人會逼著他把他們的車輛和貨堆燒毀於埃姆斯河岸。鼠疫是不保護財富的,毋寧說是有意攫取奇珍異寶,尤其喜歡把它那高燒中的喘息贈予穿波拉班特布料服的先生。這事人人皆知,但作為用農神薩杜恩的全部智慧打造成的醫生,他要把此事挑明才順心。
當商人們懇求得到一份書面文字,說明驅逐他們的理由時,格仁豪森嗖的一聲拔出寶劍,說寶劍就是他的鵝毛筆,他想知道先給誰寫,接著,他又對這些必須立馬離開“橋旅店”的客人提出緊急要求:他以皇帝的名義,也以皇帝之敵手的名義要求他們對其突然起程上路的原因保持緘默,並要他們向戰神馬爾斯及其惡狗起誓。
講過這話,旅店便很快撤空了,然而在給車輛套上馬匹時就沒有這么順暢了。不過,哪裡有人磨蹭,哪裡就有格氏的步兵幫忙。達赫和幾位詩人還沒來得及對這不義之舉表示高聲抗辯,格仁豪森就把住宿安排妥當了!詩人們雖則疑慮未消,但因有莫舍羅施和格雷弗林的勸慰,說此事無異於可笑的羊人劇,於是,他們馬上就去尋找各自應住的房間和餘溫尚存的床鋪了。
施雷格爾身邊還跟隨另外幾位出版商,分別來自紐倫堡、斯特拉斯堡、阿姆斯特丹、漢堡和布萊斯勞,均為達赫請柬的印刷者。女店主麗布希卡剛剛遭受的經濟損失極易從這些文人身上得到彌補,再說那些離店遠行的漢薩同盟商人又留下了幾捆布匹,幾根銀條,四桶萊茵河地區產的啤酒。女店主顯然從這批新顧客身上找到了樂趣。
旅店旁側有一個突前的馬廄,格仁豪森就把他的小分隊人員安頓在那裡。詩人們從前面的門廳——位於小飯廳和廚房之間,它們的後面是大門廳——登上兩級扶梯進旅店的上層。此時,人們的抑鬱稍紓,只是在選擇房間時發生了小小的爭吵。策森在同里斯特交談之後同勞雷姆貝格發生了口角。醫科大學生舍弗勒爾淚水漣漣,原因是達赫鑒於房間短缺,把他、比爾肯和格雷弗林安排在閣樓的草鋪上睡覺了。
嗣後的情形是,年邁的韋克黑爾林只剩下微弱的脈搏;與莫舍羅施同住一室的施諾伊貝索要傷膏;格哈德和布赫納都想住單間;霍夫曼斯瓦爾道與格呂菲烏斯,切普科與洛高均雙雙入住一室;哈爾斯德費爾不同意與他的出版商恩特爾分住;里斯特搬到策森處,而策森也正想去里斯特那裡。出現這些情況時,女店主及其女僕們總是來到新客人身邊,予以幫助。麗布希卡已久聞幾位詩人的大名,會背誦格哈德的讚美詩,能摘引哈爾斯德費爾作品《佩格尼茲牧羊場的小花園》中的優美詩句。當她稍後同莫舍羅施、勞雷姆貝格在小飯廳落座——兩位先生毫無睡意,而要喝淺色啤酒,吃乳酪,麵包,坐等破曉——,她善於用言簡意賅的語句概括莫舍羅施的《菲蘭德爾》中的幾首夢幻曲的內容。女店主就是如此博學地、富於創意地為詩人聚會投了贊成票。格仁豪森對她還有一個別稱,管她叫“康拉舍”。格氏作為受歡迎的住宿籌劃者稍後也坐到三人中間來了。
西蒙·達赫同樣目不交睫,躺在房裡計算著給誰發了邀請函,在半途上說服了誰,有意或無意忘記了誰,根據別人的薦舉把誰列入了他的名單,抑或婉拒了誰,誰至今尚未到達——未到者是他的朋友阿爾貝特,他房裡的第二張床就是留給他的。
既驅走睡意、又使人睏倦的憂慮是:肖特爾也許還會來吧?(這個沃爾芬布特爾人就因為布赫納被邀而拒絕來。)紐倫堡的這些人原諒了克萊耶,因為克萊耶生病了。羅姆普勒倘若來,那真會叫人吃苦頭。是否能指望路特維希親王蒞臨這次聚會呢?(這位“富饒棕櫚”文學社領袖認為自己的情感受到了傷害,故留在科騰未動;而達赫並非“棕櫚”社成員,他一再強調自己是市民,這使親王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