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葉永烈(1940—)筆名蕭勇、久遠、葉揚、葉艇。浙江溫州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畢  葉永烈
葉永烈業後到上海電影廠任編導;1980年調上海市科教技術學會擔任常委,兼上海科普創作協會副理事長,並從事專業創作;1987年調任上海作家協會任專業作家,一級作家;20世紀50年代起發表詩作,自1960年發表第一本著作起至今已經出版了300多部著作。
葉永烈11歲起發表詩作,18歲起發表科學小品,20歲出版第一部科學小品集《碳的一家》,21歲成為《十萬個為什麼》主要作者。此後,多年從事科普創作,受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的關心,並對葉永烈作了兩次批示:“調查一下,如屬實,應同上海商量如何改善葉永烈同志的工作條件。”“我看要鼓勵科普創作,這項工作在世界各國都很重視。”
由於方毅同志的關心,1979年3月,文化部和中國科協聯合舉行隆重儀式,授予葉永烈“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稱號。曾先後創作科幻小說、科學童話、科學小品、科普讀物700多萬字。曾任中國科協委員、全國青聯常委、上海市科協常委、上海市科普創作協會副理事長、世界科幻小說協會理事。
電影《紅綠燈下》(任導演)獲第三屆電影“百花獎”最佳科教片獎,《小靈通漫遊未來》獲第二屆全國少年兒童文藝作品一等獎,《借尾巴》獲全國優秀讀物獎,根據葉永烈長篇科幻童話改編的6集動畫電影《哭鼻子大王》獲1996年“華表獎”(即政府獎)。
後來轉向紀實文學創作。主要新著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葉永烈自選集》;此外,還有《毛澤東的秘書們》、《陳雲全傳》、《葉永烈採訪手記》、《星條旗下的中國人》、《我的家一半在美國》、《一九九七逼近香港》、《商品房大戰》、《何智麗風波》等。即將出版《葉水烈文集》,共50卷,其中科普作品24卷。1989年被收入美國《世界名人錄》,並被美國傳記研究所聘為顧問。1998年獲香港“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
內容簡介
 王洪文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葉劍英、華國鋒坐鎮中南海懷仁堂,以“快打慢”的戰術,一舉捉拿“四人幫”。“文革”,作為中四當代史上的一場大劫大難,終於畫上了休止符。然而,作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過的道路,卻是發人深省的。
王洪文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葉劍英、華國鋒坐鎮中南海懷仁堂,以“快打慢”的戰術,一舉捉拿“四人幫”。“文革”,作為中四當代史上的一場大劫大難,終於畫上了休止符。然而,作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過的道路,卻是發人深省的。
本書是迄今為止,海內餐惟一一部關於王洪文的長篇傳記。這次,作者又作了大量增補,印行新版,以更加準確全面的史料和新穎獨特的專訪,公正、客觀、生動地展示了王洪文不尋常的一生,成為有關王洪文翔實的有保存價值的作品。
首卷語
王洪文自白:我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在起訴書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實,以及大量證據,都是事實。在法庭調查過程中,我已經如實作了回答。就今天這個機會,我向法庭表個態。‘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參與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活動,成了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犯下了嚴重的罪行。經過幾年來的反省和交代,特別是在公安預審和檢察院的調查過程中,我逐步認識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及我個人在這個集團裡面所犯罪行的嚴重性。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在起訴書中以大量的事實,確鑿的證據,充分說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罪行是極其嚴重的,給我們黨和國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惡滔天。我是這個集團里的一個重要成員,我的罪行是大量的,嚴重的,同樣給黨和國家造成了重大損失。特別是我犯下了參與誣陷周恩來總理、陳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領導人的嚴重罪行,犯下了鎮壓民眾的嚴重罪行,犯下了組織幫派武裝,煽動民兵武裝叛亂等嚴重罪行。我在這裡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認罪。我自己感到,由於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裡邊很深,罪行嚴重,完全轉變立場還要有個過程。但是我有決心轉變立場,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給我一個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機會。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所作的最後陳述。
目錄
第一章覆滅前的瘋狂
第二章初來上海灘
第三章揭竿而起
第四章當上“造反司令”
第五章安亭事件
第六章踏平“赤衛隊”
第七章“一月革命”
第八章“上海人民公社”
第九章血洗“聯司”
第十章掌管上海
第十一章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十二章四人結“幫”
第十三章建立“第二武裝”
第十四章武裝叛亂的失敗
後記
冒著上海三十八攝氏度的酷暑,我終於寫完這部三十多萬字的長篇,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屈指算來,我進行總題為《“四人幫”的興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長篇的寫作,已進入第四個年頭。這是一次艱難的長途跋涉。
 江青經過四年的苦鬥,終於完成了四部長篇:《江青傳》、《張春橋傳》、《姚文元傳》,以及這部剛剛完成的《王洪文傳》,分別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立傳。我進行這一百多萬字的系列長篇的寫作,最初是從兩本書中得到啟示:一是當時陸陸續續讀到的巴金的《隨想錄》。巴老對於“文革”的深刻、尖銳的鞭答,給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隨想錄》中一再提醒讀者,要“牢牢記住‘文革”’。他說出了振聾發聵的話:“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另一本給我以啟示的書是美國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長卷《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作者
江青經過四年的苦鬥,終於完成了四部長篇:《江青傳》、《張春橋傳》、《姚文元傳》,以及這部剛剛完成的《王洪文傳》,分別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立傳。我進行這一百多萬字的系列長篇的寫作,最初是從兩本書中得到啟示:一是當時陸陸續續讀到的巴金的《隨想錄》。巴老對於“文革”的深刻、尖銳的鞭答,給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隨想錄》中一再提醒讀者,要“牢牢記住‘文革”’。他說出了振聾發聵的話:“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另一本給我以啟示的書是美國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長卷《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作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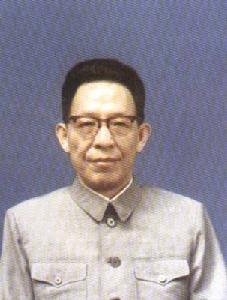 張春橋掌握了納粹德國的四百八十五噸檔案,花費五年半,寫成一百三十萬字的長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亞那的一句格言,那含義與巴金不謀而合:“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十年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創,決不亞於當年希特勒納粹給德國人民帶來的痛楚。我決心寫作長卷《“四人幫”的興衰》。我寫出了全書的寫作計畫和採訪計畫,上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當我著手實現這一龐大的創作計畫時,我這才意識到每前進一步都異常艱辛。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正因為這樣,我在進入創作之前,著手於大規模的準備工作。我曾說,我是以採訪對象為主幹,以檔案館與圖書館為兩翼。檔案是寫作這樣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是美國人,由他來寫納粹德國史,美國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噸機密檔案。然而,我卻以一個中國人去寫中國剛剛過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檔案絕大部分被視為“禁區”,不可接觸。最初,為了查閱檔案而來回奔走,花費了許多時間。好不容易辦好了手續,卻又只能坐在檔案室里抄錄,不許複印,不能拍照。我常常從早到晚坐在那些檔案室里逐字抄錄,變成了一位“文抄公”。現代化的複印機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卻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筆慢慢地抄
張春橋掌握了納粹德國的四百八十五噸檔案,花費五年半,寫成一百三十萬字的長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亞那的一句格言,那含義與巴金不謀而合:“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十年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創,決不亞於當年希特勒納粹給德國人民帶來的痛楚。我決心寫作長卷《“四人幫”的興衰》。我寫出了全書的寫作計畫和採訪計畫,上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當我著手實現這一龐大的創作計畫時,我這才意識到每前進一步都異常艱辛。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正因為這樣,我在進入創作之前,著手於大規模的準備工作。我曾說,我是以採訪對象為主幹,以檔案館與圖書館為兩翼。檔案是寫作這樣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是美國人,由他來寫納粹德國史,美國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噸機密檔案。然而,我卻以一個中國人去寫中國剛剛過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檔案絕大部分被視為“禁區”,不可接觸。最初,為了查閱檔案而來回奔走,花費了許多時間。好不容易辦好了手續,卻又只能坐在檔案室里抄錄,不許複印,不能拍照。我常常從早到晚坐在那些檔案室里逐字抄錄,變成了一位“文抄公”。現代化的複印機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卻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筆慢慢地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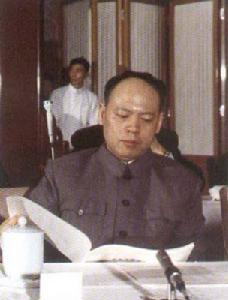 姚文元著、抄著。大量的寶貴時間,耗費在抄檔案上。儘管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畢竟積累了大量珍貴的原始檔案資料。圖書館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閱“文革”期間的報刊、雜誌、傳單、書籍,手續也是夠麻煩的。總算辦通了這些手續。我在幾家圖書館裡,閱讀了大量的“文革”報刊、傳單,掌握許多史實和採訪線索。我比較了張春橋為王洪文那“工總司”所簽的“五項要求”,發覺各種不同“版本”的傳單內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蹤”原件。在一家很不顯眼的檔案館裡,我查到了張春橋簽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據檔案上的說明,得知這三份原件是由誰提供的。儘管那位提供者已調動了工作,我頗費周折終於找到他,請他談了安亭事件的真實經過。這樣,把檔案、報刊傳單、採訪三者相結合,我才對史實有了比較準確的了解。採訪工作是最為重要的。十年浩劫剛剛過去,許多當事人尚在。對他們進行採訪,是寫作本書的至為關鍵的一環。採訪對象大致上有兩類:一類是被迫害者。採訪被迫害者,往往很順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層領導人,我也都能採訪。不過,他們往往偏重於談自己受迫害的經歷,而對於“文革”內幕所知並不太多。另一類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獄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獄,也在勞改工廠或類似的單位工作。採訪他們往往要經公安部門批准,要花費不少時間辦手續。不過,手續對於我來說,還是其次的;最艱難的是,即使辦好了手續,採訪對象往往不願深談。我儘量在事前作好詳細的採訪準備,提出一系列問題,這樣,採訪對象會逐個答覆,使採訪有一定深度。我的採訪是抱
姚文元著、抄著。大量的寶貴時間,耗費在抄檔案上。儘管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畢竟積累了大量珍貴的原始檔案資料。圖書館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閱“文革”期間的報刊、雜誌、傳單、書籍,手續也是夠麻煩的。總算辦通了這些手續。我在幾家圖書館裡,閱讀了大量的“文革”報刊、傳單,掌握許多史實和採訪線索。我比較了張春橋為王洪文那“工總司”所簽的“五項要求”,發覺各種不同“版本”的傳單內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蹤”原件。在一家很不顯眼的檔案館裡,我查到了張春橋簽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據檔案上的說明,得知這三份原件是由誰提供的。儘管那位提供者已調動了工作,我頗費周折終於找到他,請他談了安亭事件的真實經過。這樣,把檔案、報刊傳單、採訪三者相結合,我才對史實有了比較準確的了解。採訪工作是最為重要的。十年浩劫剛剛過去,許多當事人尚在。對他們進行採訪,是寫作本書的至為關鍵的一環。採訪對象大致上有兩類:一類是被迫害者。採訪被迫害者,往往很順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層領導人,我也都能採訪。不過,他們往往偏重於談自己受迫害的經歷,而對於“文革”內幕所知並不太多。另一類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獄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獄,也在勞改工廠或類似的單位工作。採訪他們往往要經公安部門批准,要花費不少時間辦手續。不過,手續對於我來說,還是其次的;最艱難的是,即使辦好了手續,採訪對象往往不願深談。我儘量在事前作好詳細的採訪準備,提出一系列問題,這樣,採訪對象會逐個答覆,使採訪有一定深度。我的採訪是抱 王洪文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進行的。我尊重事實。正因為這樣,一些“文革”要人還是願意跟我談,有的一談便是一整天。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寫出了《張春橋傳》(初稿名《張春橋浮沉史》)。這年八月,寫出《江青傳》初稿。接著,寫出《姚文元傳》初稿。這些作品,沒有一篇能夠發表。這倒並不在於作品本身,而是因為有人主張“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別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國成了敏感題材,很難問世。好在我不是一個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說過,準備十年後出版。我仍繼續我的採訪,繼續查閱檔案和報刊。我對三部作品中的兩部——《張春橋傳》和《姚文元傳》,作了大修改、大補充。我反覆研讀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內中關於徹底否定“文革”和正確評價毛澤東功過的論述,成為我寫作的指導原則。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學和史學的雙重價值。我相信手頭的長卷是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後仍能面世,仍會擁有讀者。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開,給中國文壇帶來寬鬆的氣氛。《新觀察》雜誌打來長途電話,率先連載了《姚氏父子》(《姚文元傳》初名)部分章節。不久,香港《大公報》徵得《新觀察》的同意,連載了《姚氏父子》。
王洪文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進行的。我尊重事實。正因為這樣,一些“文革”要人還是願意跟我談,有的一談便是一整天。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寫出了《張春橋傳》(初稿名《張春橋浮沉史》)。這年八月,寫出《江青傳》初稿。接著,寫出《姚文元傳》初稿。這些作品,沒有一篇能夠發表。這倒並不在於作品本身,而是因為有人主張“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別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國成了敏感題材,很難問世。好在我不是一個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說過,準備十年後出版。我仍繼續我的採訪,繼續查閱檔案和報刊。我對三部作品中的兩部——《張春橋傳》和《姚文元傳》,作了大修改、大補充。我反覆研讀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內中關於徹底否定“文革”和正確評價毛澤東功過的論述,成為我寫作的指導原則。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學和史學的雙重價值。我相信手頭的長卷是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後仍能面世,仍會擁有讀者。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開,給中國文壇帶來寬鬆的氣氛。《新觀察》雜誌打來長途電話,率先連載了《姚氏父子》(《姚文元傳》初名)部分章節。不久,香港《大公報》徵得《新觀察》的同意,連載了《姚氏父子》。 1976年粉碎“四人幫”內地多家報刊也搞載或連載。《藍苹外傳》(《江青傳》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學叢刊上發表。當時已經印好。鑒於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勢,不得不化為紙漿。該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發排的清樣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發表。刊出後,香港《大公報》即予以連載,《文學大觀》和《法制文學選刊》也全文轉載。此書以兩個月的速度出書,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萬冊。時代文藝出版社梅中泉先生來滬,取走了《張春橋浮沉史》(《張春橋傳》初名),同樣以兩個月的速度印出。這樣,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積壓了滿滿兩抽斗的文稿,竟這么快都變成了鉛字,飛入千家萬戶。江、張、姚三書的出版,使我下決心把王洪文傳寫出來。說實在的,雖然關於王洪文的採訪,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寫好一個簡略的提綱及開頭第一章之外,沒有寫下去。因為在“四人幫”之中,我覺得江、張、姚有深度,有厚度,經歷曲折,閱歷廣,寫作時拉得開,波瀾起伏。王洪文呢?與江、張、姚相比,顯得淺薄。所以,對於這位“造反司令”,我沒有太大的興趣。我寫完第一章,便擱筆了。在一九八八年春,當江、張、姚玉書都已改定,我才拿出兩年前寫的提綱,重聽當時採訪的一盒盒磁帶,著手寫《王》。我又作了補充採訪。這樣,我終於寫完這部長篇。我感謝上海國棉十七廠給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夠在該廠進行廣泛的採訪。我也感謝幾十位當事人給予的可貴的幫助,只是我無法在這裡開列長長的名單——雖然其中不少人是當年上海“工總司”的頭目,但是在我向他們進行採訪時,大都並不迴避當年的那段難堪的歷史,以歷史的見證人的身份如實地向我敘述自己當年的所見所聞。作為作者,我感謝他們的坦率和誠摯!值得順便說明一下的是,“四人幫”是一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這四部長篇又各自獨立成篇,單獨出版。我在寫作時,作了總體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張》書中一筆帶過,而在《姚》中則作為“重場戲”。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裝叛亂,在《王》中詳細鋪陳,而在《張》、《姚》中則只是“過場戲”。巴金在《隨想錄》中曾再三呼籲,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磨難重重,“文革博物館”迄今還只是處於呼籲階段。我願把我的這四部長篇,化為四塊磚頭,獻給那座迄今尚未動工的“文革博物館”吧。借本書印行之際,向給予熱情鼓勵、支持的時代文藝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謝。
1976年粉碎“四人幫”內地多家報刊也搞載或連載。《藍苹外傳》(《江青傳》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學叢刊上發表。當時已經印好。鑒於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勢,不得不化為紙漿。該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發排的清樣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發表。刊出後,香港《大公報》即予以連載,《文學大觀》和《法制文學選刊》也全文轉載。此書以兩個月的速度出書,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萬冊。時代文藝出版社梅中泉先生來滬,取走了《張春橋浮沉史》(《張春橋傳》初名),同樣以兩個月的速度印出。這樣,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積壓了滿滿兩抽斗的文稿,竟這么快都變成了鉛字,飛入千家萬戶。江、張、姚三書的出版,使我下決心把王洪文傳寫出來。說實在的,雖然關於王洪文的採訪,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寫好一個簡略的提綱及開頭第一章之外,沒有寫下去。因為在“四人幫”之中,我覺得江、張、姚有深度,有厚度,經歷曲折,閱歷廣,寫作時拉得開,波瀾起伏。王洪文呢?與江、張、姚相比,顯得淺薄。所以,對於這位“造反司令”,我沒有太大的興趣。我寫完第一章,便擱筆了。在一九八八年春,當江、張、姚玉書都已改定,我才拿出兩年前寫的提綱,重聽當時採訪的一盒盒磁帶,著手寫《王》。我又作了補充採訪。這樣,我終於寫完這部長篇。我感謝上海國棉十七廠給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夠在該廠進行廣泛的採訪。我也感謝幾十位當事人給予的可貴的幫助,只是我無法在這裡開列長長的名單——雖然其中不少人是當年上海“工總司”的頭目,但是在我向他們進行採訪時,大都並不迴避當年的那段難堪的歷史,以歷史的見證人的身份如實地向我敘述自己當年的所見所聞。作為作者,我感謝他們的坦率和誠摯!值得順便說明一下的是,“四人幫”是一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這四部長篇又各自獨立成篇,單獨出版。我在寫作時,作了總體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張》書中一筆帶過,而在《姚》中則作為“重場戲”。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裝叛亂,在《王》中詳細鋪陳,而在《張》、《姚》中則只是“過場戲”。巴金在《隨想錄》中曾再三呼籲,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磨難重重,“文革博物館”迄今還只是處於呼籲階段。我願把我的這四部長篇,化為四塊磚頭,獻給那座迄今尚未動工的“文革博物館”吧。借本書印行之際,向給予熱情鼓勵、支持的時代文藝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謝。
作者:葉永烈
一九八八,八,二十八,於上海補記:本書在初版的基礎上,作了修改補充。現作為《四人幫”興衰》亦即《“四人幫”全傳》之一印行。
一九九一,九,二十九,於上海
 葉永烈
葉永烈 王洪文傳
王洪文傳 江青
江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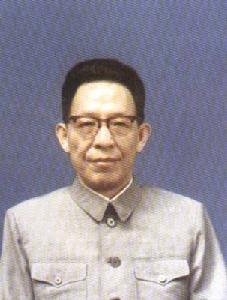 張春橋
張春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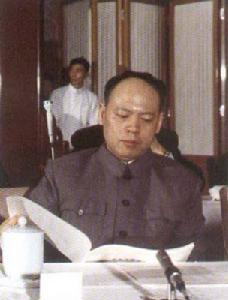 姚文元
姚文元 王洪文
王洪文 1976年粉碎“四人幫”
1976年粉碎“四人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