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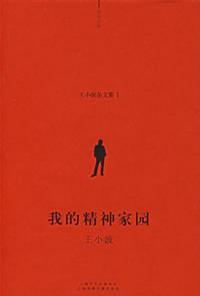 《我的精神家園》封面
《我的精神家園》封面《我的精神家園》王小波寫到安徒生寫過光榮的荊棘路,他說人文的事業就是一片著火的荊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著。當然,他是把塵世的囂囂都考慮在內了,我覺得用不著想那么多。用寧靜的童心來看,這條路是這樣的,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隻藍蜻蜒。這樣說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說服安徒生,就要用這樣的語言。維根斯坦臨終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這句話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從牽牛花叢中走過來了。雖然我對他的事業一竅不通,但我覺得他和我是一頭兒的。
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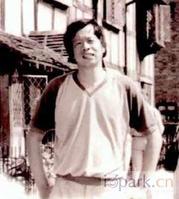 王小波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出生於北京。
1968~1970年雲南農場知青。這段經歷成為他最著名的作品《黃金時代》的背景。
1971~1972年山東牟平插隊;後作民辦教師。
1972~1973年北京牛街教學儀器廠工人。
1974~1978年北京西城區半導體廠工人。工人生活是他《革命時期的愛情》等小說的寫作背景。
1977年與當時在《光明日報》做編輯的李銀河(著名社會學家)相識相戀,後結合。
1978~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經濟系學生。就讀於貿易經濟商品學專業。
1982~1984年中國人民大學一分校教師。開始寫作《黃金時代》。
1984~1988年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生,獲碩士學位。開始寫作以唐傳奇為藍本的小說,其間得到許倬雲先生的指點。
1988~1991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1991~1992年中國人民大學會計系講師。
1992~1997年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逝世於北京(遺體解剖後證實死因是心臟病突發)。其後,他的作品盛行於世,他的文體成為無數青年仿效的目標,而他的思維方式亦影響了不少人。
生前鮮為人知,死後聲名廣播。自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去世後,他的作品幾為全部出版。評論、紀念文章大量湧現,出現了“王小波熱”的文化現象。出版作品有:《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我的精神家園》、《沉默的大多數》、《黑鐵時代》、《地久天長》;紀念、評論集有:《浪漫騎士》、《不再沉默》、《王小波畫傳》。一個嚴肅作家在死後兩年時間裡,如此地被人們閱讀、關注、討論,應該說是十分罕見的,其中所蘊涵的文化意義是非常豐富的,而它所透露出來的一個基本信息就是,王小波為許許多多的人們深深地喜愛著。
作品經典語錄
《自序》
倫理,反對愚蠢/無趣)
假設有一個領域,謙虛的人,明理的人以為它太困難,太曖昧,不肯說話,那么開口說話的就必然是淺薄之徒,狂妄之徒。這導致一種負篩選:越是傻子越敢叫喚--馬上我就要說到,這些傻子也不見得是真傻,但喊出來的都是傻話。久而久之,對中國人的名聲也有很大的損害。
在這個領域裡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仿佛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望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裡呢?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
《知識分子的不幸》
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跡象,所以不想最終皈依什麼--這塊地方我給自己著,它將是我一生事業的終結之處,我的精神墓地。不斷的學習和追求,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這件趣事從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給閹了7你有種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給我,我就不那么樂意7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
至於君主,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君主,聽到不順耳的訊息就拿信使餵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愿地只報來受歡迎的訊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里,就完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後一種君主至今是我們懷念的對象,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的思想工作,也比餵老虎好過得多。
《積極的結論》
真實/幽默感/善)
畝產三十萬斤糧食會造成特殊的困難:那么多的糧食誰也吃不了,只好堆在那裡,以致地面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這樣的速度在地理上實在是駭人聽聞;幾十年後,平地上就會出現一些山巒,這樣水田就會變成旱田,旱田則會變成坡地,更不要說長此以往,華北平原要變成喜馬拉雅山了。
我對此事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我認為,北京城原本是個很安全的地方,經過這些學生的努力之後,在它的西北郊出現了一大片槍炮轟鳴的交戰地帶,北京地區變得帶有危險性,故而這種作法能不能叫作保衛,實在值得懷疑。
假設我們說話要守信義,辦事情要有始有終,健全的理性實在是必不可少。
我認為,一個人快樂或悲傷,只要不是裝出來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樂,同情他的悲傷,卻不可以命令他怎樣怎樣,因為這是違背人類的天性的。
從過去的歲月里,我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費點勁兒,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軌道上。
《跳出手掌心》
我要說的就是:沉默地思索,是人類生活的另外一面。
由這樣的模式,自然會產生一種學堂式的氣氛,先是求學,受教,攢到了一定程度,就來教別人/管別人。如此一種學堂開辦數千年來,總是同一些知識在其中循環,並未產生一種面向未來/超越人類的文化--誰要罵我是民族虛無主義,就罵好了,反正我從小就不是好學生--只產生了一個極沉重的傳統:無數的聰明才智被白白的消磨掉。倘若說到世道人心,我承認沒有比中國文化更好的傳統--所以我們這裡就永遠只有世道人心,有不了別的。
《論戰與道德》
我聽了以後幾乎要氣死--猴戲我當然沒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斗不喜歡,就背上了反對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這些順嘴就聖化自己的人管一管--電影/電視/小說/理論文章都可以強我喜歡(只要你不強我去看,我可以喜歡(,連猴戲也要強我喜歡,實在太過分了--我最討厭的動物就是猴子,尤其是見不得它做鬼臉。
我認為像我這樣的人不在少數:我們熱愛藝術/熱愛科學,認為它們是崇高的事業,但是不希望這些領域裡的事同我為人處事的態度/我對別人的責任/我的愛憎感情發生關係,更不願因此觸犯社會的禁忌。這是因為,這兩個方面不在一個論域裡,而且後一個論域比前者要嚴重。
《“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
最能夠說明你是一件貨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乾什麼或對你有任何一種評價,都無須向你解釋或徵得你的同意。
人生活在一種文化的影響之中,他就有批判這種文化的權利。我對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批評,這是因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權利。假設我拿了綠卡,住在國外,你說我沒有這種權利,我倒無話可說。這是因為,人該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別人手裡的行貨。假如連這點都不懂,他就是行屍走肉,而行屍走肉是不配談論科學的。
《椰子樹與平等》
消除這種優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給聰明人頭上一悶棍,把他達笨些。但打輕了不管用,打重了會把腦子打出來,這又不是我們的本意。另一個方法則是:一旦聰明人和傻子起了爭執,我們總說傻子有理。久而久之,聰明人也會變傻。這種法子現在正用著呢。
《思想和害臊》
我去的時候,那裡的父老鄉親除了種地,還在幹著一件吃力的事情:表示自己是些有思想的人。
《我看國學》
我們知道,舊時讀書人都能把四書五經背得爛熟,隨便點出兩個字就能知道它在書中什麼地方。這種鑽研精神雖然可佩,這種作法卻十足是神經病。顯然,會背愛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學家;因為真正的學問不在字句上,而在於思想。就算文科有點特殊性,需要背誦,也到不了這個程度。因為“文革”里我也背過毛主席語錄,所以以為,這個調調我也懂--說是誦經念咒,並不過份。
四書也好,《紅樓夢》也罷,本來只是幾本書,卻硬要把整個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會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智慧與國學》
驢子/騾子/馬)追求智慧與利益無乾,這是一種興趣。
作為驢子之友,我對愛馬的人也有一種敬意。通過刻苦的修煉來完善自己,成為一個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無愧的好人,這種打算當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滿意的是,這個好人很可能是個笨蛋。直愣愣地想什麼東西有什麼用處,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種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類,才會時時想到“我可能還不夠聰明”!所以,我不滿意愛馬的人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也許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提出一個騾子式的折衷方案:你只有變得更聰明,才能看到人間的至善。但我不喜歡這樣的答案。我更喜歡驢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著。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著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裡就很高興。
我當然不會反對說:我們中國人是全世界上/也是全宇宙最聰明的人。一種如此聰明的人,除了教育別人,簡直就無事可乾。
《理想國與哲人王》
羅素以為參差多態是幸福的本源,把什麼都規定了就無幸福可言。作為經歷了某種“烏托邦”的人,我認為這個罪狀太過輕微。因為在烏托邦內,對什麼是幸福都有規定,比如“以苦為樂,以苦為榮”,“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廟”之類。在烏托邦里,很難找到感覺自己不幸福的人,大夥只是傻愣愣的,感覺不大自在。
照我看來,此君的可怕之處首先在於他的宏偉志向:人家考慮的問題是人類的未來,而我們只是人類的四十億分之一,幾乎可以說是不存在。
《東西方快樂區別之我見》
一種需要本身是不會過分的,只有人硬要誇大它,導致了自激時才會過分。餓了,找個乾淨的飯館吃個飯,有什麼過分?想要在吃飯時顯示你有錢才過分。你有個爸爸,你很愛他,要對他好有什麼過分?非要在這件事上顯示你是大孝子,讓別人來稱讚才過分。需要本身只有一分,你非把它弄到十分,這原因大家心裡明白,社會對個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還是個起鬨的場所。乾什麼事都要別人說好,贏得一些彩聲,正是這件事在導致自激。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這樣一來,它們的生活層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陳。人來了以後,給它們的生活作出了安排:每一頭牛和每一口豬的生活都有了主題。就它們中的大多數而言,這種生活主題是很悲慘的:前者的主題是幹活,後者的主題是長肉。我不認為這有什麼可抱怨的,因為我當時的生活也不見得豐富了多少,除了八個樣板戲,也沒有什麼消遣。
我的豬兄每天上午十點鐘總要跳到房上學汽笛,地里的人聽見它叫就回來--這可比糖廠鳴笛早了一個半小時。坦白地說,這不能完全怪豬兄,它畢竟不是鍋爐,叫起來和汽笛還有些區別,但老鄉們卻硬說聽不出來。領導上因此開了一個會,把它定成了破壞春耕的壞分子,要對它採取專政手段--
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定。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定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定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隻特立獨行的豬。
《思維的樂趣》
我插隊的地方有軍代表管著我們,現在我認為,他們是一批單純的好人;但我還認為,在我的這一生里,再沒有誰比他們使我更加痛苦了。--我對那些歌舞本身並無意見,但是看過二十遍以後就厭倦了。
《承認的勇氣》
知青文學的作者們總是這樣來解釋當年的事:這是時代使然,歷史使然;好象出了這樣的洋相,自己就沒有責任了。
相比之下,國人總不肯承認自己傻過,仿佛這樣就能使自己顯得聰明;除此之外,還要以審美的態度看待自己過去的醜態。像這樣傻法,簡直連傻X都不配作了。
很不幸的是,好多同年人連這種智慧都沒有,這就錯過了在我們那個時代里能學會的唯一的智慧--知道自己受了愚弄。
《藝術與關懷弱勢群體》
文明國家各種福利事業,都是為弱勢群體而設的。但我總覺得,科學,藝術不屬於福利事業,不應該以關懷弱勢群體為主旨。
最近應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視評論,看了一些國產影視劇,發現這種前景就在眼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加憂慮。以不才之愚見,我國的文學工作者過於關懷弱勢群體,與此同時,自己正在變成了一個奇特的弱勢群體--起碼是比觀眾,讀者為弱。
《奸近殺》
我既然不贊成婚外戀,也不贊成****剽娼,但對這種事情的關切程度總應該有個限度,不要鬧得和七十年代初抓階級鬥爭那樣瘋狂
《商業片與藝術片》
說實在的,我真有點佩服美國片商炮製俗套時那種恬不知恥的勁頭。
《關於文體》
但不管怎么說罷,那本書我還真看下去了--當然,讀完就後悔了。趕緊努力把這些傻話都忘掉,以免受到影響。作者怕讀壞文章,就是怕受壞影響。
有件事很奇怪:當地的男人還有些穿上衣的,中老年婦女幾乎一律赤膊。於是,水銀燈下呈現一片恐怖的場面。當時我想:假如我是個天閹,感覺可能會更好些。惡劣的文字給我的感受與此類似:假如我不認識字。感覺可能會更好。
《關於幽閉小說》
我總覺得小說可以寫痛苦,寫絕望,不能寫讓人心煩的事。理由很簡單:看了以後不煩也要煩,煩了要更煩,而煩這件事,正是中國人最大的苦難。
中國人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在生活中感到煩躁時,就帶有最深刻的虛無感。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筆記小說,張愛玲的小說也帶有這種味道:有憂傷,無憤怒;有絕望,無仇恨;看上去像個臨死的人寫的。我初次讀張愛玲,是在美國,覺得怪怪的,回到中國看當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這么股味。這時才想到:也許不是別人怪,是我怪。
所謂幽閉小說,有這么個特徵:那就是把囚籠和惡夢當作一切來寫--總之,是在不幸之中品來品去。
懷著這樣的信念,我投身於文學事業。我總覺得一門心思寫單位里那些爛事,或者寫那些不愉快的人際****,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
《體驗生活》
我想有人可能吃過些更難吃的東西,但不敢告訴他。說實在的,把飯弄好吃的本領他沒有,弄難吃的本領卻是有的,再教教就更壞了。
我餵過豬,知道拿這種東西去餵豬,所有的豬都會要咬死我的。
同學們見了飯食沒有活撕了我,只是有些楞頭青對我怒目而視,時不常吼上一句:“你丫也吃!”結果我就吃了不少。
吃完以後,指導員做了總結,看樣子他的情況不大好,所以也沒多說。
《欣賞經典》
根據我的人生經驗,假如你遇到一種可能的說法,這種說法對自己又過於有利,這種說法準不對。
王小波作品
| 大學裡曾流傳一句話:“男生不可不讀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讀周國平。”王小波的作品以其文采和哲思贏得了無數讀者的青睞,無論花季還是老年,都能從他的文字中收穫智慧和超然。王小波用他短暫的生命給世間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有人欣賞他雜文的譏誚反諷,有人享受他小說的天馬行空,有人讚揚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獨行。在這些表象的背後,他一生最珍貴的東西,是對自由的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