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梗概
艾伯特·斯畢卡是一個粗俗的惡棍,他和手下的一夥人以強買強賣、敲詐勒索為業。艾伯特是個性無能,於是他和美麗動人的妻子喬治娜之間夫妻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折磨和毆打。他最大的愛好和享受是大吃大喝,常帶著手下嘍羅和朋友去廚師里夏爾的餐廳饕餮。他在吃飯時又總是喋喋不休,指責身邊人衣服不得體、風度太差,不停地講下流笑話,奇聞逸事,與任何人稍有言語不合就會大發雷霆。
 海報
海報一天,喬治娜注意到了麥可,他獨自一人坐著,一邊看書一邊用小勺一點一點地吃東西,他的文雅與身邊粗言穢語的艾伯特構成鮮明的對比。麥可也發現了喬治娜的目光,兩人很快就在衛生間中開始做愛。
此後,每次與艾伯特來餐廳,喬治娜都以上廁所為名在廚房與麥可做愛,里夏爾時時地掩護著他們。但艾伯特很快得知了喬治娜的背叛,他大鬧廚房。在里夏爾的幫助下,這對赤身裸體的情侶躲在一個裝滿腐爛生蛆肉食的車廂中逃跑。
他們藏在麥可工作的書店,由廚房裡的小男孩為他們送飯菜。但男孩在回來的時候被艾伯特一夥抓住,受到殘酷的折磨,住進了醫院。艾伯特從男孩借的書上發現線索,當喬治娜去醫院看望男孩時,他帶人闖進書店,將撕下的書頁塞進麥可的口中,使他窒息而死。喬治娜求里夏爾將麥可的屍體烹成美食。復仇之夜,艾伯特帶著請柬來到因“私人用途”而關閉的餐廳。通往廚房的門打開了,全體餐廳人員推著麥可熱氣騰騰的屍體走來。喬治娜持槍逼艾伯特吃下去,當艾伯特一邊嘔吐一邊吃下一小塊時,槍響了,舞台大幕落下。“黑衣新娘”喬治娜仿佛死神,為麥可,為所有被艾伯特侮辱和傷害過的人復仇。
彼得·格林納威1989年拍攝的這部《廚師、竊賊、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象它的名字一樣複雜而古怪,在四個人物的身份和關係之間編織著一出荒誕的食慾與情慾大戲。在攝影機緩慢的移動中,一個裝修豪華,塗著濃艷燈光色彩的餐館如舞台一般展開,上演一幕幕華麗怪誕又充滿寓意的場景。
姓名和人物
最初給《廚師……》中人物的名字都是那些起初要被安排來扮演這些角色的演員的名字:艾伯特·斯畢卡(演員:艾伯特·費尼),喬治娜(演員:喬治娜·海爾),麥可(演員:麥可·甘邦,他向格林那威請求要換演艾伯特一角)。和里夏爾(演員:里夏爾·博林格)。海倫·麥倫是喬治娜一角的第三種選擇(於萬尼莎·瑞德格雷芙之後),而阿蘭·霍華德最後去扮演了麥可一角。不過最後,在《廚師……》里還是有一個命名方案在運作著。人物命名劇中別的人物,仿佛給他們打上了烙印,整部影片都在煩人地、重複地用著這些名字。艾爾伯特叫他的廚師里夏爾、里恰、里奇、博爾斯特--換著名字以奚落廚子,剝掉他的法國味和文雅講究。博爾斯特同時在每句話給艾爾伯特的話的最後都說"斯畢卡先生";這種禮節性的姓氏尊稱,是感冒子以極大的蔑視治這個強盜的方式。喬治娜警告米歇爾千萬別叫她喬治婭,而儘管他極少用她的名字(除了謝謝斯畢卡給他名字之外),喬治娜卻一旦得知他的名字就老是叫個沒完。格林那威以前的影片也使用了這種煩人的姓名稱謂,可是在《廚師……》里這一手段感覺象是管弦樂隊演奏一樣,匯聚成高度的戲劇性,突出了敘事的人為性。對格林那威影片中特定姓名的使用,人們盡可以整個做一番德希達式的解構(遵循德希達《論文字學》里特別涉及盧梭的那番對專有姓名的討論),但在此我只是想提請人們注意這種方式,憑藉這樣一種方式,《廚師……》里的姓名稱謂就極少是一種參考物或某種純擺設,相反它成了對影片裡整個語言使用方式的某種抗衡、糾纏、節奏把握和(最後)某種象徵:隨著用顛來倒去、轉著詞兒的問題表述的斷言,敘說,再敘說,顛來倒去地說(例如,喬治娜"我幹這個行,不是嗎?麥可?難道我幹這個不行嗎?麥可,難道我不行嗎……?"):語言被用作是刺人的話和奚落挖苦之語,是開胃小食和主餐前的點心,是從不糾正的誤用,是侵權和再侵權,是stychomithia,是機鋒甚健的偈句妙語(貝克特或品特的台詞的加速)。最後在《廚師……》中,姓名還是一種提喻法,以部分喻指整體,換喻性地(相對於隱喻性地)不斷鄰接又分離。最為重要的攝影機,影像的活力,不無過份的處處滲透於影片的具像存在,都不能涵括、最代姓名的語言的力量。
 《廚師、竊賊和他的情人》
《廚師、竊賊和他的情人》關於惡魔斯畢卡,已有論說紛紛,而就我對影片的理解來看,對麥可·甘邦的表演作些諷喻,對他是有害無益的。甘邦所飾的斯畢卡從未曾讓人興味索然、厭倦或隨便被曬在一邊。如果可鄙的反面是可敬,那么甘邦的斯畢卡當處於其間,興味索然,他卑鄙得令人叫絕,他的形象總是別具一格,恰如其分,這並非由於他避免了標籤化形象(他的口唇的及相似的固結在影片裡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發泄),而是由於他邊疆不斷地使用著語言這在近一段的電影史里極為罕見。這個說著話的斯畢卡,這個似乎總是缺少些什麼但從不缺少語詞口舌的斯畢卡,正是其吸引我們之所在。他的咆哮響徹了整部影片,窨的距離或攝影機的任何取位,從未改變這一如既往的咆哮。這頭獅子吼個不停,一直到他將死的那一刻;事實上,正是他的啞然無聲使那個最後場景讓人感到那樣陌生:一幫人站著面對著他;烹製過的麥可的長長屍體橫陳其間,麥可·尼曼作曲的大提琴和小提琴合奏的鏇律,推向一個惶惶不安的"當代"漸強音,還有一根中音薩克斯管在鳴奏著,從華麗的古典音樂直到刺耳的爵士樂;還有最後作環形移動的攝像機,在斯畢爾身後循環運動著,好象取位於他的視角,可實際上只是從拍從喬治娜的槍里射出的子彈。
影片中整個絕妙的表演,凸現出一種對觀眾來說極罕見的觀影經驗,一種無視角的經驗,這其中甘邦的表演是最值得注意的。我們既不能取斯畢卡觀點,也不能取位於反對著他的一個愜意的視點,也沒法兒取位於別的任何一個人物的視點:廚師的視點,不行(太邊緣化太古怪,最後也太帶窺淫色彩);麥可的也不行(太莫測高深,太不可理喻,也太被動,太呆板);喬治娜的也不行,儘管她的視點近乎於我們取任何一個人的視點,而這無異於角色認同。如果按照格林那威的觀點和他對角色認同的直言不諱的拒絕來衡量,那么最後三個場景是有點出格的,尤其是喬治娜向已死的麥可講述她的"故事"的時候的大特寫里的那個長長的獨白。她的復仇和一詞定性的"吃人禽獸"(cannibal),使前面講述的個人的故事失去了深度。她叫喊的"吃人的禽獸"應合著她從麥可的嘴裡拉出來的帶血的書頁上寫著的沉默的"革命"。麥可如此神情系之的法國大革命,就象喬治娜重新搬演的雅各賓復仇虐殺一樣,結束了一片無理智可言的恐怖烏雲中,除非有人犯罪作惡,這種肉體消滅簡直匪夷所思。喬治娜最後所做的,更多的倒不是讓艾伯特吃她已死的情人烹製了的肉體,而是讓艾伯特去吃他自己的語詞,也就是說,她迫使他閉嘴。
攝影
S.維爾尼(SACHA VIERNY)的攝影突出表現了《廚師…》里那匪夷所思的視點.阿蘭.雷奈再一次成為重要的參照因素.維爾尼做了好幾年雷奈的攝影師,現在看來他成了格林那威班子裡不可或缺的人物。格林那威公開說喜歡雷奈的影片,特點是《去年在馬里安巴》 (1961)和《穆里愛爾》 (1963 MURIEL)。《去年在馬里安巴》實際上跟《廚師…》在立意和表層敘事上頗多相合之處:一個局外人來到一處巴洛克式的地方,開始和一位已婚女人陷入一桃色事件,結果卻引來丈夫的猜忌,而且必招來他的報復。據說在拍《畫師的契約》 (1982)時,格林那威曾讓攝製組全體人員看(格林那威的引喻)表現人物的其他很少幾部影片之一,不過也因為它有一個在肉體和語言上都很卑鄙的人物,克列夫.蘭厄姆(克利夫.蘭厄姆的扮演者約韓.吉爾古德在格林那威最近據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改編的影片《普洛斯貝羅的書籍》中為所有的角色配音,替他們說話)。但是,在這兩位導演及他們共有的攝影師之間所有這種擇而論之的親密關係之處,有一個根本性的不同。無論是《廣島之戀》里架在車上走過夜間街巷的那架情緒化的攝影機,還是《去年在馬里安巴》里的那個精心設計的橢圓360度搖攝(被搖所表達的視點的那個人忽又被展現為搖攝內的我們看到的那個人),或是《穆里愛爾》里對伯爾納的那個"監視"式的攝影機,總之在維爾尼給雷奈拍片的運動如何總是和個視點。而給格林那威拍片時,維爾尼的攝影卻反其道而行之,幾乎從不落實於某個角色的視點,相反,它堅持強調空間的構形而不是角色的暫性,(因為時間和視點總是密切相關的),它突出了格林那威敘事的人工性和戲劇性,因而它也從想方設法追蹤人物視點的束縛解脫出來,去做一些頗富創意的事(比如繪畫式地使場面造型生動起來,還有處理表現荷蘭台桌畫的透視問題,《廚師…》中的情形正是如此。
出於那種自由靈活的考慮,《廚師…》中維爾尼的攝影機遵循著一種結構構型。起始於戲劇的幕布(它是這種構型的認定),攝影機從側翼沿一帶金鍊檔的藍坡道搖過鐵架,每一次都展現了同一個景像,部分模模糊糊的可讀"COURSE"(一道菜)的LA CONCOURSE(道路)標牌;霓紅燈招牌"LUNA"是月亮之幻影,也是對貝爾托盧齊亂倫的影片之暗中指涉。在通向餐廳後門邊,攝影機集中拍兩輛食品卡車和斯畢卡與他的人開的各式汽車,它們裝有很多汽車牌照,從NID(巢穴)到"HEX"(巫士)。攝影機在這一停頓處常常被很多跑來跑去的狗弄得昏天障地,有一個段落里狗跟攝影機挨得如此之近以致造成了一次黑框面切換(BLACK言之FRAME CUT)。攝影機復又從左向右搖,一個低角度的廣角鏡頭展示出高高的天花板和一個足以容得下幾架飛機的空間-一個對餐廳廚房來說太為寬敞的空間。在搖移過程中攝影機略作停頓,又拍下了標牌(斯畢卡SPICA和博爾斯物BOARST的名字),拍下了很多張切菜桌子,拍下了所有那些作為"他者"的準廚子和待者(一個如維米爾VERMEER)畫中出現的那種女人,一個鍬更斯小說中人物似的男孩,一個黑人,一個中國人,幾個說義大利語的人,一個光胸的屠夫,一個理髮師),還有比上面提到的多得多的那些半明半暗或隱遁於後的地方(一架移動梯子,一個放家禽和野味的掛著布簾的小房間,另一個放麵包和烘製食品的小房間).在廚房裡攝影機最頻繁地停下來的地方是里夏爾或帕普所在的位置,伴有里夏爾的聲音或帕普唱歌式的布道.當攝影機向餐館的布道,尼曼為餐廳作的主題)。第四堵牆並不存在,搖攝沒有停止而是游來游去。它只是延續著,從左向右,而且如果它沒有跟人物視點相配合,它確乎跟歌唱或主題鏇律相一致).總是有一段理入餐廳的戲,攝影機在此處沿著放有死鳥和家禽以及冰魚的桌子,搖拍下前景處所有的紙醉金迷、之景觀,以及後景處弗朗斯。哈爾斯的畫作《聖喬治市民公會官員們的宴會》(1614 Franz Hals:The Banguet of the offivers of the st George Civic Company ).有時,有些從婚宴上過來的人,身著猶太人曲禮時的盛裝的人們,以及坐在餐桌上的雙雙對對。攝影機在向斯畢卡的餐桌運動時"吞"下了他(它)們。我們總是可以看見哈爾斯的畫作隱現其間,這樣哈爾斯畫中的一些人物(包括一個形象頗似斯畢卡的人)就一直在旁觀著斯畢卡的餐桌。該場景依然用廣角描繪,畫面中拍天花板多於地板,但這裡空間是靠不住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哈爾斯那幅畫真正的面積大小;我們很少停下來,停在一個跟斯畢卡的餐桌離得足夠遠的有利視點之外來傳示出真正的距離(一個罕見的例外是,當喬治娜在麥可的桌邊停下看著他的書而我們看見艾伯特和里夏爾都看著她時,屋子空間顯得龐大開闊),而且,直到最後一場牆是在艾伯特進餐廳的位置時,我們才弄明白後面那堵牆的真正的面積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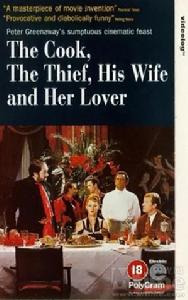 《廚師、竊賊和他的情人》
《廚師、竊賊和他的情人》在攝影機從右向左運動且亦搖拍時(這是離開餐廳的時候),常常通過推、拉、鏡頭突出表現敘述的事件(例如斯畢卡把喬治娜拖到廚房),恰在此時攝影機的運動比人物運動快,以便既使有一種速度的張力/動態又保持跟人物的感情距離。從左向右搖拍表現各種聲音元素,從右向左拍人物和退場,維爾尼的運動攝影機動作如斯。這一形式有兩次饒有意味的中斷。場與場的切換一直由後一天的各式選單來承擔,影片放到一半左右時,其中一張選單出現之後,最後一場戲之前,已由斯畢卡予以突出強調了,那時他跟米切爾說:"我不是真的要去啃他的屁股。我這是打比方。"該片中的種種雙關語說的時候也都是有隱喻的針對性的:模糊閃爍的字母博爾斯特(Boarst)既成了一道湯又變成了少年勞教機構(borstal);把"SPICA"誤排為"aspic"(凍肉),既是食物又是玩笑(因為艾伯特並非帥公子);艾伯特說"Poisson"(法語,魚)誤發音成"Poison"(口味、喜好)誤發音為"Palette"(地鋪);惡棍(hoods)和羅賓漢(Robin Hood)的雙關妙用;"酒燜子雞"(coq au vin)變成了"公雞"(cock)和"食品車"(can),等等。
隱喻的最出色的例子大概是艾伯特對濕麵包的說法,沒有把它化體(transubstantiation)成聖餅,而是化體為吞吃的生雞蛋。從吞吃的生雞蛋到羊屁股到濕麵包,都是對米切爾的一種警告。這一隱喻用法正是米切爾誤吃麥可的屁股之緣由所在。米切爾直通通從字面上去理解隱喻(羊屁股)的內容,並也隨之弄錯了比喻的這個意思。
最出色的換喻例子是從在水裡消耗體重的奶牛(產奶),到人奶及其罕見的精美度,到喬治娜的乳房(他摸著她),到一字一頓地宣稱她沒帶乳罩,到小山羊皮手套(羊奶及下仔),到沒有它們、想要它們,到後來又有了它們,如此等等。這種從艾伯特嘴裡說出來的語言涵括了跟他有關的所有一切。
隱喻玫換喻的遊戲,在確定該片中標示的各種世界背景時是頗為重要的。所謂該片中的英國既指雅各賓復仇悲劇又指瑪格麗特·柴契爾執政下的英國;影片中的荷蘭式既指數量眾多的天才畫師和台桌畫師們作的肖像,也指該餐館的名字,還包括間接暗示奇斯·卡桑德及格林那威跟荷蘭的關聯。該片中的法國式指那種讓人稱羨又難以企及的烹飪之高雅講究,也指法國大革命之狂野無度及隨之而來的恐怖烏雲,譬如麥可的書和藏書室里的各種提示。三個國家、傳統和生活方式之強行拼合既有隱喻又有換喻的意味。或許更簡而言之,它讓人啼笑皆非,也就是意味著它必須要分別對待,將兩種事物兩個時間合二為一(其最簡單的形式大概就是雙關語,最精微的形式大概是隱喻和換喻)。再說一遍,那根本性的分離無異於表明其中沒有一元性的敘事,沒有一個穩固的觀點,也不存在對影片的輕而易舉的讀解。
色彩編碼
在《廚師……》中色彩是被編碼了的,這種符碼化通常包含一種整體性,不過它們之所是跟它們之如何動作其情形截然不同(正如有了橋牌之規則然後再出各手牌)。符碼化是隱喻;其各種具體動作則表現為轉喻。在其編碼中,我們可以放心地作如是說:藍色--停車場,綠色--廚房,紅色--餐廳,白色--衛生間,黃色--醫院,金色--藏書間。在一些訪談中格林那威已談到了這些顏色的隱喻意義。
可是色彩,在運作時整個兒跟誤察錯看有關。例如,根據我的理解,醫院乃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玩笑,當時費奇正在說要保住他的耳朵,而斯畢卡的答話則是問他是否要同不說話的修女做一場夜總會表演(這正是他得到的)。影片開始時艾伯特罵喬治娜穿什麼黑衣服。她說穿著藍衣服。事實上在餐廳里她穿的是紅的,而在白色的衛生間她的衣服又變白了,還帶著黑色的羽飾(她看起來象是《去年在馬里安巴》)里的德爾芬·塞麗)。這種"運作"跟雷奈另一部片子《天命》里的色彩編碼相反,在《天命》里克勞德和索尼亞的廚房是黑白相間的,而臥室、床單、酒以及跟寫東西的克利夫·朗安(吉爾居飾)有關的所有東西都是紅的。在格林那威這裡玩笑是麥可在餐廳是棕褐色,在衛生間也一樣。而且在影片最後,里夏爾說了一大通話,為東西是黑色要價較高,說是因為"吃黑的食物就象是消費死亡",這以後,我們可能會合理地推想煮熟的麥可會有點兒變黑並焦糊。可是不,他依然是棕褐一片。另一個關於做熟了的麥可的玩笑則是我們親眼目睹了他不是猶太人,因為他的生殖器顯然未受割禮。
在格林那威的《一個Z和兩個O》里,動物園裡的各種外來動物以表示色彩編碼和隱喻色彩斑瀾的巨嘴鳥和極樂鳥,代表被肯定的生活,而黑白條條的斑馬,代表死亡和不可思議之物;在《畫師的契約》里,奈維爾的黑白色的素描,相對於被畫物的華麗色彩,其功能意義亦是一樣的。可是在《廚師……》中,格林那威仿佛是自言自語:很好,我將把色彩予以編碼,這會把懶惰的觀眾騙過來讓他們輕易地混入敘事,然後我會破壞這種編碼,開個把玩笑,和他們逗逗樂子。
聲音
麥可·尼曼,由於為《廚師……》作音樂配樂,得到了應得的讚譽,他現在頗為走俏(他給《海爾先生》寫過配樂)。尼曼之配樂吸引我的是,它重複了《挨個兒淹死》片尾和《一個Z和兩個O》全片中的音樂鏇律和主題,同時《廚師……》的配樂又把這些鏇律和主題予以延展、反諷處理,既表現出該片的華麗性和戲劇性,又傳達出餐廳場景中的蠢蠢律動。尼曼的音樂既是格林納威影片之互本文關係的最簡單明了的記錄,又是場面調度中讓人最難透徹把握或解釋的元素。有此弱的音符,把涉著性愛場景和沖洗糞便及蛆(讓人想起了Satie的《三裸舞》),還有由簡到繁的大、小提琴弦樂,應合著攝影機之搖攝和循環運動而最終作了性的喻示。我的意思是,完整理解作為電影的《廚師……》就是去理解尼曼的配樂和維爾尼的攝影如何你唱我搖、各放異彩,而不是喬治娜、麥可、艾伯特在乾什麼乾什麼。
跟各種色彩一樣,聲音也是既被編碼又被拆解的,於是原先方案中考慮便不同於完成片中的情形。聲音有時被那樣誇大以致喚起了人們對聲音本身的注意而離開了敘述事件。當喬治娜的廚房點菸時,火柴盒被劃著名的聲音是如此之響,以致跟帕普的歌聲不相上下,還一下蓋過了後者。艾伯特從廚房破門衝進餐廳,好象是穿過了哈德斯地獄之門:砰砰碰碰,動作粗野,氣勢洶洶,似乎廚房(要是我們把餐廳的各個部分想像成是一個人體)簡直就是腸子。帕普的哼哼唧唧的唱,由於維爾尼的攝影機掠過一堆金字塔形的下班器皿,百反襯出那些玻璃玩意兒發出的煩人的聲音,這甚至發生在我們看見帕普之前。當治娜跟里夏爾離開,去醫院看帕普時,麥可關上通向圖書室的一忘扇扇門,重重加鎖,而聲音則太響太軋軋刺耳,這同樣不無反諷,因為所有那一道道門和所有那些聲音都無法阻擋艾伯特及其一夥人闖入。醫院一場值得注意的是它沒有聲音,正如相對的是割下帕普的肚臍在畫面未有表現,儘管一些人會發誓說他們看見了割肚臍,但這更是通過帕普嚇人的尖叫聲表現出來的。在一個閉塞的空間裡有太大份量的聲音,而在一空闊的空間裡聲音又幾乎沒有,格林那威搞亂了我們對視聽元素比率的期待。而且這樣一種對我們觀看期待的逆反還更是達成如下效果的手段,即,使我們不尷不尬,給我們一種激靈並使我們局促不安,還讓我們無一固定視點可居。
 《廚師、竊賊和他的情人》
《廚師、竊賊和他的情人》導演介紹
畫家出身的英國人格林納威在此片中充分地展示著他對繪畫和戲劇的愛好。電影空間於是被舞台化了,鏡頭在消失了的第四堵牆的位置上平行移動,無需退出進入,就使場景從一個空間換至另一空間。影片的美術設計也更接近舞颱風格,它是非自然的,以富有強烈象徵性的不同色彩表現不同的空間(停車場:藍,廚房:綠,餐廳:紅,衛生間:白),甚至人物的服裝也隨著環境色的不同而發生明顯的變化。此外,影片的整體敘事也象戲劇一樣按時間劃分為幾幕,在每幕開場前以當天的菜譜作為標誌,在特寫鏡頭中,各種食物擺成精緻的圖案,環繞著以優美字型寫成的菜名和星期數。而且,影片以兩個侍者拉開門帘始,以猩紅大幕落下終,構成完整的封閉舞台時間。
角色分析
艾伯特就個體來說是一個虐待狂,瘋狂地將身邊的一切都降低到他的品位和享受的水平。影片一開始,他就在停車場中毆打欠債人,將他的衣服脫光,在他身上抹狗屎。隨後,這種排泄物的意象就一直伴隨著他口唇固結的行為方式,一如他自己所說,在他的享樂中,最受用的,也是最骯髒的。他一邊不停地吃(攝入),一邊不停地說(排出),他講著印度人喝自己小便的逸聞,他身邊的人時不時地嘔吐。但到最後,面對麥可的屍體時,他的兩種行為能力都喪失了,他恐懼無言,開始嘔吐,象一堆糞便一樣倒在地上。可以說,不是喬治娜射出的子彈,而是他自己強加欲望與他人的蠻橫方式反過來報復了他,使他還原為排泄物的原型。在他身上,人性充分地表現為倒錯,由於性無能而導致欲望倒退為口唇固結的行為,以及肛門固結者的貪婪和殘忍。
就象徵意義而言,艾伯特也可謂是當今消費社會肆意浪費、暴畛天物的典型形象。無論在創造的場所廚房還是文明的場所書店,他都是粗暴的闖入者,只能帶來混亂和破壞。當他在餐廳里吃喝時,外面的停車場裡總有一群野狗咆哮著撕咬人們吃剩下的肉食。這文明與野蠻的一體兩面,被消費和拋棄,被貨幣進出的原則調和。艾伯特稱自己為“藝術家”,因為他“將(互不相配的)生意(金錢)和享樂(食物)放在一起”。而他也的確是時代的藝術家,儘管與文化意義上的藝術家恰成對立。一如餐廳中荷蘭畫家哈爾斯的畫作《聖喬治市民公會官員們的宴會》與艾伯特宴會的並置,前者從畫中的食物上轉過頭來,凝視著他們的大吃大喝;並用沉默反襯著艾伯特滔滔不絕的廢話。
艾伯特一直在品評別人,喧囂地掌握著話語權,他周圍的人都迎合他、躲避他,或受到他的傷害。但影片將對艾伯特的評價巧妙地移置到了他所帶來的兩車肉食上,以駭人的意象預先宣判他的死亡。當里夏爾以保障品質為藉口拒絕使用它們做原料時,艾伯特誇口說:“我在這裡代表品質,提供品質的保護。”於是,這些“代表品質”的雞鴨魚肉就無緣進入艾伯特的體內,而是在餐廳門口悄悄地腐爛,散發出可怕的惡臭,使野狗橫行的停車場成為真正的地獄。
麥可可以說是文化與沉思的象徵,他沉溺於書本世界,只因為喬治娜的情慾而暫時地進入餐廳的世俗世界。他們的肉體神秘契合,但他們類似而有區別。在餐館的世界裡,喬治娜的衣服總是隨著環境色而敏感地改變,她似乎隨時可以毫無困難地融入每一個迥異的空間。而麥可卻是以不變應萬變,他那身棕黃色的西服從不改變顏色。甚至當他的屍體被烹熟後,也一樣是棕黃色的。也正因為喬治娜和麥可的變與不變,決定了他們各自的角色功能,使脆弱的麥可死於艾伯特對文化的粗暴借用,使柔韌的喬治娜以模仿但扭曲艾伯特欲望對象的方式殺死艾伯特。
影片評價
他們之間這種類似兩種思維方式的區別,使他們的愛成為虛幻,成為一出情慾的戲劇。在影片中,他們愛的空間或是夢幻的空間,即白色的衛生間或金黃的書店;或是食物的空間,即廚房裡的麵包櫃、碗碟櫃和肉食櫃。這是被懸置的愛,恰如他們時時採用的困難的做愛動作。從而,喬治娜在求里夏爾烹製麥可屍身時說,這是“為了紀念我們在廚房中、在幻想中做愛。”
 《廚師、竊賊和他的情人》
《廚師、竊賊和他的情人》排在片名第一位的廚師里夏爾一定程度上執行了導演本人的功能。他是影片中戲劇的背後導演,是他縱容和滿足著艾伯特食慾,是他引導和保護著喬治娜與麥可情慾。最後,也是他將麥可的屍體變成殘酷的藝術品,使整個戲劇滑向徹底的黑色。同時,他還象觀眾一樣是一雙窺淫和見證眼睛,在麥可死後向喬治娜轉述他們的性愛場景,以保證這場短暫的情慾戲劇的真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