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簡介

陝西渭河平原上一個傳奇之家三代人歷經種種苦難與愛恨情仇,在頑強求生存的同時捍衛自己的尊嚴。在本世紀的城市化浪潮中,這個村莊被納入開發區,結束了上千年的鄉村文明。在這塊土地上,繼而湧現出了在商業化生存法則中繼續奮鬥的新一代弄潮兒。該書猶如一部關中平原的《百年孤獨》式的家族史。
作者介紹
 高建群
高建群高建群,當代重要的小說家,國家一級作家,陝西省文聯副主席,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76年以《邊防線上》踏入文壇,1987年以《遙遠的白房子》引起文壇強烈轟動,1993年以《最後一個匈奴》奠定其實力派作家位置,並引發中國文壇“陝軍東征”現象,2003年以《胡馬北風大漠傳》再次引起轟動,並應邀在風凰世紀大講堂以“胡羯之血”為題演講。迄今,這位寫作者已出版長篇小說《最後一個匈奴》、《最後的民間》、《最後的遠行》、《愁容騎士》、《白房子》等五部,中篇小說《遙遠的白房子》、《伊犁馬》、《雕像》、《大順店》、《刺客行》、《菩提樹》等二十四部,散文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羅布泊大涅磐》、《胡馬北風大漠傳》、《狼之獨步》等十部。計一千五百萬字。2004年他被中國散文學會評為當年度中國散文十佳,2005年被《中國作家》評為當代最具影響的中國作家。
寫作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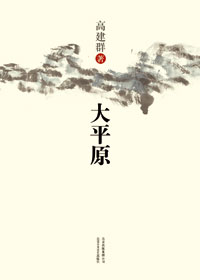
著名文學評論家閻綱曾評價高建群是“中國文壇罕見的一位具有崇高和理想主義色彩的寫作者”,正是憑藉這種理想主義精神,16年前,高建群的《最後一個匈奴》橫空出世,與《白鹿原》《廢都》等作品成為“陝軍東征”的重要作品,震動了整箇中國文壇。16年後,依然懷著這種崇高和理想主義色彩,高建群推出了他的具有史詩性質的長篇力作《大平原》。
雖然16年能讓不惑之年的中年人變成接近花甲之年的老人,能讓作家的文筆變得更加老道,不過高建群坦言自己骨子裡的“浪漫主義騎士精神”沒有變化,所以他才在小說後記中這樣評價《大平原》的問世:“中國文壇有一件大事要發生了,讓我們做好接受它的心理準備。”這種“老夫聊發少年狂”的“狂”卻讓人感到有些可愛——
這是獻給精神家園的作品
在《大平原》扉頁上,有這樣一句宣傳語:《最後一個匈奴》之後,著名作家高建群再度東征。高建群說他喜歡這樣的宣傳語:“因為《大平原》的誕生過程和《最後一個匈奴》多少有些類似,當年我在黃陵縣掛職,然後一口氣完成了《最後一個匈奴》;而《大平原》是我在高新區掛職三年後的作品,如果沒有掛職經歷,我可能無法這樣順利地完成。”
高建群的生活經歷比較特別,生在陝西臨潼,在新疆當兵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歲月,後來又在陝北延安生活了近30年,所以他說自己有三個精神家園:渭河平原、阿勒泰草原及陝北高原。“《白房子》是我獻給新疆的作品,《最後一個匈奴》是寫給陝北高原的作品,但是一直沒有一部作品寫給生我養我的故鄉——渭河平原,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寫這樣一部作品。”高建群在《大平原》中以講述自己家族故事的口吻,寫了渭河平原上以一個家族村莊為背景三代人的傳奇命運以及村莊的變遷史,描寫了村莊在都市化進程中的消失,描繪了從農耕文明到城市文明哀婉而必然的過渡過程。作品中的人物姓高,高建群說因為有其家族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其實也有我自己的影子,之所以一定要讓作品中的家族和我同姓,那樣的感覺就是在講述我自己的故事一樣。”
感謝在高新區掛職的歲月
高建群在小說中描述了一個古老的村莊在城市化進程中逐步消失,成為高新區的一部分,後半部關於高新區的描寫直接來源於其在高新區掛職的經歷,“在掛職結束前,我採訪了高新區16位企業家,深入他們內心世界,了解他們創業的艱難過程”。他說自己非常感謝在高新區掛職的歲月,“我在掛職之前就曾說過‘藝術家請向偉大的生活本身求救吧’,因為面對偉大的變革時代,不斷出現的新的人物和故事,是藝術長廊里從沒出現過的,作為藝術家有責任去表現他們,為時代立傳,給後人留下當代備忘錄。如果做不到,那是文學的缺位,是作家的失職”。
雖然《大平原》距離《最後一個匈奴》已有16年時間,但高建群動手寫《大平原》卻是在2005年,斷斷續續寫了3年,2008年結束高新區掛職後,他開始進入作品衝刺階段:“那段時間我關掉手機,每天上午拎一個小包,裡面裝著鋼筆、墨水、稿紙和香菸,就到我家附近的豐慶公園寫作,中午回家吃飯,睡個午覺,下午又如農民上工一樣又去了。”
兩部作品基本“打了個平手”
在《大平原》誕生之前,高建群的代表作無疑是《最後一個匈奴》,如今《大平原》問世,兩部同樣具有史詩性質的作品,難免會被人評價優劣,《大平原》的責編韓敬群曾說:“這也許是顯示中國文學有可能達到的一個高度的作品。”言下之意似乎是後者好過前者,而高建群自己卻認為兩部作品基本上“打了個平手”,“只是表現手法上更加圓熟老道,不過寫兩部作品時心境已然不同。當初寫《最後一個匈奴》時,我雄心勃勃,以為世界就在我的腳下,我現在很真誠地希望,自己能給人類留下一筆精神財富,給人類增加一份不動產”。
不過,高建群“騎士”精神依然,他說自己的《大平原》“會當之無愧地成為一枚炸彈,‘炸響’中國文壇,成為2009年中國文壇的大事”,“中國文壇應該有一部真正經典的作品出現了,我相信就是《大平原》,這是一部真正可以和世界對話的作品”。
高建群還說,寫完《大平原》後,他還打算寫部長篇,為偉大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立傳,然後“封筆”,“因為我們這一代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
讀書評論
 自繪插圖
自繪插圖評論一
談高建群不能離開陝西來談,陝西是農耕文明最堅強的堡壘,農耕文明是中國傳統最具核心價值意義的。隨著現代化的加劇,鄉土文學受到衝擊,處在激烈變異的階段。在這種形勢下唯有陝西的作家拿出最正宗的鄉土文學,顯然跟陝西作家生活在這樣一個農耕文明堅強的堡壘有關。《大平原》還是非常有思想價值的,我說一點,《大平原》也是一種家族敘事,家族敘事是鄉土文學很重要的敘事方式,實際上是對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的理解,高建群為什麼用“大平原”這樣一個標題,我覺得大平原里面有一種對宏大敘事的偏好,對宏大觀念的一種偏好,所以我想到一很重要的概念,其實天下觀表達了中國的關係價值,用天下建立這個社會的秩序觀,從家到國,到天下。在這種關係價值中體現個人的價值,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人否定個人價值,實際上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在倫理關係中來認識個人價值的。高建群的這個《大平原》,很深刻的揭示了這一點,通過普通的家族生活來揭示這一點。《大平原》從家族史來說有它自己的特點,體現在他把傳奇賦予了日常化的意義。像高家幾代人的生活中有很多傳奇性的東西,有很多反常的東西,有很多戲劇性的東西,但是他不是把這個傳奇推向一個極端,他不是去塑造英雄,而是揭示普通人生活中那種生命是如何呈現的。實際上他說了天下觀對關係價值重視的文化特徵,他寫了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實際上中國的這種倫理關係能夠化解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傳奇,傳奇只是個人生命面對外部環境的存在方式,這是最有獨特性的地方。我也覺得語言風格是很有獨特性的,小說具有非常濃烈的詩意化敘述。我是把它看成敘事詩,閻綱老師認為是抒情詩,這沒有關係,他是把詩和事融為一體,是家族的敘事詩。我還贊同他這種浪漫主義風格,浪漫主義在中國大平原上很難有棲生之地的,高建群是一個另類,這可能跟他的個性有關係,他血管裡面可能流著一種狂妄的血液,決定了他的寫作是不受約束的狀態。當然有很多狂妄者,有時候狂妄者往往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會壓抑自己的這種狂妄。所以在中國的文學作品,經常有不充分的浪漫主義。但是高建群是不願意屈服的人,他的浪漫主義風格是非常突出非常明顯的。總的來說,這的確是非常好的作品。但是這個作品前部分和後部分有一點不協調,我感覺還是有點拘泥於生活真實,拘泥於個人情感和生活真實,這樣寫的話有損於這個小說內在結構的整體性。我就說這些。
評論二
《大平原》的開篇,並不急於進入故事,卻用了一整章篇幅寫渭河。這在長篇創作中是罕見的。作者高建群詳盡而耐心地描繪著這條河在隴西高地的誕生及其軌跡:從千山萬壑的山崖上滲出來的一滴滴黃泥巴水,先是像萬千條蚯蚓似的,一路匯聚接納起無數小水小河,千迴百轉,蜿蜒流淌,終於有了規模和氣勢,終於衝出大散關,終於有了廣大的渭河沖積平原——八百里秦川。寫至此,作者似乎嘆了口氣,說渭河是哀慟的,沉重的,滯澀的,滄桑的。作者為何如此不厭其詳地描摹這條河,甚至在卷首題辭中,特意標明他的書是“獻給渭河平原”的?從這裡能看出什麼深意嗎?
無疑地,誰都看得出來,這是一種隱喻或象徵,既是在寫河,也是在寫渭河流域世世代代生息劬勞的萬千生靈;既寫河的艱難突圍,衝波逆折,也是寫農民生存的艱辛,傳統的沉重,伸展的不易。這段文字頗有一抹長安畫派的作風,如觀石魯、趙望雲、劉文西們的筆墨意象,又像聽大秦之腔那悲愴,高亢,響遏行雲的吼叫。這個開篇為全書調準了貫穿始終的基調,以比興構建詩化品性,營造了一種瀰漫全書的悲慨蒼涼的氛圍。這與小說作為鄉土變遷史和家族史的內涵頗為吻合。
但其意義似乎不限於此。小說寫道,渭河流經的山地,平川,溝壑里,有數不清的堡子,堡子里住著同一姓氏的人,在這個清一色的家族的世界裡,如螻蟻如草芥一樣的莊稼人,像黃土地一樣的貧瘠,像渭河水一樣的平庸;然而,幾千年來,正是他們,支撐著我們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其文化精神源遠流長。這樣的描寫,已經露出了文化透視的意向。在我看來,如果說作者逃不出寫家族史的範式,那么他也許並不想僅僅把他的藝術任務局限在陳述家族史上,而是想把自己的家族史敘述提升到吟味中國農耕文化的命脈的層面上。這是一種自覺和俯瞰。因為農耕文化與河流有著深刻的淵源,《大平原》於是用了一整章來寫渭河。
錢穆先生說:“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遊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文化。遊牧文化發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帶,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之島嶼。”他又說,“中國文化發生在黃河流域,其實黃河本身並不適於灌溉與交通;中國文化的發生,精密言之,所憑依的是黃河的各條支流。每一支流之兩岸和其流進黃河時兩水相交的那一個角里,卻正是古代中國文化之搖籃。”,他還說,“遊牧、商業民族向外爭取。農耕民族與其耕地相連繫,膠著而不能移,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祖宗子孫世代墳墓安於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間之擴張,惟望時間之綿延,絕不想人生有無限向前之一境,而認為當體具足,循環不已,其所想像而蘄求者,則曰‘天長地久,福祿永終’”(《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我在這裡大段地引征錢穆先生的話,並不是想外敷一層學理色彩以裝點門面,而是深深感到,錢氏的話對理解渭河平原的意義乃至《大平原》這本書比較重要。我也並不認為《大平原》是在詮釋錢穆的觀念——也許高建群並未注意研究過錢穆的這些觀點;我只是想說,高建群筆下的渭河和堡子里的故事恰好與錢穆的觀點相互印證,相互照亮,這對於研習中國農耕文化的脈絡,頗具典型性和象徵性——象徵中國農耕文明的歷史命運。
眾所周知,家族是中國鄉土文化結構的硬核。《大平原》仍不外是一個家族故事。但《大平原》卻不同於以往常見的家族故事,其最大不同在於:它幾乎沒有寫幾個家族之間或宅院內部的權力爭鬥,它也不正面寫重大的政治事件;它藉助於社會政治背景,卻無意於深挖社會政治本身的歷史內容,而是把大量筆墨落在自然災害、生存絕境、土地與人的關係上;它不是向空間擴展,而是一種縱向的時間的綿延。小說以“我”的口吻和視角講述,講的是我爺爺、我奶奶的故事,我父親、我母親的故事,還有我自己的故事,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從1939年花園口決堤一直寫到改革開放的今天,緊緊圍繞著高家三代人命運的變化,宛如一條蜿蜒起伏的渭河。作為長篇,這種結構是直線式連綴型結構,缺少了復調式的交響,是否失之於單一?也許是這樣的。然而,由於小說採取了象徵結構,也由於小說充沛的生命意識,逼真的原生態描摹,飽滿的質感,詩化的詠嘆,使得這種缺憾變得不那么突出了,反倒以其強烈的主觀性和寫意性,以其蒼涼的命運感,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文化信息。
小說以“鄉間美人”祖母高安氏的“偉大的罵街”開始,以母親顧蘭子的臨終遺言收筆,時間跨度70餘年。高家祖母高安氏為什麼要像潑婦一樣,每天滿世界罵街不止,居然罵了半年,成為高村的一道風景?原來,高家無男丁,過繼了一個外甥,這就是高安氏的丈夫高發生;雖然也姓了高,因為不是正宗的老高家出身,受人歧視,甚至能否順利繼承祖業都成為問題。高安氏咽不下這口氣,就挨家挨戶地罵,果然起到了震懾作用,穩住了高發生在高村的地位。這裡實際上點出了所謂家族文化,骨子裡乃是一種極強烈排它的血緣文化。就是在這樣的罵聲中,河南的難民大軍從村前浩浩蕩蕩地過來了,去往一個叫黃龍山的地方。由此引出了書中最重要的人物顧蘭子。這個從黃泛區逃來,在大水中撿了條命的小妞,爾後在渭河邊長大成人,為人妻為人母。當我們看到兩個老女人給幼小的顧蘭子“扎耳朵眼”,盼望著她有朝一日能勝過她們,過上穿金戴銀的日子,怎不為之唏噓?
顧蘭子可以看作全書中一個靈魂式的人物,貫穿性的人物。是她把豐饒龐雜的生活聚攏起來,有力地體現了作品蒼涼悲壯的格調。因為她,高安氏,高發生老漢,高二與景一虹,高大與高三,還有黑建,年饉,以及高村所有角色,匯集一起,成為有機整體。高二與顧蘭子的婚姻故事同樣內蘊深厚。高二參加了革命,成了公家人,他和景一虹好上了,而且發生了一夜情,一紙休書要休掉童養媳顧蘭子。這本是那個年代最平常不過的事。可是顧蘭子後來想明白了,男人是爭來的,於是顧蘭子與公公高發生一起去了城裡,由高老漢親自主演了一場“鞭打陳世美”的好戲。孝子高二服軟了,景一虹知難而退了。顧蘭子之所以處於弱勢竟能把高二搶了回來,並非她和公公有多么厲害,乃是龐大深固的家族宗法文化傳統給他們撐了腰。這裡每個人的命運似乎都像“渭河一樣地平庸”。作者的敘述固然含有浪漫氣息,但在具體處理情節上,卻並不想製造傳奇,而是嚴格現實主義的,甚至是原生態的。高二這個人物就很值得琢磨。他的仕途前景原本看好,但他只知苦幹,缺少權變,既不會處關係,又沒有靠頭,難成大器。說到底,高二還是一個沒有走出渭河大堡子的農民。
要問,《大平原》的主旨到底是寫什麼?我看是寫農耕文化的沉重艱辛;寫中國農民的沉默堅韌;寫活著很難,有尊嚴地活著就更難;寫社會大轉型中正在消失的村莊,如此等等。按說,這些都不算什麼新鮮的發現,很多人寫過了。但讀來為什麼仍時有震撼之感呢?秘密在於,作品關於飢餓,災荒,苦難,動亂以及勞動者的人情美和對理想的憧憬的描繪,完全出自作者刻骨的生命體驗、不可重複的細節,逼真的親歷感,以及作家主觀情志的滲透和抒發。是生活自身的感染力和邏輯力在起作用。如對飢餓的描寫就很有衝擊力,當年艾青的詩曾深深打動過我,我常背誦“飢餓是可怕的,它使年老的失去了仁慈,年幼的學會了憎恨”;張賢亮的寫飢餓,路遙的寫飢餓,都曾讓我震悚。但高建群的描寫也絕不遜色。且不說,花園口決堤,洪水千里,難民百萬,“從大平原另一頭黑壓壓過來,像蝗蟲一樣,吃盡路邊所有能吃的東西;他們頭上飛著千萬隻烏鴉,花喜鵲,那是為了收拾隨時倒斃的屍體”,讓人駭倒;單看一些小鏡頭,如顧蘭子的“搶饃”,把饃塞進牛糞;後來的黑建回鄉,村民舉手通過這外來娃能否喝黑麵糊糊;一群小孩圍著大鍋不走,眼巴巴等著吃鍋巴,隊長兒子沒擠上去,抓了一把土扔進鍋里;尤其是高二打了舐碗的黑建的那一記耳光,是一種要尊嚴要面子而不可得的惱火。
高建群是高氏家族的嫡傳子孫,從這裡走出,多年來風風雨雨打拚,歷練成熟起來的作家。渭河平原大大小小堡子里發生的一切,他都爛熟於胸。他的血管里流著祖先的血,脈動著祖先的遺傳基因,這是他的精神家園,世襲領地,獨家優勢。他用不著“採訪”,用不著專門“體驗”,從小就不間斷地讀著這本叫做生活的無字大書,天然地宿命地要成為這方水土的文學代言人。小說中一些令人難忘的亮點,皆源於高建群最熟悉的原生態的生活。生活,藝術經驗,人生智慧,表達技巧,會使原本平常的情節、細節,發生奇妙的增殖效應。於是,這些遙遠的災難,並非一風吹走的往事,或歷史書上幾行冰冷文字,而是我們民族心靈深處彌足珍貴的永恆記憶。
家族是一個寫不盡的話題,甚至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就近三十年寫鄉土家族的作品來看,像《白鹿原》《秦腔》《塵埃落定》《古船》《第二十幕》《繾綣與決絕》《紅高粱》《活著》等等,好作品不勝枚舉。但必須看到,過去大量的家族史文本,擅長於寫“最後一個”,寫燈盡油乾,大廈將傾,寫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崇尚所謂文化秘史式的,審父式的,寓言式的寫法,漸成模式。《大平原》的最後部分,寫了高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建高新區,科技園,不可避免地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古老的地名也“從大地上殘忍地抹去了”。為此,作者展開一個個企業家的發家故事。這些描寫直接來源於高建群在高新區掛職的經歷。他說:“在掛職結束前,我採訪了高新區16位企業家,深入他們內心世界,了解他們創業的艱難過程,面對偉大的變革時代,不斷出現的新的人物和故事,藝術長廊里從沒出現過的,作為藝術家有責任去表現他們,為時代立傳,給後人留下當代備忘錄。如果做不到,那是文學的缺位,是作家的失職”。於是他把這本書同時獻給“所有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村莊”。這使我想到了家族史寫作的創新問題。一種意見認為,小說寫到高二去世結束最為圓滿,後面的是畫蛇添足;另一種意見認為,後面的工業化城市化極為重要,不可或缺。我承認,歷史早已大踏步前進了,中國鄉土的現代轉型也有二十年了,不能總是迴避。然而,把這種正在行進中的生活納入農耕文化的模式,寫作確有難度。這本書中,最後部分與前面的生活節奏明顯不同,後面的近乎報告文學。表現生活的完整性,是否一定要表現它的全過程;寫舊的解體,是否一定要把未經醞釀成熟的生活拼貼進去?在我看來,也許寫到顧蘭子去世一面唱秦腔,一面把高家的老槐樹整棵挪走收尾是最好不過了。應該把象徵進行到底。不管怎么說,如何把農耕文化與城市文化的節奏揉為一體,可能是今後鄉土中國家族史的作者再也無法迴避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