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背景
 毛澤東同印度總理尼赫魯
毛澤東同印度總理尼赫魯1954年10月,應中國政府邀請,尼赫魯偕女兒英迪拉·甘地夫人踏上中國的土地,進行了長達十二天的正式訪問。在北京機場尼赫魯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長久以來,我就懷抱著訪問這一偉大國家的願望,今天這個願望得到了實現,我感到很高興。從歷史的黎明開始,印度和中國一直就在完美的友誼和相互和諧的氣氛中共處著……”尼赫魯是第一位來華訪問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五十多萬北京人扶老攜幼,從機場到賓館夾道歡迎印度貴賓,開創了建國以來歡迎外國領導人來訪的先例,是世界歷史上歡迎外國領袖絕無僅有的盛大場面,對尼赫魯表示了極大的尊重。周恩來在歡迎宴會上高度評價了尼赫魯,稱他為印度傑出的政治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39年8月,尼赫魯曾作為國大黨領袖到重慶進行了十天的友好訪問。
毛澤東極盡地主之誼,同尼赫魯進行了四次談話,並破例出席印度駐華使館舉辦的招待會。在尼赫魯離開北京前夕,毛澤東親自將他送到車門,臨別前他用一雙大手緊握尼赫魯的手,嘴裡喃喃吟道:“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這是屈原《楚辭·少司命》中的詩句,表達了對尼赫魯的相識之情。
劉少奇接見並宴請了尼赫魯,兩國總理更是多次舉行會談。周恩來陪同尼赫魯參觀了中國最大的石經聚集地——北京房山石經室。看到堆積如山的石經,尼赫魯十分羨慕,作為佛教發源地的印度,也難有如此之多的寶物。尼赫魯半開玩笑地對周恩來說,願用等量的黃金換得石經。周恩來笑著回答,黃金有價,石經無價。這次訪問增進了兩國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好關係。
尼赫魯歸國後,更是對新中國的成就由衷敬佩,大力宣揚。他說,在中國每一塊土地上的每個人臉上,看到了欣欣向榮的景象,看到了這個國家萬眾一心的團結,看到了她光輝無限的前景。這段時間他如同朝聖歸來的聖徒,三句話不離“偉大的中國!”
全文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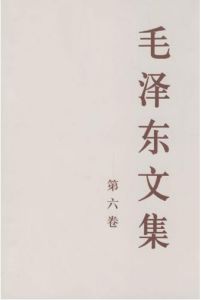 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四次談話
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四次談話一
我們所有東方人,在歷史上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日本雖然是一個東方國家,但是過去它又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它也欺侮別的東方國家,可是現在連日本都受欺侮了。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們的國家受欺侮的時間更長,有三百多年。現在日本人也處在受壓迫的境地。因此,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賴嘉文大使在中國已經幾年了,一定懂得中國人民愛國的感情和中國人民對印度人民及其他東方國家人民的感情。儘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尼赫魯總理不要以為中國已經完全獨立,沒有問題了,我們還有很大的問題,台灣就還在美國和蔣介石的手裡。離開大陸幾公里的地方,我們有三十多個島嶼,其中大的有三個。這些島嶼都被美蔣盤踞著,我們的船不能通過,外國船也不能通過。美國飛機飛到我們內地的上空,空投特務。這些特務以七人到十人為一組,帶有電台。到現在為止,已經有幾十組這樣的特務空投到我們內地各省。在四川和靠近西藏的青海,美國飛機都曾空投過特務,並且空投武器給那裡的土匪。這就說明,美國當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機會就要整我們的。
此外,尼赫魯總理知道,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工業國,而是一個農業國。我國的工業水平比印度還低。我們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後才能取得一些成績。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是看不起我們的。我們兩國的處境差不多,這也是東方國家的共同處境。我讀了尼赫魯總理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說,尼赫魯總理所表示的情緒同我們的差不多。
我們兩國人民對互訪的兩國領導人所表示的歡迎,說明他們著重的不是思想和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們的共同點。
應當把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係中去。尼赫魯總理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說中就說過,應當按五項原則來受約束,承擔義務。如果一個國家說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來指責它,它在人們眼中就輸了理。問題是有些大國不願受約束,不願像我們兩國那樣,根據五項原則訂立協定。不知道它們有什麼想法?據我知道,美國和英國也說,它們要求和平,不干涉他國內政。但是,如果我們要同它們根據五項原則發表聲明,它們又不願意乾。
不能構想任何國家會開軍隊到美國去。至於說美國怕喪失它在世界各地占據的地方,可是我好像聽說美國是反對英、法殖民主義的。美國的恐懼也實在太過分了。它把防線擺在南韓、台灣、印度支那,這些地方離美國那么遠,離我們倒很近。這使得我們很難睡穩覺。
美國做事是不管別人能不能受得了的。例如,搞東南亞條約,它就沒有問問中國和印度。亞洲有許多國家,但是它只問了三個: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
尼赫魯總理說東南亞條約是美國對日內瓦協定的一個反應,這很對。日內瓦會議做了好事,美國就來破壞。
艾登曾經建議搞一個亞洲洛迦諾公約,但是後來又放棄了,反而接受東南亞條約。這樣的大國,竟這樣膽小。我們兩國就不怕。美國邀請印度參加馬尼拉會議,印度就有膽量不去。在恢復中國在聯合國中的地位問題上,印度也有膽量投票贊成。但是像英、法這樣的大國卻如此膽小。我們向它們建議,把它們的大國地位給我們,好不好?
英國常說是我們不承認英國;我們對英國說,是它不承認我們。我們勸英國學印度,果真如此,英國就能同我們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北歐的一些國家,例如挪威,也敢於投票贊成恢復我國在聯合國中的地位,因此我們同挪威也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
澳大利亞說怕我們,說共產黨要去侵略它。可是我們連船都沒有,怎樣去法呢?澳大利亞參加馬尼拉條約,說是為了防禦。但是我們向它提出五項原則,同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它又不乾。
我有兩點懷疑:
第一,美國叫著反共的口號,它反對共產黨倒是實在的事。但是,它是否真的害怕中國共產黨呢?中國只有幾枝爛槍,我們有的只是人、農業和手工業。我看美國不是真怕中國共產黨,而是以此為題目,另有其他的目的。
第二,像英國、法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為什麼要跟著美國走,而印度、印尼、緬甸和北歐的一些國家卻不一定跟著美國走呢?我看這是因為英國、法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把它們的利益套在美國車子上,美國火車頭下一個命令,它們不得不服從。印度、印尼、緬甸和北歐的一些國家沒有把它們的利益套在美國車子上,或者套得不緊,因此沒有必要跟著美國走。
(十月十九日)
二
我們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的五項原則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中國古代的聖人之一孟子曾經說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就是說,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馬克思主義也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的,這是同形上學不同的地方。
國與國之間不應該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國家之間。像我國同美國這樣互相警戒著是不好的。
(十月二十一日)
三
我們不贊成過去希特勒德國的說法,希特勒德國和日本過去曾說,它們是“無”的國家,要向“有”的國家取得東西。日本在過去,在十年前,倒的確是“黃禍”。
我們現在需要幾十年的和平,至少幾十年的和平,以便開發國內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不願打仗。假如能創造這樣一個環境,那就很好。凡是贊成這個目標的,我們都能同它合作。毫無疑問,印度是贊成的,印尼和緬甸也是贊成的。
我想泰國也不會懷疑中國要大舉進攻它。我們是想同它搞好關係的,但是泰國政府古怪得很,不理我們。
菲律賓說怕我們侵略,但是我們要同它搞好關係,它又不乾。既然怕侵略,那末我們就交朋友吧,互不侵犯,並且像中印兩國一樣,發表一個聲明。但是它又不乾,它不願意承認我們國家的存在。我們想不出這是為了什麼,唯一的理由就是它聽美國的話,同美國走在一條軌道上,美國說什麼,它就做什麼。
說到美國,我們上次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談完,那就是戰爭問題。尼赫魯總理說,美國想打仗,想用戰爭的辦法得到更大的利益。關於戰爭是否有好處,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可以看一看兩次世界大戰究竟對誰、對哪些國家有好處。可以說兩次大戰對三類國家有利,對其餘的國家都是有害的。
第一類國家是美國帝國主義,它在兩次大戰中獲得了利益,得到了發展。
第二類是在兩次大戰以後建立起來的、由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
第三類是被壓迫的民族和國家,這些不是共產黨領導的,而是由愛國的團體和政黨領導的,像印度、印尼、緬甸、敘利亞和埃及這樣的國家屬於這一類。
要搞戰爭的話,就要動員人民,就要使人民處於緊張狀態,並且使他們學會打仗。但是,人民結合起來以後,勢必會產生革命。例如,中國革命就是這樣,印度的革命也是這樣。我們兩國的獨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沒有第二次大戰,很難取得獨立。
另外一些國家被戰爭削弱了,例如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法國雖然是戰勝國,但是也削弱了。在中國,由於日本和蔣介石削弱了,我們就起來了。由於英國削弱了,印度、緬甸和埃及起來了。由於法國削弱了,越南、敘利亞起來了。由於荷蘭削弱了,印尼起來了。
如果再要打仗的話,不知道美國軍事集團是怎樣的想法。他們過去的經驗是在兩次大戰中得到利益和發展,他們希望通過再一次戰爭得到更大的利益和發展。他們是根據自己的經驗這樣想的,但是,這只是一方面的經驗;另一方面,兩次大戰以後還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和愛國黨派領導的國家。如果再打大戰,我看美國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國本身就會發生問題。如果再打大戰,西亞和非洲的大部或全部、整個拉丁美洲都會脫離帝國主義。
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得到機會才能起來的。布爾什維克如果沒有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那末十月革命就會有困難。我們在中國打了二十二年仗,但是勝利還是在最後幾年取得的。第二次大戰以後,我們得到了機會才起來的。這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方面。
愛國黨派領導的國家方面,我們在東南亞和西亞也可以看到一些例證。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我看,再打大戰,對美國來說是划不來的,整個世界或世界的絕大部分將處於革命狀態。我這樣說,並不是故意危言聳聽,而是根據兩次大戰的實際情況。如果再打大戰,我看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只能使它的統治範圍縮小。
在武器方面,美國以為它有核子彈和大炮,以為它的海、空軍強大,因此它依靠這些東西。我想武器雖然有變化,但是除了殺傷的人數增多以外,沒有根本的不同。古代使用的是冷兵器,例如刀、槍等。後來使用熱兵器,例如步槍、機關槍、大炮等。現在又加上核子彈。但是基本的差別就是,冷兵器殺傷的人較少,熱兵器殺傷的人多一些,核子彈殺傷的人更多。除了死傷的人數以外,沒有什麼差別。過去,冷兵器和熱兵器雙方都有,現在蘇聯和美國也都有核子彈。因此隨著武器的變化,無非是死傷的人數更多而已。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戰,那末死傷的人數恐怕就不是以千萬計,而是要以億萬計。中國現在沒有核子彈,不知道印度有沒有。我們正在開始研究,核子彈是要花本錢的,我們一下子還搞不起來。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戰,那末這一方有死傷,另一方也有死傷,因此就平衡了。最後決定戰爭勝負的還是人,看誰拿著武器,看掌握著武器的戰士們認為什麼對他們最有利,看誰會打仗,而主要的還是前二者。至於說武器的多少,印度國大黨和中國共產黨在開始的時候都是沒有武器的,現在我們都有了武器。
此外,還有一條經驗。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是防禦者勝利,進攻者失敗。第一次大戰中,德國軍隊在西邊打到巴黎,在東邊幾乎打到彼得格勒,但是結果進攻者還是失敗了。第二次大戰中的進攻者,德國、義大利、日本也都失敗了。而防禦的一方取得了勝利,雖然在防禦這一方面的一些國家被戰爭削弱了,例如英國、法國。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不應該再打大戰,應該長期和平。再打大戰的結果,是對侵略者不利的。
我們雙方的分析雖然有些地方相同,有些地方不同,但是結論是相同的。尼赫魯總理在對美國進行分析時說,一方面美國從戰爭中得利,另一方面又遇到了困難。這種分析是很好的。至於戰爭工具,我們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弓箭、大炮和核子彈。尼赫魯總理說有性質上的不同,這是對的。我剛才談武器時,只是就戰爭的結果而言。
不管用什麼武器,不管是哪一個時代進行的戰爭,不管戰爭的規模是地方性的或是世界性的,結果多是一方摧毀另一方。固然,戰爭也有不分勝負而講和的,例如三八線戰爭和十七度線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沒有任何一方根本打敗另一方。但是在大多數的戰爭中,總是一勝一敗,敗者的力量被摧毀得更多些。所謂力量,不僅包括有生命的力量,而且包括物質力量。因此歸根結底,還是看力量損毀的範圍和大小來決定勝負。
當然,我是指戰爭的最後結果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德國的軍隊被全部毀滅,而蘇聯的軍隊不但沒有毀滅,而且還打到柏林。德國、義大利、日本的軍隊都被解除了武裝。尼赫魯總理推想,第三次大戰會使全世界處於混亂時期,這種推想是可能的。核子彈不僅會毀滅人,而且會毀滅物質,但是,是否許多國家就會沒有政府呢?不會的。只要有人存在,總是會有政府的。一個政府被摧毀了,另一個政府又會起來。人類總是要找出路的,剩下來的人也是會求生的。還應該估計到,現在的人比過去的人有很大的變化,他們要求解放和獨立的覺悟已經大大提高,這在無論哪個國家都是如此,包括美國在內。
歸根一句話,不打仗最好。如果我們能替艾森豪當個參謀長,那末他就可以聽我們的話,而不受他的顧問的包圍了。尼赫魯總理做這件工作會比我們順利些。如果我們去做這個工作,他就會說我們以革命來恐嚇他,並且說他不怕革命。我想,不僅戰爭,就是緊張局勢也使製造緊張局勢的人一方面得利,另一方面又受到損害。我想問問,究竟是使人民感到安全有利呢,還是使人民每天處於緊張有利?緊張局勢會促進人民覺悟,使他們做好準備,抵抗壓力。這是有助於革命的。
很明顯,中印之間沒有緊張局勢,我們互相之間也不進行神經戰,也不每天戒備著,像我們同美國之間以及蘇聯同美國之間那樣。
尼赫魯總理到中國來已經有幾天了,一定已經知道了我們的情況。我們現在正執行五年計畫,社會主義改造也正在開始。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全盤計畫就會打亂。我們的錢都放在建設方面了。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經濟和文化計畫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個戰爭計畫來對付戰爭。這就會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延遲。但是把中國全部毀滅,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難的,中國人是會永遠存在的。印度也是這樣。幾千萬年前有一種大動物叫恐龍,它在冰河時期就消滅了。但是後來又出現了別的動物,最後出現了人類。現在在中國還可以看到冰河的遺蹟。
總之,我們應該共同努力來防止戰爭,爭取持久的和平。
(十月二十三日)
四
大約兩千多年前,中國的一個詩人屈原曾有兩句詩:“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我曾經在一次宴會上對尼赫魯總理談起我們對印度的感覺,我說我們同印度不需要互相防備著。我們沒有感覺到印度要損害我們。
我曾經問,我們兩國總理兼外長在談話中如果說錯了話,能不能改?我想是能改的。但這是在我們兩國之間如此,在別的一些國家可能是會抓住我們說錯的話的,我們也會抓住別的一些國家說錯的話。中國有一句話,叫做“抓辮子”。但是我們同印度是不互相抓辮子的,我們並不互相防備,說錯了話也不要緊。
印度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聽袁仲賢大使說,印度南部的人民在農業方面精耕細作,把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都利用了,這有點像我們成都附近的情況。印度的每一個好訊息都使我們高興。印度好了,對世界是有利的。
我很高興能有這幾次會談,使我們相互交換了意見。同時尼赫魯總理又同周恩來總理進行了會談。我們兩國的外交是很容易辦的,不需要吵架。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有時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紅耳赤。但是這種吵架,和我們同杜勒斯[13]的吵架,是有性質上的不同的。
尼赫魯總理這次來訪,一定會看出來,中國是很需要朋友的。我們是一個新中國,雖然號稱大國,但是力量還弱。在我們面前站著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是美國。美國只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因此我們需要朋友。這是尼赫魯總理可以感覺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這一點可以從我們這幾次會談,從過去幾年我們的合作,從周總理訪問印度時受到的歡迎和進行的懇談看得出來。
尼赫魯總理主張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並且表示希望贊成和平的國家日益增多。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是一個很好的口號,我們贊成。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中印簽訂了關於西藏的協定,這是有利於消除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的。我們共同宣布了五項原則,這也是很好的。華僑問題也應該適當地解決,免得有些國家說我們要利用華僑搗亂。如果華僑保持僑民身份,他們就不應該參加所在國的政治活動;如果取得了所在國的國籍,那末就應該按該國的法律辦事。華僑也應該遵守所在國的法律。
凡是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問題,我們都要來解決,這就能達到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對任何一方有害,否則就不能持久,一定會破裂。不論是朋友之間、國與國之間或是政黨與政黨之間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則誰還乾呢?
(十月二十六日)
相關注釋
 這是1954年6月下旬,應邀訪問印度時,和印度總統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右一)、副總統薩瓦帕利·拉達克里希南(右三)、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合影。(相關圖片)
這是1954年6月下旬,應邀訪問印度時,和印度總統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右一)、副總統薩瓦帕利·拉達克里希南(右三)、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合影。(相關圖片)洛迦諾公約,全稱《洛迦諾保證條約》,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英、法、德、意、比、波、捷(捷克斯洛伐克)七國代表在瑞士洛迦諾會議上通過,同年十二月一日在英國倫敦正式簽字。公約包括一個議定書和七個條約,其中最重要的《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和義大利相互保證條約》(又稱《萊茵保全公約》 )規定,簽約國相互保證德法、德比邊界不受侵犯;遵守《凡爾賽和約》中關於德國萊茵區非軍事化的協定;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一切爭端。一九三六年三月德國法西斯政府毀約進軍萊茵區,一九三九年四月宣布廢止洛迦諾公約。五十年代初,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曾主張在東南亞地區搞一個類似洛迦諾公約的集體安全體系,後因美國的反對未能實現。
布爾什維克,指布爾什維克黨,原蘇聯共產黨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三八線戰爭,指韓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美國和蘇聯商定在朝鮮國土上以北緯三十八度線,作為對日本採取軍事行動和受降範圍的臨時分界線,這條界線通稱“三八線”。一九五○年六月,朝鮮半島三八線北南兩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韓國)發生戰爭。隨後,美國打著聯合國的旗號出兵干涉,並越過三八線向中朝邊境大舉進犯,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國人民志願軍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沉重打擊了美國的侵略,迫使它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籤字。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四年越南人民抗擊法國侵略的戰爭。一九四五年九月,越南宣布獨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法國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統治,隨即入侵越南。越南人民為保衛民族獨立進行了長達八年多的抗法戰爭。一九五四年五月,越南人民經奠邊府戰役取得抗法鬥爭的決定性勝利。七月,根據日內瓦協定,越南人民軍和法軍以北緯十七度線為臨時軍事分界線實行停火;法國承認越南獨立並撤出印度支那。
艾森豪,當時任美國總統。
袁仲賢,當時任中國駐印度大使。
杜勒斯,當時任美國國務卿。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國和印度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協定明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兩國關係的準則,並以此確定了促進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貿易及便利兩國人民互相朝聖往來的各項具體辦法。主要內容是:雙方互設商務代理處;雙方商人、香客在指定地點進行貿易和按慣例朝聖,並經一定山口、道路往來;關於兩國外交、公務人員及國民過境事宜的規定等。協定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生效,有效期八年,一九六二年六月期滿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