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簡介
孔明於多洱河畔設寨,堅守不出,待獲兵疲乏而四擒四縱。
禿龍洞洞主以的毒之四泉(啞泉,滅泉,黑泉,柔泉)敗蜀兵。
孟獲之兄孟節為蜀兵解毒,蜀兵掘地得水。
蠻方二十一洞主楊鋒擒孟獲獻孔明,孔明五縱之去。
正文
 《三國演義》第八十九回
《三國演義》第八十九回卻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為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河為壕塹,以浮橋為門,壘土為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
卻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眾將簇擁而出。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諸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
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探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將曰:“汝等敢出戰否?”眾將欣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進。卻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卻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卻斷其後。”張翼受計而退。孔明只教關索護車。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
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優曰:“諸葛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急之事:若非吳侵,定是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為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不可錯過。”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為筏,以備渡河;卻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卻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是日,狂風大起。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徑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奔走,方才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天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裡相遇。汝等奮力前去,連人帶車砍為粉碎!”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趷踏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並諸甸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蠻兵皆感嘆而去。少頃,張翼解孟優至。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不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獲曰:“吾今誤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拿住吾,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孔明即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報仇。兄弟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朵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見了朵思大王。朵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訴說前事。朵思曰:“大王寬心。若蜀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獲大喜,問計於朵思。朵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眾,不能進也。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蠍;黃昏時分,煙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個毒泉:一名啞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必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濺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暖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此處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自此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壘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敝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定然飲水,雖百萬之眾,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設!四泉之水,足以報敗兵之恨也!”自此,孟獲、孟優終日與朵思大王筵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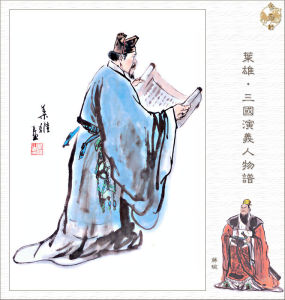 蔣琬
蔣琬卻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有後人詠南方苦熱詩曰:“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又有詩曰:“赤帝施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喘,海熱巨鰲驚。忍舍溪邊坐?慵拋竹里行。如何沙塞客,擐甲復長征!”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蔣琬曰:“孟獲四次遭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況今天氣炎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卻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徑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峰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塑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碑,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託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佑三軍!”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東南有一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暖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敝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煙瘴甚起,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余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
孔明曰:“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託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處,可以解之。”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汲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更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眾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繞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絛,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至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眾兵殘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飲。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眾軍到萬安溪中沐浴。
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蠍,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為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眾軍盡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嘆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為王,可乎?”節曰:“為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高士幽棲獨閉關,武侯曾此破諸蠻。至今古木無人境,猶有寒煙鎖舊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心驚慌。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即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後人有詩曰:“為國平蠻統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耿恭拜井甘泉出,諸葛虔誠水夜生。”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朵思大王聞知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擔,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朵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于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朵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於是大賞蠻兵。
正欲起程,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鄰兵助我,我必勝矣!”即與朵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蜀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跳而入,群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杯詣孟獲、孟優前。二人接杯,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朵思大王卻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侄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
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朵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令入,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侄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並朵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正是:深臨險地非容易,更展奇謀豈偶然!
未知孟獲整兵再來,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賞析
在本回演義中出現了這樣一個人物,孟節,孟獲的哥哥,與蠻王孟獲不同,孟節顯得文質彬彬,更象一個儒家文士,所以諸葛亮在得知孟節的身份後大吃一驚,隨後便感嘆盜跖、下惠之事。
盜跖、下惠是什麼樣的故事呢?相信不少人知道柳下惠的故事,坐懷不亂的君子,其實柳下惠本姓展,乃是一個清正嚴謹的官員,後來歸隱,柳下其實是他日後歸隱的地名,而“惠”乃是他死後的諡號,這在古代也是常見的事,他被世人稱為君子,不過最出名的還是那坐懷不亂的故事了。(一直以來有很多人質疑甚至嘲笑柳下惠的坐懷不亂,不過也很正常,君子就如英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指望每一個人都象君子一樣坐懷不亂是不現實的,君子英雄畢竟是少數。)至於盜跖在傳說中是柳下惠的弟弟,乃是手下有著數千人橫行天下的大盜匪,打家劫舍,無惡不作,便是一般的諸侯見之也要躲避,《莊子》中製造出孔子見盜跖的故事,為得是嘲諷儒家。盜跖柳下惠的故事都是傳說,所以諸葛亮稱之不信,因為兩兄弟一極善一極惡實在是很少見的事。(當然,現代大有將兩者顛倒的觀點。)所以見到孟節孟獲兩兄弟時,諸葛亮便說到這故事了。
還是回到我們的主題上來,其實兩兄弟善惡相反,雖然不常見,但是也不是太希奇的事。孟節變得如儒家謙謙君子或者說漢化一些也不是什麼令人驚奇之事,演義中的孟節雖然是虛構,但是少數民族的君王甚或一城之人變得如中原習俗一般,這在中原東西南北都有例子,尤其是在中華強盛之時,一些國家甚至有小中華之稱。不過,即便有這樣的例子,但是那些在草原上,叢林中的少數民族卻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習俗,無論中華強盛無比也沒有改變,然而令人驚奇的是,那些少數民族在進入中原後,卻迅速的被同化,漢化,變得和一般的漢族無疑,甚至連自己的族群都忘記了,他們的民族消失或者說融合了。
對這一現象,史學家稱之為我們偉大的文明文化的功勞,是的,確實如此,但是這只是一個結果,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呢?不是一句我們的漢文化漢文明包容一切的套話就可以說明的。
“夷入夏則夏,夏入夷則夷”這句話存在已久,這句話的解釋也很多樣,在我看來,這句話正好可以解釋“同化”一事。
中原文明的根本是建立在什麼上面的?我們都說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中原文明是在黃河流域農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我們是農耕文明,這十分的自然,只有農耕才能保證穩定的收成,在穩定的收成之上,文明才得以建立,東西方的文明莫不如此,也就是說,那些耕地,那些稻穀,是我們文明的基石。和我們不同,草原中的民族以遊牧為生存方式,叢林中的民族以採集或者遊獵為生存方式,這些差異決定了我們和他們的文明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我們的差異是建立在生活方式而上,這是沒辦法避免的問題,所以即便有著一兩個部落或者城市會因為種種緣故漢化了,但是這並不能改變大體的格局,就好象在中原,再進行任何的胡化政策,能把所有的漢人頭後留上大辮子,讓漢人的服裝消失,但是骨子裡也改變不了漢人的文明,反而因為他們進入了漢人的地方而變得漢化。
這一切是為什麼?因為他們在草原上的那一套到了中原行不通,他們只能下馬做起耕地的農夫來,既然做起了農夫,那就要接受農耕文明,而建立在農耕文明的漢文明是最適合的,這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他們再掙扎,再徘徊,再痛苦,也回不到以前,因為這是在他們選擇進入了中原的那一刻便決定的了。漢化的魔力便在於此。當他們漢化完畢,做了正宗的農夫,建立起巨大的物質文明,回首那些草原叢林,看著他們祖先曾經馳騁過的土地上現在的那些牧民獵手們,不會惺惺相惜,而只會從鼻子裡輕蔑的哼出一句:
“那些蠻夷!”
是的,他們那些當年的蠻夷已經成為中原的一部分,完全有資格稱呼那些還留在草原叢林上的人為一句“蠻夷”,這與血統無關,即便再正宗的中原人進入了草原叢林,適應了那些生活方式,接受了他們的文化之後,也只能做蠻夷。
與東方相似的故事,在歐洲,蜂擁而入的蠻族進入了古羅馬帝國的大地,他們看到了大道,看到了黃金,看到了他們以前從沒見過的文明,而且他們可以用刀槍得到這一切,於是他們燒啊,砸啊,搶啊,當一切結束,他們站在古羅馬文明的廢墟之上,他們發現,他們也不得不放下刀槍盾牌,占得一塊土地,做起農夫,重新修路,重新迷戀上那些奢侈品,重建一次文明,即便這個文明在不久前是被自己或者自己的祖先親手毀滅的。
我們腳下的土地決定了我們的文明,這就是一個現實,假如中國在蠻族入侵的那一刻被殺光了所有人,當蠻族發現這塊土地上只有他們自己時,除非他們把那些土地變為牧場,否則他們也只有乖乖的下馬,放下弓箭,在漢文明的廢墟上建立起另一個農耕文明。
幸運的是,這一切並沒有成為現實,我們並不需要在完全的廢墟上重建,雖然同樣有著蠻族入侵,但是我們幾次為文明保留下了一顆種子,即便這幾個種子喜歡內耗,北伐也總是功虧一簣,以至於我們稱其為“偏安”。但是這至少是個種子,是個模式,當那些蠻夷們定下心來,發覺騎馬不能解決一切,牛馬不能代表文明,在這塊土地上,只有那些從地上長出來的稻穀才是一切的基石,他們才小心翼翼的從馬上跳下,戰戰兢兢的握起了鋤頭,他們不再滿世界跑,他們腳下的那一塊土地才是他們的一切呢!當得到了收成,不需要擔心在寒冬中看著自己的牛羊死去,不需要憂心明年的族爭能不能活下來,不需要過著那些血腥的日子後,他們需要文明了。而當他們發現這一切在原先的天朝,現在的偏安政權有這么一個現成的文明,而這些文明是如此的適應現在腳下的土地時,他們還不馬上學習模仿嗎?
自然,學習模仿完畢,他們終於紮根於這塊土地之上,他們不單對著草原叢林那邊投去輕蔑的目光,也開始對南方的中原文明挑戰了,這是一場誰代表中華的戰爭,但是實際上,無論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他們都是這個文明的捍衛者。
每一次的蠻族的入主中原,結果都是如此,唯一變化的便是漢文明的留存多少,變異多少而已,而這決定於原本遵守漢文明的那些人死了多少,那些偏安的政權能堅持多久,死得越少,堅持越久,甚至復興成果,那漢文明留存的越多。在這裡,我們的漢化實在要感謝我們龐大的人口基數與那些堅持抵抗外地的英雄們。
這是一個宿命,這是農耕文明與草原或者叢林的宿命,因為生存方式的差異,決定了他們不可挽救的宿命,當來自草原和叢林的人們來到中原那些農田,他們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擺脫不穩定的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存活下去,享受文明的果實;第二個選擇:回到那個大草原,進行不穩定而且殘酷的戰鬥。前者總有一天會面對後者的挑戰,即便兩者可能是兄弟,但是他們選擇了不同的路,盜跖與下惠的道路。
千百年來,儘管有些草原叢林變成了耕地,一些耕地變回了草原甚至沙漠,但是總體上看,草原叢林一直存在著,上面不時有著牧民趕著牛羊經過,有著獵人背著獵物回家,農田也一直存在著,農夫在自己的土地上注視著自己的果實。戰鬥永不停息,直到鐵路帶來了火車的轟鳴,機器展現著鋼鐵的力量,一切才告終止。
或許,那又是另一個文明與蠻夷爭奪的開始。
回評
毛宗崗批語
瀘水之險不可涉,西洱河之險不可方舟,可謂險之極矣。不謂又有啞泉、柔泉、黑泉、滅泉之惡,尤有甚焉。南方屬火,炎天如火,蜀兵方苦於火,而忽又苦於水,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惟南方險阻出於意料之外,乃愈顯丞相功績,出於意料之外耳。
四擒孟獲,以假棄舊寨為欲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退為進也。五擒孟獲,以深入重地為不可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進為進也。五擒之難,倍難於四擒;則五縱之難,亦倍難於四縱。於四擒見孔明之智,於五擒見孔明之勇,於四縱五縱見孔明之仁。
孔明乃先主之所謂水也,而有四泉以難孔明,則是以水厄水矣。又有二溪以助孔明,則又以水濟水矣。至於拜井出泉,而水又自能生水。然則蜀人之有孔明,其亦如魚得水乎!
每讀《封神演義》,滿紙仙道,滿目鬼神,覺姜子牙竟一無所用,不若《三國志》中之偶一見之也。如伏波顯聖,山神指迷,入山求草,祝井出泉,未嘗不仰邀神助,恍遇仙翁;然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使盡賴鬼謀,何以見人謀之善;使盡仗仙力,何以見人力之奇哉!
文章之妙,妙在極熱時寫一冷人,極忙中寫一閒景。如萬安隱者,飄飄然有世外之風,其地則柏澗松岩,其人則竹冠藜杖。孔明之遇之,殆與先主之遇水鏡,劉璝之問紫虛,陳震之謁青城,幾相仿佛矣。然先主遇水鏡於難後,孔明則求萬安於難中;紫虛、青城未嘗賴之以救敗,萬安則實賴之以救死。是彼雖極閒,而見者之心極忙;彼雖極冷,而見者之心極熱:又不似前三人之有意無意,為可見可不見之人也。最相類又最不相類,豈非絕世奇事,絕世奇文。
孔明之見隱者不足奇,而奇莫奇於即孟獲之兄也。有四泉之惡,則有二溪之美以為之反;有助虐之孟優,則有助善之孟節以為之反:地既有之,人亦宜然。然我謂孟獲之五擒而不服者正在此。何也?納孟獲之弟之詐降以誘孟獲,與以孟獲誘孟獲無異也;賴孟獲之兄之相救以制孟獲,與以孟獲制孟獲無異也。以孟獲誘孟獲,而孟獲不服;以孟獲制孟獲,愈不服;惟以孔明勝孟獲,而孟獲始傾心折服。則吾得而更觀五縱之後矣。
李贄總評
孟獲卻也頑皮,孔明卻也耐心。想欲藉此消閒過日乎?不然,何不憚煩一至此也!
或曰,孔明不去征吳伐魏,乃與這伙蠻人頑耍,亦沒正經極矣。不知世上蠻人極多,然一血未嘗不可化誨,只要耐心誨訓,自然變化。若一性急,蠻人便使起蠻性來,愈多事矣。此為後世待蠻秘訣,作者借孔明徵蠻而寓言之也,勿太認真也。
鍾敬伯總評
世上蠻人極多,未嘗不可化誨,只要耐心。若一性急,蠻人便使起蠻性來,愈多事矣。此為後世待蠻秘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