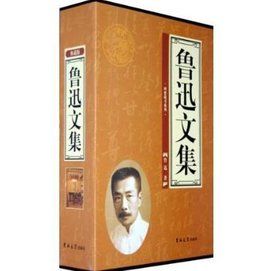人物信息
魯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他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髮像刷子一樣直豎著,濃密的鬍鬚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毛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
 魯迅像
魯迅像| 中文名: | 周樹人 |
| 別名: | 原名樹人,又名樟壽,後改名豫才 |
| 國籍: | 中國 |
| 民族: | 漢族 |
| 出生地: | 浙江省紹興府 會稽 縣 |
| 出生日期: | 1881年9月25日 |
| 逝世日期: | 1936年10月19日 |
| 職業: | 文學家,思想家,評論家 |
| 畢業院校: | 南京路礦學堂,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
| 主要成就: | 領導新文化運動 |
| 代表作品: | 《 吶喊 》《 彷徨 》,《 故事新編 》《 狂人日記 》《 朝花夕拾 》 |
| 身高: | 161厘米 |
| 重要事件 : | 新文化運動 |
圖書信息
作者:魯迅 著
 魯迅像
魯迅像錢理群 王得後 選編
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10月
ISBN:978-7-5339-0441-8
字數:316千字
定價:19.50元
目錄信息
《吶喊》
本集出版收小說十五篇,作於1918年至1922
年間,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列為該社
“文藝叢書”之一。1926年10月第三次印刷時
起,改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列入作者所編的
“烏合之眾”。1930年1月第十三次印刷時,作者
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後改名為《補天》,
收入《故事新編》)此後印行的版本均從1930年版。
自序
狂人日記
孔乙己
藥
明天
一件小事
頭髮的故事
《風波》
《故鄉》
阿Q正傳
端午節
白光
兔和貓
鴨的喜劇
社戲
《彷徨》
本集出版收小說十一篇。作於1924年至1925
年間,1926年8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列為作
者所編“烏合之眾”之一。
祝福
在酒樓上
幸福的家庭
肥皂
長明燈
示眾
高老夫子
孤獨者
傷逝
弟兄
離婚
《故事新編》
本集初版收小說八篇。作於1922年至1935年
間。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列為巴金所編“文學叢刊”之一。
序言
補天
奔月
理水
採薇
鑄劍
出關
非功
起死
《集外作品》
懷舊
2005年版《魯迅全集》
第一卷 墳 熱風 吶喊
第二卷 仿徨 野草 朝花夕拾 又名《舊事重提》 故事新編
第三卷 華蓋集華蓋集續編 而巳集
第四卷 三閒集 二心集 南腔北調集
第五卷 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拾零集
第六卷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
第七卷 集外集集外集拾遺
第八卷 集外集拾遺補編
第九卷 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
第十卷 古籍序跋集譯文序跋集
第十一卷 兩地書 書信(1904-1926)
第十二卷 書信(1927-1933)
第十三卷 書信(1934-1935)
第十四卷 書信(1936 致外國人士)
第十五卷 日記(1912-1926)
第十六卷 日記(1927-1936)
第十七卷 日記(人物書刊注釋)
第十八卷 附集 魯迅著譯年表 全集篇目索引 全集注釋索
補充書目《如果魯迅活到今日》121分鐘
小說藝術風格
鑑賞
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源於自然,高於自然。魯迅先生的小說,亦正如此。魯迅先生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魯迅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同時他也一再地表示,他所強調的是“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難,並非真勸人都到山裡去”;他自己更是絕不願意躲到“鶴唳一聲,白雲郁然而起”的田園詩中去,他要“活在人間”,即使是遭到人們的孤立,排擠,也仍然不離開“人海”,讓生命的“沉鍾”永遠“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鳴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宣稱,他“對於自然美,自恨並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卻念念不忘記載著人間奮鬥歷史的“遺蹟”。魯迅本質上是一個社會感與歷史感都極強的思想鬥士,離開了社會人生的自然及自然美,對於他是沒有意義的。他讚賞自然和自然美,完全著眼於從中發現社會和發現自己。從這樣的審美觀點出發,魯迅喜愛的自然美是“人們和天然苦鬥而成的景物”,即從中可以發現社會和人生鬥爭精神的深沉雄大、壯闊古拙的力的美。在《野草》里,魯迅也曾描繪過江南明麗的風光,如《好的故事》,他所著重的依然是從“永是生動,永是展開”的“美的人和美的事”中去捕捉“飛動”的美,從而感到一種生命力的存在。但總的說來,他對秀麗的江南風景,“並無敏感”,他直截了當地表示:“我不愛江南。秀氣是秀氣的,但小氣”。他批評杭州的風景“顯得小家子氣,氣派不大”,以為“北方風景,是偉大的,倘不至於日見其荒涼,實較適於居住”。在《野草·雪》里,“與滋潤美艷之至”的“江南的雪”相比較,他顯然更醉心於“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後,卻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粘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為屋裡居人的火的溫熱。別的,在晴天之下,鏇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霧,鏇轉而且升騰,瀰漫太空,使太空鏇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魯迅曾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祥林嫂、愛心這樣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這樣的人際關係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係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採取的是一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並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洩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鬱積的怨憤之氣。誠然閱讀魯迅作品,總喜歡與“階級鬥爭”掛鈎。其實,細細品來卻會有別一番風味。《狂人日記》,我不能給它下個定義,在一開始讀它時,我甚至摸不著頭腦,我不清楚自己這是在看一篇什麼樣的文章,有點害怕,有點疑惑,那嚇人的語句,吃人的歷史,仿佛就發生在身邊使我不禁聯想自己所生活的生活,是該怎么樣?也許他的“吃人”也可理解為當今社會中金錢為上,以利為友的沒有親情友情可言的只顧自身,榨人不眨眼的冷酷的競爭吧,沒有錢就不能生活,就只能乞求,去要飯,這不是跟吃人一樣嗎?但生活中,我也是相信有那么些溫暖可言的,畢竟每天的太陽是溫暖的,在人類越來越文明之際又怎么可以發生人吃人的這種野蠻行為呢。很欣賞阿Q的那種心滿意足的自認為得勝的心態,稱之為妙法不為過。但被人打了之後還有愉快心情,還能和別人調笑一通,回到土谷祠倒頭就睡著了,這就是阿Q精神嗎?有點愚甚至有點蠢,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個調節心理的好辦法,凡事換個角度想或許會有收穫吧。讀書後,回望一下各部小說,凜然發現魯迅先生其實是在博大的、運動著的“自然”中,發現與肯定了人。
風格
魯迅的小說之所以開掘深,立意新,主要是因為他在構思時高瞻遠矚,熔鑄古今,他是從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從現實與歷史血肉相連的深度來認識、分析、發掘事物的內在本質,鑄造藝術形象的。因此,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人的精魂,魯迅的精魂將不斷奮鬥,向上,閃耀!
編輯推薦
《魯迅小說:經典文存》收入魯迅先生的小說精品數十篇。其中《孔乙己》、《狂人日記》、《故鄉》、《阿Q正傳》、《祝福》等是國人所耳熟能詳的篇章。這些作品內容豐富,題材各異,構思精巧,文筆精巧、語言幽默、內蘊深厚、風格恬淡,充分顯示了魯迅先生的文學功底及豐富的人生閱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創作風格,非常值得一讀。
現在,讓我們再次領略一下魯迅先生留給我們的精彩文筆。
這時候,我的腦里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那猹卻捋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文摘
吶喊
自序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檯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里,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里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裡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裡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裡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么,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賓士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著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僥倖的事,但僥倖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吶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於北京。
(原刊1923年8月21日《晨報·文學旬刊》)
狂人日記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訊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型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於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