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走鬼
走鬼“走鬼”始於三、四十年代
香港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走鬼”這一名詞呢?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主席林貴昌回憶說,他已經入行40多年,在他入行時人們已經開始叫“走鬼”,起碼也有四、五十年歷史了。
早在三、四十年代,香港經濟不景氣,沒有製造業,也沒有街市(菜市場)及大型百貨商場,卻有大批內地移民來香港謀生。當中許多人來自廣東鄉下,沒有文化也沒有一技之長,為了養家餬口惟有跟著已經做開小販的同鄉或親戚朋友做小販。當時的港英政府就以維持治安為名,對滿街小商、通巷小販開始橫加打擊,採取一律不準在街頭擺賣的政策。
而香港三、四十年代許多僱傭警察來自印度與巴基斯坦,這些印巴人長相明顯有別於華人,有的還是紅毛混血兒,所以香港人稱他們為“紅毛鬼”。
由於民族不同,語言不同,他們對做小商販的華人自然沒有什麼感情,執起法來特別嚴厲,一點情面也不給,每每抓到小商販非踢即打特別兇殘,所以那時的小商販很害怕這些紅毛警察。每當紅毛警察一出現,第一個見到的小販便大喊:“紅毛鬼來了,快走哇!”,聽到喊聲,其它小販就即刻抄起貨品一鬨而散。久而久之,為了簡單易喊,便改為“走哇,鬼來了!”及後來的“走鬼呀!”。
看法
 走鬼
走鬼危機當前,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如何紓解就業壓力,從政府官員到專家學家,不斷奉獻出或驚奇或雷人的主意。2月8日《羊城晚報》訊息說,廣東省政協常委、九三學社廣東副主委溫洋認為,大學生一畢業就必須是白領、公務員屬於就業觀念固化。在就業難的情況下,大學生也不妨轉變觀念——噹噹個體戶、小商販。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08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創紀錄的559萬人,比去年增加近13%,加上此前未就業的,今年全國將有超過700萬的高校畢業生需要就業。高校畢業生人數連年攀升,再加上新《勞動契約法》的實施、美國次貸危機以及往年積壓未就業畢業生等因素,毋庸置疑,2008年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
形勢嚴峻更需要得力舉措。既然現有產業規模暫時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就業崗位,那么,當個流動小販如何?溫陽先生的“創意”其實並不算新鮮,早在很多年前,不少大學在搞“注水就業率”的時候,就有了類似的奇思妙想:要求畢業生必須提供就業協定書和就業接收函,否則不發放畢業證,於是也就默許部分學生為了拿到畢業證書而找學校附近小店“簽約”。更幽默點的說法,能留在學校周邊小賣店就業,也可以簡稱“留校”了,這就業的層次還不低。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小商小販也不是什麼低賤的工作,但是,選擇職業不是玩腦筋急轉彎,總得有些價值的考量。就個人而言,不是所有大學生都適合做銷售;從投入產出來說,十年寒窗,數萬成本,最後竟然要求人參賣出白菜價,以此解決“成交量”頹勢,恐怕大學生和家長都不能樂意;從就業率來說,古今中外還沒見把小商小販也統計進就業參數的,這顯然不是轉變觀念的問題,而是偷換概念;從社會發展來說,鼓勵大學生去做走鬼,也不利於最佳化人力資源配置。
拋開以上考慮不談,大學生去做走鬼,城管能答應嗎?前幾日,有地方城管號稱要做“最可愛的人”,而公眾的價值期待顯然更低,普遍認為城管只要能做“最不可恨的人”就很感動了。城市管理如果不能釐清價值取向,作為弱勢謀生的走鬼與作為基層執法的城管必然會形成對壘而引發矛盾不斷。溫陽先生說,現在不少大商人,當年不也是“走鬼”出身?
一提到就業問題,就有人要求求職者“轉變就業觀念”,彷佛就業難都是觀念惹的禍。觀念是主觀的,崗位卻是客觀的。大學生再怎么轉,合適的崗位恐怕也不是“轉”出來的。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走鬼式就業解困法”,倒不在於這個主意有多荒唐,而是透露著一股推卸責任的怪味兒。就業也好,創業也罷,都離不開政策支持,離不開產業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責任。就業難不可怕,只要經濟面向好,辦法總比困難多,當下而言,還是踏踏實實為大學生就業想點辦法、指點出路,少來一些忽悠人的歪主意吧。
角色
 走鬼
走鬼流動小販在很多城市裡,就是一個近乎“過街老鼠”的角色,他們的生存境況是充滿艱辛甚至讓人同情的,新聞中所提到的將“流動小販”稱之為“走鬼”,雖然是廣東的一句由來已久的俗語,但也從一個側面對“流動小販”的生存處境做出了真實而形象的“註解”。城管的打擊與罰款是制約這個就業群體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如以前報導過的——有的城管沒收流動小販的物品如同掠奪,有的城管甚至私分“戰利品”。在小販看來,這簡直是“鬼子進村”。於是,小販天天逃城管,在城市的街巷間展開了“游擊”戰。——這樣的“創業環境”又如何能讓大學生對做流動小販有信心、有興趣?
溫洋又說:“其實,不用舉李嘉誠等人的例子,我國起家於八十年代的那些富豪,很多人的第一桶金都來自於乾“流動小販”,這種就業方式對我國經濟的促進是有目共睹的,但從90年代中期開始,城管的出現,讓這一就業方式光輝不再。由於全球經濟的不景氣,“流動小販”在“夾縫裡生存”的處境,似乎有了一些轉變,一些地方紛紛想起了流動小販對解決就業所能起到的作用,並出台了一些有利於小販生存的政策,這是值得提倡的,但這樣的政策應該長遠堅持下去,而不是應付經濟困境的一種臨時手段,如果是一種臨時手段,又如何能解除選擇這種方式就業者的後顧之憂?一旦經濟形勢好轉,會不會又以“市容”為由對“流動小販”進行打擊?“過河拆橋”的故事會不會又重演?這都是選擇“流動小販”創業者心中所不能不考慮的。
在一些管理者眼裡,城市的“市容”似乎和“流動小販”的存在是一對不好調和的矛盾,但這種觀念實際上是錯誤的,在一些國際大都市,“流動小販”到處可見,不僅沒被當作影響市容進行嚴厲打擊,反而成為街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比如美國街頭的賣肉狗和飲料的流動車。
應該說,對“流動小販”適當的管理與引導是有必要的,但“管理”不能搞成一見就抓的“處理”,管理也不能僅僅只是限定流動小販只能在某個區域比如跳蚤市場營業,而要客觀考慮到應有的“流動”性,現在的跳蚤市場的商販與城管的矛盾不多,矛盾和偏見多半發生於“流動”問題中。因此,與其批評大學生就業觀念固化,眼高手低、“傲慢”而不願意選擇當“流動小販”,還不如反思我們的相關部門對“流動小販”這種就業方式有著怎樣的“偏見”,只有管理者改變把“流動小販”認作是“麻煩製造者”的觀念,平等與人性化地對待“流動小販”,給“流動小販”創造一個寬鬆的創業環境,才能重塑這種就業方式應有的尊嚴,才可能讓這種就業方式對大學生有吸引力。
而要達到這種轉變,我想不是靠一兩次呼籲就可能完成的,需要一個政策的長期寬鬆對待與扶持過程。
試點
政策
廣州市人大常委會昨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將於9月1日正式實施。新《條例》實施後,城管對“走鬼”的管理方式將出現重大突破。據廣州市城管局局長李廷貴透露,天河、番禺、蘿崗、南沙等區的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將試點,在不影響交通、市容和市民正常生活秩序的情況下,允許流動商販設攤擺賣,就地規範並引導其入場入室經營。據悉,相關管理辦法正在制定當中,試點成功後將在全市231條城中村中推廣。
區分亂擺賣與民生就業
可賣自產農副產品,嚴管燒烤攤
多年來,對“走鬼”一味的“禁”和“堵”,並沒有真正管住亂擺賣;相反,在城管執法中,暴力抗法的事件卻屢屢升級。據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力介紹,此次《條例》在立法調研中,不少常委會組成人員、人大代表、專家以及網民等認為,城市管理應當疏堵結合,對流動商販一味的“堵”,不僅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有可能會引發更多社會矛盾。
,新《條例》規定,“市、區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引導流動商販入場(室)從事合法經營。”針對這一“方向性”的規定,李廷貴透露,《條例》施行後,城管對亂擺賣的管理已有新的思路,即延續蘿崗、花都模式,在天河、番禺、南沙的城中村或城鄉結合部開設流動商販試點,允許“走鬼”在劃定時間和劃定路段,在不影響交通出行、市容市貌以及市民正常生活秩序的條件下,設攤擺賣。據悉,黃埔、白雲區的試點也正在選址中。
對於“就地規範,入場入室經營”的新思路,李廷貴解釋說,首先是建議由市、區政府指定區域或路段,允許銷售自產農副產品的農民、下崗工人、零就業家庭以及低收入家庭和殘疾人等確實有困難的人員擺賣,以明確區分亂擺賣的違法問題與民生就業問題。但對一些重點違法行為則絕不放鬆監管,李廷貴表示,對重點地區和路段、重點時間段、重點違法行為(如燒烤)等,將繼續嚴加管理。
李廷貴還透露,對城中村流動商販規範管理的工作已經展開,目前在試點的同時正制定相關管理辦法,待總結完善後,這種管理模式將向全市231條城中村推廣。
明確正職與聘用人員職責
協管員無權處罰小販
廣州現有的城管隊伍中,正規隊員3196人,而聘用的協管員則有5321人。據市民反映,一些協管員的素質修養實在是不敢恭維。在去年12月11日的《羊城論壇》上,市民王老伯反映親眼看見協管員追趕街邊擦鞋小妹,“個個像劉翔一樣跑過來,抓起人家的塑膠凳就摔爛在地上。”
據了解,目前城管不文明執法的行為多是聘用的契約工、臨時工等不具備法定執法資格的人員所為。筆者搜尋不文明執法的相關報導發現,雖然事隔3年多,海印電器城附近兩名協管毆打擦鞋妹的網帖至今仍時常被提起。
李力表示,新頒布的《條例》,將明確禁止城管機關聘用的契約工、臨時工實施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這就意味著除了正職的3196名城管,其餘協管員只能在巡查中發現問題、報告問題,但決不能查扣流動商販的物品,或者實施其他形式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條例》還明確規定,對於城管機關不制止聘用人員實施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情節嚴重,或者安排聘用人員實施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將受到行政處分。
市民如何從著裝上區分正規隊員和協管人員?李廷貴解釋稱,正規隊員的制服為天藍色,而協管員的服裝為灰綠色;此外,服裝上的標誌也有所區別。李廷貴表示,招協管員也有一套嚴格的程式,需經過專門的法律法規培訓,考核過關後,才能持證上崗。
規範查扣條件及程式
勸告無效才能查扣,30天未處理須通知領回
城管執法過程中,是否應當賦予城管扣押流動商販物品的權力,以及如何規範這一行為,也成為《條例》制定中的熱點問題。
根據新《條例》,只有當“走鬼”的行為同時符合以下兩個條件時,城管機關才能實施扣押。一是占用公共場所設攤經營、兜售物品,且市民多次投訴或者占用的公共場所屬於城市主幹道兩側、城市廣場、機場、火車站、汽車客運站、客運碼頭、會展中心、商業步行街、黨政機關周邊等重要區域;二是經城管機關勸告改正,流動商販仍拒不改正的,城管就可以對其商品實施扣押。
“城管要當場交付扣押物品清單和查封、扣押決定書,當事人拒絕在清單上籤名或者不在現場的,城管機關應對清單予以見證、公證或者清單上註明情況。”李力表示,《條例》對查封、扣押的程式作了明確的規定。
被查扣物品的去向問題,一直為市民所詬病。新《條例》實施後,扣留物品不僅要開列清單,處罰完成後,城管還要主動通知小販來領回物品。《條例》規定,查封、扣押一般不得超過30日,在法定期限內未作出處理決定的,查封、扣押措施自動解除。一旦解除,城管要在3天內通知小販來領回物品。
如何防止城管隊員野蠻執法?《條例》也給城管隊員的執法行為上了“緊箍咒”:不得辱罵、威脅、毆打當事人,不得違法損毀當事人的物品,否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試點選址
天河:龍洞
花都:新華街
蘿崗:夏港街普暉社區
南沙:裕興花園、南沙舊鎮
番禺:市橋東江、橋南市場
白雲、黃埔選址正在研究中
他山之石
◎2008年下半年,甘肅省政府下發檔案:在不影響城市道路交通和公共衛生的前提下允許臨時性便民經營活動。隨後,節假日期間,流動商販上街擺攤宣布開禁,市民商販紛紛叫好。
◎2008年,東莞嘗試在新城市中心區建起流動小商販集中經營點,希望收納“走鬼”進入社區。同時,城管等部門也可集中對各社區經營點實施衛生監管工作,確保食品安全。
◎今年3月,上海市市容環衛局擬定了一套《城市設攤導則》,被老百姓所接受的,能夠起到便民作用的攤點,在不影響道路交通和環境的情況下,將不再被封殺。
◎《南京市市容管理條例》今年8月1日施行,全市在不影響市容、交通且方便市民生活的前提下,對1萬個路邊攤點有限開禁。每個攤點必須申請辦理合法許可證,申請人必須具有本地戶口、家庭確實困難,申請的攤點必須由本人經營。
相關評論
就地招安可望
解決“走鬼”回流
羅彥軍
城市亂擺賣,即廣州人俗稱的“走鬼”,一直是困擾城市管理的“老大難”問題。各地在實踐中發現,一味的查扣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可能引發更多社會矛盾,因此以“疏”代“堵”逐漸成為“走鬼”管理的主流思路。但是,怎么做才能既保“走鬼”生計又不影響市容,仍是各方探討的焦點。
此前有些地方劃出一定的閒置區域,把“走鬼”請進去,但由於地段不好生意不佳,“走鬼”還是回流到老地方。應該看到,“走鬼”之所以屢禁不止,部分原因是因為有市場需求,自發形成的市場才最有生命力。因此,將於9月1日實施的《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條例》提出了“就地規範,入場入室經營”的新思路,主張對城中村或者城郊結合部一些已經自發形成的“集貿市場”進行“就地規範”。對走鬼而言,搬遷的問題不復存在,生意也照舊,只不過加以規範而已。以此方法疏導,可望解決“走鬼”回流問題。
當然,上述條例目前只是作出方向性和原則性的規定,成效如何還有待試點檢驗。一些具體的實施方案,像如何對流動性極強的“走鬼”進行規範管理,如何在完善管理的同時不加重“走鬼”的負擔等,也尚待有關部門細化。新條例能否解開“走鬼”難題,構築和諧社會,我們拭目以待。
新聞
遍布城市的“走鬼”,一直是城管的“心頭大患”。在如今科技日新月異的年代,“走鬼”和城管之間的“躲貓貓” 遊戲又有了新的玩法:“走鬼”為生計不惜動用“高科技”與城管周鏇。近日,在廣州珠江新城南天大廈便有這么一群“走鬼”,他們腰包藏著對講機, 崗哨分明,城管來時從容退去,讓路人驚嘆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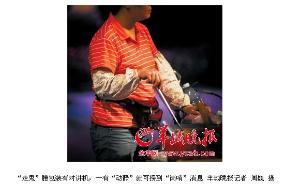 走鬼
走鬼城管一來,“走鬼”狼狽逃走。這是一個已被習以為常的城市片段, 如今位於廣州珠江新城南天大廈的“走鬼”卻打破了這個“傳統”。近日,網友“幸福的米蘭迷”在微博上發帖稱:“為躲避城管, 珠江新城南天大廈附近小販———包括賣煎餅果子的、盜版碟的、煎豆腐和火腿腸的———都配備了對講機,至於觀察哨在何處,不得而知。通知響起時,各位撤退從容不迫,過去的狼狽不復。通話質量貌似很清晰,甚是驚奇,是以記之。”該微博一出迅速被廣大網友轉載評論,紛紛感嘆“人民民眾的智慧是無窮的”,“科技以人為本”,“對講機的市場好大啊”。
網友“doremi-nini”甚至戲謔稱:“這是公民科學素養提高的標誌。”
17 日晚, 記者穿過捷運五羊邨站出口處的天橋,到達南天大廈的西側,看到那群傳說中的“高科技走鬼”。從外觀上看,這些“走鬼”與普通“走鬼”似乎並沒有什麼差別,臭豆腐火腿腸、盜版碟、鮮花……各種商品琳琅滿目,不時夾雜著大聲吆喝。天橋底下更是香氣四溢,橋底不大的面積內擺有六家小攤販。由於來往行人川流不息,生意尚算火爆。
但仔細留意,這些小販“內有乾坤”。
記者觀察到,他們的黑色腰包普遍都是鼓鼓的,裡面竟然能發出聲音。不時能傳出一些清晰的對話聲, 說的既不是粵語,也不是國語。
“裡面裝的是對講機,他們用這個跟附近的崗哨互通信息,防止城管突擊。”有知情市民告訴記者,“他們把對講機別在腰間連腰都不彎就能自由通話么? ”記者十分疑惑。“當然能。” 該知情市民還透露, 觀察哨像烽火台一樣將警報傳達下來,“走鬼” 們聽到後便相應地採取戰略。
不過, 記者在南天大廈周圍仔細排查,並沒有發現疑似 的觀察哨身影。
對於這個問題, 小販們更是諱莫如深。在採訪過程中,不少小販都統一以“自己是新來的”、“不了解情況” 等理由推脫, 似乎對講機一事是個高級“軍事機密”。不過有小販卻表示,小販配備“對講機” 在廣州並不“新鮮”,“這有什麼可稀罕的,廣州很多地方的走鬼都這樣,天河那邊到處都是。”賣雞蛋餅的小販對記者的“大驚小怪”有點不屑。
就在聊天的過程中,賣雞蛋餅女子腰包里傳來了一段清晰的通話聲, 語氣急促,聽完這段話後她平靜地對人群說了一句:“走吧。”這時在場的所有小販不慌不忙地架起東西, 緩緩地向天橋方向離去。
但一個賣光碟的大哥仍留在那裡樂此不疲地向顧客推銷自己的商品。“是不是你們的警報聲啊,這樣說城管快要來了喔。”
記者在旁邊提醒。“我知道啦,我都不急你急個啥。”他顯得有點不耐煩。十幾秒後,他也推起車子, 慢悠悠地走上了天橋,五分鐘之前還熱鬧熙攘的場面瞬間便冷清下來。記者隨後在現場等候了將近五分鐘,並沒有發現類似城管的工作人員前來查看。就這樣,這群“高科技”小販緩緩消失在夜幕中。
關於對講機等“高級機密”,小販並不願多說,但對於種種生活苦況,卻願意大吐苦水。小販們坦言,他們都是外地人,如果不是為生計,也不會冒著被抓的危險來當小販。如果能選擇,有誰願意做這種不體面的“工作”? 有小販建議, 希望政府部門多關注他們這群外來打工仔的生活, 而不是一味驅逐。
羊城晚報: 你們一般是什麼時候出來擺攤?
小販: 我們每天都是下班時間偷偷摸摸地賣一些, 最多五六個小時就回去了。白天不敢出來, 只好在家呆著。我們這些“走鬼”的事情你就不要報導了,我們做點小生意不容易。萬一報導出街被城管看到, 我們在這裡就呆不下去了。
羊城晚報: 你們在這裡擺攤能賺到錢么?
小販: 像我每天最多也就賣個六七十塊錢,除去成本,收入十分有限。
如果運氣不好被城管查到罰款, 相當於白幹了好幾天, 甚至連營生的工具都有可能被沒收。
羊城晚報:你們是廣州本地人么?
小販: 我們基本上都是從外地來的,家鄉沒有賺錢的門路,來到大城市混口飯吃。家裡兩個孩子都是嘴,實在沒辦法,如果能選擇,有誰願意做這種不體面的“工作”?
羊城晚報:前些時候廣州創文對一些地區的小攤販進行了集中整治,你們為什麼不搬進去統一的經營市場裡面呢? 這樣就不用每天都擔驚受怕了。
小販: 你覺得在那些市場裡能賺到錢么?我告訴你,那些地方其實沒什麼客流的。你問問市民,誰會去那裡買小吃。我有一些朋友在市場裡邊做,沒有什麼生意,還要每月擔負租金,受不了,好多人於是又出來賣了。
羊城晚報: 那這樣長期下去也不是辦法吧?
小販: 所以希望政府部門能多關注我們這群外來打工仔的生活, 而不是一味驅逐,應該為我們多想想辦法。
透視金融危機下的經濟學名詞
| 金融風暴影響了世界的各個行業,政府以及民生大眾紛紛“自救”,一些有趣的經濟學相關的名詞開始走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