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華文學是繼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開始出現的,至今已走過70多年的歷程。在這70多年的風風雨雨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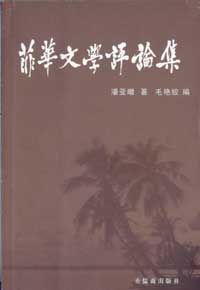 菲華文學
菲華文學出現
據菲律賓考古發現,至遲在晚唐中菲兩國即開始有貿易關係。隨著貿易的發展,華僑也開始出現。至16世紀80年代前後,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在馬尼拉的華僑大約有一萬左右人,以後即逐漸增多,至今華僑華人已達100萬人左右。由於早期華僑是作為僑居海外的中國公民而存在的,為了薪傳中華文化,他們積極創辦華文報刊,發展華文教育。1888年,楊匯溪獨陽辦了第一份華文報紙——《華報》;1899年,中國駐菲首任總領事陳綱創辦了世界上第一所新式華僑學校——小呂宋華僑中西學校。此後,其它華文報刊和華文學校又陸續出現。
發展
於是,華文文學也隨之產生、發展起來。也許可以說,華文文學是在華文報刊和華文教育的基礎上產生的。因為早期前往菲律賓創辦華文報刊和華文教育的人大多是飽學之士,除了培養出一大批文學骨幹以外,自己在編務之餘或課餘也濡墨揮毫,賦詩作文。此外,早期的文學作品也大多是向華文報紙商借版位發表的。
20世紀初期,華文報紙所刊載的國際新聞與本島時事,大多譯自英文,所發表的文章亦均轉載自祖國的報紙雜誌。1923年(或此之前),華文報紙就開始在綜合副刊發表文藝作品,如同年《華僑商報》就發表了俞嘯川的《了緣》、《蝴蝶魂》兩篇小說。在面其時的作品大多是風花雪月的言情小說,缺乏創造性。1928年,林籟余結束了在《小說叢刊》的業務後,應聘主編《中西舊報》和《公理報》。在他的積極提倡和竭力扶持下,文藝作品源源不斷刊發,無論是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甚為讀者喜愛。現代意義的菲華文學即自此肇始。
文藝刊物
1933年,洪光學校校長楊靜桐與王雨亭、盧家沛創辦《洪濤》三日刊(《前驅日報》前身),由深受周作人、俞平伯影響的新詩人許蔓任主編,內容以小品文、雜文、短評為主。經常在該刊發表作品者有林一萍、林健民、蔣江玉與高若嘯等人。但幾個月後,隨著《前驅日報》的創刊,《洪濤》也就停刊了。在此期間,洪文炳創辦《學生文壇》,發表學生文藝作品:王雁影、蔡遠鵬、曾逸雲創辦《唯愛》旬刊,由曾逸雲任主編,只談風月,不論時事。然而,這兩個刊物均僅出版數期壽終正寢。《前驅日報》經過幾年刻苦經營,成績斐然,但也因經濟困難於1936年被迫停刊。
文藝團體
隨著文藝刊物的陸續出現,文藝團體也應運而生,首先揭竿而起的是“黑影文藝社”。該社於1933年成立,成員有林健民、李法西、林西谷、莊奕岩等人。他們積極開展文學創作活動,作品都在上官世璋主編的《華僑商報》的周刊發表。林健民在《黑影文藝》“發刊詞”中寫道:“當你向光明前進的時候,後面曾留下了一條黑影。”表達了他們憧憬光明、追求進步的理想。
與此同時,《新閩日報》也兼辦《民眾周刊》雜誌,由學貫中西的廈門名記者葉渚沂任主編。由於有《新閩日報》和經濟支持,刊物辦得有聲有色,成為當時一個很有特色的綜合性刊物。於是,很多青年作者便轉移陣地,向它投稿。林健民(筆名林孤航)首次翻譯的菲律賓國父黎剎的詩作《我的訣別》(《My Last Farewell》),即發表於《民眾周刊》1934年元旦號上。該詩在40年代經過施穎洲的譯作推介,成為世界名詩。
1934年8—9月間,林健民、李法西、林西谷、高若嘯等人創辦了《天馬》月刊,林健民任主編,李法西負責發行。該刊為純文藝刊物,印刷精緻,每期約32頁碼。主要作者除本地的林健民、李法西、林西谷、高若嘯、莊奕岩等人外,還有國內泉州、廈門等地的作者投稿支持。出版經費主要領先廣告維持,也有一部分私人津貼。每期印800冊,除了一半左右出售以外,部分寄贈國內親友。《天馬》月刊大約維持一年半左右時間,至1936年出版元旦號以後,即因李法西回國升學而宣告停刊。
1935年,盧家沛、蔡遠鵬等人創辦了《海風》綜合文藝荀刊。盧家沛任發行人,蔡遠鵬任經理,林健民、林一萍任主編。主要作者有李法西、溜生(即林騮、林文思)、莊秀環、高若虹等人。可惜僅出版半年左右,也因經濟拮据而停刊。
1936年,藍天民自廈門赴菲,與王文廷一起向《公理報》商借版面出版《前哨青年》,自己又在該報開闢《大眾哲學》專欄。不久,藍天民轉任《華僑商報》“新潮”副刊編輯,並與葉向晨主編《小商報》。藍天民積極提供新文學運動,在“新潮”副刊上發表了不少有一定質量的文學作品。同時,他又聯絡了一批文學青年,組織“新生社”。社員有藍天民、藍明珠、曾文輝、曾月娥、施穎洲、謝德溫等人。[2](p22)這對於推動菲華文學的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在此期間,菲律賓華僑總工會於1928年成立後,不久就創辦《菲島華工》,除報導菲華工運情況以外,每期均有一定版面發表文藝作品。此外,“旗音社”也創辦過一個刊物——《旗幟》,鼓吹愛國工人運動,可惜沒有維持多久即告停刊。
抗日救亡活動
中國1931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三省,海外華僑積極開展抗日救亡。菲律賓華僑也不例外。1936年,馬尼拉成立了“菲律賓華僑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接著,“學生救亡協會”、“青年救亡協會”、“婦女救亡協會”、“工人救亡協會”、“店員救亡協會”等組織相繼成立,菲華社會興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估計此時大部分報刊和作品必定是配合這一愛國運動,表現這一重大主題的。有一事例可以為證。曾任《前驅日報》負責人兼總編輯的王雨亭,因反對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曾作《偉人歌》,把其時的中國政要、聞人逐一吟唱抨擊,遂被國內當局“邀請”回國,以後就沒有聲色了。
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作者,除了上述提到的以外,還有來遠甫、吳研因、錢抱器、王榮宣等人。由於廣大作者勤奮學習,努力提高創作水平,有幾位作者的作品還發表於國內的重要刊物:葉向晨的詩刊發於方治發行的《中國文藝》,鄺榕肇的散文發表於林語堂主辦的《宇官風》,施穎洲的《新詩與譯詩》刊發於巴金主編的《烽火》。
堅定抗戰信念
1937年,中國“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海外華僑聞風而動,同仇敵愾,積極支持祖國人民抗戰。為了動員廣大華僑與祖國人民共赴國難,菲律賓華僑劇團“嚶鳴社”、“前進”“八·一三”和“國防劇社”經常到各地巡迴演出,以提高僑胞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鼓舞鬥志,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
宣傳運動
隨著宣傳運動的轟轟烈烈開展,一大批文藝作者也拿起筆,作刀槍,投入洶湧澎湃的抗日救國洪流。標語、漫畫貼遍大街小巷,各種刊物紛紛出台。“勞聯會”(即“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接辦了《菲島華工》,繼承以前的辦刊風格,為不定期綜合性刊物,每期都刊載詩歌、散文、小說等文藝作品;“店員救亡協會”中路區分會創辦了《群聲壁報》,刊發評論、詩歌、散文等作品;南洋中學學生創辦了《黎明周刊》和《學徒周刊》,宿務華僑創辦了《民族解放》,怡朗出版了《民族鬥爭》。此外,還有《革命先鋒》、《抗戰月刊》、《救國導報》、《中山日報》等等。這些報刊除了報導祖國抗戰訊息,聲討日寇侵華罪行外,還號召廣大僑胞抵制日貨,出錢出力,以實際行動,動搖祖國抗戰。
創辦各種刊物
為了適應鬥爭形勢的發展,“勞聯會”於1940年5月又創辦了《建國報》和《華僑通訊》雜誌。其屬下組織也紛紛創辦各種刊物,如“洋衣工會”創辦《晨鐘》,“救會”(即“店員救亡協會”)創辦《戰時店員》,等等。《戰時店員》每期印刷2000份,分發馬尼拉各店員及呂宋島各會員,該刊曾發表不少詩歌、散文等,有些作品甚為民眾喜愛,有一首悼念一位溺水身亡同志的新詩這樣寫道:
天剛曉/晨風拂著椰梢/一片滄涼的海水/向你呼召//你脫掉了衣裳/投入她的懷抱/萬條浪花把你纏繞/想不到你有為的生命/就在一剎那喪掉//朋友!永別了/從今救亡陣線上/失掉了一位/英勇的步哨/無數熱血的青年/繼續你底壯志/願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含笑!
作者在悼念不幸溺水身亡的同胞時,也沒有忘記把他與抗日救亡運動聯繫起來,其時華僑支援祖國抗戰的熱潮於此可以想見。同時,作者以這種方式來念死難同胞,必將進一步鼓舞廣大僑胞的鬥志。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國主義偷襲珍珠港。接著,就向東南亞國家進攻,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1942年1月2日,日軍占領馬尼拉之後,就對當地人民和華僑實行殘酷鎮壓。於是,華僑的各種救亡組織只好停止活動,於1942年3月成立了地下組織“菲律賓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簡稱“抗反”)。接著,“華僑工人抗日反奸同盟”(簡稱“工抗”)、“華僑店員抗日反奸同盟”(簡稱“店抗”)、“華僑文藝青年抗日反奸同盟”(簡稱“文抗”)等組織相繼成立。“文抗”屬下的文藝社有“野草”、“激流”、“黎明”、“燎原”、“繁星”、“晨曦”、“野火”、“原野”等等[6]。此外,“華僑抗日義勇軍”、“華僑戰時血乾團”、“華僑抗日除奸迫擊團”、“華僑抗日除奸團”、“迫擊閉三九九部隊”、“華僑抗日除奸義勇軍”、“華僑青年戰時特別工作隊”也紛紛揭竿而起。一個地下抗日反奸活動迅速在菲律賓大地如火如荼地展開。
為了動員廣大僑胞積極投入抗日反奸鬥爭,“抗反”於1942年4月創辦了《華僑導報》。不久,“文抗”出版了地下刊物《野草》,由姚國梁、蔡文炯、邦池和景河負責編務,內容除抗日反奸以外,還報導反法西斯戰爭訊息,並刊載小說、詩歌、散文、雜文等文學作品。“婦抗”和“學抗”分別出版了《地下火》和《鐵流》,也發表了不少文藝作品 。與此同時,華僑抗日義勇軍出版了《大漢魂》,血乾團出版《導火線》和《血乾團戰地通訊》,特別工作隊出版了《前鋒》,三九九部隊出版《迫擊》,鋤奸迫擊團出版了《掃蕩報》,等等。這些地下小報除了報導戰時情況以外,也都發表一些文藝作品,尤其是詩。雖然它們大多是手寫油印,字寫得密密麻麻,印刷也相當粗糙,但在當時惡劣的條件下卻是很不容易的。此外,還有吳金燧、林克、楊波、張羅網等一批愛好文學青年組織的“五月文藝社”,也積極開展文藝創作活動。
這些地下報刊的印刷出版,是配合當時華僑地下抗日反奸鬥爭需要的。《大漢魂發刊導言》云:“這就是大漢民族的國魂,這國魂是我們祖先五千年民族精神教育所造成的,明順逆,別忠奸,重氣節的抗敵救國的國魂。我祖先以此大漢魂特質,遺留在我們後世子孫的骨血中,散布於四肢百體。故不論於國內國外,莫不千人一意,萬里同心,始有此偉大壯烈的表現。”其激勵廣大僑胞抗日救國的豪情壯志洋溢於字裡行間。因此,大部分文藝作品都圍繞著這一主題來展開。例如,《迫擊》創刊號上發表了一首題為《快舉》的詩這樣寫道:“
死,不要馬虎死,/為著自由與解放,/為著被壓迫不願做奴隸,/不得不戰!/弟兄們,起來!/只有戰才可解脫桎梏的束縛。//快舉起拳頭,/振作精神,/對敵一戰,/才有真正的出路!/弟兄們,起來吧!/我們有熱的血,/我們有堅強的意志,/我們還有滿腔的勇氣!/莫管敵人炮火怎樣烈,/兵員怎樣多,/惟憑著我們的“熱血”“勇氣”,/弟兄們!起來吧!/快起來戰!/戰!戰!戰!
這首詩淺白如話,朗讀之下,令人熱血沸騰,鬥志倍增,猶如一支戰鬥的號角,激勵軍民奮勇殺敵。又如,《血乾團戰地通訊》上曾發表莊復初的古體詩《北呂從軍行(自序)》,詳細地記述了一次戰鬥歷程。詩曰:
宗鹹莊澤蘭為血乾團第五大隊隊員,參加該團赴北呂,與盟軍配合作戰。此次由前線歸來,詳述戰地狀況,為作此歌。
盟軍乘勝追窮敵,華胄健兒開呂北。青年擲筆赴戎機,冒雨荷槍越阡陌。插天籠霧巒山青,攀藤附葛披荊棘。衝鋒陷陣唱凱歌,叱吒風雲盡變色。電閃旌旗瞽鼓喧,掃穴犁庭渠醜殛。絕獻層巒撻伐張,嶺上屍骸已滿白。搜尋除孽見寇窩,洞裡物資如阜積。土著工兵蜂擁前,爭運回家作糧食。村莊父老具壺漿,犭乞鳥蠻花悉怡悅。夜來全部扎峰嶺,刁斗無聲森壘壁。長林茂草攢人頭,潛伏倭奴突鳴鏑。勇士爭先不顧身,馬革裹屍欽八烈。人生何處不青山,民族英雄留氣節。嘉名宏錫血乾山,國徽飄蕩符名實。奏凱歸來列隊行,夾道欣呼手加額。
此詩雖然是用古風體寫就,但層次清楚,敘述詳細,使我們仿佛看到血乾團官兵配合盟軍英勇作戰、八位烈士壯烈捐軀的場面,以及勝利歸來受到民眾熱烈歡迎的景象。菲律賓華僑戰時藍徽社編的《霹壢》上也曾發表過一首《紀念“八·一三”短歌行》,雖然略遜一籌,但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菲島淪陷期間
在菲島淪陷期間,有幾本重要著作值得介紹。首先,李成之的《碧瑤集中營》。作者在書中真實地記載了自己被囚禁於集中營的慘絕人寰的遭遇,強烈地控訴了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罪行,歌頌了菲華僑胞與當地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正義鬥爭,確實是菲華文學史上值得一提的佳作。其次,吳重生的《出死入生》。吳重生(原名“吳半生”)是《新閩日報》社社長。他在書中記述了自己與家人、友人如何避難山中、幾次死裡逃生的驚險經歷。作者是基督教徒,書中有濃烈的宗教成份。可是,其離奇曲折的經歷,確是值得我們了解的。該書原用英文寫作,在美國出版。後來,又出版了華文譯本、挪威文譯本、菲律賓文譯本、瑞典文譯本。20世紀80年代中,還在中國大陸出版社印刷兩版,共七萬冊。因此,它在菲華文學史上也將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再次,潘葵屯阝的《達忍三年》。潘葵屯阝是華僑曙光學校校長,傳統詩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積極參與抗敵工作。菲島淪陷後,他避居內湖省達忍島三年之久,度過了一段艱難困苦、漫長黑暗的歲月,《達忍三年》收有《達忍島逃亡生活回憶錄》、《達忍島逃亡紀事詩》36首及附錄傳統詩19首,律詩論文3篇。這些作品忠實地記載了作者在三年逃亡期間,幾為日寇迫害、歷盡艱危、瀕臨死亡的經歷,表現了作者不屈不撓、堅韌不拔的浩然正氣。誠如有識之士對其逃亡紀事詩的評價所云:“正氣磅礴,而觀從容、情趣活躍,真傳世之作也。”茲錄其詩兩首如下:
療飢薯葉連三月,充飢柳渣歷一秋。
猶記在陳夫子厄,弦歌如故獨忘憂。
何堪出晝留三宿,且莫登樓賦七哀。
我似杜陵聞捷喜,狂歌縱酒買船回。
在此期間,還有不少其他傳統詩人的作品也是值得注意的。他們 都或多或少地從不同層次、不同角度表現了積極支援祖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豪情壯志,以及菲島淪陷在日寇鐵蹄下的各種感受。茲舉二例如下:
(二)施子榮:《夜懷二弟純亮》
萬里河山血戰酣,三年猶未罷征驂。
逞身衛國心何壯,矢志從軍苦亦甘。
瀰漫烽煙迷塞北,瘡痍滿目遍江南。
男兒欲把乾坤轉,倭寇強瞄一例戡。
(一)鄭衍蕃:《元旦書懷》
烽煙密密罩菲濱,虎口唯余歷劫身。
萬里家園音訊杳,三年海嶠夢魂親。
戰雲藏月山河碎,鼙鼓驚春歲序新。
白髮萱堂應健在,天涯救子倚樓頻。
據筆者所經眼,除上述兩人外,有涉及這一類題材的傳統詩人還有李根香、陳仲瑾、李淡、李古愚、楊虛白、蘇二庵等人。依筆者寡見,這一時期的傳統詩詞似乎比新文學作品來得成熟。這大概是因為這些傳統詩人大多是其時國內當地較有名望之士,有較深的國學功底,有的甚至是大學畢業後才應邀往菲,或辦報,或辦學,或在社團任職。他們寫傳統詩詞本就得心應手,加上有切身的體會,故其作品能取得較大的成功。而新文學作品的作者大多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初涉文壇,故作品略顯稚嫩。因此,筆者以為,我們不應該把傳統詩詞遺忘在菲華文學之外。
重新崛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丘宣布無條件投降。全世界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中國人民也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菲華僑胞一片歡騰!
早在半年前的2月3日,馬尼拉就得以光復。面對一片飽受戰爭創傷的土地,菲華僑胞和當地人民一起,憑著勤勞勇敢和聰明才智,另起爐灶,重建家園,使之逐漸恢復了原來的面貌。菲華文藝也隨之重新崛起。
華僑青年文藝工作者協會地下鬥爭時期的青年音樂、戲劇、文藝各團體聯合組織了“華僑青年文藝工作者協會”,聘請杜埃(曹家)、葉向晨、蒲劍(林林)為顧問,林谷峰為主席,成員有林桌華、蔡文炯、黃衍芳、顏影、蔡流揚、丘榮章等人,積極開展文學藝術活動。《婦女吼聲》、《抗反快報》等報刊紛紛出版,號召僑胞繼續抗日鋤奸,開展救濟活動。
各組織的機關報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下鬥爭時期的油印小報大多成為各組織的機關報,如《華僑導報》、《前鋒報》等一些報紙連同戰前各報都辟有“副刊”園地,發表文學作品,即《華僑導報》“筆部隊”、《前鋒報》“北望”、《華僑商報》“新潮”、《新閩日報》“新副”、《公理報》“晨光”、《中正日報》“文藝工場”、《大華日報》“長城”、《重慶日報》“丹心”、《僑商公報》“星火”等,林林總總,異彩紛呈。菲華文學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華僑導報》副刊“筆部隊”由林林主編,主要發表新詩、散文、小品等。林林經常以楊墨、蒲劍等筆名發表詩文。記述“華支”(即“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戰鬥生活的長篇報導也曾在該刊連載。經常在“筆部隊”發表作品的作者有杜埃、林卓華、李清泳、王鶴籌、王尚政、張道揚、雷波林等人。據介紹,經常在《華僑導報》“筆部隊”和《僑商公報》“星火”上發表文章的作者中,“寫作成績最為顯著的是王思籌同志。他從國內外時事及當地僑社思想政治鬥爭中廣泛獵取題材,以老五、少思、鶴籌、迪人生、茉、燈蛾、尤奮、王兄、劉忤……等10多個筆名發表近百篇立場鮮明、富有戰鬥性的各種文藝作品,對於當時進步報紙文藝園地的繁榮起了一定的輔助作用。”抄錄他1946年5月11日所寫的《這支筆是人民的》一詩以見一斑:
“這支筆,是人民的,/我樂然獻給人民。/我要蘸著人民的血汗和淚水,/寫出人民的建造世界,/艱巨、犧牲、不畏縮;/還有飢餓、困苦、被踐踏的屠殺,/還有人民的慰藉與歡樂。/筆,/我樂然獻給人民,/這支筆是人民的。”
群音樂社
1944年7月30日,詹在看、丁金注、蔡長良、李金波等一群華僑青年在馬尼拉組織了“群音樂社”,配合抗日工作,開展宣傳演唱。在日寇敗退前的最猖獗階段,不得不停止活動。馬尼拉光復後,群聲樂社恢復活動,易名為“群音研究社”。除了仍設有“音樂組”外,增設了“文藝組”、“體育組”與“兒童組”。“文藝組”有李亞度、李賢達,楊煒華、蔡長良、施性等、黃明德、黃瑞楷等人。他們積極撰寫文藝作品,然後在《華僑商報》“新潮”或《中正日報》“文藝工場”發表。據現有資料,在1946年,李賢達《筆名“亞達子”)發表的散文、小說有《重會》、《復仇》、《懺悔》、《新生的路》、《人與人之間》等,楊煒華(筆名“韋樺”)有散文《南飛》、《活力》、《黃金的鞭子》等。
文學著作
1947年7月,杜若主編了菲華青年的第一本文學著作《鉤夢集》 ,作為《大華日報》“長城”副刊叢書之一出版。書中收入杜若、芥子、亞薇等18位青年作者的新詩、散文、小說、隨筆、戲劇等作品,共144篇。作品主要反映日寇統治菲律賓時期,菲華僑胞與當地人民進行黃勇抗戰的事跡,具有一定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正如杜若在該書《跋》中所寫,其之所以出版這本書,是為了“聊以紀念幾個為抗戰而犧牲的同志,也算是造個塔兒來收埋這些無歸宿的夢魂。”後來,施穎洲主編出版了《一九四六年文藝年選》。
晨光之友”社
1949年,《公理報》“晨光”副刊主編何祖燈斤聯絡一些青年作者組織了“晨光之友”社,社員120人,大多是華僑學校學生。“晨光”副刊所發表的作品以新詩為多。同年,李維宣(筆名“白雁子”)的18首、434行的長詩《高山晉壽》在“晨光”發表以後,曾引起一場長達一個多月論戰。對《高山晉壽》提出批評的蔡景福(筆名“亞薇”)在《詩的題材與技巧》一文中,提出了文學作品應該具有四個要素:(一)情感;(二)想像;(三)思想;(四)形式。[2](p40)雖然這種提法未盡科學,但至少表明菲華文藝界人士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從理論上來探討文學創作了,這相對於其時尚屬起步階段的菲華文壇無疑是一個突破。尤其是對於初學寫作的文學青年更是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促使他們有意識地向較高的層次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