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茗戰 | |||||
| 拼音: | |||||
| 解釋: | 1.猶鬥茶。品茶。 | ||||
 茗戰
茗戰茗戰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鬥茶,它是我國古代以競賽方式, 評定茶葉質量優劣、沏茶技藝高下的一種方法,可謂是中國古代品茶的最高表現形式。用今人的話來說,就是古人用戰鬥的姿態,進行品茶比賽,與當今的名茶評比大致相當。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鬥茶乃是人們運用審美觀對茶葉進行鑒評和欣賞,是中華民族高潔清雅風尚的一種體現,是人們精神生活的一種追求。
簡介
 茗戰
茗戰歷史起源
 茗戰
茗戰在我國飲茶史上,鬥茶最早大約出現於唐代中期。據無名氏《梅妃傅》載:"開元年間,(唐)玄宗與妃鬥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鬥茶今又勝我點。這是鬥茶的最早記錄。不過,在歷史上最講究、最熱衷於鬥茶的則要算宋代了。由於宋代品茶之風大盛,於是使唐代開始的鬥茶之風在宋代達到高峰。連宋徽宗趙佶也樂此不疲,他曾寫就《大觀茶論》一冊,其中談到:"天下志士,勵志清白, 競為聞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筐筐之精,爭鑒裁之別,雖下乾於此時,不以蓄茶為羞。"還盛讚此舉謂"盛世之清尚也"。北宋文學家范仲淹更是將鬥茶寫得惟妙惟肖,在他的《和章岷從事鬥茶歌》中寫道:"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為了向"天子"獻上最好的北苑龍鳳團茶,就要在上貢前,雄豪們就要先舉行鬥茶。而鬥茶時,"其間品弟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結果是"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
“鬥茶味兮輕醍醐,鬥茶香兮薄芝蘭,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在我國豐富悠久的茶史中,“鬥茶”是茶文化的一種,是我國茶文化藝術長河中的一朵奇葩,這個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對今日世界的茶文化發展產生著重要影響與貢獻。您一定不會想到,昔日民間的“鬥茶”風俗,就是今日的茶道之母。南宋開慶年間,這種鬥茶遊戲漂洋過海,傳入日本,才逐漸發展成為今日的“茶道”。可見中國的茶葉及茶文化能走出茶鄉,走向世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鬥茶”可謂功不可沒。
後續發展
對如何鬥茶,宋代唐庚的《鬥茶記》寫得較為詳細: 二三人聚集在一起,獻出各自所藏的珍茗,烹水沏茶,互斗次第。書中還談到,鬥茶茶品,"以新為貴";鬥茶用水,"以活為貴"。據北宋江休復的《江鄰兒雜誌》記載:"蘇才翁嘗與蔡君謨(即蔡襄)鬥茶, 蔡茶水用惠山泉,蘇茶小劣,改用竹瀝水煎,遂取勝"。可見茶水關係至深,所以新茶配活水,可謂相得益彰,這是符合現代科學道理的。據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記述,宋時鬥茶,味以"香甘重滑"為上,香以"真香"為佳,色以"純白"為優。到了南宋,不僅名茶產地及寺院有鬥茶之舉,就連民間也普遍開展。南宋畫家劉柏年的《鬥茶圖卷》 更生動地展現了集市買賣茶葉民間鬥茶的群象。這種鬥茶,很有些現時評茶的味道,並與茶葉市場交易聯繫在一起。
元代,鬥茶之風雖不像宋代盛行,但仍流行於世,這可以從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1254-1322年)所作的《鬥茶圖》中找到蹤影。
明代以後,人們崇尚的是品茶的雅趣,因此,鬥茶之風漸弱。
在今人看來,儘管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對古人鬥茶進行評說,但鬥茶開當今茶道、茶藝之先河,今人的品茶、評茶、鑒茶,它的技術很大程度上是由鬥茶演變而來的。歷史上許多名茶、貢茶的產生,也與鬥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所以,鬥茶對中國茶文化的發展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對此,茶學界和史學家都是認可的。
茗戰方法
 茗戰
茗戰接下來把研碎的末茶放在杯盞中,兌入少量沸水,調成膏狀,稱為“調膏”。然後是點茶的過程,拿水瓶的手臂要靈活轉動,讓瓶中的水形成穩定的水柱,水柱不能使斷時續,忽粗忽細;水注滿杯盞六分左右的時候,水柱嘎然而止,不能殘留零星水滴。點茶的同時用茶筅不斷的鏇轉攪拌,以手腕帶動手指,輕重適度,緩急有度,讓茶湯泛起純白的湯花。宋徽宗的《大觀茶論》把調膏,點茶的過程總結為七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手法。
怎樣確定鬥茶的輸贏結果呢?首先是目測湯色和湯花的優劣。餅茶在製作過程中榨去了茶汁,因此烹茶完成以後湯色應該發白,純白表明茶葉鮮嫩,製作精細,是最上之選。湯色發青說明“蒸青”的火候不夠,泛灰表明蒸青火候過猛,泛黃說明採摘的是老葉,發紅則表示烘焙過度,這些都是劣等茶的標誌。湯花的品鑑更考究。湯花泛起時要均勻細密,觀之如疏星朗月,甚至幻化出鳥獸蟲魚的形狀,而且貴在經久不散,湯花要緊咬盞沿,不能很快消失。如果湯花散去,就會在杯壁留下水痕,當時就是以水痕出現的早晚來裁定輸贏,水痕出現得越晚,就越容易在比賽中取得勝利。正因為宋人重視湯色的純白和咬盞的持久,茶具就成了決定鬥茶勝負的關鍵因素。當時鬥茶者最喜愛建窯的黑釉兔毫盞,這種杯盞色澤油黑反襯出茶湯的潔白,內壁有兔毫般的花紋與湯花相映成趣,因此大受歡迎。也是出於鬥茶的需要,宋人把茶葉為白色的稀有茶樹當作無上的珍品。
隨著散茶全面替代團餅,宋人的斗茶之趣也煙消雲散。此後,再未出現以一種廣泛的社會參與為特徵的“茶道活動”。
 茗戰
茗戰決定鬥茶勝負的標準,主要有兩方面。
一是湯色。即茶水的顏色。一般標準是以純白為上,青白、灰白、黃白,則等而下之。色純白,表明茶質鮮嫩,蒸時火候恰到好處,色發青,表明蒸時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時火候太老;色泛黃,則採摘不及時;色泛紅,是炒焙火候過了頭。
二是湯花。即指湯麵泛起的泡沫。決定湯花的優劣要看兩條標準:第一是湯花的色澤。因湯花的色澤與湯色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湯花的色澤標準與湯色的標準是一樣的;第二是湯花泛起後,水痕出現的早晚,早者為負,晚者為勝。如果茶末研碾細膩,點湯、擊拂恰到好處,湯花勻細,有若“冷粥面”,就可以緊咬盞沿,久聚不散。這種最佳效果,名曰“咬盞”。反之,湯花泛起,不能咬盞,會很快散開。湯花一散,湯與盞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線)。因此,水痕出現的早晚,就成為決定湯花優劣的依據。
興盛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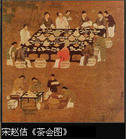 茗戰
茗戰五代時,福建建安就有“鬥茶”活動,入宋,建安成了當時最負盛名的茶區,北苑又是太宗圈定的貢茶區,為決出進貢品種,遂使鬥茶在建安興隆起來,每年新茶上市,各茶區的茶家攜帶珍品,身懷絕招,前來比試。當地職官在福建轉運使的率領下,充當評判,作出裁決。
范仲淹有《和章岷從事鬥茶歌》以紀此事: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
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
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
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
終朝采掇未盈,唯求精粹不敢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圓中蟾。
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
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
鬥茶味兮輕醍醐,斗余香兮薄蘭芷。
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
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
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
眾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卻得聞雷霆。
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
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
長安酒價減百萬,成都藥市無光輝。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
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鬥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這是一首膾炙人口的茶詩,古人把它和盧仝的《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相比美。但是,宋蔡正孫認為盧仝詩優於范仲淹詩。他在《詩林廣記》中說:“胡苕溪云:‘《藝苑》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之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邪!”
蔡正孫貶范揚盧有失公允。
應該指出,盧仝的《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以浪漫主義手法抒發了對茶飲的身體感受與心靈感受,符合當時玄說茶道的風尚;同時,又對茶農寄予同情,是一首極言茶功、超脫飄逸的好詩。
蔡正孫說它優於范詩,主要著眼於自出胸臆和得詩人句法這兩點。
希文詩何嘗不自出胸臆呢?
其一,每年主持和參與建安鬥茶的主角是朝廷命官,鬥茶的勝負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升遷榮華,希文詩由鬥茶揭示世態:“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鬥草,贏得珠璣滿斗歸”,刻劃了這些人物的神態與心理。
其二,希文詩拓展茶飲感受至做人的氣節:“眾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同時,不無譏諷地指出醉心茶功的社會時弊:“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君臣神會茶域,國計民生休要過問了!
從兩詩對社會生活的關注和對茶功感受的延伸來看,希文借詠鬥茶暗示對國事的憂慮,展現了一個政治改革家的胸懷,這是盧仝詩比不上的。
再說,希文詩何嘗不得詩人句法呢?
玉川詩直抒胸臆,固然是好;採用排比句式,引用典故,是表意的一大進步,與直抒胸臆無優劣之分。在頹風日熾、涉及聖上的情況下,希文也只能委婉表達心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