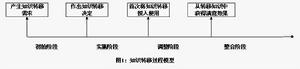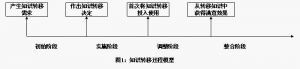 知識轉移過程模型
知識轉移過程模型戰略聯盟反思
解讀該模型分兩部分進行。其前半部分表明,做出知識轉移決定不是偶然的,而是需求動機導致的行為結果。知識轉移不同於知識擴散(Knowledge Diffusion),它不是隨機的而是有目的、有計畫的知識共享。任何戰略聯盟的形成不是盲目的,而以雙方有明確的知識轉移需求為前提,目標模糊的戰略聯盟知識轉移的有效性也較差,聯盟成功率會受到影響。模型後半部分表明,知識轉移是雙方共同努力的過程。知識不斷地從源單元經過調整、適應,最終成為接受單元的一項制度,是聯盟各方在該項知識上的“勢差”不斷降低的過程。“勢差”降低到零時,戰略聯盟中的知識轉移以成功而結束。
當前加盟企業對該模型的前半部分把握良好,過半數加盟企業都有明確的知識轉移意圖,52.38%的加盟企業希望獲得先進技術信息,61.90%的加盟企業希望獲得互補性技術開發資源等。但更多的企業在戰略聯盟中對模型後半部分認識不足,並從以下兩方面影響聯盟成功率:
一是知識源單元對知識轉移的主動性不足。由於聯盟成員的知識結構在客觀上存在差異性與分布的非均衡性,知識源單元對知識擁有信息不對稱的壟斷性,因此聯盟中不論是加盟企業還是企業中的個人,都有充分的動機隱瞞個人知識。同企業內部知識轉移不同,戰略聯盟中的知識轉移缺乏行政命令和科層制管理手段來提高知識源單元的傳遞意願,甚至出於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原因而弱化這種意願。調查表明,8%的企業技術聯盟以“保護核心技術”為主導性管理模式,這顯然不利於知識轉移;同時,43%的企業認為聯盟中技術共享不充分。可見,提高戰略聯盟成功率對知識源單元提出的挑戰是,如何在有限框架內提高知識轉移的主動性。
二是知識接受單元自身知識消化能力和吸收能力欠缺。模型表明,知識接受方並非被動等待知識來臨,而需要發揮自身能力將知識內化。戰略聯盟是否成功應該以企業能夠將對方的知識演化為本企業的日常制度為衡量標準,即Szulanski所說的“在新環境下,重建和維護一套程式和規則”。但當前部分企業對戰略聯盟定位不準確,40%的企業在戰略聯盟中有機會主義行為,甚至存在又一種“等、靠、要”心理,希望僅僅通過聯盟獲得突破性發展,這在政府主導型聯盟中表現尤為突出。
對戰略聯盟的啟示
Senge將知識共享定義為協助他人發展有效行動能力的行為活動。戰略聯盟中知識轉移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包括知識源單元在內的各方共同參與制定符合雙方特點的知識轉移方案。但是,聯盟畢竟是競爭性的合作。尼考拉斯・萊斯切爾(1999)指出,合作不是出於道德奉獻,不是出於對別人的幸福和福利的關心,而是出於對自我利益的慎重考慮。因此,單從口頭上要求知識源單位提高知識轉移意願、助推知識轉移是很蒼白無力的,而需要切實的聯盟效益來引導。
建立聯盟雙方信任機制是提高知識源單元知識轉移意願的重要中介變數。當前42%的企業反映“成員相互信任不夠”成為阻礙聯盟順利發展的關鍵問題,40%的企業在聯盟中有機會主義行為。由此可見,信任缺失是導致聯盟高失敗率的重要原因。信任作為一種微妙的心理感知也需要管理手段介入。
首先,培養信任機制需要讓企業成為選擇聯盟夥伴的主體。當前的政府主導型聯盟中有很多企業並沒有真正成為聯盟決策主體,包括聯盟夥伴的選擇往往也是出於非市場因素。而企業只有在自主制定聯盟方案時,才能不斷增進雙方了解和認識,充分認識雙方互惠互利的機會,也有利於培養相互信任機制。在聯盟運行中,知識源單位出於對自己選擇負責,出於對對方稀缺性資源的嚮往,而自發地產生將自身知識資源轉移到對方企業的意願。調查中部分企業表示,當雙方信息存在嚴重不對稱時,在知識轉移中他們很難做到針對接受方特點對知識進行處理,以增加知識轉移助動力。因此,讓企業成為聯盟真正主體有利於規避今後聯盟運行中的眾多不合作行為,有利於消除知識勢差。
其次,培養信任機制對聯盟雙方的領導者提出要求。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加盟企業的雙方主管之間的信任在培養聯盟成員之間的信任中扮演重要角色。主管信任除了可以像同事信任一樣能產生資源交換意願以外,雙方企業的成員出於對各自主管的信任會移情到對對方企業的成員表現出可信行為,而產生間接資源交換意願。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很多學者還借用了更多的知識轉移模型對戰略聯盟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如日本的Nonaka等人提出的SECI模型就曾被多次運用。SECI模型對戰略聯盟的啟示集中在它強調了隱性知識的重要性以及成功的隱性知識轉移對整個戰略聯盟成功的影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