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皋蘭鼓子
皋蘭鼓子據考證,最早提出蘭州鼓子始創於北宋的是20世紀初甘肅學者慕少堂。他在《甘寧青史略》副卷五所收“皋蘭鼓子詞”條目楣首批註:“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疇者,始創商調鼓子詞”。其後是張維鴻先生,他在《蘭州古今注》一書中寫道:“鼓子以鼓為名也,蘭州鼓子俗訛為鼓子,其曲牌爾雅而多繁聲,以一人獨唱,猶有南曲餘響”。但這兩位學者均談的是“鼓子詞”,並未明確道出:“鼓子詞”就是蘭州鼓詞或者蘭州鼓子,提法也就較為含混,而真正提出這一定論的是李海舟先生。他認為:“蘭州民間流行的鼓子,原名叫鼓子詞,簡稱鼓子,又叫小曲,系宋末安定郡王趙令疇所創,即蘇軾稱趙德麟者,始創商調鼓子詞,譜西廂之事。”解放後,他又撰文說:“蘭州鼓子可能始創於宋,曾繁於元、明之際。”從而將這一論點具體化、明確化,但他沒有列出幾條依據,也沒有作進一步深入的闡述,實不能說服讀者。對蘭州鼓子進行系統研究,並以翔實的實事依據做出定論的是王正強先生,他在《蘭州鼓子研究》一書中,對始創於宋、元之說提出了異議,認為“儘管蘭州鼓子中有一些元曲曲牌存在,但卻不能以此籠統地說它產生於元代,或者說元曲就是蘭州鼓子的直系祖先。這就像樹木的年齡不等於木具製造的時間,磚瓦的出窯不等於樓房竣工的日期一個道理。”在談到曲牌曲本淵源時,他說:“對於它所擁有的48個曲牌,甚至包括各個曲牌的多種變體唱調,我們不僅能夠從八角鼓、眉戶等同類地方曲藝中逐一考出它各自的來龍去脈,而唯獨不能找出一首當地的民歌曲調來”。為此,他提出了“蘭州鼓子的產生,應當在北京八角鼓、陝西眉戶的成型之後,而且應該說由外地傳來,並非由當地某人始創”的論點。在談到蘭州鼓子的成型時,他說:“由北京八角鼓繁衍而生的蘭州鼓子,大約在清道光前後,即1830年左右,便開始在當地娛樂場所慢慢傳唱了”。
鼓子的曲牌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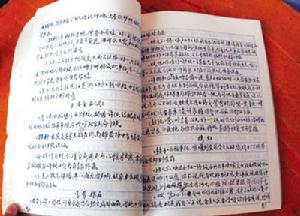 皋蘭鼓子
皋蘭鼓子蘭州鼓子曲牌,按其組織程式與連線格式,分為鼓子和越調兩大腔系,它們總共包括48個曲牌,其中多數曲牌又因其用場、詞格、曲調上的某些細微變化,又派生出少則兩個,多則五個不等的變體唱調,以此構成極為豐富繁雜的表現情緒的專長。如“邊關”、“皂羅”的悲傷憂悒,“一點油”、“太平年”、“倒秧歌”、“緊訴”的喜悅歡快。還有敘述情節的“詩牌子”,多樣用場的“石榴花”、“刮地風”、“疊斷橋”等,足供人們在相當寬裕的幅度內酌情使用。曲牌清雅悠揚,飄渺自如,幽靜化神,適用於表達喜、怒、哀、樂等各種思想情緒。
演唱形式
 牛萬炳唱起了悠揚的鼓子
牛萬炳唱起了悠揚的鼓子鼓子在演唱中以三弦為主,揚琴、板胡、二胡、古箏、琵琶、簫、笛、梆子、碰鈴、八角鼓、瓷碟子等為輔。三弦採用的是越調定弦法,即151。除越弦而外,還有三種定弦法:一種是平弦定弦法,即563,它為“進蘭房”、“四大景”、“繡荷包”等平調專用弦;第二種是海弦定弦法,即152,此弦也叫“三不齊”,僅用於伴奏《蒼龍哭海》,故稱海弦;第三種是官弦定弦法,即514,僅伴《哭五更》調。此三種定弦法比較古老,加之目前會唱平調、海調者寥寥無幾,故已近失傳。一般定調依演員聲嗓音域來確定高低。一般常用的調有D調(俗稱口調)、bE調(俗稱一調),個別演員還可定F調或C調、C調(俗稱凡字調),藝人們還把帶升降號的定調,音高用軟硬來表示,如bE調稱硬口調等。
皋蘭鼓子的形成、發展和分布
清同治、光緒時期,堪稱蘭州鼓子的全盛階段。不僅金城的茶館酒肆演唱蔚然成風,附近農村也常作為婚壽筵慶的助興之曲,尤其非職業藝人的走鄉串戶、爭相競技,使它的流傳範圍擴大到蘭州以外的郊區縣城,作為甘肅省會首縣的皋蘭縣便理所當然地成了蘭州鼓子形成發展傳播的地區之一。水阜鄉水阜村王三級(1858年—1899年),光緒年間在蘭州隍廟說書期間認識了鼓子藝人朱爺(其名不詳),並拜朱爺為師學唱鼓子和三弦,同時邀請朱爺到水阜傳藝帶徒,帶出的徒弟有王熙元、王科元、劉延秀等十多人。什川鄉南莊村魏孔吉(1904年一1987年),因隴原人劉爾炘的繼母是什川人,他跟劉爾圻接觸的機會較多。民國23年(1934年)冬季,劉爾圻在五泉山舉辦重修五泉山廟會,由他介紹什川魏至平、魏建經等在五泉山聽鼓子,此後潛心學習鼓子藝術,經常出入於茶館酒樓,主攻三弦,能彈平弦、海弦、越弦,懂得牌調甚多,在金城頗有影響。水阜鄉老鸛村魏學堯(1898年一1963年)曾拜蘭州暢家港尕兔爺(其名不祥)為師,學唱鼓子,成為鼓子名流,1956年受到鄧寶珊省長的接見。水阜鄉砂崗村牛得千(1947年一1989年),一生酷愛鼓子藝術,能彈會唱,曾投師於蘭州名藝人羅萬一,在白塔山、隍廟、雙城門等地的茶館演唱,評價頗高。彭維弟(1922年一1961年),忠和鎮豐登村人。早年在蘭州唱鼓子時受到一些人的譏諷,為此,他立志要把鼓子學好,特意拜蘭州安寧崔家莊其舅崔小林為師,一邊學唱鼓子,一邊學習銀器製作技術,雙業俱精。1955年,他再次到白塔山演唱時,得到了鼓子名家的一致好評。黑石川鄉馬家灣楊連元(解放前去世),本人不但能彈會唱,在世時常以此邀朋會友,經常往返於水阜、水源、什川、鹽場堡、白塔山等地連日演唱,帶出徒弟二十餘人。以上六人是將鼓子引入皋蘭縣的主要人物。
蘭州鼓子傳人皋蘭已有一百三十年之久。皋蘭能彈會唱者很多,今四鄉四鎮均有分布,尤以水阜、什川、忠和、石洞、黑石等地最為盛行。特別是老人惜愛之至,視其為民間文化的瑰寶,對其興趣不亞於早登大雅的眉戶、秦腔。鼓子藝人走鄉串戶,使它的流傳範圍十分廣泛,加之各鄉業余自樂班紛紛興起,鼓子好家的大量湧現,使它成為名噪一時,男女皆習之,人人喜聽之的俚巷之曲。
 皋蘭鼓子
皋蘭鼓子20世紀初,鼓子已在皋蘭初具規模,成為各種節會的主要活動之一。1922年,水阜村召開的物資交流大會,歷時十五天。期間,除蘭州老十二紅(李奪山)的得勝社演出秦腔外,還專門邀請蘭州鼓子名家鍾爺、張百生、竇傑三等和本地好家一起演唱,交流技藝,各地聞風而來的好家四五十人,可謂盛況空前。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鼓子發展的鼎盛時期,期間文化生活相對貧乏,唱鼓子便成了皋蘭民間藝人的唯一選擇,農閒、節慶、紅白大事、雨雪天,便成了好家們邀朋會友、交流技藝的最好時機。好家們你拿一塊煤,他提一瓶油(點燈用煤油),晚上不約而同來到演唱地點,一唱就是一個通宵,連唱四五個晚上的情況很普遍。不僅中老年人參與演唱,許多婦女、青年也愛上了鼓子。較大的村一個演唱地點根本滿足不了好家們的需求,像水阜、什川、莊子坪等地,同時有幾個地點在演唱,部分居住較分散的好家則要跑幾里,甚至更遠的地方去演唱,村與村之間,鄉與城裡的交流十分頻繁。據估計,當時全縣演唱人員不下千人。“文化大革命”期間,鼓子被當做“四舊”、“精神垃圾”,受到批判和禁唱,演唱地點打成了“黑俱樂部”,許多組織者被扣上了“黑俱樂部頭頭”的帽子,致使很多珍貴的資料被燒毀,樂器上交,從此鼓子處於停頓狀態。鼓子再度興起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期間演唱人員雖沒有以前那樣多,但都是些實實在在的好家,鼓子演唱較集中的水阜、什川兩鄉鎮,不但演唱人數穩中有升,在器樂更新方面,或集資或個人購買,增加了如三弦、揚琴、古箏、二胡等常用樂器。近年來,創作隊伍創作的《皋蘭頌》《引水帶頭人》《抗洪英雄高建成》《千里隴原跨駿馬》等,在重大節會的演唱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縣、鄉文化部門的大力支持和輔導,愛好者的廣泛參與和交流,不少有文化、有志趣的年青人的加盟,近年來重大節會的頻繁演出,使得皋蘭鼓子從器樂配置、演唱水平、人員結構方面都有了質的飛躍,大大地提高了皋蘭鼓子的知名度,使皋蘭鼓子走向省城,走向全國,飛到了異國他鄉。
一個多世紀以來,經過廣大愛好者的共同努力,皋蘭鼓子引起了文化部和省上有關部門的重視。1987年文化部文化司黃河文化考察團一行8人在什川了解蘭州鼓子的有關情況。2002年11月,省藝研所專家專程赴皋蘭了解蘭州鼓子在當地的情況,準備將其收入《中國曲藝志·甘肅卷》。皋蘭水阜、什川、忠和、黑石4個鄉鎮,現共有鼓子藝人469人,僅什川就有鼓子藝人206人,經常在田間地頭自娛自樂,為此皋蘭縣文化館還專門成立了蘭州鼓子協會。皋蘭鼓子取得輝煌的成就,曾代表省、市、縣參加過許多頗有影響的重大活動。1956年,全省“百花齊放”匯演在定西舉行,本縣選送了4名鼓子藝人參加演唱。1982年,水阜村4名藝人在省文化廳參加了錄音工作。1984年,水阜村藝人應美國哈佛大學音樂界人士的邀請,在蘭州大學完成了錄音、錄像工作。1994年,在第四屆中國藝術節上,以水阜、什川為主的演唱人員參加了為期十天的演出活動,中央、省、市廣播電台、電視台均進行了錄音、錄像。這次演出中,不僅老藝人們都拿出了自己的“絕活”,而且湧現出了許多後起之秀。1996年,皋蘭縣創作的《引水帶頭人》在全市調演中獲得二等獎。2003年.水阜村演唱人員參加了市政府牽頭主辦的文化廟會,在五泉山進行了為期六天的演出活動。願蘭州鼓子開出更絢麗、更壯美的民間藝術之花。(陳增三)
皋蘭縣鼓子協會
皋蘭縣蘭州鼓子活動情況簡介
皋蘭縣歷來文化底蘊深厚,自蘭州鼓子傳入本縣以來,雖經歷了許多坎坷,但在幾代藝人們的共同努力下,這朵民間藝術奇葩,最終得到了保護和發展,時至今日,皋蘭的蘭州鼓子不論從人員、隊伍、年齡等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和提高。演唱人員達四百多人,近年來培養了一批女青年和藝術新秀,年齡最小的十八歲,成為鼓子隊伍中的一支生力軍。從演唱形式來說,走出了一條炕頭藝術向舞台藝術轉變的路子。演唱中有服裝、有道具、有動作、有表情、使這門古老的民間藝術得到了升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上級有關部門的支持下,縣鄉、村相繼成立了鼓子協會,文化站和活動室,逐步形成了以水?、什川西鄉鎮為中心,輻射其它鄉、村的演唱網路。做到了場地、人員、活動三落實。把純民間組織變為政府領導的民間組織,各級組織在組織開展好經常性的活動外,積極組織藝人參加省、市、縣舉辦的重大活動。使鼓子的知名度得到了提高。湧現出了如牛萬炳、陳增三、張德信、宋渾祖、劉艷玲、劉錫花、牛曉玲、牛彩萍、牛有義、王文彩、魏周江、魏周權、陸發安、魏孔亮、陶世棟、劉東悔、魏孔林、陸孝蘭、陳增祿等一大批藝術骨幹。在他們的帶動下,皋蘭鼓子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蘭州鼓子在皋蘭縣來說,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能彈會唱者甚多,農閒、節慶、婚喪嫁娶、雨雪天便成了好家們邀朋會友,交流技藝的最好時機,較大的村一個活動地點根本滿足不了好家們的需求,像水?、什川、莊子坪等地,同時有幾個地點在演唱,部分居住較分散的好家則要跑好幾里,甚至更遠的地方演唱。創作隊伍創作的“皋蘭頌”,“引水帶頭人”,“抗洪英雄高建成”,“千里隴原跨駿馬”等,在重大節會的演唱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縣、鄉文化部門的大力支持和輔導、愛好者的廣泛參與,不少有文化,有志趣的年青人加盟,近年來重大節會的頻繁演出,使得皋蘭鼓子從器樂配置,演唱水平、人員結構方面都有了質的飛躍。大大提高了皋蘭鼓子的智名度,使皋蘭豉子走向省城、走向全國,飛到了異國他鄉。多次代表市、助參加了許多重大演出活動。一九三四年(民國廿三年)劉爾?在五泉山舉辦修五泉山廟會、什川藝人魏孔吉,魏至平,魏建徑等人參加了鼓子演唱會;一九五六年,全省“百花齊放”匯演在定西舉行,皋蘭選送宋克芳、劉憲忠,魏學堯、肖振仁參加了演出,並受到了鄧寶珊省長的接見;自二00六年蘭州市第五屆黃河風情文化周,蘭州鼓子的四個專場,皋蘭代表隊就參加了三場;二00六年,由省委宣傳部和省文化廳主辦的“甘肅首屆農村文化調演”中,“千里隴原跨駿馬”獲得了三等獎;二00六年十二月,甘肅電視台《百姓經濟》欄目專題報導了皋蘭鼓子;二00六年,市上有關部門出版的“蘭州鼓子詞曲選”收錄了陳增三的大量作品。
蘭州鼓子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無疑為這門古老的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相信,蘭州鼓子的又一個春天即將到來。
探訪皋蘭鼓子世家
“昔日蘭州人生活離不了的蘭州鼓子,如今正在面臨著失傳的絕境。”,儘管蘭州鼓子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由於唱腔、表演手段陳舊,注定蘭州鼓子漸行漸遠。
就在人們為鼓子的處境擔憂的時候,許多民間藝人卻默默地堅守著鼓子的陣地。11日,記者專程趕赴皋蘭縣水阜鄉砂崗村探訪那裡的鼓子追隨者。
 皋蘭縣砂崗村
皋蘭縣砂崗村冬季的鄉間異常寒冷,在砂崗村一個普通農家,卻熱火朝天。六七位鼓子好家聚在一起,唱起了鼓子。他們中間有一位叫牛萬炳的老先生,不僅是砂崗村及周圍幾個村裡的鼓子領頭人,而且他家是一個鼓子之家。他們祖孫三代都因喜歡唱鼓子而遠近聞名。
唱了50多年的好家
牛萬炳今年75歲了,前幾天感冒了,但是精神旺盛,說話底氣十足。
“我唱鼓子50多年了。”說起唱鼓子的經歷,老人的話匣子就打開了。牛萬炳出生在一個鼓子世家。他的父親非常喜歡唱鼓子,在父親的感染下,他也逐漸喜歡上了鼓子。從 1954年開始他就和鼓子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的引導下3個兒子都是鼓子好家,有的善於彈奏三弦,有的能奏揚琴,幾個孫子也喜歡唱鼓子。
調試樂器,上弦、定音、樂器之間的配合演練,在說話之間,一切已經準備就緒了。戶外的寒冷漸漸地散去了,一種久違的暖意瀰漫在屋內。這是幾百年來鼓子藝人需要尋找的那種感覺。一把三弦,一把二胡,一架揚琴,再加上七八位痴迷於鼓子的好家。冬日的鄉間,在寒風凜冽中鼓子婉轉悠揚的唱腔,便瀰漫在一方黃土上。
在牛萬炳老人的引領下,不僅自己的子侄中有許多人喜歡上了鼓子,而且其鄉親們也成為鼓子的愛好者。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是蘭州鼓子最為紅火的時候。”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使鼓子遭受了滅頂之災,改革開放後,鼓子曾經興旺過,到 1994年以後隨著電視等文化傳播體系的日益普及,鼓子就從人們的視野中漸漸地消失了。
目前,蘭州市內大約有五六百人仍在堅持演唱鼓子,儘管許多正式的演出場合已經與他們無緣,但他們對蘭州鼓子的渴望之情卻始終沒有改變。
牛萬炳老人病體初愈,他堅持著給我們唱了一段《子榮降虎》。這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蘭州鼓子的集大成者李海舟創作的,算來也將近半個世紀了。
老人盤腿坐在“炕”上,地下靠近烤箱的地方擺著揚琴,在揚琴的兩邊則是二胡和三弦。隨著揚琴“丁丁東東”敲起,三弦、二胡也跟著響了起來。
祖孫三代痴迷鼓子
“蘭州鼓子”原來稱之為“鼓子詞”、“鼓子”,蘭州人習慣稱為“蘭州鼓子”。蘭州鼓子的音域幽靜,弦律清雅,唱腔激昂。它的句式有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十一字。雖在句式上有長有短,但在格式上要求非常嚴格,不允許有加字、加句和減字、減句的情況出現。蘭州鼓子的曲調有越調頭、銀扭絲、三朵花子、太平年等曲調。
“蘭州鼓子”大多數以三弦為主,揚琴、二胡、笛、簫為輔,還有敲棒子、打瓶子、擊小鈴者。在過去,蘭州鼓子的普及不亞於秦腔,老蘭州人常聚於一處一人唱眾人和。以前,蘭州鼓子的曲調有 110多種,後來許多曲調如大平調、小平調、滄海困龍等,都慢慢失傳了。現在老藝人中間傳唱的曲調只有60多種,經常唱的只剩十幾種了。
如今鼓子的好家範圍比較狹窄。大部分愛好者的年齡都在40歲以上,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非常少。牛萬炳在“炕”上唱的時候,他的小兒子牛有清也拿起了三弦給他伴奏,孫子則在地下看著。
唱完了,牛萬炳告訴記者,幾十年他參加了許多民間藝術活動。其中影響最為深刻的就是 1994年在蘭州舉行的第四屆藝術節,在那個會上,他和孫女共同在白塔山,為來自四面八方的友人們表演了蘭州鼓子。當時,他的孫女只有12歲。
艱難的守望者
民間藝術是一個孤獨者的事業,伴隨他們的不僅有孤獨,還有清貧。這是記者近些年採訪民族民間藝人時最為深切的體會。
蘭州鼓子是一個非常悠久的民間藝術。關於蘭州鼓子的產生時間許多人一直爭論不休,從唐、宋、元、明、清各有一套說法。《武林舊事》記載說:在宋代就已經有了“鼓子詞”,有些人認為,宋末安郡王趙令畸是鼓子詞的首創者。在鼓子藝人中流傳的一個故事,將鼓子產生的年代提前到了唐代,儘管不足為憑,但至少說明,蘭州鼓子是有些年頭的了。鼓子詞有一個曲調名叫打棗竿,據說它是唐太宗李世民打棗子時所唱的。
採訪中牛萬炳老人也給記者講述了50多年來為鼓子付出的艱辛,有些是精神上的,有些是經濟上的。別的不說,這些年到市裡的各種民間藝術活動,都是他自費前去。有些時候,需要的人多,必須邀請鄉親們共同完成節目,他就要負擔所有參加者的吃住花銷及車費,而活動的組織者卻從沒有給他們提供過任何的報酬和補貼。為此,他還曾經被鄉親們所誤解,儘管如此他對鼓子的激情卻一直沒有改變。
砂崗村的村支書牛有禎告訴記者,這些年村里對鼓子等民間藝術活動給予了大力支持,逢年過節,各種活動都要組織鼓子好家們演出。如今村裡有一個農民文藝協會,其主要作用就是組織村民開展各種文藝活動。這個活動成立的目的就是弘揚傳統文化,他們不僅組織會員開展秦腔、鼓子演唱活動,而且下大力氣從年輕人中發現和培養文化骨幹和新人。通過農民文藝協會的努力,經常開展各類文化活動,用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服務農民。
其實不僅是鼓子面臨困境,其他的許多民間藝術也面臨失傳的境地。流傳在我省境內的民間曲藝主要分為唱、說、有說有唱三種形式,而唱又分為唱書和唱曲兩種形式。主要的唱曲有:隴東道情、秦安老調、蘭州小曲、蘭州鼓子、民勤小曲、河州賢孝、涼州賢孝等20種形式。
由於這些曲藝的愛好者日漸減少,絕大部分年輕人都投向了時尚的流行的各種節目。據記者了解,現在蘭州鼓子的老藝人不足60人,再加上散布在榆中、皋蘭等地的“鼓子”愛好者,全部人數不超過五六百人。
同時,這些民間曲藝的形式也不適應當前人們的生活節奏和審美取向,儘管有些人大聲叫好,但在年輕人中間沒有多少市場。有關人士認為,應當把這些唱曲按照公益事業性質來給予扶持。
雖然前途艱難,但牛萬炳和其他鼓子愛好者依然堅持不懈地為鼓子的明天努力。幾十年來,他們編寫了不少的鼓子新詞。去年,他們結合建設新農村編寫了《建設新農村》的鼓子詞:
(鼓子頭)黨政英明,華夏飛騰,舉國上下齊行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大灶歌)黨中央真英明,為人民建奇功,“三個代表”指航程。
(羅江怨)深化改革,突飛猛進,祖國繁榮,人民安寧,五洲四海齊歡慶。
(銀紐絲)1.中央決策似春風,經濟建設為中心,人民齊讚頌,各個帶笑容,男女老少齊上陣。
2.農村的面貌煥然一新,廣播電視村村通,樹立榮辱觀,人人爭先鋒,脫貧致富把小康奔。
3.科技興農有良方,增產增收民富國強,為黨要爭光,共同創輝煌,和諧社會人民興旺。
(鼓子尾)新農村建設,樂民心,農民高唱幸福歌。這才是,社會穩定,前程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