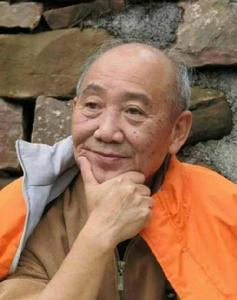獎項由來
據了解,首屆“楊牧詩歌獎”於2016年6月正式啟動,每兩年舉辦一屆。讓楊牧非常高興的是,“楊牧詩歌獎”是中國當代首個以健在詩人命名的官方詩歌獎。該獎因是中國詩歌學會和達州市渠縣人民政府聯合主辦,而落戶四川渠縣。其中金獎1名,獎金10萬元;銀獎2名,每名5萬元;銅獎3名,每名1萬元;優秀獎5名,獎金每人5000元。
另外,鑒於楊牧先生《我是青年》的廣泛傳播與影響,在“楊牧詩歌獎”金、銀、銅獎外,單設“楊牧詩歌獎·青少年詩人獎”。凡年齡不大於36周歲(這是楊牧創作《我是青年》時的年齡),均可參評此獎。“楊牧詩歌獎·青少年詩人獎”5名,獎金每人1萬元。 讓人意外的是,“楊牧詩歌獎”,楊牧本人並不擔任評審。“中國詩歌學會將邀請國內有影響力的詩人、詩歌評論家擔任評審。我就不擔任評審了,萬一有渠縣詩人獲獎,我得避避嫌。儘管我很希望有家鄉詩人獲獎,但我給主辦方提出的建議仍然是以詩歌文本為準,把大獎頒給真正寫出好詩歌的詩人。”楊牧透露,為了顯示公正性,此次“楊牧詩歌獎”面向全國(不局限於四川),所有參賽詩作都將抹掉作者名字,再讓評審們“看詩歌打分,讓文本說話”。
據了解,達州方面不僅設立了“楊牧詩歌獎”,昨日還提出打造“中國西部詩歌城”的文化戰略。值得一提的是,昨日舉行的“在蓉達州籍著名詩人見面交流座談會”,參會的凸凹、向以鮮、山鴻三位《詩歌集結號》名家導師,都來自四川達州。
三大亮點
亮點一:為楊牧成名作《我是青年》 設“楊牧詩歌獎·青少年詩人獎”
鑒於楊牧先生《我是青年》的廣泛傳播與影響,在“楊牧詩歌獎”金、銀、銅獎外單設“楊牧詩歌獎·青少年詩人獎”。凡年齡不大於36周歲(此年齡為創作《我是青年》時的年齡),均可參評此獎。“楊牧詩歌獎·青少年詩人獎”5名,獎金每人1萬元。
亮點二:所有詩歌去名評選 面向全國(不局限於四川)
讓人意外的是,“楊牧詩歌獎”,楊牧本人並不擔任評審。“中國詩歌學會將邀請國內有影響力的詩人、詩歌評論家擔任評審。我就不擔任評審了,萬一有渠縣詩人獲獎,我得避避嫌。儘管我很希望有家鄉詩人獲獎,但我給主辦方提出的建議仍然是以詩歌文本為準,把大獎頒給真正寫出好詩歌的詩人。”楊牧透露,為了顯示公正性,此次“楊牧詩歌獎”面向全國(不局限於四川),所有參賽詩作都將抹掉作者名字,再讓評審們“看詩歌打分,讓文本說話”。
據了解,達州方面不僅設立了“楊牧詩歌獎”,還提出打造“中國西部詩歌城”文化戰略。
亮點三:中國首個以當代健在詩人命名的官方詩歌獎
2016年7月,成都商報記者從達州市詩詞協會與大巴山詩刊在成都舉辦的“在蓉達州籍著名詩人見面交流座談會”上意外獲悉,中國首個以當代健在詩人命名的官方詩歌獎——“楊牧詩歌獎”落戶四川。
獲獎作品
2637 號《一捆艱難移動的苞穀草》(作者:楊鳳龍(山風))
1478 號《我望著他們——》(作者:玉珍)
114 號《老家的老母親》(作者:趙春)
745 號《故鄉的那些大》(作者:孫勝)
4592 號《亡魂之歌(組詩)》(作者:王增弘(一墨))
學術評論
與英雄和讀者一起疼痛——評王增弘獲獎組詩《 亡魂之歌 》
增弘斬獲“首屆楊牧詩歌獎·青少年詩人獎”,可謂名至實歸,但我還是有些意外——畢竟在以破壞語言純度、製造閱讀障礙、虛構玄幻意象而迎合報刊編輯的詩歌潮流下,增弘的詩算不上“潮”,更在“主流”外,投之茫茫詩海中,是很難進入方家法眼的,他的組詩能從成千上萬件參評作品中脫穎而出,足見其獨特之處——這是詩人站在時代坐標上滿懷激情創作的一組亡魂歌,正應了第二屆華語詩歌獎得主、青年詩人朵漁的獲獎感言,“詩人應該回到時代的現場,重新充滿激情”。這也許是一種巧合,但我情願認為,這是一種必然,一種理性的回歸——詩歌已經遠離讀者太久了,身邊的詩友們總在抱怨,“能讀懂古體詩,卻讀不懂現代詩”。增弘詩歌的獲獎,是對所謂主流詩歌創作的反省和矯正,也是對大眾化詩歌創作的肯定和張揚,讓我們能夠從另一個維度來解構詩歌的創作路徑和方向。
每次談到詩,我都想拿汪國真和余秀華說事,並非我要像某些人那樣貶低他們,相反,我很認同他們的創作態度,即絕對的真誠、絕對的真情。增弘與他們之間沒有任何關聯,無法相提並論,但我要說的是一種詩歌現象,就是他們都擁有很多讀者,而以著名自詡或者被人冠以著名的詩人不計其數,卻大多只在圈內曲高和寡,圈外則知音寥寥。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們是孤傲的,也是孤獨的,不知這是詩歌的悲哀還是詩人的不幸。增弘和他的詩與之截然不同,他融入了民眾,融入了生活,把一顆真誠的心交給了讀者,其詩在語言上沒有任何閱讀障礙,小學生也能理解,清新自然得如同一潭見底的湖水。我始終認為,他和汪、餘一樣,都是用心在寫作,沒有半點裝腔作勢,那些打動人心的詩句絕不是刻意碼出來的,而是內心世界的自然流露,真情實感的強烈迸發,就像一眼甘泉在汩汩流淌,所以能直抵讀者心扉。
增弘是我在報社工作時結識的詩友,我們情趣相投,常常談文論詩。7年前,一場草原火災奪走了22個鮮活的生命,其中15名官兵壯烈犧牲。那時,我作為成都軍區戰旗報社記者被派往現場採訪,增弘則守在報社做著信件收發工作,沒想到他會以詩歌的形式投入這場備受社會關注的輿論戰。在巨大的悲痛和情感衝擊面前,任何技巧都顯得拙劣和多餘,不難看出,增弘創作這組詩時,幾乎沒用到什麼“特技”,如果非要說技巧,那就是他不怕犯忌,讓自己“死”了一回,以“我”這個烈士的身份和視角,拉近了與讀者的情感距離。相信很多人都不願這么做,增弘卻大膽選擇了這個角度,因為他在滇西部隊服役時曾多次參與撲火救災,幸運地與死神擦肩而過。他感同身受,最能理解那些為撲火而壯烈犧牲的戰友,而且,他還從網上得知,22名烈士中,有2名是和他同期入伍的廣東籍戰士,相同的經歷、相同的年齡和相同的籍貫。一個個情緒“引爆點”,引發了詩人“非寫不可”“不得不說”的創作衝動,讓詩人和烈士的靈魂在一場特殊的情感遭遇中碰撞出靈感的火花,於是萌生了一個“奇異”想法——代表犧牲的戰友“說”出想說卻沒來得及或無法說出的心裡話,與親人、戰友進行一次非常意義的靈魂對話。這組詩最初的題目叫《補遺》,按增弘的解釋,就是想替烈士們補上幾句告慰親人和戰友的遺囑。“火燒著我/我用盡全力/卻動不了僵硬的軀體/如果可以,我想用盡全力呼吸/可我已經沒有任何知覺/這是哪?/火燒著我/我看到自己/躺在殯儀館的火爐里/我聽見了身體裡的每一塊骨頭/被燒焦並吱吱作響,斷裂……老天啊!”讀到此處,怎能不教人撕心裂肺,疼痛如絞!詩人言猶未盡,又繼續寫道:“火燒著我/我將化為灰燼/可火卻沒有燒掉記憶/沒有燒掉我眷戀著塵世的感情/沒有燒掉我的靈魂和精神/我沒有‘死’!”烈士不朽的靈魂躍然紙上,我們仿佛聽到了來自遙遠天國的聲音。
普希金說:“詩人最寶貴的東西就是真摯。”悲天憫人的情懷是詩歌創作的感情基礎,增弘的創作始終處於悲痛狀態中,情感真摯而熱烈,早已與烈士、親人交融為一體,甚至模糊了自己的角色。在另一首詩中,詩人分別以“兒子”“丈夫”“爸爸”身份,與“爸爸”“媽媽”“老婆”“孩子”傾述衷腸,這是逝者對生者的真情告白,字裡行間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折射出革命烈士“無情未必真豪傑”的人性光輝。組詩中,這樣的情感表達一貫到底,且逐漸得到了思想和藝術的升華。詩人飽含真情,與英雄和讀者一起疼痛,用質樸無華的語言,寫出對軍營和戰友的不捨,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家鄉故土和戰鬥過的地方的眷戀。這種全景式立體抒寫,在讀者心中塑造了烈士們血肉豐滿、胸懷博大、靈魂崇高的群體形象,彌補了新聞宣傳無法直抒胸意的缺憾,達成了詩歌抒情、言志、記史的功能和使命,使之迅速躍升到了史詩的藝術高度。也許,這正是首屆楊牧詩歌獎的評審們青睞這組詩,並將其列入獲獎篇目的一個重要理由。
詩人撫慰的永遠是人類不安的靈魂和受傷的心靈。創網、辦刊、寫作,增弘都秉承了為人民、為時代、為讀者創作的文學理念,他的這組獲獎詩是能點燃我們信念和激情的星火。在那個寒意徹骨的冬天,在那些愁雲慘澹的日子裡,他讓我們看到了一絲驅散陰霾、溫暖靈魂的亮光,進而以堅強之手翻過悲痛的一頁。這,就是我們能感受到的詩歌力量!反觀當下喧囂浮華的詩壇,實在有些令人沮喪,彼此讀不懂詩作、故作高深者有之,扯大旗另立山頭者有之,復古倒退走老路者有之,更遑論給人以鼓舞和力量。這樣的詩人、這樣的詩作,倒是越少越好!網際網路上,捍衛詩歌尊嚴的勇士們口誅筆伐,向偽詩發起一輪輪宣戰。濃濃的火藥味,讓我們不得不回首檢視那些分行排列的文字,有幾多是真正的詩?有幾多是時代、人民和讀者需要的好詩?
詩歌是生活的審美超載,也是心靈的絕美迴響,希望每一首詩都能抹平我們的創痛和憂傷,給我們帶來陽光和希望,喚起我們對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嚮往。
增弘和他創建的5星文學網一直在這么做,他一定會這么做!
註:評論作者系首屆巴金報告文學獎獲得者,簡約主義詩歌倡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