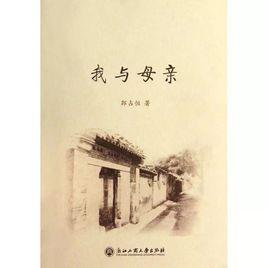內容簡介
《我與母親》由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郭占恆,男,1954年9月生於北京市通州區,1974年12月入伍,1982年2月杭州大學經濟系本科畢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7年7月浙江省委黨校研究生畢業,1988年9月獲中央黨校經濟學碩士學位,先後在海軍航空兵第一機務學校和武警杭州指揮學校任教,1994年9月轉業到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現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浙江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浙商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浙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會副會長,浙江省委講師團兼職講師,浙江省委黨校、浙江大學、浙江工商大學、浙江工業大學兼職教授,杭州市諮詢委員等。在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20年來,參加了這一時期的省黨代會、省委全會、全省經濟工作會議、專題經濟工作會議的準備工作,參加了五年規劃建議研究制定和浙江發展道路經驗的總結工作,參與了省委一些重大戰略部署的研究、決策和實施工作。自1981年在《學術研究》發表首篇論文以來,三十多年先後發表論文、研究報告以及主編和參編的教材、專著200餘篇部,總計350餘萬字,多篇被人大報刊複印中心轉載或其他文庫收集,主持承擔省、部級以上重大課題十餘項,獲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十餘項
媒體推薦
黃亞洲詩人、小說家:郭占恆的這種表述風格無疑是很聰明的,在進入生活之前他首先讓你撫摸生活,讓你逐漸沉入一種境界,而且,最後,往往讓你自己得出結論,你沒有結論也不行。這就是文學的魅力。從這個層面上說,郭占恆可謂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
鮑觀明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社長、出版人:郭占恆有一種可姑且稱為“親切的洞察力”的特質。敏銳而不尖銳,包容卻有原則。六十歲,老郭已經到了可以回首人生的年紀了,在《我與母親》這本自傳式的散文集中,或難得或常見的人生經歷在他老辣的眼光下、簡樸的文筆中,顯得黑白分明,大俗大雅,有聲有色。勸君讀一讀這本書,因為書里的智慧不沉重。
沈嫻《我與母親》責任編輯:
《我與母親》中有一條路,從北京城郊的泥土地延伸,越來越寬闊,路邊的風景越來越繁盛。路遙遙,塵滾滾,但低下頭,看見的仍是那沾滿泥巴的稚嫩雙腳。《我與母親》的力量來源於文字間的泥土與根須。我想,這也許就是郭老師堅持用“我與母親”為書名的原因——堅持最初,才能行至更遠。
圖書目錄
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讀郭占恆散文 黃亞洲
我與母親
兒時過年
年關思故鄉
文昌過年
婚禮上的祝詞
三十年來相會
高考紀實
濃濃井岡情——記井岡山幹部學院
大有莊100號院——我所知道的中央黨校
慢的遐想
體驗日本
走進台灣
三國紀行
新疆印象
想不到臨沂這樣好
行走山西
再訪安徽
我的農家院
老郭的尷尬事
拼將一生為信仰
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相結合的探索者
印象江南項棟輝
牛人李春波
養個小孩兒有多貴
後記
後記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我作為1954年出生的小駒,如今已過一個甲子,成為老馬了。今年又是馬年,關於馬的成語典故和美麗傳說又被人們一一倒騰出來,大家最喜歡說、喜歡聽的無非是些“馬到成功”“一馬平川”“快馬加鞭”“走馬上任”等吉祥之類,還有些不斷衍生的“馬上封侯”“馬上有錢”“馬上有房”“馬上發財”等期盼之類,我倒是喜歡些“信馬由韁”“放馬南山”等悠閒之類。
人老了就會有些懷舊。懷舊不是存心要懷的,而是腦海里自己冒出來的。如果一個人眼前的事記不清、記不住,而過去的事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記得倍兒清,不停地往外冒,越來越戀舊,越來越想家,越來越想念父母,越來越想念兒時的夥伴和村落炊煙,那就是老了。這幾年,每逢佳節、工作稍淡的時候,我就會滋生一種思鄉情,而每當這種情愫襲來的時候,又衝動著自己寫一點文字來釋懷。於是乎,在春節、在節假日、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從床上爬將起來,披衣寫作,寫下了《我與母親》《兒時過年》《年關思故鄉》等文字。
人老了就會有些灑脫。一個人活了半個多世紀,鹽吃多了,橋走多了,碰壁多了,可謂飽經滄桑,終於懂得了順應天意、順應自然、順應規律的道理。孔子日,“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人老了,積攢了許多談資,增加了許多自信,臉皮也厚實了許多,難免會倚老賣老,說一些大話,爆一些囿事。於是乎,我也效仿王蒙先生,斷斷續續記下了一些《老郭的尷尬事》。因為,人在旅途亦在囧途,每個人都有“過五關斬六將”的得意春光,也有過“走麥城丟城池”的失意秋色,真實的生活就是這個樣子。
人老了就會有些閒情。過去年輕時,工作壓力大,生活節奏快,只知道往前沖,就如爬山直奔山頂,無暇顧及路邊的花花草草,無心欣賞山徑的美景美色。而這幾年,隨著單位年輕人快速成長,分管的工作壓力小了;隨著女兒成家,與內人早早過起了二人世界的生活。為了打發漸漸多起來的空閒時間,只好學點閒情雅致,寫點閒散文字抒發情懷。於是乎,無論是出國考察,還是省內外調研,在工作的大線條外,更加注重一些親眼所見的生動細節,寫下了《體驗日本》《走進台灣》《三國紀行》,以及《新疆印象》《行走山西》等長篇隨筆。當然,走過的地方遠不止這些,只是過去無暇欣賞、無心記述罷了,這或許也是人生的一種憾事。
真是沒想到,寫了半輩子的領導講話、政策檔案、調研報告、經濟論文等,竟還能集萃一本粗糙稚嫩的散文集。這無疑要感謝支持和幫助我的家人、領導、同事和摯愛親朋,特別是要感謝那些從不看我的經濟學文章,而願意看我的散文隨筆的冬粉們。
感謝家人。我是外地人,按最初的戶口本論,我們家的一家之主是趙濤女士。她既是內人,又是同學。同學知根知底,會永遠與你平等,永遠平視你,你也就永遠高大不起來,所以不要輕易找同學。當然,既然找了就要不拋棄不放棄。其實,內人很有才,大學考試成績一直在我之上,但就是懷才不用,偶爾寫篇《一米線的啟示》等,亦能發表。那年我去日本,寫了幾段簡訊發給她,她說很好,你應該寫下來。於是我就遵旨,走一路寫一路,回國後形成《體驗日本》,後來的許多習作也都是在她的批評指導下寫出的,當然,她批評居多,指導偏少。再一個生命中的女人是小女郭璇,小時候她是我的天使,我是她的偶像,大起來她移情別戀了,我就靠邊站了,也挺鬱悶。小女學文化創意,重點研究時尚,聰穎漂亮,與我略有代溝。我一直以為她理解不了我們這一代人,直到有一天女婿告訴我,漣漣(小女乳名)看老爸寫的《我與母親》哭得稀里嘩啦,紙巾滿地,才恍然大悟,血到底是濃於水的。家人當然包括老家的人,如今父母仙逝,偶爾能看到我作品的是大哥占元、四弟占營、五弟占榮、小妹雪玲和六弟占立等弟妹,他們很喜歡看,有時打來電話談一些感受,有時拿到村子裡看,引起村民如張二叔等人的詢問,這不免有點顯擺,但對我卻是個鼓舞,如有機會一定寫篇《我與兄弟姐妹》的散文記之。
感謝領導、同事、戰友和朋友。寫東西是為了給別人看的,猶如一塊石頭丟進水裡要有浪花,浪花越大石頭越高興,於是浪花成就了石頭。這幾年,我之所以在工作之餘堅持寫作,是與領導和朋友們的鼓勵分不開的。記得《大有莊100號院——我所知道的中央黨校》寫好後,李書磊等副校長看過初稿,舒國增主任鼓勵我去發表,趙洪祝書記批示給予鼓勵,趙一德秘書長講,凡去黨校的學員都應看看,於躍敏副部長看到我總微笑地說一句“大有莊100號院”,中央黨校進修部將全文收錄在“廳局級進修班(第58期)‘戰略思維與領導能力,研究專題”《課題研究報告與讀書報告》集,特別是還收錄到《我與中央黨校——校慶80周年紀念文集》,給我以莫大鼓舞。
記得我的一些散文隨筆寫好後,通常先給單位的董俊平、李曉華、黃巧敏、任春娟、張勤文、費映潔、張蘇敏、吳彬、沈亞偉、蔣劍平等幾個同事看看,聽聽意見,讓他們或她們幫我修改糾錯,指點迷津,因涉及人員很多,這裡就不一一報姓甚名誰了。記得陸立軍、汪水波等老師,張仁壽、傅吉青、黃河等同學,杭州的李火林、桑士達、黃國范、潘育萍、項棟輝、王承武、陳敏、池永斌等朋友,北京的武延年、武通來、秦浩、周莉、何曉鷗、萬洋等戰友,以及部隊的老領導馮孝新、張若青等,都對我的作品給予過鼓勵。張仁壽說我寫的東西“有知識點,可讀性強”,這大概是一個大學校長對好文章的基本要求和評價。周丹處長不僅自己看了,還推薦給全處的同志看。車隊小秦看後發來簡訊,說我十分了解外地打工者的情況和心情,很受感動。其實,他的話也感動了我。 感謝那些甘為人梯的刊物編者。我歷來認為,刊物是連線作者和讀者的橋樑和紐帶,編者更是成人之美的君子也。我的這些粗糙稚嫩文字,有幸在《學習時報》《浙江日報》《華夏散文》《貴州日報》《中國經濟時報》《浙江作家》《浙江工人報》《浙江經濟》《聯誼報》《中國城市化》《杭州我們》《發展規劃研究》《足跡》《幹部教育研究》《紹興日報》《臨沂日報》《吳越風》等報刊發表,得益於高海浩、李丹、金波、徐忠良、柴國榮、王祖強、馬力宏、桑士達、楊祖增、方宇紅、賴華東、鄭休白等的傾心幫助。尤其是《浙江雜文界》《樂清灣》的主編董聯軍,不僅全文發表了我的長篇習作,而且還常打電話向我反饋讀者的反映,並進行精彩的點評。孫君、王水君、姚國海、葛美芳、潘改良、施衛華、施愛珠、趙利平、李軍、鄭利軍、李敏等好友多方面鼓勵和支持本書出版,方使拙作得以同大家見面。
感謝大作家黃亞洲先生。我與亞洲相識時間不長,但印象頗深,印象頗好,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他水平高,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文學高手,詩歌、散文、小說、劇作無一不精,已出版詩歌小說16部、電視劇本數百集,多次榮獲國家圖書獎,國家“五個一工程”獎,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特別獎,中國電影華表獎。電影《落河鎮的兄弟》還榮獲第12屆美國芝加哥國際兒童電影節“聯合國宣言獎”,第20屆德國法蘭克福國際兒童電影節大獎、評審會獎等。他出手快,下筆成章,近幾年更是寶刀出鞘,鋒利無比,每年創作出版1部小說、2部詩集、30餘集電視劇本,而且許多詩歌散文都是在路上完成的,往往是上飛機開始寫作,下飛機列印成文,可謂飛天文字,浪漫得很。他為人謙和,沒有大作家的架子,公益意識很強,不惜花時間主編《浙兵歲月》,把“浙江生產建設兵團那些事兒”搗鼓出來;不惜花時間關注一位老軍人的訴求,連續寫下了《只能抓一把糖給老劉》《盼望更多的人關注屋檐下的老劉》等動情文字;不惜花時間組織朋友深入基層,調研採風,到筆者的安吉小院來,不僅寫下了優美的詩作,還愉快地與我沒見過多少世面的弟弟、妹妹合影。他作風樸實,幽默風趣,性情之下,常常手舞足蹈,甚至將穿著有些破舊的衣褲撩起,展現率直童真的一面,與他一起喝茶閒談,真是一種享受。他在文壇的地位很高,是第六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浙江作家協會名譽主席,還是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於是乎,請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來為本書作序壓陣,我就可以攀高枝、狐假虎威了。當然,我很清楚,亞洲先生序中所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著實過獎,實不敢當,但卻指出了我今後的努力方向。
序言
序
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讀郭占恆散文
黃亞洲
我一向以為,細膩,是文學諸品格中最為高貴的品格之一。細膩到有了觸感,“生動形象反映生活”的文學便站住了“形象”二字,可以稱作是文學了。
小說里的細節、散文里的精雕細刻、詩歌里的細密情愫的表達,都是“細膩”的面孔,其音容笑貌,足以使人怦然心動。我們也許永遠做不到像普魯斯特、茨威格那樣精細人微、滔滔不絕的描摹,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真正的骨頭是包著皮膚和筋肉的,只有透過豐富、魅力無窮的表象才有可能順暢地到達事物深處。
我第一次讀郭占恆的散文,是數年前,有人推薦的,發在我信箱里,題目大約叫“兒時過年”吧,頓然為他敘述的細膩所打動。他用他樸實無華的字句把我們帶到他家鄉過年,將淳樸的年俗逐一娓娓道來,“我一直相信年是有味的,能夠聞得到”,於是我先後聞到了鉻餷、芝麻花椒鹽、豬頭肉、淋上香油的餃子、“小鋼鞭”爆竹的硝煙,飄蕩在村坊里的所有味道都那么具體、那么濃郁、那么的有華北農村的地方特色,我以為,這就是文學的芬芳,文章所要表達的主旨自然不用說了,全在氣味之中。
郭占恆的這種表述風格無疑是很聰明的,在進入生活之前他首先讓你撫摸生活,讓你逐漸沉入一種境界,而且,最後,往往讓你自己得出結論,你沒有結論也不行。這就是文學的魅力。
我知道郭占恆的本職工作是經濟研究及這一研究的準確表達,且是巨觀為主,這項工作要求特別嚴謹的邏輯思維,一般情況下與文學所要求的形象思維是兩條路徑,據說在人腦中引起興奮的區域都不一樣,常聽得曾經熱愛文學的機關秀才們哀嘆“成天埋在公文堆里我的文學夢算是完了”。這種嘆息很符合邏輯,但是顯然,郭占恆的兩把板斧都掄得很好,這裡的一個關鍵字,恐怕就是“勤奮”。
郭占恆的勤奮是出了名的,下筆勤奮倒還其次,首先是思想勤奮。對於生活,他始終在思考,思考其中的異同與溫差。同樣去中央黨校學習一陣,大多數是一篇論文交差,還不確定是自己一個鍵一個鍵敲出來的,還是由秘書甚至是由一個寫作班子發到信箱里的,但郭占恆卻是除了論文之外,又洋洋灑灑寫了萬把字的《大有莊100號院——我所知道的中央黨校》,又有外在描述,又有內在分析,文章發來一看,直教我這個也在“大有莊100號院”拿過結業證書的人汗顏。他去中國的山西、新疆、安徽、台灣,去日本,都是行一路寫一路,我當然也有此習慣,但更多的是寫一些短小的詩歌,風花雪月而已,不像郭占恆那樣,既要以他的形象思維描述種種表象,筆法追求細膩,還要以他的邏輯思維點明處處關節要害,顯示其整體骨架,力求全盤把握,這是很累人的活,但是郭占恆樂此不疲。對此,光是歸之於習慣已不能說明問題,顯然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再文雅一點說,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就是如此的——他自己善於感知,並且善於讓別人諧振。
希望郭占恆多寫一點,不僅現在多寫,而且希望在有朝一日擺脫了繁重的機關勞作之後,更有時間把自己的筆觸大面積地投向生活,並且,依舊如此細膩地表達自己的所見所聞,用極其綿密的字句捆綁我們,讓我們幸福得動彈不得。
2013年8月15日於聖何塞
(序言作者為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影視委員會副主任。曾為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六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第六屆浙江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魯迅文學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