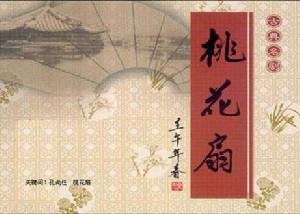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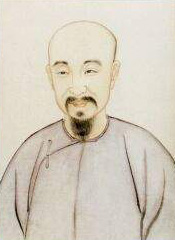
尚任自幼聰慧,熟讀經史,好詩文,通音律。父親的好友賈鳧西,對他從事戲劇創作影響頗深。雖高才博識,但屢試不中,便捐納了國子監生,三十五歲之前隱居石門山中。康熙二十一年 (682年),應衍聖公孔額所之請,出山為其夫人治喪。後主修《孔子世家譜》及們閾里(新)志》,訓練禮生、樂舞生,在把孔時做贊禮,還選聘工匠,監製禮樂器、舞器、祭器達數十種。他日夜忙碌一年有餘,因辦事認真,才能出眾,成績卓著,受到孔毓圻的贊常。康熙一二十三年(16幼年)十一月,皇帝南巡北返,親臨曲阜祭?巳孔於,孔尚任經孔毓圻保舉,充任講書官。他剛講完《大學》首章,康熙帝即傳諭大學士明珠和王照;“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例議用。”他被破格授予國子監博士,遂赴京任職。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奉命隨工部侍郎孫在豐去淮揚,疏浚黃河海口,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冬才回到北京。其間,他結識了明朝遺民冒辟疆、鄧孝威、杜於皇、僧石濤等人;在揚州登梅花嶺,拜史可法衣冠系;在南京登燕子磯,游秦淮河,過明故宮,拜明孝陵,還到棲霞山白雲庵拜訪了張琈道士,注意蒐集野史逸聞,對南明王朝的覆滅已有深切感受。回京後,任戶部主事、廣東司員外郎等職。
當時的清都北京,戲曲演出極為繁盛。孔尚任在公餘致力於戲曲創作。康熙三十二三年(1694年),與顧采合作的《小忽雷傳奇》在景雲部演出,頗得觀眾讚許。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經過他十餘年苦心創作的傳奇劇《桃花扇》脫稿。該劇以復社名士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滅亡的歷史,“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以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和觀眾。王公顯貴爭相傳抄,清宮內廷與著名崑曲班社競相演出,一時轟動了京城。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桃花扇》稿本。當時與《長生殿》作者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稱。第二年春天,他因一件疑案被罷官。
孔尚任罷官以後,在北京逗留兩年多,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冬回到曲阜石門山老家。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春天,孔尚任病故於家,入葬孔林。他一生著作甚豐,有《石門山集》、《岸堂文集》等傳世。
康熙五年(1666年),孔尚任19歲中了秀才,順利地踏上了科舉的第一個階梯。但接著就在考舉人的鄉試中碰了壁。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主要是考八股文,考題只從《四書》、《五經》里出,內容只能是根據宋代朱熹的注釋來發揮,不準隨意發表意見,更不準唱反調,文章也必須按照規定的框子寫,不合八股的規格是不行的。所以,真正有才學的、能獨立思考的人,未必就能考得上。孔尚任雖然是孔子的後裔,從小念《四書》、《五經》,對孔子的理論自然也不會發生懷疑,但從他對賈鳧西頗尊重,對賈鳧西用鼓詞別出心裁地解釋《論語》頗讚賞的態度看,思想並不很保守。因而,他在科舉上碰壁是可以理解的。
青年時代的孔尚任是很想得到功名,擠進封建官僚的行列的,考不上舉人,自然很苦惱;到了30多歲的時候,他就想另找出路。清聖祖玄燁康熙十七年(1678年),下令開博學鴻詞科,要各地的官員保舉“學行兼優,文辭卓越”之士,到北京去考試,由朝廷直接選拔錄用,讀書人要能得到地方官員的保舉,那在地方上就得有點名氣。孔尚任聽到這個訊息後,就想在當地沽名釣譽了。第二年,他就到曲阜城北40里的石門山,蓋了3房茅屋,隱居讀書了。
《桃花扇》卷一試一出《先聲》、卷三加二十一出《孤吟》,均有“康熙甲子八月”的下注。這說明孔尚任在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歌之餘,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見《桃花扇本末》)。他是聽了族兄孔尚則講述南明弘光遺事及秦淮歌妓李香君面血濺扇的軼聞之後,而激發了創作靈感的。但他幸遇康熙皇帝這件事,卻使他對清代統治者充滿了無限感激之情,如果他懷著這種心情在國子監里度過的話,恐怕日後也不會有多大的出息,他也不會寫出名垂後世的《桃花扇》,在歷史上留下大名了。
三
特別是冒襄,他是《桃花扇》描寫的弘光王朝興亡始末的目睹者,可以說是劇本里沒有出場的劇中人。《桃花扇》里寫到馬士英、阮大鋮迫害東林黨和復社文人,以及復社中的四個書生——所謂“四公子”斥罵阮大鋮的事情。冒襄就是“四公子”之一。冒襄與《桃花扇》的男女主角——侯朝宗和李香君,都是很熟悉的朋友,他們時常在一起出入秦淮河畔。他與名妓董小宛的結合,和侯方域與李香君的結合,都是當時文人中艷稱的風流韻事。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秋,冒襄到揚州拜訪負責治河工程的孫在豐,並和揚州一帶的老人,如黃雲、李沂等,做了最後的一次聚會。孔尚任也參加了。於是,黃雲等人便向冒襄介紹孔尚任的為人,表達了孔尚任想向他們了解弘光王朝遺事的心愿。隨後,冒襄以80歲的高齡,到孔尚任的寓所住了30天。在這30天裡,他向孔尚任詳細地講述了弘光王朝的興亡始末,講述了他與陳定生、侯方域等人在當時和馬士英、阮大鋮作鬥爭的事跡,自然也講述了侯方域與李香君相識、結合、結局的故事。
除了冒襄,杜浚也是孔尚任在揚州一帶結識的一個頗值得注意的人物。杜浚同《桃花扇》中寫到的那個兩面派人物楊龍友頗為熟悉。清兵攻占南京後,他在那裡久住下來。他也可以算是弘光王朝興亡始末的一個目睹者。杜浚在當時是頗有名望的詩人,他的詩作《燈船歌》,描寫明末秦淮河上歌詠沸天的繁華景象,表現了濃郁的興亡之感。明亡後,杜浚長期流蕩南京,生活非常窮困,曾受到老藝人柳敬亭的接濟,可見他與柳敬亭的交往密切,感情頗深。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孔尚任與杜浚相識了,並應邀到孔尚任的船上飲酒暢談。他無疑也給孔尚任提供了許多弘光王朝興亡始末的活資料。於是,孔尚任便從這些人的談吐中,知道了南明弘光小朝廷更多、更具體的種種軼聞、遺事,並加深了對它的認識和理解,從而也就更激起了他的創作欲望。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孔尚任由揚州渡江經儀真前往南京,特意去遊覽了一番弘光王朝的興亡之地。
南京是歷史名城,南朝的晉、宋、齊、梁、陳,都曾建都於此。這些短命的王朝,也曾留給人一種繁華盛景、轉瞬即逝的興亡之感。歷代文人來此遊歷、憑弔,總要抒發一番滄桑之感。而孔尚任這次來游,卻不再泛泛地弔古傷今,因為他頭腦中只有一個弘光小王朝在,他感興趣的也只是這個弘光小王朝的興亡始末。
孔尚任剛剛踏上南京的土地,便整裝去遊覽秦淮河。被稱為六朝金粉地的秦淮河,是明末風流繁華之地,這裡聚集著許多歌館舞榭。每到夜晚,遊船上燈火點點,歌聲沸雜。這些遊客中多數是醉生夢死的官僚、商人,他們來此取樂,固不值得稱道,但那些與眾不同的清流文人,也往往在這裡聚會,一方面宴飲唱酬,留下風流韻事,一方面也藉此議論政事,抨擊時政。侯方域在這裡結識了名妓李香君,冒襄在這裡結識了董小宛。他們借著這種風流活動,串聯起來,與弘光小朝廷的權奸馬士英、阮大鋮之流進行鬥爭。
孔尚任在遊覽秦淮河的時候,找到了一些舊日的老人暢談往日的故事,回想著舊日秦淮河繁盛的光景。於是,他在《阮岩公移樽秦淮舟中同王子與韻》一詩中寫道:
宮飄落葉市生塵,剩卻秦淮有限春。
停棹不因歌近耳,傷心每忘酒沾唇。
山邊水際多秋草,樓上船中少舊人。
過去風流今借問,只疑佳話未全真。
從詩中可見他們當時談的什麼內容了:時間已經過去將近半個世紀了。當日秦淮河上的名流,大概早已不在人間,當時10多歲、20多歲的伎人,現在也有七八十歲的高齡了。現在雖然不如那時候繁華了,但親歷其地,總還能得到些感性的印象。並且,還有人能夠向他講述當年李香君的故事呢!
南京是明代開國時的都城,明故宮依然保存在那裡,孔尚任也去憑弔了一番。他看到昔日的舊殿已經倒塌,只留下殿基;大殿內的紅牆,也已經斷缺;御河橋上的石柱,也傾斜了。於是,他深深地感到,一代王朝簡直如同一盤棋一樣,很短時間就結束了。
孔尚任這次來南京遊歷,除了實地看看他要寫的《桃花扇》故事發生的地方,獲得實際的感性印象,更重要的是他還要去找熟悉弘光王朝政事的人作進一步的調查。他在南京拜會的人物中,除大畫家龔賢、學者王弘撰外,與《桃花扇》關係最重要的要算是明末的大錦衣張怡了。
張怡字瑤星,號薇庵,江寧上元人。李自成攻破北京時,他當時是錦衣衛千戶。崇禎皇帝吊死後,他曾一度獨自守靈戴孝。李自成看他行為可嘉,便“義而釋之”。他由北京到南京,在弘光王朝依然任錦衣千戶之職。明亡後,他便一直隱居在南京郊外的棲霞山白雲庵中避不與人打交道。
在這次拜會中,張怡回答了孔尚任提出的許多問題,談了前朝發生的重大事件,也講述了弘光王朝時清流文人反抗馬士英、阮大鋮的鬥爭活動。因為是親歷親聞,孔尚任感到這是:“數語發精微,所得已不淺。”並且對張怡的人品表示了極大的敬意:
先生憂世腸,意不在經典。
埋名深山巔,窮餓極淹蹇。
每夜哭風雷,鬼出神為顯。
說向有心人,涕淚胡能免?
孔尚任在這首詩中,雖然寫得十分概括、含蓄,但張怡隱居白雲庵的生活狀況和思想精神,還是清晰地勾勒出來了。
這次會見張怡,給孔尚任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後來他在創作《桃花扇》時,便把張怡寫進去了。讓他在第二十齣《閒話》、第三十齣《歸山》和第四十齣《入道》中充當了主角,起了向瀆者和觀眾啟示劇本主旨的作用,藉以揭示深藏於作品之中的愛國思想,進而把讀者和觀眾的感受、感慨,由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生死離別之情,引向興亡之感。這顯然是孔尚任這次與張怡會面的結果。
孔尚任這次南下治河,對他創作《桃花扇》起了很大的作用,不僅獲得了極為豐富的創作素材,獲得了豐富的社會生活知識,而且在實地考察南明遺址、廣泛接觸明末遺老中,受到民族意識的薰陶,從而加深了他對南明興亡的感慨,動搖了他對清朝統治者的那種感恩圖報的態度,這對發掘《桃花扇》的主題和思想傾向起了積極的作用和影響。
四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二月,孔尚任回到了北京,依舊做他的國子監博士。
然而,他從揚州回京後,並未受到特別的恩寵,國子監祭酒對他也不再特別重視,他自己也習以為常,每月六次去國子監,大部分時間是空閒的。他住在北京宣武門外的海波巷裡,日子過得頗為悠哉。從他寫的《博古閒情》這支曲子裡,就可以看出他當時的生活情調:
僑寓在海波巷裡,掃淨了小小茅堂,藤床木椅,窗外幾竹影蘿陽,濃翠如滴,偏映著瀟灑葛裙白擰衣。雨歇後,湘簾捲起,受用些清風到枕,涼月當階,花氣噴鼻。
由於生活的清閒,孔尚任從此對古董文物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經常去琉璃廠、崇仁寺閒逛,見到有中意的古書、古玩,便買回來賞玩,常常把俸錢花得精光,以致變成了收藏家。
在這期間,孔尚任與大詩人王士禎相識了,並過往甚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王士禎任兵部督捕侍郎,與孔尚任雖然地位懸殊,但王士禎一來是詩壇領袖,以風雅自命,喜歡延攬騷人墨客,雖為高宮,卻未改名士風流;二來他與孔尚任同為山東人,一起在京為官,也是大同鄉了,更何況孔尚任身為國子監博士,官雖微卻頗清高,非一般部曹可比;三來孔尚任也能詩,在揚州三年,他在詩壇上也贏得了一些小名氣。這樣,王士禎就把孔尚任帶進了北京官僚文人的圈子,結識的人物也就愈來愈多了。居京閒暇,他就經常參加官僚們的東皋宴集、梨園聽歌、月下聯吟種種活動,過著一種閒官生活。
孔尚任在北京做閒官,逐漸對戲劇也發生了興趣。他的《燕台雜詠四十首》其八云:
十丈紅塵一洞灰,高車短扇河如雷。
太平園裡閒簫管,演到新詞第九回。
自註:“太平園,今之梨園部也,每聞時事,即譜新聲。”可見,他是不只一次地去聽曲、觀劇。
這期間,孔尚任結識了一位工音律的無錫人顧彩(字天石,號夢鶴居士),兩人結為好友,開始了戲劇創作的試筆。孔尚任在北京搜得的古董中,有件唐代的古樂器,名叫“小忽雷”。他在得到這個樂器後,有所感觸,認為這樣的古物,包含著前代的興廢之跡,能寄託人們的興亡之感,所以,就和顧彩合作了《小忽雷》傳奇。這個劇本,是孔尚任構思劇情,顧彩填寫的曲文。這部劇作顯然是不成功的,但是,孔尚任卻由譜寫此劇,得到了鍛鍊,摸索到了戲劇創作的訣竅,特別是進一步掌握了音律的規律,這就為他長期經營、反覆構思的歷史名劇《桃花扇》的創作,做了藝術上的準備。因此,如果說孔尚任的淮海三年是為《桃花扇》的創作完成了題材方面的準備,那么,京中閒官幾年,正是為保證這部歷史名劇的創作成功,做了藝術上的準備。
五
康熙三十八年(1699午)六月,繼洪升的《長生殿》傳奇之後,經過孔尚任10餘年嘔心瀝血、3次易稿的《桃花扇》傳奇終於脫稿誕生了。
《桃花扇》是一部傑出的歷史劇,它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部劇作,以明末復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兩人的悲歡離合的故事,作為全劇的主要線索,圍繞著這一線索,揭示了南明福王的興亡始末。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說:他寫這個劇,就是要使人知道明代“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他以鮮明的愛憎,褒貶的態度,頌揚了忠貞的愛國者,抨擊了誤國的昏君奸臣,如劇中人物柳敬亭所說的那樣:“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還他個揚眉吐氣;那般得意的奸雄邪黨,免不了加他些人禍天誅”。
劇作一開始,便透過笙歌曼舞的昇平景象,揭示出明王朝垮台後的南京城“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當侯方域等文人還沉溺在歌館舞榭之中時,馬士英、阮大鋮等已在暗中活動,企圖死灰復燃,侯方域等清流文人,雖然比較正直,起而與馬士英、阮大鋮進行鬥爭,但也只不過是書生意氣,既無力制止馬、阮之徒擁立福王的活動,也無法改變當時的政治形勢。馬、阮結黨營私,打擊異己,江北四鎮互相傾軋,結果連自己也陷入奸黨之手。弘光王朝在四分五裂中,在清兵壓境的情況下,很快就垮台了,明代300年的天下,也再無恢復的可能了。《桃花扇》真實地反映了弘光王朝從建立到滅亡的歷史,確是“當年真如戲,今日戲如真”。
《桃花扇》對禍國殃民的馬士英、阮大鋮之流的揭露是有力的。他們是乘國事多故之機,來發展自己的勢力,借擁立福王之功,占據要津,獨攬大權。他們對上阿諛奉迎,儘量滿足福王的聲色之好;他們對於異己,則大肆打擊、屠殺,排斥忠貞的關心國家大事的正直人物,把半壁江山搞得四分五裂,把南京城搞得烏煙瘴氣。劇本通過李香君的嘴,罵他們是“出身希貴寵,創業選聲容”,“乾兒義子從新用,絕不了魏家種”。
劇中作者懷著崇敬與沉痛的心情,塑造了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形象,歌頌了這位愛國將領。他赤膽忠心,力圖挽救南明王朝的危局,但受到馬、阮權奸的排擠,固守揚州,孤軍無援,直戰到一兵一卒,眼看大勢已去,感到“江山無主,無可留念”,便從容脫下官服,縱身跳進了滾滾的波濤之中,沉江自殺。展示了史可法對大明王朝的一片忠心。
《桃花扇》更值得稱道的是塑造了李香君、柳敬亭、蘇崑生等幾個地位微賤的人物形象。他們在封建社會裡屬於“賤人”,李香君是妓女,柳敬亭、蘇崑生是說書、唱曲的藝人。但是,孔尚任丟開了傳統的封建觀念,把他們寫成善良、正直、智慧,關心國事的高大形象。侯朝宗幾乎陷入阮大鋮的政治圈套,而李香君卻心明眼亮,及時識破了阮大鋮的詭計,毅然拔簪脫衣,使侯朝宗擺脫了奸人的陷阱。在她被強拉去供馬、阮二奸人取樂的時候,她當面慷慨陳詞,怒罵馬、阮,鞭辟入裡地揭露他們禍國誤國的罪行。柳敬亭任俠好義,為伸張正義敢於赴湯蹈火。當他聽到左良玉要引軍東下,引起了南京的驚恐,於國事不利的時候,他自告奮勇擔任下書勸阻左良玉的任務。在左良玉的帥府,他敢於指責這位握重兵、性暴戾的將軍。總之,在孔尚任的筆下,李香君、柳敬亭等人,不只是一般的善良、正直,而且在國事上明辨是非,對奸黨深為厭惡,在亡國後毅然離去,表現了高貴的節操。
特別是《桃花扇》第四十齣《入道》,寫侯朝宗和李香君於國破家亡、景物全非的時候,卻又喜得重逢。當他們二人在法壇前纏纏綿綿,互傾心中的離情別話時,張道士卻當場把記有他們千愁萬苦的桃花扇扯碎,並給了他們一頓嚴厲的訓斥:“呵呸!兩個痴蟲,你看國在哪裡?家在哪裡?君在哪裡?父在哪裡?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它不斷嗎?”
這裡,是作者借劇中人之口,對當時那些沉浸於兒女情中而忘卻了亡國之痛的人的當頭棒喝!它深刻地啟示觀眾,在國破家亡、身處異族統治之下,只追求個人的幸福是很難做到的。侯、李的結局只能是個悲劇,作者這樣處理是符合當時歷史真實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僅僅滿足於對《桃花扇》的上述分析、理解,而且應該更深刻地領會《桃花扇》在客觀上所隱寓的愛國主義精神。孔尚任創作《桃花扇》不是再現歷史,而是通過這些生動地描寫,通過劇中的那些可歌、可泣、可憎的人物,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之情。
當然,《桃花扇》在反映歷史真實這個問題上,也是有缺陷的。比如,作者在《桃花扇》中,曾借左良玉之口說:“那李自成、張獻忠,幾個毛賊,何難剿滅!”對明末農民起義軍充滿敵視的態度。作者要人們不忘記“亡國之痛”,卻又不主張走奮起反抗的道路,只是叫人們埋名民間、藏身於山林田野之中。這說明,孔尚任在觀察、概括歷史生活時,是受到他的時代和階級的制約的,他仍然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來認識和反映這一特定的歷史事件的。
由於《桃花扇》寫的是剛剛過去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自然是會引起許多在朝在野的文人們的極大興趣,特別是一些曾經經歷過,或聽人講述過明亡清立這段歷史的人們的興趣。再加上顧彩乃至著名演員丁繼之的幫助,劇本寫得非常緊湊,人物形象生動,文詞也精美,符合音律。所以《桃花扇》一寫成,就有許多人借閱、傳抄,時有紙貴之譽。
一年除夕,戶部左待郎李柟,是孔尚任的頂頭上司,派人給孔尚任送“歲金”,並且索取《桃花扇》作為春節期間消遣的讀物。李柟是弘光王朝大理寺丞李清的兒子,江蘇興化人,孔尚任在淮揚時,李清已逝世,但他結識了李柟的叔叔李沂。孔尚任也曾在李柟父親的映碧園中住過多日。對李柟來說,他對他父親經歷過的弘光王朝的遺事,自然感興趣。所以他讀見《桃花扇》興致大發,出資讓“北斗”班子排演,到了元宵節,就在自己的宅第中大演《桃花扇》了。
此後,北京城裡盛演《桃花扇》,而且不只一個戲班在演,幾乎是天天在演。其中以已故的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李霨的別墅寄園中的演出最出色。每次演出,名人大臣、文人士子坐得滿滿的。主持人是李霨的孫子。他不惜揮霍巨金,聘請了兩個戲班,購置大量戲裝和道具。演員們也演得非常賣力,唱作俱佳。常常是在演出中感動得觀眾流下淚來,特別是那些從明代生活過來的“故臣遺老”。《桃花扇》的演出,使孔尚任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
六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初,名滿京華的《桃花扇》演出的熱潮還沒有冷下來。孔尚任每次在劇場的笙歌聲中看演出,觀眾總要把他推在上座上,還讓演員們向他敬酒,有的演員、觀眾還當場請他題詩、簽字。這時候,許多觀眾都轉過頭來指指點點,流露出羨慕、讚許的眼光。孔尚任自己也感到無比榮幸,心情非常舒展。正在這個時候,孔尚任又接到了朝廷晉升他為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的官報,猶如“鮮花著錦”,在他的面前展現了一條通向朝廷顯官的金光大道。
不料,官場翻雲覆雨的變化來得如此之快,僅僅十來天的時間,戶部員外郎的座位還沒坐上幾次,同僚們的賀喜聲還沒有停止,他就被罷了官。
孔尚任這個由康熙皇帝親自破格提拔進官僚行列來的朝官,犯了什麼罪過?為什麼又被皇帝一腳踢出了官僚的行列呢?
原來在上年的秋天,當《桃花扇》傳奇轟動了整個北京城的時候,也引起了精明的康熙皇帝的注意。於是,康熙便在七月七日之夜,命令內侍向孔尚任索取劇本,並且索取得十分急促。孔尚任只好半夜裡送進宮去。玄燁看過劇本後,自然很不高興。儘管劇本寫的是弘光王朝的腐敗,也講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逼死了崇禎皇帝,即使頌揚史可法是忠臣,從大節上看,也不能說不對,教忠教孝是有益於風化的。但是,劇本對明代的滅亡流露出惋惜之意,對那些不肯出山做清朝臣子的人們也作了表彰,這畢竟會引起一些前朝遺老遺少的故國之思嚮往明朝,就會與清朝疏遠。這表明,他親自賞識、提拔起來的孔尚任,並不是一個忠心耿耿為清朝效力的人。但他又不便於公然加給孔尚任什麼罪名,《桃花扇》畢竟沒有悖逆之詞,再說作者又是他破格任用的人。轉過新春正月,康熙考慮的結果,便是授意戶部以“莫須有”的原因,解除了孔尚任的職務。
不明原因的被罷官,孔尚任自然感到突然。他對前來慰問的朋友,表現得很達觀。
他對朝廷還存在著幻想,繼續留在京城裡,希圖弄明真相,期待覆官的可能。可見,孔尚任雖然做了18年的官,畢竟處在閒官的地位,閱歷不深,還有些書生氣。
康熙四十年(1701)正月,孔尚任邀請了李塨、萬季野等人到海波巷寓所宴飲。李塨是當時的進步思想家,自然比孔尚任看問題深切,萬季野熟悉明代的歷史掌故,也比孔尚任懂得政治上的奧妙,他們都勸孔尚任丟棄幻想,儘早離開北京。然而,孔尚任仍不死心,便又拖了很久。就這樣,罷官後,他在北京逗留了兩年多才不得已懷著依戀和激憤的心情,回到了曲阜老家。
孔尚任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回到曲阜的。這年他56歲,從此以後,他一直住在石門山中,重又過起了隱居的生活。
家居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遇上了天災,農田歉收,又因他長期耽於吟詩,回鄉後也往往到處遊山玩水,即使薄有積蓄,二三年過後,日子就愈來愈緊迫了。他一次出遊濟寧回來,想到自己這個曾經受到皇帝眷顧的人,竟落到窮困得無法養活高壽的母親,感慨地吟詠道:
古槐門巷冷於秋,人看歸來季子裘。
對雨昏燈三鼓話,無柴濕灶一床愁。
耕耘未足供親膳,姓字偏勞記御舟。
盡道君王能造命,馮唐頭白未封侯。
他覺得有點滑稽!可是,事實畢竟是“君王能造命”。他不理解,使他平步青雲的是康熙,使他又從青雲之中跌落下來的也是康熙啊!他也不理解,在他未出山之前,貧寒的生活已習慣了,並不感到什麼;然而,18年的京官生涯,畢竟是比農民富裕舒適,現在再回頭過那種苦日子,他就感到受不了了。為了生計問題,他雖然年近花甲,還是要外出找點出路,以致在最後10年中,他四處奔波,竟冒著嚴寒酷暑,跑了許多地方。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孔尚任跋涉千里,赴真定府去找在北京結識的友人劉中柱。劉中柱,字雨峰。他曾是戶部曹郎,過往非常密切。劉中柱對《桃花扇》極欣賞,孔尚任被罷官時,劉中柱也曾贈詩送之,就寫得非常誠摯、深沉。孔尚任來真定,他留在府中,邀請郡僚,觀賞《桃花扇》的演出,著實地款待了一番。然而朋友處住的日子久了,也就索然無味了。孔尚任是那年五月到達真定的,七月便回程返鄉了。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秋,孔尚任又離家去山西,經太谷,到達平陽府。平陽知府劉棨,山東諸城人。大約過去曾相識,又是山東同鄉,劉棨修《平陽府志》要找一位大手筆協助,於是便邀請孔尚任來參與這項文事。貧窮難耐的孔尚任。也就只好屈身應邀前來。從這年冬天開始,到次年二月修成。《平陽府志》的撰修,雖然是代人捉刀,但總算是一種正當的事業,而且最後成書還署上了孔尚任的名字。可是,他後來的境遇就更可憐了。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春,天津詩人佟(左“王”+右“宏”)來游曲阜,拜訪了孔尚任,讀了《桃花扇》,大為讚賞,立即拿出了50兩銀子雇匠人開刻,從而為《桃花扇》流傳後世奠定了基礎。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孔尚任又離家南遊,走走停停,半年時間才到達武昌。這時的湖廣巡撫陳詵,原籍浙江海寧,與曲阜的“衍聖公府”有世誼,孔尚任也認識。他在湖廣巡撫府中過了新春佳節,便旋即北返。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孔尚任雖然已到了65歲的高齡,為生活所迫,仍不得不到萊州為知府陳謙做幕僚。他在萊州編修了將近一年的府志。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67歲的孔尚任,在寒冬臘月,頂風冒雪到淮南去造訪了一位與他神交已久,但卻從未見過面的朋友劉廷璣。
劉廷璣字玉衡,號在園,遼海人。孔尚任同他雖然沒有見過面,但從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以來,卻經常書信往來談論詩歌問題,非常投機,用劉廷璣的話說就是:“心心相印,言言莫逆。”孔尚任就是從這種“神交”來投奔劉廷璣處的。
在淮南,孔尚任受到劉廷璣的友好接待,兩人準備蒐集當代詩人的詩篇,編成一部詩叢,題曰《長留集》。在3個月的共同生活中,他們相互討論,先選定自己的詩作,由劉廷璣出資付梓刊行。原先構想的叢書由於工程繁巨,未能編成,所以《長留集》,便成了孔尚任詩集的書名。孔尚任在淮南,也為劉廷璣編成《葛莊分類詩鈔》。劉廷璣為了對孔尚任表示謝意,按照孔尚任的意思,在淮南選材命匠,建造了一座石門山亭。孔尚任帶著亭子的構件在詩集編成付梓之後,便心滿意足地回到了故鄉。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元宵節的那天,孔尚任病逝在他的石門山寓所中,享年7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