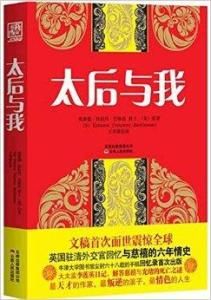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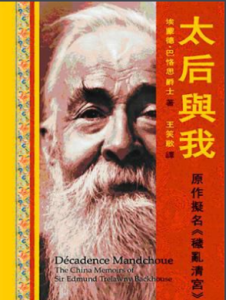 太后與我
太后與我1898年,巴恪思來到北京,由於精通漢語、蒙古語和滿語,很快成為《泰晤士報》以及英國外交部的翻譯。1903年,滿清政府擢升他為京師大學堂(後來成為北京大學)法律和文學教授;一年後成為英國外務處專員。
1910年巴恪思與《泰晤士報》記者布蘭德(J. O. P. Bland)合作,出版了《太后統治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一書,風靡世界。該書首次以全面的視野向讀者展示了清朝末年中國帝制上最後一位統治者慈禧太后的形象。
1913至1922年之間,巴恪思把大量珍貴的中文印刷書以及部分捲軸和手稿,都捐獻給牛津大學博多萊安(Bodleian)圖書館。
巴恪思於1944年1月辭世於北京,在臨終前一年,他完成了自傳體著作《太后與我》(DÉCADENCE MANDCHOUE)。在書中巴恪思以回憶錄的形式記錄了他在清朝末年寓居中國的生活。巴恪思身後,《太后與我》的手稿由其友人賀普利(R. Hoeppli)醫生轉交給牛津大學博多萊安圖書館保存至今。本書的出版是該手稿塵封68年之後首見天日。
巴恪思一生中稱自己不但見過許多赫赫有名的文學和政治人物,而且曾與他們同床共枕。他記述了他與不少名人的性交往,其描寫可說細緻入微,包括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保羅·魏爾倫(Paul Verlaine)以及索爾茲伯里(Salisbury)首相 。他所披露的曖昧關係幾乎都是同性戀,只除了在本書中披露的一人例外,而此人竟是石破天驚的大人物:中國一代專制統治者慈禧皇太后。
編輯推薦
《太后與我》:文稿首次面世震驚全球,英國駐清外交官回憶與慈禧的六年情史,牛津大學圖書館塵封六十八載的手稿回憶錄首次出版,大太監李蓮英日記,解答慈禧與光緒的死亡之謎,最天才的作家,最叛逆的浪子,最情色的人生。
媒體推薦
以我之見,任何人細讀過此書,都不會為如下事實感到吃驚:在芸芸老少浪子之中,吾之放蕩無人可敵。
——埃蒙德礠拉內巴恪思爵士 1943年
這不是純粹的情色書,除了其中的轟動效應之外,它還有文學方面的意義。他這本最後的著作,是對清朝的頌歌;是寫給一個逝去時代的性愛情書。我本人並不認為此書在編造事實,即使是,也是一個淵博的語言天才花了無數心血寫出的一部令人驚嘆的歷史小說。
—— 英文版編輯 Derek Sandhaus 2010年
以譯者之見,此種黍離之悲,正是本書與《金瓶梅》神似之處,亦是本書的精華所在。雖然情色滿眼、真假莫辨會影響世人對於此書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太后與我》就具備了長久的價值。
——中文版譯者王笑歌2009年
《太后與我》收錄了20章內容,描寫清朝宮廷的見聞以及與此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人物。慈禧太后是關注焦點;作者在大多數場景中都親臨其中,但只有極少數有其他人證明。整本書出色地刻畫了一個行將就木的王朝。從歷史學家的觀點看,最重要的一節莫過於已經提到的皇帝和太后之死。
——R. 賀普利 (R. Hoeppli)1945年
圖書目錄
出版前言
譯者序
中文版說明
* * *
致桂花吾卿
作者誓言
· · · · · · (更多)
出版前言
譯者序
中文版說明
致桂花吾卿
作者誓言
題記
第一章 京城插曲: 桂花
第二章 一個時代的開始
第三章榮祿大人
第四章頤和園夜曲:麥瑟琳娜的遊憩時光
第五章 眾位太監
第六章 浴室里的不速之客
第七章 秘會桑樹下
第八章 吸血鬼親王
第九章 天堂之火,愛侶之厄
第十章 現實中的「密室」
第十一章 危機一發
第十二章 術士之能
第十三章 處置匿名信
第十四章 魔鬼伏身的太監
第十五章白雲觀
第十六章 太后最後的秋日野餐
第十七章 他們殞命之時
第十八章 被玷污的陵墓
第十九章 追憶舊日榮光
賀普利1946年編輯後記
太后形象
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紅的無襯裡袍子,繡著代表皇后的鳳凰和象徵長壽的仙鶴圖案,外罩同色的羅紗罩裙,印著一束蘭花。外穿一件繡著“壽”字的古銅色馬甲,配了一根色澤華貴的珍珠項鍊。她的手上戴了許多戒指,其中一隻翡翠紅寶石戒指尤其可愛······。還有一顆碩大的黑珍珠,嵌在鋁框中,和她中指上戴的一枚罕見的粉紅鑽石相映生輝。應著當時的時尚,她蓄了指甲,其中兩隻戴了金的護套,長三寸有餘。她腕上有數個玉鐲,每一隻都精美稀有。······太后的臉上敷了厚厚的粉,但沒有搽胭脂······。她坐在一張紅漆矮凳上;她告訴我她和她深為欽佩的維多利亞女王身高相同(大約四英尺十一寸)。她顯得比實際身高高得多,因為她的秀髮盤成當時滿族流行的式樣,用厚紙撐起框架,上面復蓋綢緞,基座是皮製的,高達數寸。腳下穿著所謂的“花盆底鞋”,有個木製的細跟,大約四寸高。······老佛爺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位親切、溫和的老夫人,······。然而,她講話之時若敘及麻煩的人或事,眼中表情有時會徹底改變,令人迷惑恐懼。
名家書評
《太后與我》出版:70歲慈禧性愛觀念“百無禁忌”
李銀河 □學者,北京
圍繞《太后與我》這本書的主要爭論集中在它究竟是真實還是虛構的這一問題上。如果說它是作者的親歷,其史料價值是無與倫比的;如果說它只是作者的虛構,那就毫無史料價值,只能把它當小說來看。
由於作者是一位混跡於清末貴族生活中的人,即使我們把他的文字只當文學虛構來看,其中所反映出來的清末貴族生活氛圍應當說還是很傳神、很有趣的。尤其因為作者特殊的性取向(同性戀和虐戀),對他生活的那個時期社會的性氛圍、性活動和性規範除了常規的性關係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觀察和描寫,顯得更加豐富、多元。
書中所寫的關於同性戀的內容,既有世俗社會中同性戀男妓的活動,又有宮中太監的同性戀類性活動,寫得相當翔實可信,比如當時同性戀類買春活動的嫖資細節,以及對活動的詳盡描寫。史家有一種說法,解釋清末同性戀類性交易的興盛:由於當時政府禁止官員嫖娼,所以不少官員轉向少年,大城市中出現了很多相公堂子,以及被叫做“相公”、“像姑”的男妓。社會學界的老前輩潘光旦先生在相關著作中亦有提及。由此可見,作者對同性戀嫖娼行為的描寫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由於作者有虐戀傾向,書中對當時性服務行業中的虐戀類服務也有詳盡描述。比如性鞭笞及其價格等等。
書中有一章專門寫獸交,其中涉及多種動物,包括狗、鴨、鵝、猴、牛、羊、狐狸等等。比較值得關注的是人們對獸交的態度和規範。從書中的描述看,當時的人們對此類活動視為尋常事,並無任何焦慮感或負疚感。
筆墨最重的當然還是作者與太后的性關係,涉及多種行為規範:
首先是君臣關係。男性皇帝有三宮六院,名正言順地享受一夫多妻制,得到的全是正面評價。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女性,性行為規範又該如何?顯然要尷尬扭曲得多。民間對武則天早有種種負面議論,比如驢頭太子之類的醜惡傳聞,暗指女皇與動物通姦。這是男權社會對男女兩性的雙重標準所致。從書中看,既然皇帝能有很多女人,太后也可以有很多男人。在歷史真實中,慈禧恐怕真的並不是守身如玉的。
其次是年齡規範。作者與太后交往時是30多歲,太后已是70歲上下。在這種年紀還保持旺盛性慾,應當說是比較驚人的,但是從性學角度看,並非全無可能。按照兩性交往的一般年齡規範,年輕的作者是相當屈辱的。正是從這點上看,書中所寫可能是真事。換言之,僅從年齡規範上看,作者把這些寫出來,並沒有給自己貼金增色,反而是自爆其醜。
再次是性行為規範。從書中所涉及的各種細節,可以看出,太后的性觀念是百無禁忌的,絕不會把某類性行為歸為正確,某類歸為錯誤。對於身體的各種部位、性交的各種方式全都視為“快感的享用”,毫無褒貶。她雖然是個異性戀者,可是對於宮人太監的同性戀、虐戀、獸戀之類的行為,均採取一種好奇的旁觀態度,不聞不問,放任自流。恰恰像福柯有次所說,東方國家都有各自的性愛藝術,唯獨我們西方有的是事事要分出對錯的性科學。
總之,在我看來,《太后與我》這本書即使只是虛構的作品,它對於想了解彼時彼地的性風俗、性觀念以及一般百姓和社會上層人士的性活動狀況的人來說,還是有一定價值的。這就是這本書除史料價值、文學價值之外的性學價值。
百年奇書《太后與我》由已去世69年的英國埃蒙德·巴恪斯爵士撰寫,該書以自傳體回憶錄形式詳盡敘述了作者寓居北京期間與慈禧之間長達4年的性愛關係。該書中文簡體版今年1月國內上市後,引發了諸多爭議。是真實歷史還是意淫故事?據了解,該書的海外著作權人晏格文上世紀70年代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找到了這本書的手稿。記者近日通過出版方,對率先在海外出版本書的英國著作權人晏格文先生進行了郵件採訪。
晏格文先生本名Graham,中文名字中“晏”姓來自於他在香港時的粵語啟蒙老師的姓,“格文”則是由相識於1997年至今仍保持聯繫的金庸先生起的。他曾做過新聞編輯和記者,還是一名作家,翻譯家,他翻譯過金庸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現長居上海。他對中國歷史了解頗深,國語和廣東話都十分流利。他還嘗試詞曲創作,目前已成功發行了兩張自己操刀的唱片。
記者: 你是怎么碰到《太后與我》這個書稿的?
晏格文:我第一次聽到有這樣一本書是在20世紀70年代,接著又花了許多年去找這本書。最後,我終於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找到了這本書的手稿。手稿本身很亂,存有三個版本。版本之間在許多地方存在不一致,而且手稿也不完整。我們整整花了兩年的時間準備手稿的出版。
記者: 為什麼要翻譯這本書?
晏格文:從今天21世紀人的視角來看這本書,我們只能說我們無法判斷它的真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指巴恪斯)是絕對有機會和有條件認識他所提到的那些人,也絕對有可能親身經歷他所提到的那些事情。本書確實存在極大的爭議性。這也是唯一一本以第一人稱描述的晚清歷史。如果這個人能夠去虛構整個故事的話,那么最後的這部作品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富有想像力的天才之作了。
記者:關於本書描述的歷史事實真偽,特別是作者自稱是慈禧太后的異國情人,你是否相信?
晏格文:我無法證明巴恪斯在撒謊。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像他這樣一個能說流利的漢語和滿語的外國人是比較容易進入清朝皇宮的。中國的帝王經常用性作為展示他們權力的方式,當然,慈禧也不例外。
記者:中國讀者痛斥或者排斥此書的人大有人在,作為一個出版人,你是否料到?
晏格文:如果說這本書有哪個部分是非常真實的描寫,那一定是關於性的描寫。我覺得這本書中對性的描寫非常有趣,而不是像有些人認為的那么噁心。不否認,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的。如果他們不想讀,那也挺好。我們期待這本書的出版會引發更大的討論、爭論和辯論。(據《揚子晚報》)
序言
相信本書的讀者會和譯者一樣,經歷下面的閱讀之旅:初則為其深度、廣度驚人的情色信息衝擊,感覺天翻地復,心、腦茫然;大浪涌過之後,留於心底的,卻是中國式的黍離之悲,它純粹而靈性,超越了沉重的肉身。
由此,冒著過譽的危險,譯者願意把《DM》稱為當代的《金瓶梅》。
下面分四個部分,講述譯者的所見所感。
一、名人之性愛
男男、男女性事,受虐、虐待,口部、肛部行事,人獸行事,形式豐富多彩,描寫明確直白,譯者估計,全本的《金瓶梅》也不過如此。乍見之下,實在震撼。
更加讓人驚嘆的是,這些性事、愛事的主角常常是中國歷史、外國歷史上的名人。
作者著墨最多的乃是慈禧太后。這位統治中國近五十年的人物,乃是此書的女主角。書中情色內容的大半,即是對於慈禧性生活的描寫。慈禧的搭檔,是林林總總的男性。與之相偕出鏡次數最多的,正是本書作者。此人系英國爵士、學者,一生中的大半時間工作、生活於京師(後改名為北平),1944年七十一歲時在此離世。作者曾為《泰晤士報》、北京大學、英國領事館工作,出版過學術和通俗著作,因此亦非無名之輩——雖然在此前,譯者並未聽說過此位人物。與作者“同情”諸人之中,最著名者,當是清廷重臣榮祿。雖然書中並無正面描寫,但是二人的精神、肉體之愛亦反覆被提及。
清室的幾位皇帝也各有特點。嘉慶喜好同性,橫死之時,正與男寵行事;同治出人風月場所,染上梅毒,不治身亡;光緒亦有同性之好。
因為本書作者的同性取向,男同的事例遂令人目不暇接。嘉慶、光緒故事尚屬耳聞,作者親歷的喜好同性或雙性的皇親國戚足有幾十位。宮中眾位太監,如李蓮英這樣名噪一時的人物,幾乎都樂於此道。作者並提及其他古代!當代的名人同好,如王爾德、米開朗基羅、蘇格拉底、愷撒、黎留塞主教、張勛等等的此類軼事,不一而足。
相形之下,除了作者與慈禧,男女之事反倒少見。不過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與其僕從約翰·布朗之戀)、法國總統福爾(與妓女行事時中風死去)、英國人赫德(曾長期擔任清朝的海關總稅務司)等等,也都是重磅人物。
與男女之事同樣數量不多,卻奇異得很多很多的,乃是人獸行事。樂於此道者,包括李蓮英等太監、某些與宣統皇帝同輩的貴族。人雖名氣不大,有此與常人迥異之能,連本書作者都感覺不適,譯者更是瞠目難言了。
如此種種,可以概括為名人的“月之暗面”。自然,這些人並非清心寡欲之善男信女,但是,人們此前對於他們的認知,總是局限於比如說慈禧的政治舉措、蘇格拉底的言辭思想。其中某些人、事,比如同治的非正常死亡、王爾德的同性之好,在坊間多有流傳,但只是涓涓細流,今日忽而成為汪洋大海,難免令人恍惚。讀者看慣了雖有圓缺、卻總歸是正面的月色,忽然被暗面籠罩,會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本書與《金瓶梅》情調有種種相似,這是最奪人耳目的一種。如所周知,《金瓶梅》作為情色作品的名氣實在太大,掩蓋了其傑出小說之名。讀者看到《DM》,第一印象恐怕也只會是上文所述名人之性愛。
不過,再震撼的景致供應過量之後,也難免令人疲勞。所幸,本書的性愛作為前景固然出彩,背景所展現的時代一樣頗有可觀之處。
二、清末人物、國政與風俗
清代末期既是多欲之秋,亦是多事之秋。本書敘及,慈禧一身所系,從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難,到宮廷起居、光緒的幽禁生活、光緒與慈禧之死、東陵被盜掘,無一事不引人注目,幾乎在在關涉重大——不僅是當事者的存歿悲喜,更是中國億萬小民命運改變的源頭。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層之利,在本書中或直接白描、或通過相關人物口述,為諸事提供了真切的細節、獨特的視角。
以光緒皇帝為例。此人一生,乃是慈禧威壓之下的傀儡,但畢竟是一國之君,行止值得關注。本書作者敘及兩次與他相見,時間不長,卻亦展現出其人性格。從光緒之言語、神態判斷,其確知本書作者與慈禧的暖昧關係,但是交談之間,光緒只是以“私下”、“秘密”等詞暗示,並不明言——應該是無此膽量——對於慈禧的命令,其唯唯諾諾之態難以掩飾,所以譯者有此推測。不用說,慈禧及其手下對於光緒非常輕蔑,李蓮英即曾在背後直呼“載湉”,本書作者也以“鄉下人”蔑稱之,他的同性取向,甚至是否有性能力,也是人們議論的焦點。在慈禧眼中,光緒更是無知兒童一般,不妨當面斥責、呼來喝去。矛盾的是,慈禧諸人完全認同皇權。他們心目之中,“當今皇上”無用,“皇上”之地位卻是至高無上。所以,慈禧對於光緒總是稱呼“皇上”,僅有一次,惱怒之下,“賤骨頭載湉”脫口而出。反觀光緒,其可憐自不必言,但其個性中的懦弱在本書作者筆下躍然紙上:在慈禧背後、面前,他一樣全無血性。慈禧手下的太監將其殺害,完全沒有心理負擔,也根本沒有遭遇抵抗。這個人物在本書中著墨不多,但是作者提供的細節符合人們對於其性格、命運的了解,又有新的內容,因而相當有價值。一斑想見全豹,可見本書作者除了有能力提供豐富的性信息,對於人情事態的描摹一樣細緻。
與政治高層同樣難為人知、卻又引人人勝的,是關乎天意、鬼魂的神秘事件。本書中有不小篇幅敘及水晶球占卜、扶乩、通靈、魔鬼附身等等,今人觀之,或許難以盡信,但是一百餘年之前,統治中國人的思想世界的,正是這些怪力亂神。
其他方面的人情風俗。比如打賞仆傭的例錢,比如市風開放因而少年時的榮祿與慈禧可以相偕趕集,等等,也為本書提供了背景的寬闊和縱深。
三、事實還是想像?
其實,在本文一開始,這個問題就應該提出。或許,讀者也會早早地懷有大大的問號:這些,是否真實?
作為私人寫作的歷史,本書中頗多記載與官方歷史所記錄者大相逕庭,讀者生疑,非常自然。以譯者所見,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師的同性戀盛況、慈禧的性生活、慈禧與光緒的死因。
本書之中,京師的同性戀愛及其交易蔚為大觀,涉及人物主要是梨園優伶、皇親國戚和宮中太監;慈禧性慾極其旺盛,因而男寵眾多,常常通宵雲雨。這兩方面,對於譯者——虛度三十餘歲,閱讀量在同齡人之中不算太小——而言,卻基本是聞所未聞。
為什麼會這樣?先說對於慈禧的認知。人們所知的慈禧,究竟是什麼樣子?看看下面的文字即可。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稱“西太后”、“那拉太后”。清成豐帝妃。滿族。葉赫那拉氏。1861年(成豐十一年)鹹豐帝死,子載淳六歲即位(年號同治),被尊為太后,徽號“慈禧”。殺輔政大臣垂簾聽政,鎮壓民眾起義,立光緒,採用洋務派政策,對外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破壞維新變法,利用義和團、對外宣戰,簽訂《辛丑條約》,“預備立憲”抵制資產階級革命。後病死。
這是權威的辭典《辭海》之1999年版對於斯人的描述。為節省篇幅,“殺輔政大臣”至“資產階級革命”部分系引者的概括。
這就是現代標準的宣傳、教育文字:描述、評價人物,著眼於“群體的人”,即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等方面的外在的行為、特徵,而對於“個體的人”,即人物之性情、心態、情愛等等全不措意。不可否認,辭典的形式限制了這些文字。然而,更大的限制顯然是當前歷史敘事的兩極分化:一極是學術化的嚴肅文字,另一極是娛樂化的荒誕遊戲。兼得兩極之利的作品並非沒有,卻如鳳毛麟角。像“慈禧及滿族貴族之性生活”這樣的題目,不適宜以學術文字講述,遂只能墮落為獵奇故事,完全喪失歷史價值。在兩種路線之外平實地討論歷史人物的性生活,反而成了不正常,這實在令人悲哀。同性戀話題雖然日見開禁,畢竟還未完全進入大眾認同的敘事,更是難得見到平實可靠的文字。本書所描寫者,在程度上給人過度之感,但是譯者缺乏可靠信息與之比照,因而無從確定其真偽,只好存疑。
慈禧與光緒的死因萬眾矚目,本書的說法明顯只是孤證。通常認為,二人均系病亡,慈禧之死因從未見到異議。近來的研究表明,光緒乃是死於急性砒霜中毒,但砒霜的來源並無定論。以此論之,本書只是一家之言。作者已逝,我們無法請其提供證明。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自行考證。譯者認為,無論是否事實,作者的描寫細節豐富、且保持了足夠的自省,已然具備了獨立的價值。
四、黍離之悲
黍離,字面意思是植物茂盛之狀。《詩經》某篇以此為名,據說是周人行經故國,見昔日之堂皇宮室盡已成廢墟,生滿黍稷,遂有人情世事無常之傷痛。
中國朝代興亡倏忽,轉眼物是人非、滄海桑田,如《三國演義》開篇詞所言: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中國人卻正是於此種無常之中,體味到深切的存在之感:以人之渺小,參天地之悠悠,會心在遠,才能超脫物我。
比如《金瓶梅》,艷名遠播,但是識者如袁宏道、魯迅見其“描摹世態,見其炎涼”,“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故將之歸為“世情書”。這就是透過三級之幕,洞悉黍離之悲。
以譯者之見,此種黍離之悲,正是本書與《金瓶梅》神似之處,亦是本書的精華所在。雖然情色滿眼、真假莫辨會影響世人對於此書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備了長久的價值。
比如第二章,慈禧將要出場,讀者正在企盼、想像,作者卻盪開一筆,寫道:“彼時她剛從東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後,她那安放在靈柩之中的聖體被扯出壽衣,完全赤裸,復以可怕的黑斑,頭髮蓬亂,雖細微處亦清晰可辨,暴露於陵前,任由‘庸眾’圍觀。”這幾句所描述的慘狀,在第十八章“被玷污的陵墓”之中通篇皆是。但是此處的幾十個字,比起那一章所有的文字更加黑暗。繁華逝去、尊榮不再,突然之間,讀者會感到,整個世界都失去了光明。
本章還有如此文字:“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紅的無襯裡袍子,繡著代表皇后的鳳凰和象徵長壽的仙鶴圖案;外罩同色的羅紗罩裙,印著一束蘭花。外穿一件繡著‘壽’字的古銅色馬甲,配了一根色澤華貴的珍珠項鍊。她手上戴了許多戒指,其中一隻翡翠紅寶石戒指尤其可愛,我猜是來自寧境街的式樣。”
明快燦爛的描寫之後,作者卻筆鋒一轉:“我怎能想到有一天會看到她乾癟的屍體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陽光下。即便是不朽的漢尼拔或愷撒,最終也是塵歸塵,土歸土。”
此處的悲涼更加濃重。生死本是人之常情,而在與慈禧相關的大量的性事細節展開之前,作者即以黍離之悲籠罩全局,令所有的享樂、高潮都存在於“色即是空”的陰影之下。如此筆調,使作者自己從第一人稱敘事的強烈的“在場感”之中抽離出來,既得近距離描摹之細緻,亦使其間炎涼無處可遁。
本書中更有一些文字滄桑沉痛,即使完全沒有語境,仍屬傑出。 斯人去矣,如雪化無痕,而我總是希望,他仍在世間,不再拘於促狹之生、男妓之身與嫖客之癖,自由自在。或許,他會偶爾想起,曾有一個異國青年,與他繾綣如許。“虛空的虛空”:或者如荷馬筆下的海倫所言:“並非儘是夢幻!”當靈魂化做肉體,與無可言喻的、無盡的、靈肉合一的狂喜融化在一起;如是種種,可能莫非蜃景與幻覺:靈魂受難、心愿成空,然而,畢竟也為浮生所系,縱是身化塵土,追思仍為之燦爛:“直至破曉,暗影飄逝”。(第一章)
如果沒有想像,記憶全無用處。想像是不可知論者對於永恆的真實頌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時光。這些關於過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讓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對生活的煎熬。“活過,愛過”:我復何言?(第九章)
這些思緒、這些文字,出自母語是英語的西人之手,令人驚嘆。由於語言、文化的隔膜,西人理解此中曲折,已屬不易。本書作者能以西文表述此中堂奧,殊可讚賞。
這恰好也是一個極妙的隱喻。孔子早就說過,禮失而求諸野。在學術化文字的嚴肅難近和娛樂化文字的荒誕無稽之間,有《DM》這樣的作品出現,譯者幸甚,讀者幸甚。
——中文版譯者 王笑歌
作者簡介
埃蒙德·特拉內·巴恪思男爵(SirEdmundTrelawnyBackhouse),1873年出生於英國約克郡的里奇蒙(Richmond),祖上是曾經顯赫的奎克(Quaker)家族,後就讀牛津大學。
1898年,巴恪思來到北京,由於精通漢語、蒙古語和滿語,很快成為《泰晤士報》以及英國外交部的翻譯。1903年,滿清政府擢升他為京師大學堂(後來成為北京大學)法律和文學教授;一年後成為英國外務處專員。
1910年巴恪思與《泰晤士報》記者布蘭德(J.O.P.Bland)合作,出版了《太后統治下的中國》(ChinaundertheEmpressDowager)一書,風靡世界。該書首次以全面的視野向讀者展示了清朝末年中國帝制上最後一位統治者慈禧太后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