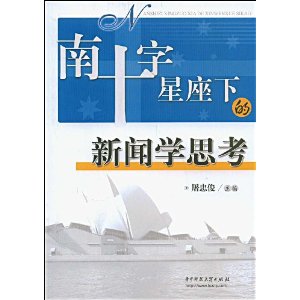圖書簡介
"幫助我們的中國同行在中國,傳播因其意識形態和信息功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自三十年前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新聞傳播領域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中國傳媒的市場化。與從前比較,當今的傳媒更加迎合市場的需求。改革開放使得被中國教育部列為一級學科的新聞傳播學的教育持續發生變化。教育者和研究人員在自行探索的同時,嘗試了解世界上該領域的最新進展。不幸的是,對他們來說,接觸西方的相關知識是頗有難度的。
難以接觸相關知識導致中國新聞傳播研究存在若干問題。中國的新聞傳播研究經常被指責有如下問題不是偶然的:不了解相關文獻,缺乏實證,好爭論,方法使用不到位,描述性內容過多。這些問題的存在說明中國新聞傳播界需要大量吸收該領域內的最新知識。人們當中求知慾最強的是對世界更加好奇、更善於接受新鮮思想的青年教師和博士生。雖然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精通英語,但是他們接觸國外出版物的機會卻是有限的。西方出版的圖書和期刊的費用對於中國的教師、學生,甚至一些圖書館都高昂得令人生畏。儘可能接觸這些出版物對他們是很費周折的。就算有足夠的資金和信息,中國人向海外購書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任何一位和中國的青年教師以及研究生交談過的國外學者都會感受到他們強烈的需要:幫助他們解決在接觸這些資源時出現的經濟和體制上的困難。收入本書的一系列文章最初發表在2000年至2005年出版的《澳大利亞新聞研究》上,這些文章對於消除中國新聞學者和學生與澳大利亞新聞教育界的工作者們在新聞傳播領域的知識差異能起到一定作用。選擇和翻譯收入本書的文章的工作是由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的部分師生承擔的。
目錄
"新聞業處於黃金時代嗎?(1)
揭示鴻溝的報導:社群服務報刊的批判性訓導作用(9)
體驗廣播:培訓、教育與社區電台(20)
組織事務(38)
記者個人情感的表露(53)
援助人員、情報蒐集和媒體自我審查機制(62)
審判前報導:導致陪審團的判決偏頗(80)
敏感還是漠視?涉齡報導的準則(99)
愛滋病報導二十年(108)
三城記——約旦、阿聯、埃及的媒體城(124)
後記(141)
南十字星座下的新聞學思考目錄16,25,30"
序言
2004年底,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組團赴澳大利亞參加在布里斯班市的昆士蘭大學召開的以“亞太地區智慧財產權、傳播與公共領域(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Communication and thePublic Domain in the Asia-Pacmc Region)”為主題的智慧財產權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ect ual Property Rights)。會議期間,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與昆士蘭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就雙方教學、科研、學術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問題進行了專題會商。在會商過程中,我提出向中國讀者譯介澳大利亞新聞傳播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動議,當即得到昆士蘭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簡·舍萬斯(Jan Servaes)教授的熱情回應。他慨然允諾授權我院在中國翻譯出版由他們編輯出版的《澳大利亞新聞學刊》(Australian Stu diesin Journalism)上的所有學術論文,並在會上及會後陸續向我們贈送了《澳大利亞新聞學刊》的樣書,為我們的譯介工作提供了方便。
後記
2005年,參加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市的昆士蘭大學召開的以“亞太地區智慧財產權、傳播與公共領域”為主題的智慧財產權國際會議回國後,我們即組織2004.級的博士研究生(按照本書對論文的編輯排序,他們是:何志武、余紅、佟春玉、黃蓉、劉永昶、滕朋、殷旎、高海波、張振亭)翻譯在《澳大利亞新聞學刊》上選定的論文,把它作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與昆士蘭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教學、科研、學術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的一個重要內容。為了保證譯文質量,譯文初稿由外語專業畢業的李萌(我院2005級博士生)對照原文認真校對,並重譯了其中一篇論文;校對後的譯文由主編者進行審定,除了訂正一些有關原文涉及的各專業、文化背景、歷史及時事知識方面的誤譯外,對中文的表達亦作了潤飾。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好的譯文的價值不亞於自行寫作的論文的價值。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了“信達雅”的譯文標準。他根據自己的翻譯體驗,說道:“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易日:‘修辭立誠’,子日:‘辭達而已’。又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
書摘
南斯拉夫 插圖
插圖援助人員的困境引起澳大利亞媒體的大量關注。比如,全國性大報《澳大利亞人》的一項調查顯示,從4月10日事件曝光起,普拉特和華萊士以及圍繞他們展開的營救努力,占據18天頭版中的6個;而且,有3天的社論主題集中在此事件上(McCarthy,1999)。澳大利亞國內報導的基調可以從4月13日的一篇社論中看出來,當時他們剛剛被捕不久。澳大利亞,歐洲及美國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澳大利亞在新聞學教育前景的討論上是落後的。相較於美國和歐洲,澳大利亞仍然努力在一系列彼此矛盾的新聞學教育主張間尋找平衡,諸如:為培養新聞記者應提供職業教育還是大學教育(如果其中一種是合適的,該培養到什麼程度,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是順應學生的自然天性還是強調養成訓練,乾新聞這一行是一種藝術還是一種手藝,要搞專才教育還是通才教育,該看重理論還是著眼實踐,重在讓學生搞作品製作還是對製作作品進行反思(關於此類討論的文獻綜述見Rakhonen, 2007)。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雖然新聞學教育有各自的獨特背景,關於平衡問題的討論,一般傾向於“還是”後面的主張(Lavender, Tufte and Lemish, 2004; Leung, Kenny and Lee, 2007; Huysmans and van der Linden, 1991)。在大西洋兩岸,人們逐漸注意到新聞學教育的共同趨勢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當前,主要由哥倫比亞大學校長Lee Bollinger在美國發起新一輪對新聞學教育的審視。他在2002年年中為該校聲譽卓著的新聞學院遴選院長。Lee Bollinger發現:“人們對現代新聞學院的構想差異很大。”於是,他組織一個特別工作小組來審視新聞學教育的未來圖景。經過從2002年10月到2003年3月的6次會商,這個特別工作小組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優秀大學設定的優秀新聞學院應該與新聞業界保持一定距離。新聞學院的教師應由頂尖的新聞業從業人員組成,他們應該與大學裡其他教師一樣承擔教學和科研任務。在科研工作中,他們要積極探索新聞業最大限度的發展可能性,對新聞業進行反思,關注業界重要事件,研究解決問題的途徑,將自己的發現與學生、業界、利益相關的公眾進行溝通、交流。”新聞學院要用獨立的視角來審視新聞業及社會,如同新聞業對整個社會進行審視一樣。此外,新聞學院還是新聞業忠誠的評論者。在持續反思的學術氛圍中培養的思維習慣必然貫穿整個教育過程,導致職業生涯的某些方面被強調而某些方面被擱置或摒棄。一所好的大學應該能為專業學院提供相關領域的人才實行知識與智力的交流,而專業學院也會為大學的其他部門提供知識與專業上的支持。理想的情況是,專業學院在教學與研究方面與大學結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Bollinger,2003)。
另外,一份歐洲新聞中心的調查(Bierhoff and Schmidt, 1997)以及2001年一次針對美國高校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教育狀況的研討會(Brynildssen,2002;Cohen, 2001)都也得出相同的結論。這些結論可表述如下:
(1) 新聞學教育要為公眾提供服務,而不是僅僅面向業界。
(2) 新聞學教育要迎接經濟、技術、文化和社會的現實所帶來的各種挑戰。
(3) 新聞學教育要有多樣性、包容性,兼具全球性與本地性。
第一個問題關注的是新聞學教育主要為誰服務。與“遵從業界需要”,甚至有時“引導業界的需要”的研究範式(這是澳大利亞新聞學教育的主要研究範式)不同,歐美學者倒置新聞學教育服務對象的金字塔,將人數比重最大的公眾——新聞產品的讀者和閱聽人作為最重要的服務對象。從前的新聞學教育研究不是被動地回響業界就是未雨綢繆地引導業界,這種研究趨勢已被更多的客群研究取代。在未來的信息和知識社會裡,新聞記者必須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Breit and Servaes, 2005; Charron, Chica and Hamilton, 1999)。為了復歸“實踐”這一新聞核心價值,新聞記者們可能必須不去聽從行銷和公關工作者提供的煽動性十足的建議(Breit,2004;Louw, 2005)。
相較於傳統的職業技能訓練,人們更偏重於背景分析(只有將新聞業從歷史、技術、文化、法律和經濟的角度進行定位和研究才能完成這一分析)。Tom JacobsonTom Jacobson是美國天普大學傳播與戲劇學院的教授。——譯者注在一次研討會上說: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導致很多新聞編輯室的“企業殖民地化”以及令人擔憂的“信息娛樂化”潮流的出現。他還警告說,如果這個潮流繼續下去,新聞學教育者們對新聞學核心知識的討論將失去意義,民主制度將失去作為第四等級而存在的新聞界(Cohen,2001:20)。
隨著信息及傳播技術的影響日益擴大,媒介市場解除管制,媒介產品、服務的文化全球化/地方化,人們開始重新評估現有的新聞學教學安排。新聞學教育不得不打破傳統的國家框架,開始走國際化路線。特別是澳大利亞,因為經濟上越來越倚重付全額學費的國際學生,它將面對“如何擺脫新聞學教育中的民族性的陳腐觀念”,以及“如何改變對媒介和新聞的帶民族偏見的程式化理解”等問題(holm,1997:48)。未來新聞學教育者將面對的挑戰是:更多的多文化、國際性的“真實”學習體驗,更多的創新性、批判性反思,更專注於解決問題,更多的信息、知識的社會溝通及合作。這些挑戰將極大地影響新聞學的教與學。與之適應的教學方法將教師的角色由信息傳播者轉變為學習促進者,即幫助學生主動研讀相關材料以建構自己的理解力(Blurton,1999:49)。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此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它為開發中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出版了一些新聞學教育課程的模板材料,直接採用這些模板或者對其作出調整對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新聞教育會有所助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這一做法是有趣的並且可能是行之有效的(see UNESCO,2007)。
上述觀點可以總結為“社會參與式的傳播與新聞研究”模型(圖1)。該模型改編自David Perry(1996:8)的文章。模型中的四部分分別代表公眾對(大眾)傳播的關注、相關研究、教育及客群行為。它們形成一個會受外來因素(比如媒介產業)影響的相互依賴的開放的動態系統。“模型所代表的整個過程是沒有終結的。相反地,任何一個要素起變化都會影響其他的要素……整個模型是動態的。當其他成分有改動,或者外部情況有變化,比如大眾傳播的形式或者內容出現變化,各要素就可能處於持續變化的狀態中……究其實質,因為世界是時刻變化的,那么對社會的探究會無終結地持續下去。”(Perry,1996:9)
上述的社會參與式的傳播與新聞研究觀點十分合乎廣義的“致力於發展與社會變革的傳播”(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CDSC)傳統。我簡單解釋一下一些最重要的理論原理,CDSC傳統是以它們為基礎的(更多細節請見Servaes, 1999 and 2007)。
CDSC的研究和教學主要發端於這樣的觀念:所有形式的傳播在文化上都植根於社會變革過程。
Jef Verhoeven (1986:19)給出“社會變革”的一般定義。他定義社會變革為“結構化社會行為的劇變及/或角色承擔者、群體、集體文化的劇變”。這個一般的定義可以在某些標準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說明,比如社會變革的範圍(微觀、中觀、巨觀),發生的時間間隔(短期或長期),變革過程的等級(演變或革命)、方向(進步或倒退)、內容(社會文化的、心理的、組織的)以及評價社會變革是平靜的或是衝擊性的。
在這個語境中,“發展”可以被稱之為社會變革的一種特別形式。人們常常認為“發展”可以大致等同於分層次的完成被明確界定的階段,這些階段將通向令所有人滿意的普遍的終極社會。這個模式效法的實際上是西方標準。這樣的概念往往暗含一個價值判斷,它涉及一個具體的目標群體(誰需要被發展)以及目的(發展什麼)。這就是“發展”這個術語總是與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相提並論的原因。但是,這樣做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整個世界都在發展。因此,關於發展或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傳播的議題或討論並不局限於針對第三世界國家。
社會變革也不是僅著重於某一方向的,它不僅涵蓋發生在西方的社會文化變革過程,也涵蓋其他國家的變革過程。比如,全球化與地方化,婦女解放,日常生活中的種族偏見,某些理念意識、政治經濟解放和經濟自由化。雖然社會學家主要關注計畫的、刻意為之的社會變革,但是社會變革經常是無意中發生的。計畫的、刻意為之的社會變革有明確的目的,這些目的和特定的情況相關,因此不具備普適性。在這些經過策劃的社會文化變革過程中,傳播已成為關鍵字。
人類所有的行動都基於觀念、知識和經驗的交流。人們通過語言來溝通。語言上的誤解大部分不是因為語言能力的缺乏,而是因為溝通雙方思維方式和文化模式的不同。我們可以“聽見”對方,但是不能“理解”對方。這些誤解可能是來自語言的,也可能來自非語言的緣故。因為有了這些誤解,我們就不能達成自己的目標。有效傳播的特點是根據接收信息的對象來調整信息。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當傳遞的信息符合接收者的文化,傳播才是有效的。為了達到有效傳播的目的,一個重要的條件是溝通雙方必須知道並且理解對方的文化。只有當雙方的交往有質量保證並且基於真實性的承諾時,這樣的理解才能實現。
國際傳播是跨國界的數據、信息、知識的交流。對跨文化傳播來說,其社會用途和傳播雙方的社會文化背景都很重要。除了文字元號的含義,語言本身也是與文化相關的。在這種語境下定義文化並不是易事。文化包括特定生活方式的物質方面和非物質方面,它通過社會化過程以及意識形態的工具(學校、媒體、教堂……)向社會成員傳遞和得到確認。文化不僅僅關乎像善與惡、美與醜的價值或判斷,而且也與我們的飲食、居住、穿著方式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可以被描述為一種社會背景,在這個社會背景里,特定的參照系可以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或固化為指導和安排人們互動和溝通的制度化形態。這樣的參照系可以通過四種實證維度來區分:世界觀、價值體系、符號性的表達方式和社會文化的組織性制度架構。這個架構使上述種種各就其位。
從這個方面來說,各種制度(比如說新聞制度)發揮著關鍵作用。制度在社會認可的基礎上,將行動的狀態以基本標準化和不證自明的慣例形式固定下來,制度可以起到限制負面因素或者解放正面因素的作用。它因其“特性”而與眾不同。
這種解讀文化的視角隱含一個動態的特徵。文化永遠不會被“完結”,它總是處於“發展”的狀態。而且,人們在塑造社會存在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大部分是無意識地)根據他們文化的價值觀和提供的選項做出特定的選擇。因此,社會現實可以被看做是一種其確立和形成都源於特定價值觀的現實,一種價值體系和社會體系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現實。由於不同環境下不同文化共同體發展的需求和價值觀不同,它們就呈現不同的特性。文化的“特性”源自這樣一個事實:文化是以擁有共同的世界觀和民族精神的制度網路為基礎的。不同文化的“特性”是不同的。
換言之,必須根據其自身邏輯結構來分析一種文化。確切地說,每種文化都是根據其自身邏輯運作的。只有相關各方理解這樣的邏輯基礎並且以平等的心態予以接受,跨文化傳播才能成功。與所有的社會過程一樣,文化不是一個純粹的理性過程,不能預先加以安排。所以,文化應被視作相互聯繫、互動的人群混合行動的不能預期的結果。

一個文化學派的觀點和一個解釋性的方法
 在過去的五十年里,對社會變革以及在社會變革中傳播和文化的角色的看法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期間,我們看到了三種範式或者說觀點的演變:現代化範式、依附性範式以及多樣性範式(Servaes, 1999)。這些範式是互補的而不是彼此替代的。它們形成反思致力於發展和社會變革的傳播的基礎。對傳者與受者關係的片面想法已被扭轉。很多人意識到客群是積極的,理論家也開始意識到科學不是價值中立的。
這些一般性觀點為其他觀點所補充,比如所謂的批判理論和其拉美變體,它們都強調改變現存社會結構的必要。這一傳播研究的風潮批判地審視社會,並且把其分析與媒介效果相聯繫。我們也可以提一下巴西的Paolo Freire,他創造了意識提升方法(consciousness?raising method),這個方法更多涉及參與和對話。
對現代化範式和依附性範式的批評導致研究社會變革與傳播的新觀點的產生。對社會變革觀點的轉變主要體現為兩種趨勢:第一,人們發現並且承認理論、研究、社會結構從來都不是價值中立的;第二,對客群的看法在改變,人們不再被視為消極、易受影響的生物,而是被看做動態過程中的積極個體。發展不能被強加,它應該是內生的。坦尚尼亞前總統Julius Nyerere (1973:60)曾精闢地指出:“人是不能被發展的,他們只能自我發展。別人可以給某人蓋一所房子,但不能給他作為‘人’的驕傲與自信。人必須通過自己的活動和決定,以及在自己生活的社會作為平等個體的充分參與來獲得驕傲與自信。”
多樣性範式認為,積極的客群找回自我的背景是重要的。這也意味著通用的發展模式是不存在的。發展是針對特定社會的獨特歷程,它基於以下原則:對基本需求的滿足;自發的審視其文化(內生性);利用自己的潛力(自力更生);生態良性循環的發展;追求參與式民主以及結構性轉變(可持續性發展)。
特別是,這個方法重新評估了人際傳播。與早期的範式不同,這個方法更重視參與傳播和關注地方文化,注重互動性及參與性的社區媒體。
以多樣性範式和Freire觀點為基礎,參與和對話的作用在致力於社會變革的傳播過程中越來越重要。直接與參與及對話關聯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以及對人類的積極看法。它主要強調,在致力於社會變革的傳播中,人不被視為消極因素或其行為被上方力量直接影響的撞球(“自上而下”)。人可以積極地為他們的日常生活、社會環境和媒體環境賦予相關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這個視角是以科學哲學的解釋進路為基礎的。
我們可以找到“致力於社會變革的傳播”與其他社會科學(特別是人類學)之間普遍的、明顯的聯繫。與人類學的聯繫不僅僅存在於理論方法和專題的相關性,還體現在使用質化研究方法和三角測度法的水平上。三角測度法指的是同時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參與、“自下而上”的方法和對人類積極的觀點都是人類學中非常熟悉的概念。
另外,作為人類學的主要研究領域,文化觀念有其重要地位。我們認為,參與和文化是文化學派方法裡緊密相連的兩個概念。如果不承認文化差異以及沒有對雙方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參與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我們在談到致力於社會變革的傳播時,既可以使用解釋性的觀點,也可以使用文化學派的觀點。
現代化範式和依附範式的基礎是政策選擇以經濟和政治為導向,多樣性範式則與此有別,它專注於這樣的觀念:沒有通用、普遍有效的發展策略,發展必須被視為一個整體的、多維的、辯證的、每個社會都有所不同的過程。
上述說法同樣適用於為社會變革制定的政策和規劃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和規劃者面對若干重要選擇:不僅僅是關於傳播和其解決方案的問題,也包括對組織和實施那些政策和規劃的方法的判斷。不同的問題和情況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法。再次強調,沒有永遠的、在每個地方都能使用的普適方法。這就是為什麼在今天,同理論的形成一樣,政策和規劃也在尋找一種混合的方法,這個方法以不同的理論為基礎,融合了不同的規劃方法:“致力於發展的傳播沒有特定的‘任務’,而是有很多的任務。” (Middleton & Wedemeyer, 1985:33)
除了考慮這些基礎的、不能缺少的事項,政策制定者和規劃者還需要一個更通用的概念和操作的框架。事實上,我們要深入探討的不僅是理論,還有以實踐為導向的學科,以及“為給政策制定者提供實用的、以行動為導向的、解決問題的建議而進行的研究或分析基本社會問題的過程” (Majchrzak, 1984:12)。在這個定義中,我們認為有兩個方面與多樣性範式的理論命題緊密相關:對重要的、基本的社會問題的關注;研究建議的可實踐性、可操作性和行動導向性。
結論:“致力於發展與社會變革的傳播”的基本前提
作為結論,我們認為:不同的教學和研究,也就是說,針對不同的理論、方法、媒介、範圍,都必須具備下列的共同價值觀和出發點。CDSC的連貫性體現在若干共同的、根本的前提中。這些前提、價值觀和出發點如下。
運用文化學派的觀點。這樣的觀點使我們給社會變革中的傳播與文化以特別注意。將文化置於研究視域的中心位置,其他傳統社會科學,如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和文化研究就會對“致力於發展與社會變革的傳播”的研究領域作出貢獻。
運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和解釋性的觀點。參與、對話和對人類的積極觀點是極為重要的。要高度推崇對特定情勢和本體性的唯一性的尊重和欣賞。
運用整合的觀點和理論。在“致力於發展與社會變革的傳播”領域,重要的是研究中選擇的方法必須與使用的理論觀點緊密聯繫。這也意味著重視方法的開放性、多樣性和彈性。在實踐中,就是注意使用三角測度法和偏重於質化研究方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完全排除量化研究方法。
顯示相互理解並重視正式和非正式的跨文化訓練和教學。只有當不同(子)文化中的成員不僅傾聽對方,而且理解對方的時候,才會有大度、領悟、包容及尊重。相互的理解是社會變革的先決條件。為防止所有形式的錯誤傳播,應該重視正式和非正式的跨文化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