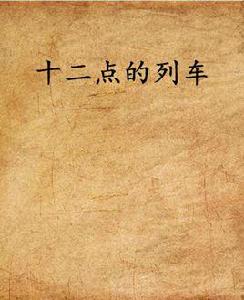作者
埃及 荒誕派作家賽義德·舒爾巴吉
正文
正午時分,時鐘照例敲了12下。火車慢慢啟動。就在這時,麥斯歐德迅速跳上最後一節車廂。他已經累得氣喘吁吁。車廂里擠滿了乘客,一個空位子也沒有,連過道上都站滿了人。這是一節三等車廂。他決心為自己找一個座位,哪怕一寸寬的地方也行,眼下他已經精疲力竭,不能這樣站一路,他知道,這次旅途是漫長而勞累的。他看見有個座位上放著一隻手提包,想先去搶座,免得給別人占去。他從站在過道上的人群中用肩頭艱難地為自己開路,終於走到那座位前。
他伸手將包拎起,問也沒問一聲就將它塞到座位地下。坐在他對面的一位姑娘大聲嚷起來,問他要乾什麼?他冷冷地反問道:
“這是你的提包嗎?”
“是我的!”
“那好,位子是給人做的,不是放提包的!”
說完他便仰靠在座位上,帶點歉意地向那姑娘微笑。姑娘把臉轉到一邊,沒理他。
一會兒,檢票員來了。乘客們都拿出自己的車票。麥斯歐德買的是終點站的票,引起了姑娘的注意。她也是到終點站才下車。這么說,他倆是同伴了,他將和她一起坐到終點站……噢,要改變改變對他的態度才行。姑娘以女人的眼光把麥斯歐德周身上下偷偷地打量了一番:他是一個不滿30歲的青年,臉上還沒有皺紋,鼻子和耳朵顯得有點大,棕色皮膚;從穿著上看,是個從鄉下來的人,領帶象根繩索一樣套在脖子上,更可笑的是領帶是藍色的,西服卻是棕色的。
就在這時,麥斯歐德也用男人的眼光,把她上下巡視了一番:她是一個24、5歲的美麗的姑娘,皮膚白皙細嫩,長著一對藍藍的大眼睛;穿著入時,但並不昂貴。她的目光和行動都說明她對自己十分欣賞,看來她是高傲的 ……她實在長得很漂亮,不能使人對她不在意或不去看她。他在想能用什麼辦法吸引她……他掏出煙盒,點燃一支煙,一邊抽一邊卻在想著她。她也不時偷眼看他,一會兒,煙霧嗆入她的鼻子,她一邊用手扇開煙霧,一邊使勁咳嗽。他趕忙把煙熄滅,並向她致歉。她面帶慍色地大聲指責他,要他注意周圍的人,火車上不能只顧自己嗜好,不顧旁人。她說話的方式使他感到惱火,便挑釁地回答道:要那么說,那他還要抽,愛怎么抽就怎么抽,別人愛怎么講就怎么講……他重新點燃一支煙,並有意地把煙霧朝姑娘方向噴去。儘管這樣,姑娘並沒有發怒,而且似乎並不在乎,她只是冷冷地看著他,目光中表現出對他這種小動作的鄙夷。他沒有抽完,就把煙掐滅了。
一小時後,火車在下一站停車。一些乘客下去了,同時也上來另外一些乘客。檢票員過來查票。他在一位乘客面前停下,要他下車,因為他的票已經到站。那位乘客回答說:
“不,先生!我買的是到終點的票!”
“所有乘客的票都是到終點站的。但每一站都必須有一些乘客要下去,給新上來的乘客騰出地方。”
“你為什麼偏偏要我下去呢?”
“這不是你的事,我說了,讓你下去你就得下去!”
“真是怪事,世界上沒有一列火車會發生這種事。乘客應該自由地上下車。”
“我們這次車上有自己的規定。你必須下去!”
“票呢?”
“作廢!”
“我說過,我的票沒有作廢,它是到終點站的。”
“對你來說,這一站就是終點站。”
“先生,我求你……希望你能理解我,或者我能理解你。”
“聽著,假如你再不下去,我就命令乘警把你從視窗扔下去。聽見了嗎?”
“等等,讓我再買一張票。”
“你的票已經結束,沒有新票賣給你。”
“我付錢……”
“一個乘客只有一張票。票一作廢,他就必須下去。明白嗎?請吧!”
“可是……”
“你是在有意浪費我的時間……”
檢票員對身後的四個乘警示意,讓他們把這個乘客從車窗扔出去。沒有一個乘客相信這是真的。大家都愣住了,直盯盯地望著那乘客和那些警察。說時遲,那時快,乘警像閃電般撲向那乘客,迅即抓住他把他從視窗扔了出去。一會兒,火車便開動了,離站台越來越遠,那乘客悽慘的呼喚聲漸漸消失。檢票員和乘警在乘客的驚懼中離開了車廂。
麥斯歐德看了看姑娘,禁不住和她攀談起來。姑娘由於剛才的驚恐,也希望有人和自己說說話,減輕一下剛才目睹的事給他造成的心理影響。麥事歐德說道:
“剛才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怎么啦?難道我們坐錯了車,這車上都是些魔鬼?”
“不知道!”
“可是,這事可能發生在我們任何人身上!”
“不知道!”
麥事歐德沖她喊道:
“難道你什麼也不知道?”
姑娘沉默了一會兒,搖搖頭,說:
“真的,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不敢相信剛才看見的是事實……”
“那讓我們忘掉它,用不著費心去思考。就把它看作一場噩夢,如今已經清醒……你叫什麼名字?”
“我的名字?”
“對,任何人都有名字的。”
“可這不是說名字的地方。”
“我們一塊在這可惡的火車上,這就至少應該使我們互相認識。”
“可我不了解你……”
“那好,讓我先作自我介紹吧,然後你再介紹自己。我叫麥斯歐德,是個農業工程師,教過書,後來辭職不幹了。現在我到終點站去領取分給我的土地,我要在那兒耕耘播種,成家立業。你看,這不比干公職強多了嗎?”
“那么說是處女地啦?”
“是啊,我將改造它,使它變成我的財產,我將成為土地的主人……難道不好嗎?”
“這就是說,你要在那土地上度過一生?”
“這有什麼不好呢?土地是我的!”
姑娘感到失望,轉過臉去,淡淡地說:
“總而言之,這是你的事,與我無關。”
他明白她的意思,趕快親切地說道:
“可是你必須同意我的觀點。”
“我?我必須……為什麼?”
“我是指……讓我向你解釋……我肯定是正確的。我將去迎接的生活是值得為之作出犧牲的。在新開墾的土地上,我將建造一座小屋,你明白它的含義嗎?在城市裡,人們找不到一寸土地、一所空屋,住房問題已經成為解決不了的危機,城市的擁擠已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相信我,新土地上的生活將是極其美好的,它將成為天堂的一部分,特別是……如果有一位妻子陪伴著……”
“妻子,你指你的妻子?為什麼你不跟她一起走?”
“我還沒結婚哩!”
姑娘感到有點尷尬,但她力圖不朝這方面想:
“你說得對。一開始你必須把全副精力用在新開墾的土地上,最好不結婚,以免婚後生活影響你……”
“正相反,如果沒有妻子,新生活將是單調乏味、過不下去的。有了妻子,它才是美好的。我們將在濃郁的樹陰中營造新居,在肥沃的土地上耕種莊稼,我們可以養鳥、養雞、養鴨、養鵝……還可以建一座塔棚養鴿子,我很喜歡鴿子,你喜歡嗎?”
她的問話打斷了他的遐想,問道:
“你說什麼呀?”
“你喜歡鴿子嗎?”
“噢,好極了……”
“那么,你的意見怎樣?”
“什麼意見?”
“我已經談得夠多了……我把我的名字、工作、理想都告訴你了。現在該輪到你了,我想知道你……”
“知道我不會使你感到多大愉快。”
“正相反,我感到好象從生下來那天就認識了你。”
“我是從城裡逃出來的。”
“逃出來……”
“城裡到處是腐臭、垃圾……背叛……”
“這是什麼意思?”
“我曾和一個青年相愛結婚。我曾認為他是一位天使。……誰知還在蜜月里他就背叛了我。”
“在新土地上不會發生背叛的。”
“我想到遙遠的荒蕪人煙的島上去生活……”
“一個人?”
“一個人!”
“這不是自殺嗎?”
“再跟另一個男人生活在一起才是自殺。我費了好大勁才脫離那個不忠的丈夫,在證實了他的不忠後,我和他離了婚。一次經歷就夠我受了,我不想再重複一次……”
“假如你的丈夫不是這個背叛者呢?”
“這是什麼意思?”
“難道你願意過獨身生活?”
“可他是個背叛者……”
“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男人都是寡情薄義的。有許多妻子也是不忠的,但這不能說所有的女人都不忠。總之,在新開墾的土地上是不會發生背叛行為的,因為它是處女地,乾淨純潔,沒有受到城市中你爭我奪和工廠煙囪的污染……請問芳名……”
“我的名字?”
“到現在你還沒把你的名字告訴我。”
“我叫納吉娃。”
“她真是我心中的嬌娃。”他這么想著,不覺兩眼向她瞟了過去,那一雙藍藍的大眼睛……就象天上的仙女……那個人怎么會背叛她?男人還會夢想到比這更美好的妻子嗎?”
“你在想什麼呢?”
她的問話打斷了他的思路。“我,噢!”他趕忙笑了笑,一應付這窘境。他眼睛盯著自己的竹籃子,滿臉堆笑地對她說:
“你不覺得餓嗎?我這兒有烤鴿肉……”說著,就要伸手拿竹籃。姑娘攔住他:
“等等,我這兒有吃的,在這小提包里。”她打開放在腿上的提包,取出幾個三明治,帶著甜蜜的微笑遞給他。
“雞肉夾心……”他伸出手,呆呆地盯著她,忘了接三明治。
“請,請拿著……”
他沒來得及接過三明治,便被停車的聲音驚醒過來。他心頭一緊,看了看四周,用帶著驚懼的聲音低低說道:
“火車停了。”
姑娘笑了笑,說:
“沒關係,反正我們還要坐好長一段,我和你都到終點站。”
“是的。”
檢票員走過來,看了看姑娘:
“請把票拿出來。”
姑娘心頭一緊,三明治從她手裡掉下來。她想起了前一站發生的事情……麥斯歐德打量著檢票員,看他那臉,就象勾人魂魄的死神阿茲拉依爾。他想減輕一點她的恐懼,對她說:
“把票給他看,你的票不是到終點站的嗎?”
“噢,是的,票在這兒。”
她戰戰兢兢,勉強堆著笑把票遞給檢票員,嘴裡不住地說道:
“前面還有很長一段路,是吧!”
“很遺憾,你的票到此為止!”
“你說什麼?”
“請你下車!”
麥斯歐德忍不住喊了起來:
“不,這不可能!”
檢票員向他投來冷峻而帶威脅性的眼光:
“這與你無關……”
麥斯歐德一陣戰慄,喊叫聲變成了咕噥聲。他結結巴巴,差點哭出來,說:
“我是說,我是說……您仔細看看她的票……也許您弄錯了……”
“我們絕不會錯的,先生。我們列車上的一切都是經過精確算計的。她的票到此為止。請下車吧,太太!否則我將命令乘警把你從視窗扔下去!”
“不,”她驚懼地喊了一聲,“我自己下去。”
她從座位站起。麥斯歐德也站起身,對她說:
“我和你一塊下去,納吉娃!我不讓你一個人走。”
檢票員用力一推,把麥斯歐德推回座位上,衝著他吼道:
“我們不允許任何人下車,除非他的票已經到站!”
“我能和她一道下去嗎?”
“你的票還沒到站!”
“可是……”
在檢票員那嚴峻的目光下,麥斯歐德恐懼得渾身都像要融化似的,僵坐在自己得位子上。姑娘離開了座位,手提包和其他東西都沒有帶走。麥斯歐德仍呆呆地坐在位子上,目送納吉娃走下火車,淚花在眼睛裡翻滾。納吉娃消失後,火車又慢慢啟動了。
麥斯歐德的眼淚忍不住簌簌流了下來……這時又過來一位姑娘,請他允許她坐到他面前的空位子上……他長久地凝視著她,發現她是個快活的姑娘。她注意到他那含淚的僵滯的目光在看著自己,於是嫣然一笑,說:
“為什麼哭得淚汪汪的?我又沒搓洋蔥頭!”說罷便坐了下來,講個不停:
“你想像不出,我哥哥最怕的就是洋蔥頭,只要一提到它,他就流眼淚。其實洋蔥頭對健康很有好處,我最喜歡吃蔥頭拌沙拉……人們都說洋蔥頭內含有生命之水,和洋蔥頭氣味一道流出來。淚水是污穢的,污穢的淚水流完後,你的眼睛就會變得明亮……瞧,你的眼睛已經變得明亮了……你用鏡子照照……你有鏡子嗎?我有,給你,你照照……”
麥斯歐德瞧了瞧鏡子,發現他的頭髮已經突然變白,臉上全是皺紋。他像大夢初醒,發現車廂幾乎全都空了,大部分乘客已經下車。姑娘望著他,爽朗地笑著說:
“嘿,老大爺,你的淚水已經幹了,眼睛已經變得清澈明亮。該笑笑了,跟我一起笑吧!老年人是絕不哭的,這是我爺爺告訴我的,他就跟你一個樣。我多喜歡他呀!老大爺,你要上哪兒去呀?”
“到列車的終點站,姑娘!我的票還沒有作廢……”。
賞析
被強迫中止的生命之旅——作者:黃建國
一百四十多年前,波德萊爾在法國巴黎出版了他的詩集《惡之花》。詩人以他那尖刀般犀利的筆觸,首先向他居住和生活的世界大都市巴黎的醜惡邪祟現象發難,第一次發了反抗傳統的怪異之聲。這無異於一枚重磅炸彈投向法國文壇,轟開了多年來一直平靜的傳統文學的水面,在法國乃至世界文學領域掀起了一股軒然大波。於是,一種新型的文學樣式——象徵主義文學誕生了,此後各種各樣的新興文學形式也接踵而至,從而引發了世界文學潮流的巨變,出現了表現主義、未來主義、幻想主義、達達主義、存在主義和荒誕派等等,這便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潮流的濫觴。
二十世紀,現代派文學又由歐洲波及拉美及亞非國家和區域,特別是上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現代派文學洪流蕩滌到阿拉伯國家的時候,現代派文學已是日上中天了。然而,作為現代派分支的荒誕派文學卻是方興未艾。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埃及出現了著名作家陶菲格·哈基姆創作的荒誕喜劇《爬樹的人》和《人有其事》以及荒誕小說代表人物賽義德·舒爾巴吉的《十二點的列車》。
《十二點的列車》故事情節很簡單,表現手法簡潔明快,但在荒誕的背後,卻隱藏著豐富而又深遠的人文意蘊,這一意蘊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去理解,一是作品所指的社會意義,一是作品能指的生命意蘊。
小說寫一對邂逅的男女青年,他們同乘一輛列車,都將在終點站下車。他們兩個人分別都要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麥斯歐德不到三十歲,是一個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青年,他曾經教過書,後來成為一個農業工程師,現在他則辭職要去另一個地方。他乘這趟列車,為的是要到終點站所在的那個地方領取一份分給他的土地。他將在那兒耕耘播種,成家立業,乾一番全新而有作為的事業。錦繡前程,以及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在麥斯歐德眼前鋪展開來,正像他本人所嚮往的那樣,新土地上的生活“將是極其美好的,它將成為天堂的一部分”,“如果再有一位漂亮的妻子陪伴著”,更是好上加好,妙不可言。可以想像這未來的新土地上一定是陽光燦爛,風景亮麗,又充滿希望的。肯定地說,麥斯歐德對自我設計的美好前程懷有無比的自信和有施必成的決心。而坐在麥斯歐德對面的年輕漂亮的女子叫納吉娃,她的身世和日後的打算卻令人感到傷心和沮喪。她是一個在新婚蜜月的日子遭受丈夫背叛的不幸女子,她由於太善良太純真,所以才受了騙。她因此對人產生了深深的失望乃至絕望。她消極厭世,乘車逃離。現在同在這一列駛向終點的火車車廂內,同時對人生和社會涉世未深的一對年輕人,一個躊躇滿志地要去開創自己的新生活,一個則是灰心喪氣地到那荒無人煙的孤島上去過與世隔絕的寂寞生活。他們面對面坐著,內心卻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但是,他們都必須面對共同的現實世界。
麥斯歐德氣喘吁吁地登上火車的最後一節車廂,穿過擁擠的過道,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空位子坐下來。他發現對面坐著的女子很漂亮,穿著人時,她和他一樣買的都是終點站的票。從女子的目光來判斷,他覺察出她對他是持欣賞態度的。起初,他只是想和她搭訕以消解行旅之孤寂,於沉悶無聊中尋一點刺激,於是就大口大口地抽菸以引起女子的注意,結果是因嗆著了對方招來指責和冷遇。而最終促成他們彼此之間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卻是因一件令車上每一位乘客十分害怕和震驚的偶發事件,兩位年輕人為了緩和驚悸與恐怖的心理,需要交流和語言撫慰。
小說的情節主線基本上是傳統的,表現手法卻是荒誕的。荒誕性從火車發車一小時後,在第一站停車檢票員檢票時顯現出來。有位旅客買的也是終點站的票,可是檢票員硬說他的票已經到站了;旅客不相信這是真的,便向檢票員解釋;檢票員不但不聽,而且態度專橫,粗暴野蠻,不講道理。另一位旅伴想替這位乘客討公道,結果他得到的卻是威脅。那位乘客還沒來得及自己下車,就被檢票員叫來的幾個乘警強行從車窗扔出車外。然後,火車在那個被遺棄的乘客悽慘的叫喊聲中向前徐徐啟動。列車上的檢票員和幾個乘警個個面孔陰鷙,冷酷無情。這一事件對在座的每一位旅客都引起了極其強烈的震撼,給他們心靈造成了極其強烈的撞擊和刺痛。人們心裡所受到的巨大傷害,形成了一道又寬又深的傷口,以致難以彌合。於是所有人共同擔心的是這種情形會再一次出現,更有可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嚴峻冷酷的現實告訴人們,這是一趟失去理智和正常秩序的列車,列車上每一位乘客的旅行隨時會受到威脅,人的正常合法旅行會隨時被強行中止。在這裡,一切正常秩序合理要求都沒有了保障。
當然,更駭人的情形還在後面。當麥斯歐德和納吉娃兩顆年輕的心靈剛剛呈現出溝通的希望,麥斯歐德因納吉娃的美貌、善良和清純而對其發生熱烈的情愛;當他正設計著他們若一起為未來的新事業而奮鬥,共同創造甜蜜的新生活時,可怕的厄運終於也落在了他們身上。凶神惡煞般的檢票員過來查他們的票,那一張“就像勾人魂魄的死神阿茲拉依爾”的可憎的檢票員的臉,“使姑娘心頭一緊,三明治從她手裡掉下來”,因為“她想起了前一站發生的事情”,她的擔憂終於成為事實,檢票員粗暴地宣布她的票到此為止。麥斯歐德不服,替她喊起來,然而他得到的是同樣的威脅。麥斯歐德不忍心讓納吉娃一個人中途下車,就請求和她一塊下去,卻被推回座位,禁止下車,原因是他的票還未到站。未到站的人被強行地趕下了火車,想要陪著被趕下去的人一起下車卻被粗暴地禁止下車。這是一種怎樣荒誕不經的生活呢?生離死別和孤苦伶仃的遭遇不是個人原因,完全是由外部世界的荒謬無理而造成的,具有不可抵抗性。當納吉娃在麥斯歐德的淚眼中消失後,火車又一次啟動了。這時又過來一個更年輕的姑娘,坐在納吉娃空出來的位子上。姑娘發現了麥斯歐德滿面縱橫的眼淚,讓他照照自己“澄清”後的明亮的眼睛(這怎樣能澄清得了呢)。就在這塊鏡面上,麥斯歐德驚駭地發現自己老了,頭髮全已變白,臉上爬滿了皺紋。這時,車廂里幾乎全空了,大部分乘客已經下車(當然都是被迫下車的),而他們的票卻都是“到終點的”,“都還沒有作廢”。
從表面情節與事態發展來看,如果單從政治與倫理道德觀念出發,很容易得出如下結論:這趟列車是正在運行著的國家機器的象徵,在這趟列車上一切秩序本來都是好好的,但代表這趟列車(也就是國家)意志的檢票員和乘警由於他們的粗暴專橫和蠻不講理,把整個列車的秩序搞得混亂不堪。由此,給乘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完全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把握自己的行為和命運,他們也根本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他們的行動與存在是被動的和被迫的,所有不幸的事件和可怕的厄運都會偶髮式地突然降臨到這些人的頭上,他們被完全掌握在這一幫兇惡蠻橫的檢票員和乘警的掌心裡。在這些不幸的事件和厄運面前,人們完全是防不勝防、無能為力的,既無法逃避,更無法抵抗,所以只能聽之任之,任由擺布。可以認為,列車上的檢票員和乘警正是國家機器的象徵,他們的意志和話語正是統治者的意志和法律的體現。然而,如果對《十二點的列車》的理解僅限於這一層面,僅限於小說所指的社會意義,而未向人生的更深層去開掘和剖析,那么,就可能造成一知半解或誤讀。
拋開社會意義,從哲學的角度進行更深一層的探究,就會得到另外一種理解。固然,文學作品可以被當作社會現實的一面鏡子,它是對現實生活曲折或折射式的反映。西方文藝理論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一直主張藝術模仿生活的觀點,但文學作品畢竟不是對現實世界的複製,它滲透著作者更多的主觀意念、理想和對現實生活以及對人的生命狀態的特殊理解。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文學流派異彩紛呈,思潮迭起,每一種思潮或流派都代表著不同作家對社會、對現實、對人的生命狀態的特殊認識和不同理解,而體現在文學形式中,就有了這樣那樣的反映角度和表現手法。在波德萊爾的眼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病態和頹廢的;在卡夫卡的眼裡,人就像甲蟲一樣生活在地球上;在薩特的眼裡,他人是地獄,存在是虛無的;在加繆的眼裡,世界則是一片荒誕狀態……荒誕派作品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根據正是來源於存在主義、尼采哲學和伯格森的直覺主義。舒爾巴吉的《十二點的列車》表現的內容也正如加繆所說的那樣,列車上的這些人的生命存在完全是荒誕的,他們生活在一個荒誕的世界。 《十二點的列車》不僅表現手法是荒誕的,內容也是荒誕的。
順著小說的思路,完全有理由這樣理解: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像是乘坐在生命和命運這趟列車上的乘客一樣,災難和不幸完全是偶然的和不可預測的,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到每一個無辜者的頭上,人生存在蒼茫的時空環境裡,顯得極其渺小和有限,生命之路確實具有不可測性。特別是上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集團性的有意識有組織的破壞(指戰爭因素),使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片無秩序的混亂狀態,過去的一切傳統觀念,幾乎全被冷酷無情的現實所打碎,現實世界的各個方面都出現了深刻的危機,人的精神世界也陷入空前的混亂和一片空虛之中。小說一開篇描寫的車廂內擁擠不堪和行李亂堆的景象,全景式又象徵性地披露了這種秩序和混亂狀態,結尾處則落到虛無和幻滅的感覺上。兩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的災難,給不止一代留下了難以治癒的精神創傷,使人們產生了全面的幻滅感。正如尼采所說的那樣,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上帝已經死了,昔日那些堅定的信念和信仰早已崩潰瓦解,過去那些美好、明亮的希望與理想在頃刻之間也都破滅了,原先那種安全感、穩定感和秩序感都消失了,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捉摸、瞬息萬變又令人無所適從。生活在這樣一個混亂、虛幻、茫然的環境中的作家們,他們會更甚於普通人敏銳而又強烈地感覺到現實世界的動盪不安、冷酷無情和陰森恐怖。現實對他們來說,完全是一種廣大的、無力抗拒的,又不可測知的深淵。他們從存在主義觀念出發,擴大、發揮並且強化了加繆關於世界是荒謬和荒誕的這種意識,並且力圖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出宇宙存在的偶然性和茫然性,以及人的一切行為舉止都是“沒有意義、荒誕、無用的”這樣一個母題。 《十二點的列車》表現出的深層思想意蘊,就是人與世界、人與人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
文學作品不能僅僅滿足於對現實世界的反映這一層面上,它有更多的內容蘊含著作家對整個人類生命與生存狀態強烈的自我感受、個性意識以及特殊理解。人生活在世界上,世界是人的活動場所,是人賴以生存和生息的搖籃,但它同時又可以拘囿和框限人的自由意志與行動,甚至還會毀滅人的生命;同樣作為人類的所謂強大無比的那一部分,卻完全支配掌握和左右擺布著另一部分比較弱小的人的生命和生存權。在文藝復興時代,莎士比亞盡可以驕傲而自豪地站在曠渺廣袤的天地間高喊一聲:“人是天地之精華,萬物之靈長!”而到了二十世紀以後,作家、藝術家包括哲學家們卻非常悲哀地將人比作毛猿、甲蟲之類異種東西,可見人已經貶值到了何等的地步,人類渺小無用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十二點的列車》中所描寫的每一位乘客,可看作是生活在現代社會普通人的縮影,而這趟列車完全可以理解為整個人類命運載體的象徵,也可以理解為自然規律的象徵,檢票員和乘警之類可以理解為一種制度或某一種強大群體支配、左右、擺布另一部分弱小群體命運的可怕的外部力量的象徵。人作為具體的生命,他總是有著一定的來處,也同樣有著一定的各自不同的歸宿,命運這趟列車正是從起點負載著他們向著既定的終點目標按照一定的速度行使前進,途中發生在車廂內的各種故事就構成了人們的具體生活。在行車途中,在不同的停車站點上,總是隨時有人要被迫提前下車或被無情地拋棄,被扔下車去。然而在生命這趟列車上,在還未到達終點站之前,誰又願意在中途被遺棄,被拋下車去,從而被強行中止旅行呢?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們,誰手裡又沒有持著一張去終點站的車票呢?但是這趟列車上可惡又兇惡的檢票員和乘警就是不讓你平平安安地到達終點站。
《十二點的列車》給我們的思考是深刻而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