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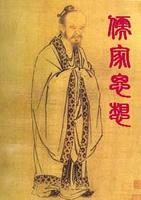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眾所周知,一些西方人對自己的民主制度深感驕傲。這些人對中國的看法大抵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看法認為,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極權國家;另一種看法認為,中華民族自始至終都在各種各樣的束縛之中,人民已經習慣了與鎖鏈相伴的生活。這兩種看法都明顯有居高臨下的優越感,雖然第二種看法顯得還較有同情味。不可否認,這些人對中國通常很真誠,但是,他們的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只要看看他們批評中國政府制度和政治實踐時所用的語言就可以了。他們要么從明確的經濟利益出發,並不為人民實際的民主利益考慮;要么含糊其詞地從當代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出發,不切實際地加以發揮。
在當今世界上,許多人期望中國國內出現重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在西方,持這種觀點的大多數是具有使命感的資本家,還有主張進行自由式民主改革的人。在他們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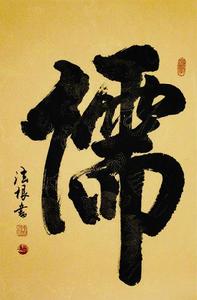 儒家民主主義
儒家民主主義來,民主制度的變革理應沿著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繼續向前發展,但是,其實民主制度的改革並不見得存在非要這么做不可的充足理由。
在儒家思想中,不難發現發展亞洲民主模式的思想資源。在提出儒家民主主義時,並不將其限定為僅僅具有“亞洲特色”的民主。發展儒家民主主義不僅有益於亞洲的民主化倡導者,而且有益於西方社群主義民主的倡導者。正是由於儒家民主主義必使雙方受益,所以提倡儒家民主主義可以提升中國民主的希望。可以這樣說,儒家民主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而且在今天還很有希望實現。
典籍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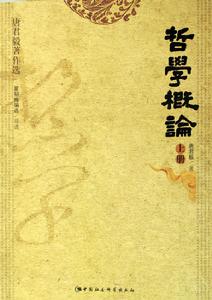 儒家民主主義
儒家民主主義在共享的社群中,個人對自由的認識絕不僅僅停留在“不受拘束”(theabsenceofconstraints)的層面上。社群主義民主認為,個人的自由身份意味著在社群中成長,並在社群需要時隨時修正個體的行為。在社群需要時,能夠隨時修正個體行為的能力恰恰是自治的精髓所在。
在今天的美國社會,這樣一種社群主義自由概念已經不再對美國的民主起推進作用。由於企業文化與國家政府的雙重擴張,曾經緩衝於個人與政府之間的組織機制被削弱了。曾幾何時,象家庭、居民區、學校、工會、社區俱樂部和教區都曾經在教育公民遵守社會文明公德方面起過較大的作用。可是今天,就公民自由而言,個人自由身份已經成了公民選擇自己目標時的單一能力。
現在,美國民主變得越來越程式化和中立化,其目的僅僅在於確保一種權利框架,在這一權利框架中,人們有選擇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目標的自由。原則上說,政府既不鼓勵也不阻止人民對任何美好生活的憧憬。這種概念化的自由給社會留下一個真空,使得形形色色的帶有偏狹性質的說教迅速乘虛而入,比如,自衛組織,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激進的反墮胎主義,新納粹主義,白人優越主義,有組織的戀童癖,等等。
桑德爾的分析表明,有兩種觀點通常被認為與公民對自由的理解背道而馳。第一種觀點認為,世界已經變得極為複雜,地方自治的理念已經不合時宜;第二種觀點認為,教育公民遵守社會公德就必然要犧牲個人自由,而且這種個人自由的犧牲常常是在強制狀態下實現的。
桑德爾沒有否認,獨立自由的自我是一種個人解放,個人灑脫的理想,他們不受外在道德或社群關係的約束。但是,僅僅追求獨立自由的自我並沒有給美國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事實上,已經阻礙著美國的社會進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那些表面上看似不民主的概念其實都有一定的價值,例如,禮儀制度下的社會角色和社會關係,等級制度,服從,互相依賴等等,先前都把它們與儒家哲學相聯繫而認識不到它們的民主價值。在當今世界各種文化日益相互依賴的情形之下,借鑑儒家思想資源對於美國民主來說,是暗示著一個新的、更有活力的方向。最起碼,當代美國的問題對一些亞洲文化可以起警戒作用。一些亞洲文化有拋棄儒家思想的傾向,卻沒有認真研究儒家思想對亞洲特色的民主可能作出的貢獻。
這樣做必然會出現問題,因為解釋以往的事件,幾乎都可以跟當今的事務有所共鳴。然而,還有無數偶然因素,特別是那些不易覺察的因素,都可能影響到當今這種或那種生活形式的制度化。正如政治學家愛德華·弗里德曼(EdwardFriedman)所說,所有文化都包含著矛盾性的政治潛能,如果中國領先於歐洲實現了民主化,那么歷史學家們可能宣稱,整箇中國文化都是民主的,而且這種民主是獨一無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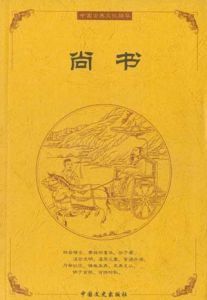 《尚書》
《尚書》《論語》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象好的實用主義者一樣,孔子強調緊密的、內心自發的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孔子強調協調個人與家庭、進而協調個人與社群之間的關係,力圖建立一個繁榮昌盛、自治的人類社群,並將其視為保障個人自由的最重要條件,也就是說,只有這樣的人類社群才能確保個人與社群的理念共享以致完全融和。儒家民主主義模式靠兩個強大的卻又是非形式化的力量來維繫,一個是“恥”字,一個是“禮”字。雖然,強迫作為維繫秩序的一種手段是有效的,但孔子拒絕採用這種手段。在孔子看來,自治(Self-ordering)是明確的追求。
在中國古代傳統中,家庭被視為社會的細胞。個人首先是家庭的成員,每個人都先要在家庭內部關係中認識自己,然後才擴展到更為廣泛的社會關係中去。正如儒家經典《大學》所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self-cultivation)為本。”國家是家庭的延伸,對國家的認識是在修身過程中逐步加深的,對自身的認識也是在人與人的角色和關係中逐步深化的。儒家民主主義同意這種以家族為核心的思想,因為這一出發點為“公民”(citizen)或“公共個人”(publicindibidual)這樣的概念提供了比自由主義民主傳統更加合理的解釋。
杜威與孔子
 儒家民主主義
儒家民主主義很大程度上,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是圍繞以下問題展開的:個人與社會,私人與公眾,自然法與成文法,權利與義務,國家的強制力(即權威合法性),正義觀念,等等。
從杜威關於民主的思想入手,比較容易理解什麼是“儒家民主主義”。在杜威看來,民主的基礎是溝通的人類社群。在溝通的人類社群中,那些出於個人目的刻意求新和譁眾取寵的做法會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
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在中國文化里能夠和諧共處,不但體現在單一文化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三教合一能在特定個人身上體現出來。這樣一來,對於西方人來說,就有必要弄清在中國文化中,什麼是西方多元論(pluralism)的對應術語。在儒教社會裡,文化的共識性往往表現在美學和實踐層面上,而不表現在思考或理性層面上,這點跟杜威的民主思想非常接近。西方那種認為“合理的思維”(rightthinking)就是要對自己的宗教信仰忠貞不二的立場,跟儒家思想和杜威實用主義的美學意義完全不同。
在中國歷史上,不論文化形態多么多元化,傳統都力圖使不同的文化形態達到和諧統一,並且將此視為社會公善;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義提倡包容各種不同聲音,蘭迪·皮倫布姆(RandyPeerenboom)在比較這兩點時說:“思相自由是當代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核心。能夠進行獨立思考的權利是最為珍視的權利,思想自由是其他一切權利的基石。”追求思想自由必然追求合理的信仰多元論,也必然因此反抗一切教條的保守主義和正統觀點。
《論語》中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和”這個術語在儒家思想里,意味著各種不同成份的和諧相處,這層含義可以說是非常強烈而且清晰的。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儒學對社會和諧追求的前提是,默認各種不同的成分,並力圖使之和諧。
如果考察“思考的權利”(righttothink)和“合理的思維”(rightthinking)之間的區別,就會發現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s)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不認為思想與行動既可以合為一體,又能夠彼此分離。在中國傳統中,思想、性情與行動是相互關聯的,這與西方傳統的主導意識形態截然相反,西方人認為,思維、行動與情感都是各自獨立的。
其實,中國與西方社會都非常關心如何維持社會穩定。在語言多種多樣的多民族社會,比如古希臘社會裡,要在不同的語言、神話、風俗與禮儀之間找到一種具體而有效的方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夠保障社會和諧的原則和標準一開始就是抽象出來的,而後又能普遍適用。
在比較了“追求真理的人”和“追求道的人”之間的區別以後,如果一個社會對思想和道德行為有明確的區分,那么提倡多元論就會更容易。如果人們不能將思想付諸行動,那么其思考的自由也是有限的。象中國這樣的文化傳統不對思想與行為加以區別,認為思考就是一種行為。
無論是孔子還是杜威都認為,人是“具體環境下的人”(person-in-concrete-context)。自由主義“個人”概念不但與中國文化無關,而且在美國實用主義那裡也無跡可尋。儒家思想既不象自由主義民主模式那樣,把“手段與目的”做嚴格區分,將社會作為實現個人目的一種手段,也不象團體主義模式那樣,將個人作為社會的一種手段。儒家思想與杜威都認為社會群體的廣泛目的產生於個人的而且是社群的目標,他們在這點上幾乎完全一致。儒家思想中,家庭模式的特權和義務是不可分割的,擴展到家庭以外的範圍,就成了合理的政府統治基礎。
在儒家思想里,基於被禮教化了的人的角色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沒有西方意義上的超越含義。與西方精神超越塵世的意義相反,儒家思想中的人的角色和人際關係所指的是具有社群生活形式的文化遺產。這文化遺產是精神發展和宗教生活生生不息的源泉。要想了解中國精神,僅僅了解“天”(一般翻譯成Heaven)與“道”(theway)這樣的範疇是不夠的,而且應當了解能夠將社群統一在追求公善目標之下的禮教,了解禮教之上的社會角色和人際關係,也就是說,“禮”是了解中國精神的重要範疇。事實上,禮儀制度正是“天”與“道”兩個範疇在社群生活中的具體內容。“禮”、“天”和“道”這些概念充分表達了淵遠流長的歷史延續下來的儒家文化精神。
杜威也曾經表述過類似的觀點。他說:“原因和結果構成的社群,是後人生存其間的無限之網,它是那么廣闊無邊,深不可測,充滿著各種神秘的存在,這個社群是被織為一體的象徵,想像力只好將其稱為宇宙。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中國人尊崇自己的傳統文化,而基督徒對上帝很依附,這顯得有些旗鼓相當。但是,尊崇祖先與文化英雄的儒家民主主義真正是一種“先人的民主”。雖然他們已經不在人世,但是“他們的民主”仍然很有生氣。正是這個道理,當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子貢回答誰是孔子的老師時,子貢回答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一個哲人的意義在於他所創建的價值和思想為人傳頌。中國人重視葬禮,重視家族的延續,重視孝道,重視落葉歸根,他們對祖先的尊敬可以說是一種“宗教”習慣,而這也是活生生的社會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