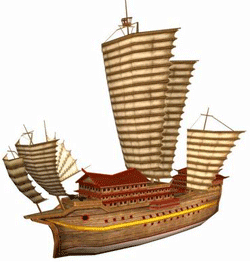述略
 中國古代海軍史
中國古代海軍史古代中國在海軍建設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光輝成就,無論在艦船製造、艦隊航海、海軍武器,或者在海軍軍事思想等方面,均不斷發展、創新,長期居於世界前列。中國還是世界古代海軍發源地之一,兩千年間一直是太平洋上的海軍強國。
中國歷來就是海洋大國。中國位於太平洋西岸,既擁有遼闊的陸土,又具有浩瀚的海洋國土。從遠古時代開始,中國就萌發了自己的造船和航海事業,並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偉大貢獻。
海洋既是天塹又是通途。中國不僅與東北亞、東南亞是海上近鄰,而且與美洲、大洋洲隔太平洋相望,中國面臨著寬廣、複雜和多方位的世界海洋態勢。中國海軍依託自己眾多優良港灣和沿海島嶼,馳騁於遼闊的海域。
中國的東部和南部瀕臨太平洋,渤海是內海,東、南兩面為北太平洋西部的邊緣黃海、東海和南海。中國海岸線長達1.8萬多公里,沿海良港眾多,島嶼星羅棋布,面積500平方米以上的島嶼有6500多個,還有很多礁和沙洲。從渤海的廟島群島,經黃海的長山群島和東海舟山群島、台灣島到南海諸島,構成環圍大陸的島嶼鏈,自然形成一條海上天然屏障和海防前哨,特別是我國南沙群島前出,在戰略上更具突出地位。
中國的航海事業歷來就十分發達和先進,是世界最早走向海洋的國家之一,也是古代海洋文明的先驅。早在距今7千年左右的原始社會時期,已經發明了舟船,並開始了水上交通。新石器晚期,已發展了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以及和台灣、沿海島嶼的近海航行。夏商西周和春秋時期,中國的民用船隻和艦隊業已逐步頻繁活動於我國沿海海域。戰國秦漢時期,我國航海事業有了長足的進步,已由瀕海走向近海。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航海事業繼續向前發展,我國船隊往來於今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翼他群島,以迄印度之間,形成“舟舶繼路,商使交屬”的航運繁榮局面。隋唐時期,中日朝海上交通十分繁忙,南方航線甚至遠達大食(阿拉伯帝國)。宋元明初時期是我國古代航海事業的高度發展時期,中國的船舶已遠航印度洋和今非洲東部和西北部等地,無疑是古代東方最大的海洋國家,控制了“從日本到非洲東海岸遼闊地區的霸權”。
中國古代造船和航海的光輝成就,通過海洋向世界傳播,加速了資本主義和海洋時代的來臨,從而改變了世界的面貌。無庸諱言,“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
中國古代海軍的產生
遠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古代海軍業已誕生。中國古代海軍不僅活躍在江河湖泊,創造了許多水戰戰績,而且至遲在春秋末期已有渡海作戰的記載。
海上作戰,關鍵是要有艦船。夏、商、西周三代造船和水上交通事業的逐步發展,為戰船建造和水戰、海戰的出現創造了前提條件。春秋時期,由於青銅工具的進步,尤其是鐵質工具的使用,造船能力和技術得到空前提高,為古代海軍的產生奠定了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地方經濟的發展,各地諸候的力量日益強大,沿江傍海的各諸候國為了爭霸的需要和面臨頻繁戰爭的局面,紛紛建造戰船,建立“舟師”。
戰船和民用船的本質區別,在於是否配置作戰設施。春秋時期的造船業以吳、越最為發達。越國有“戈船”、“樓船”“大翼”、“中翼”、“小翼”。吳國有“大翼”、“小翼”、“突冒”、“樓船”、“篙船”等多種形制的戰船。吳楚共有長江,齊國瀕臨黃海,楚齊也擁有類似具有初步分工的戰船。
春秋時期已出現專門用於水戰的兵器。據《越絕書·札記》所載,吳國戰船已配備射程較遠的“弩”、“矢”和近距離接舷戰使用的“長鉤矛”、“長斧”,以及防護使用的“甲”、“兜黎”等。公輸般為楚國專門設計創製了“舟戰之器”—“鉤強”(鉤拒)。這種兵器,“退者鉤之,進者強(拒)之”,既可用於攻,也可用於守,大大增強了舟師的水戰能力。
春秋時期各國已正式編組艦隊,艦隊司令均系臨時指派,尚無常設,既是陸軍將領,也可充任水軍將領。“王僚二年(前525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吳伐楚,……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余皇。”由此可知,公子光是率領一支艦隊伐楚的,可以稱他為“艦隊司令”。“王舟”、“余皇”即為其“旗艦”。這時的水兵已進行專門訓練。《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述了越攻吳,曾派“習流二千人”參戰。“習流”就是“習水戰之兵”。當時戰船人員組成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操舟者,即航行保障人員,二為作戰水兵,三為“艦長”等指揮人員。水陸攻戰銅鑒的圖象上,指揮人員已有了明確的指揮位置。
舟師執行作戰任務,有“艦隊司令”和“旗艦”,有專門訓練的“水兵”,戰船上設定“艦長”等指揮人員的位置,有的水戰一次出動2千水兵,足見當時艦隊的端倪。特別是在前468年,越國由會稽(今浙江紹興)遷都琅挪(今山東膠南)時,隨行有“戈船三百艘”之多。已是一支威武雄壯和實力強大的艦隊了。
我國最早的水戰,開始於春秋中後期。“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爆發於前549年的這場楚吳水戰,是史籍明確記載的我國第一次水戰,從而開創了中國戰爭史的新局面。此後,吳越水戰繼之而起,並逐步擴展于海。由於“海周回齊、吳、越三國”所以最早的海上軍事行動,首先發生在這三國之間。前485年,吳國派大夫徐承帥舟師遠航奔襲齊國,史稱“徐承帥舟師將自海人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另稱“齊鮑氏拭齊悼公。吳王聞之,哭于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這是兩條有關此事件的僅有的史料。其中的具體行動細節雖不清楚,但可以斷言,當時的吳國艦隊已具備了海戰能力。三年後的前482年,越王勾踐“命范鰲、後庸率師沿海溯淮,以絕吳路”。越國艦隊切斷了吳軍退路。這次海上軍事行動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戰略協同任務。確實“海道出師已作俑於春秋時,並不自唐起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備,人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這時(伍子骨水戰兵法內經)已問世,這不僅表明水軍作戰行動的頻繁和擺脫了始初狀態,而且在水戰戰法方面也達到一定水平。
綜上所述可知,春秋中後期,由於爭霸鬥爭的需要,沿江傍海的楚、吳、越、齊等國發展造船事業,創製水戰兵器,編組艦隊,建立“舟師”,水戰、海上軍事行動頻繁,且有水戰戰法的著作出現,說明這時我國古代海軍已經產生,而且中國當為世界古代海軍發源地之一。
中國古代海軍建設的偉大成就
船體、動力和海軍武器等技術裝備因素,構成海軍發展歷程階段性的主要標誌。世界古代海軍所使用的艦船均為木質船體,動力則有人力與風力之別,而武器又有冷兵器和火器(火藥武器)之異。據此,中國古代海軍歷史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冷兵器時代的棹槳艦隊時期(春秋時期到隋唐時期)和火器、冷兵器並用時代的帆船艦隊時期(五代十國時期到清朝鹹豐年間)。
自然,棹槳艦船和風帆艦船、冷兵器和火器之間難以劃分一個十分明確的界限,它們有一個漸進演化和混合使用的過程。秦漢時期,中國已出現帆船,但直到唐代,主戰艦船仍為棹槳船,其中“樓船”、“拍艦”、"鴿航".“車船”、“海鵲”等可作為中國古代海軍棹槳艦船的代表艦種;具有突出特點的艦艦攻擊武器為“拍竿”;除接舷、沖角外,拍擊和火攻成為中國棹槳艦船時代的海軍戰術特色;艦隊主要活動於內河長江水域和沿海海域,並開始走向近海。唐代發明了火藥。五代十國時期明顯地成為冷兵器向火藥兵器的過渡階段。這時的“沃油”,“煙幕”和始初的“艦炮”等多種先進的海軍兵器用於艦隊攻擊;南方各國中央政府設定水軍和專門的水軍統領人員,說明水軍(海軍)開始從陸軍中分離出來,形成了獨立的軍種,這一切標誌著海軍建設史上新時代的來臨。緊接著的北宋時期,開始在水軍中裝備火藥武器。從宋代到清代鹹豐年間,中國海軍普遍使用風帆戰艦,逐漸由近海邁向遠洋;先後裝備一了火藥箭和火銑、佛朗機炮、水雷等各種火器,且在實戰中有效運用;海防建設日臻完善;火器攻擊成為海軍戰術的主要特點,海戰指揮藝術有了新的發展,諸如海上奔襲、海上伏擊、攻擊海上要塞,以及千艘戰船大艦隊的遠航進擊等等,都是前所未有,這一切足可說明,中國古代海軍已跨人火器和冷兵器並用的帆船艦隊時代。
冷兵器時代的棹槳艦隊
1.戰國秦漢時期—中國古代海軍的初創和初步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海軍的產生和初創階段。戰國初期的水戰圖象,迄今共出土4件。現以較為完美的山彪鎮1:56銅鑒為例,可知當時的戰船為2層,無帆蓬和尾舵,擊棹在下,戰鬥在上;武器裝備約略可分為兩類:一為水戰武器,遠用弓矢,近用長戟和矛,跳幫擊殺則用短劍;一為用以指揮進退的旗、金、鼓。關於水戰,“宴樂銅壺”有水兵泅水前進配合艙面戰鬥的情景,“嵌錯銅壺”有接舷戰的具體描繪,“水陸攻戰銅鑒”則鮮明地展示了沖角、接舷這些古代海軍的典型戰法。
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海軍初步發展並開始走向海洋的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統一,造船技術和能力有了明顯的進步和提高,戰船種類也日益完備:秦代已將樓船發展為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戰船。漢代戰船按用途可分為:“先登”(衝鋒戰船)、“蒙沖”(攻擊戰船)、赤馬”(輕捷戰船)、“檻(重型戰船)、“斥候”(偵察用船),尤其是作為主戰戰船的“樓船”,高達10餘丈,上建樓槽二三層,甚至四層,可載員千人,所以秦漢時期的海軍統稱為“樓船兵”或“樓船”。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艦”,《釋名》卷7,“上下重床曰艦,四方施版,以御矢石,其內如牢檻也。”戰艦之名由此而來。
漢高祖時,已組建樓船軍。前120年,漢武帝又在長安附近挖掘方圓40里的“昆明池”訓練樓船軍。西漢海軍力量強大,已有“樓船十萬師”、“樓船士二十餘萬人”的記載。。樓船軍還規定,每年八九月間舉行一次校閱,稱之為“都試”。海軍官兵已開始專業化。中央設“樓船校尉”,分管海軍事務,但艦隊司令仍委派陸軍將領,加以“伏波將軍”、“樓船將軍”、“橫海將軍”等名號統率艦隊出征。西漢武帝時,樓船將軍揚仆曾率樓船軍5萬出海遠征。東漢光武帝時,曾令伏波將軍馬援統領戰船2000艘“浮海”出征。當時,中國艦隊已自由馳騁於黃海、東海和南海海域,由瀕海走向近海。
秦漢時期,中國已經出現帆、舵、錨等船具配置比較齊全的木帆船,並已開始鐵釘連線船體結構,西方各國則到14世紀後才開始使用鐵釘造船。
2.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海軍的曲折前進和繼續發展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又一個長期分裂爭戰時期。中國古代海軍的艦船、武器、作戰藝術在艱難中卻仍不斷演進,尤其是南方的吳國、東晉和南朝的海軍建設持續發展,甚至湧現出不少新成果、新發明。
吳國以水軍立國,沿海的造船場如溫麻船屯(今福建連江北)、橫、真船屯(今浙江平陽)的規模都很大;在建安(今福建福州)特設典船校尉,監督管轄造船事宜。由於吳國造船能力的增強,於是建立了一支擁有5000艘戰船的龐大水軍,動輒可出動萬人大艦隊出航。兩晉時,“艦”已作為戰船的專用稱謂而廣泛使用。三國時,我國海船使用的帆已可轉動。南北朝時,我國開始懂得以壓艙物保持船體平衡,以增強穩定性。
艦船種類也日益紛繁。西晉滅吳,王溶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槽,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盧循起義,造巨型“八槽艦”9艘,該艦樓高4層,高達10餘丈。。南朝的艦種更多,出現了防護力極強的‘、裝甲皮艦”和均“衣以牛皮”的三王艦、青龍艦、白虎艦,以及專門從事軍事運輸的“軸重艦”等。陳朝傑出的戰艦設計師和海軍兵器發明家、海軍將軍徐世譜設計製作了“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不僅顯示了高超的智慧,而且說明他是車船的始創者。此外,南朝候景所造“鶴航”千艘,該船船舷兩側各80名“掉手”,航進快速異常,“捷過風電”,可謂槳船艦船中具有代表性的艦種。
中國古代掉槳艦隊時期具有突出特點的兵器為“拍竿”。它是從古代汲水工具桔梅演化而成。最早施用這種武器於水戰的為西晉末年起義的杜弢。他曾“作桔梅打官軍船艦”,並“以桔梅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這種兵器一經出現,就顯示了作為艦艦重型攻擊武器的巨大威力,在實戰中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成果。火器出現前,我國發明和使用的這種重型艦艦攻擊武器,實為世界古代水戰兵器之獨創。拍竿一直沿用到南宋。楊么起義軍的大型車船上就設定了高達10餘丈的拍竿,頂端系巨大石塊,底部用轆護轉動,較前更為先進,但此後即逐漸被火器所替代。
令人驚異的是,東晉王嘉在《拾遺記》中,曾構想創製一種可以“沉行海底,而水不浸”的船隻,名之為“滄波舟”;又因形似螺,也稱“螺舟”。此書雖帶有濃厚的神話性,但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世界最早提出了水下潛航構想的傑出人物。
三國時代,保障艦隊指揮的通訊設施已初具規模。水軍駛航、駐泊、作戰均有明確號令,鼓音為進,“金音”和“舉青旗,船皆止,不止者斬”,鼓音幾通,皆有具體規定;戰船進發、錨泊必須按照次序;白天使用金、鼓和不同顏色的旗幟,夜晚則以旗幟和“炬火”配合使用,這可說是信號旗和燈號的雛形。英國海軍到1340年才正式規定了2種信號旗,我國水軍使用旗號要比西方早千年之久。
這個時期海軍活動最頻繁的要算吳國了。230年,吳王孫權曾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萬人大艦隊,浮海尋求直洲、夷洲(今台灣)。雖未達宜洲,但到達了夷洲。這是大陸人民首次航抵台灣的有史記載。此後,他曾分別派遣萬人和3萬人的龐大艦隊北上南下,航達遼東和海南島以南海區。吳國還派遣官員朱應、康泰出訪,航抵林邑(今越南東南部)、扶南(今高棉)以及南洋群島的許多島嶼。東晉末年,孫恩、盧循起義軍的艦隊和東晉統治者的艦隊曾在沿海活動,相互攻擊,不僅反映了當時海軍建設的成就,而且在水戰戰法方面也較前有了明顯的進步。208年的赤壁水戰,孫劉聯軍周密策劃,果斷抓住戰機,出敵不意採用火攻,全殲了曹水軍,創造了中國古代水戰史上最早的以少勝多的出色戰例。
280年,西晉滅吳之戰是6路水陸大軍協同並進、以艦隊為突擊力量的大規模戰爭。王溶等率7萬水軍的龐大艦隊浮江東下,巧妙地破除了水下、水面障礙,摧毀了吳國自認為固若金湯的長江封鎖線後,直駛建業(今江蘇南京)城下,在滅吳戰爭中發揮了主導和突擊作用。他們創造的破除長江障礙的出色戰法,充分展示了我國古代海軍將士的傑出智慧和卓越才能。
3.隋唐時期—中國古代海軍的興盛和再次走向海洋
隋唐時期隨著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海軍武器裝備水平不僅達到了冷兵器時代的頂峰,而且造船能力和造船技術也得到空前提高。中國古代海軍再次走向海洋。隋時的永安(今四川奉節)和東萊(今山東掖縣)成為內河和海洋戰艦的製造基礎。唐代專設“將作監”統管全國戰艦建造。唐政府在揚子(今江蘇儀征)一地就設立了10個造船場,其它如揚州、常州、杭州、越州(今浙江紹興)、婆州(今浙江金華)、洪州(今江西南昌)、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和四川的劍南道(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皆為造船極為發達的地區。
造船技術往往集中體現於戰艦製造水平。據《通典》記載,唐代戰艦分為樓船、蒙沖、鬥艦、海鵲、走炯、遊艇等,其中“海鶴”更為別致,該艦“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鵲之狀。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鶴翅翼,以助其船”,雖遇風浪,不易傾覆,仍可繼續作戰,這種穩性和抗沉性較強的江海兩用新型戰艦,實為前所未有。隋唐時的車船製造較前又有進步。隋場帝時宇文愷造出使用輪軸轉動的巨型戰艦。唐德宗時,荊南節度使李皋改進了用於水戰的車船,該船“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這種人力操縱的的明輪船,歐洲直到15世紀才出現。唐代海船,大者長達20丈,可載員六七百人,較東晉法顯航海所乘載員200餘人的海船更為宏大。當時中國帆船巨大,抗風能力遠勝於其他各國船隻。
隋唐戰艦武器配置有矛、弩、拋石機、鐵汁、火炬等。
隋唐時期規模較大的海戰水戰,主要有隋滅陳水戰和隋唐海陸協同遠征高麗、百濟的戰爭。588年、隋軍51.8萬,分8路對陳發動全面進攻,其中楊素、王世積兩支艦隊破除了長江障礙,大敗陳艦隊,牽制了眾多陳軍,有力地配合了對建康的合圍;燕榮艦隊由東海(今江蘇連雲港東南)沿海南下,溯江入太湖,在包山湖面大敗陳艦隊,完成了對陳的戰略包圍;高穎艦隊迫降了護衛京城建康的陳艦隊,為最終滅陳創造了條件,這一切均充分顯示了海軍艦隊的戰略地位和特殊作用。隋唐進攻朝鮮的戰爭規模巨大,海戰空前激烈。隋文帝、煬帝先後派水陸大軍30萬、戰艦300艘出征,艦隊均由東萊浮海直趨平壤。唐太宗曾先後三次派500艘戰艦、萬人艦隊,3萬人艦隊泛海航進。660年,唐高宗應新羅之請,派海陸大軍10萬擊百濟,蘇定方率艦隊由成山(今山東榮成)渡海,大敗百濟艦隊於熊津江口(今朝鮮西南部的錦江口)海域。663年,失敗的百濟王引日本海陸軍2.7萬人,攻擊留守唐軍,駐守新羅的唐將劉仁軌統率艦隊與日艦隊在白江口遭遇,海戰異常激烈,“煙焰漲天,海水皆赤”,四戰四勝,毀沉日艦400艘,日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火器和冷兵器並用時代的帆船艦隊
1.五代十國宋元時期—中國古代海軍裝備由冷兵器向火器的過渡和海軍建設發展的高峰
火藥的發明和火藥武器運用於作戰,開創了軍事史和海軍史的新時代。它對海軍技術裝備、海軍建設、海戰、海軍軍事思想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是最早發明和使用火藥和火器的國家。約在公元前後的西漢末年,我國就發現了火藥的主要成分。808年,我國煉丹家用硫磺、硝石和木炭三種原料製成的雛形火藥配方已經公諸於世。北宋仁宗(1023年至1063年)時,由曾公亮等編著的《武經總要》曾記錄了火藥配方和火球、火藥箭等火器。13世紀,火藥的製造技術經印度傳人阿拉伯國家,此後又傳人歐洲。西方學會製造火器是14世紀,比我國至少晚了400年。
南宋高宗(1127年至1162年)時,陳規發明了用竹筒製作的“火槍”,理宗(1225年至1264年)時又發明了“突火槍”,堪稱近代槍炮的鼻祖。
宋代武器製造規模龐大,由專設機構“軍器監”和“御前軍器所”負責,工匠達8700人之多,名州的軍匠尚不在其數;該機構內部分工細密,並已設立專門製造火器的“火藥作”。宋代的火器,可概略分為三類:一為燃燒性火器,如引火球、羨慕火球、火藥箭等;一為爆炸性火器,如霹靂炮、鐵火炮等;一為管形火器。宋代的荊州(今河北江陵)是火器製造中心之一,每月可製作鐵火炮一二千隻,產量驚人。火器最早裝備艦船,開始於北宋初期的真宗時。鹹平三年(1000年),神衛水軍唐福將所造水戰火器(如火藥箭、火球、火羨黎等)呈送政府,並受到獎勵。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監察御使林之平建議在戰艦上裝備火炮、火箭等,以加強今福建、廣東的海防。後來,南宋艦船均逐步配備了火炮等火器。兩宋艦隊在抗擊金和蒙、元的水戰、海戰中,也都廣泛頻繁地使用了各種火器,發揮了巨大效能。
元代也設定了專門製造和管理兵器的機構“軍器監”(兵改為“武備寺”)。元統一全國後,火器製造技術有了新的突破,至遲在13世紀上半葉,已發明了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火銑。此後,火銑即逐步推廣,並裝備艦船。
五代到元代的400多年間,為冷兵器向火器的過渡時期,冷熱兵器雖並用,但冷兵器逐漸減少,此時,還出現了幾種新穎的海軍兵器,這一切都表明海軍武器裝備的更新和面臨巨大轉折。
火攻既是中國古代海軍戰法的特點,也是突出的優點之一,在世界海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當時海戰水戰實施火攻使用的武器主要是火箭和火船,此後還使用過“火炬”等。南北朝時的陳朝在水戰中,曾以“熔鐵灑之”焚燒敵艦,威力極大。。五代十國時期,“沃油”、“猛火油”(石油)被用來攻擊敵方艦船,成為一種新型的海軍火攻武器。當時,我國已懂得石油的一些性能如“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槽,敵以水沃之,火愈熾’。919年的梁晉德勝水戰中,後晉將李建及以“木嬰載薪,沃油燃火”,從上游施放,“須臾煙焰騰熾”,“火發亘空”,大敗後梁艦隊。這是世界最早以石油作縱火劑的水戰。
最早使用煙幕於水戰,也發生在919年。當時吳越王錢鑼命水戰諸軍都指揮史錢傳罐率艦隊進擊吳艦隊,兩軍艦隊激戰於狼山江(今江蘇南通狼山江面)。吳越艦隊搶占有利陣位,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白晝如霧,吳師迷方’。鏇即乘機縱火突擊,俘吳戰艦400艘,大獲全勝。這是世界最早使用煙幕於艦隊編隊攻擊的水戰。
拋石機的使用由來已久,歷代皆有發展。五代後周世宗於956年進攻壽州(今安徽壽縣),“以方舟載炮(拋石機),自胡巴河中流擊其城”。這可說是艦炮的雛形。宋代,拋石機有了較大的發展,已可用來拋射火球、火炮等火器。這些新型海軍兵器的出現,當為宋元時期武器裝備發生轉折性變革的先聲。
五代宋元時期,中國的造船技術和規模,尤其是戰艦製造,均達到了又一高峰。在隋唐造船業發展的基礎上,短暫的五代十國時期的戰艦製造仍十分興盛:地處江河湖海地區的南方各國,常常一次出動戰艦四五百艘相互攻戰,甚至有一次派出千艘戰艦的記載C戰艦艦身龐大,其中還有可“容甲士千人”的巨型戰艦。造船規模和能力也相當驚人,後周僅開封一地,一年即可建造數百艘之多。
宋代是我國古代造船業的輝煌時期。當時的今江西、浙江、湖南、福建、湖北、江蘇、廣東、廣西、山東、四川等沿海沿江地區,均建有大批造船場,甚至山西、陝西等內地也設造船場。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廣州等地所造海舶尤為著名。各造船場一般每年額定造船300艘左右,也有高達i00艘、甚至六七百艘的。元代造船事業繼續發展,造船基地遍及沿海沿江地區,廣州和泉州所造海船繼續馳名於南洋各地。
宋代造船技術之先進更為舉世矚目。“造船務”為管轄修造戰艦的機構和場所。北宋戰艦造前,往往先繪製“海戰船式”(戰艦圖樣)。南宋則進一步先繪出“大軍船小樣,並長闊高卑步數”後,才開工打造;或者先製作“戰船木樣”(戰艦模型),然後比照仿製。處州知州張賞曾為造大船,事先“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這種運用圖樣、模型於戰艦製造,是對世界造船事業的重大貢獻,西方比我國晚了三百年。我國最遲在8世紀的唐代,已採用水密隔艙的船體結構,大大增強了抗沉性。宋代則廣泛採用了這種先進的船舶結構技術。
歐洲到17世紀才仿造我國帆船,造出具有水密隔艙結構的海船。指南針在宋代已裝備艦船,海上航行時“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櫻南北”,所以中國海船巨大,航行安全,已可載員數百乃至千人以上。宋代開始用棉布取代竹篷為帆,並造有10桅10牆大海船,桅桿設輪軸,可任意起伏,還採用了滑車掛帆。歐洲直到18世紀還僅有3桅帆船。為了修造艦船,北宋政府還在金明池(今河南開封西)修建了世界最早的船塢。西方則到1495年才在英國朴茨茅斯修建了歐洲第一個船塢。
宋代戰艦種類愈益增多,分工日趨細密。“多槳船”頭尾狹尖,平底,長83尺,闊20尺,置槳42支,載水軍200人,是一種內河瀕海兩用快速戰艦“海船”面闊而底尖,艦上配置“望斗、箭隔、鐵撞、硬彈、石炮、火炮、火箭(火藥箭)及兵器等”,是一種大型海戰艦船。車船到宋代已發展到頂點。南宋水軍裝備有“飛虎車戰船”、“海鰍車船”等多種類型車船。隨著帆船的發展和火器的推廣使用,車船和拍竿遂逐漸被淘汰。宋代出現的“鐵頭船”和“鐵壁樺嘴平面海鵲戰船”,更是世界造船史上的創舉。池州(今安徽貴池)船場曾由秦世輔主持設計製造了“鐵壁樺嘴平面鵲戰船”2艘,各長10丈和9.2丈,載水軍108人、水手42人和水軍70人、水手20人,兩舷裝設鐵板加強防護,艦首安裝似樺犁的犀利鐵嘴,以之衝撞敵艦,顯系一種防護堅固,攻擊力又強,既安車又置槳,“委是快便”的新型攻擊型戰艦。。這種世界最早使用金屬材料建造的戰艦,無疑在設計和製造方面均有高新的突破,也可視之為近代木質鐵殼輪船的先聲。
元代海船龐大。伊本·白圖太記載的元代戰艦,可張3一12帆,載水兵600名和水手400名。
總之,無論就造船規模、造船能力,或者造船技術、造船材料、艦船設備以及新型艦種的設計創製,宋元時期都超過了以前各代。隨著武器裝備的發展,這個時期的水軍也起來越強大。
中國古代海軍軍制方面的史料既稀少又不完整。漢代中央和沿江傍海的郡國均組建樓船軍,實行與陸軍相同的兵役制度,在訓練和校閱方面也有一定的規定。三國基本沿襲兩漢的體制,水軍仍為附屬於陸軍的兵種。但到三國末西晉初已有變化,海軍高級指揮人員開始專業化,已設“水軍督”職位。東晉時的“都督石頭水陸軍事”雖由陸軍將軍擔任,但可看出海軍地位的顯著提高,“水陸”已相提並論。南北朝時期的變化尤為明顯,設定了“水軍都督”、“上流水軍都督”、“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等高級海軍指揮官員,水軍地位和重要性頓顯突出。南朝的水軍訓練和校閱常在長江沿流的瓜步和南京玄武湖實施,北朝則在山東半島進行。隋唐海軍艦隊更加龐大,由行軍大總管、行軍總管統領出征,同時也設有“水軍總管”、“沿海水軍都知兵馬使”等高級海軍專業指揮人員。
五代十國時期在海軍軍制方面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南方的閩、吳、南唐、吳越、南漢等國中央政府均組建水軍,並設“樓船指揮使”、“樓船軍使”、“戰掉指揮使”、“水軍都指揮使”等海軍將領統領政府海軍艦隊。各國對水軍的訓練都十分重視。後周世宗為了攻滅南唐,在汁水造戰艦數百艘,利用南唐防卒訓練水軍,邊打邊練邊建,打到長江時已建成一支相當規模水軍。隨著海軍武器的發展和相互爭戰的需要,這時期的水軍開始從陸軍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軍種,形成國家海軍。
宋代,尤其是南宋的水軍規模更大。早在宋初,趙匡胤為了統一戰爭的需求,即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水軍。按照北宋軍制,禁軍在京都駐屯有神衛水軍、殿前司和步軍司所屬的兩支虎翼水軍,以及澄海弩手水軍等四支水軍。另在登州(今山東蓬萊)駐有強大的海軍艦隊,經常出海演練,系中央政府直接指揮的戰略性艦隊。廂軍中的水軍人數更多,分布在全國沿海、沿江地區的河東、陝西、京東、淮南、兩浙、江南、荊湖、福建、廣南、四川等10路。,從今山東到廣西的欽、廉,以及長江沿流均有水軍駐守,擔負海防、江防和治安方面的任務。北宋水軍設有“樓船戰掉都指揮使”、“巡海水軍指揮”、“沿海都巡檢”、“海上巡檢”、“水陸都巡檢使”等官職。由於南宋及其都城所處臨江傍海的地理位置和戰略態勢的嚴峻,水軍地位更為突出,作為國家海軍和獨立軍種的特徵更為明顯。紹興二年(1132年),南宋政府建立沿海制置使司專門管轄全部海軍,機構設在定海。當時海軍基地有許浦和定海兩處。為了阻截金軍南下,李綱建議於沿江、淮、河各帥府應各建“水兵二軍”,要郡另建“水兵一軍”,次要郡則另置中軍,號“凌波樓船軍”。南宋海軍建制計有:沿江水軍、明州水軍、鎮江駐紮御前水軍、沿海水軍、潮州水軍、江陰水軍、廣東水軍、平江許浦水軍、江州水軍、池州都統司水軍、漳州水軍、泉州水軍、殿前橄浦水軍、鄂州都統司水軍、採石駐紮御前水軍、建康都統司水軍、馬軍行司唐灣水軍、通州水軍、池州清溪雁漢控海水軍和兩淮水軍共20支分艦隊,官兵達52000人。,已是一支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各分艦隊分散部署在從今武昌到常熟、杭州灣的橄浦到欽州的江防、海防戰略要地,重點為長江下游和兩浙路沿海,協同定海、許浦兩基地的中央直接統率的戰略機動艦隊,以確保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安全。南宋艦隊由“沿海制置使”、“水軍制置使”、“沿江制置使”、“沿江水軍制置使”、“提領海船”、“海船指揮使”、“水軍統制”等各級海軍將領指揮統帶。金朝在與南宋的對抗中,也建立起一支具有一定規模的海軍艦隊。
元朝接管了高麗和南宋的海軍後,進一步建立起比南宋規模更大、兵力更強的海軍艦隊。元朝海軍建制為水軍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水軍萬戶府設達魯花赤1人、萬戶1人、副萬戶1人、經歷知事、提控案犢各1人、鎮撫2人統領。萬戶為世襲,將領和指揮骨幹均由蒙古、回回水軍充任。元朝海軍作為一大軍種,與陸軍統歸樞密院直接轄制。平時水軍萬戶府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重要港口和基地,遂行江、海防的防衛;戰時則統一調動,隸屬戰時指揮系統,遂行海戰任務。此外,元朝還設有“水軍元帥府”、“水軍總管府”和“水軍招討使”、“水軍總管”等統領機構和指揮人員。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元朝海軍還設立“炮軍、弩軍、水手軍”等專業兵種,以水弩手、水弩炮手組成,從而設定了“炮水手元帥”的職銜。專業兵種及其統領的出現,是中國海軍軍制建設新發展的重要標誌。
五代十國時期的南方諸國彼此爭戰和後周、北宋的統一戰爭,均須臾難以離開海軍。宋元時期的海戰水戰更為頻繁,精彩紛呈,戰法運用得當,甚至奇妙絕倫。這個時期既有國內江湖水域的水戰,也有大規模浮海遠征的海戰;既有使用冷兵器的水戰,更有運用火器的海戰,從而譜寫了中國古代海軍史的新篇章。
金宋戰爭中的水戰、海戰頻繁,規模大,戰法新穎。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金艦隊攻占明州後,追擊宋帝的船隊於浙江海域。宋將提領海船張公裕率艦隊,乘風雨大作,在定海畸頭海面,以大艦擊潰金艦隊,挽救了南宋。同年正月十五日,宋將韓世忠由江陰率水軍8000、海船百艘復還鎮江部署江防,阻截金軍北撤。三月十五日,金軍10萬分乘輕型戰船渡江北返至鎮江,埋伏於鎮江江面焦山兩側、隱蔽待機的韓世忠艦隊,迅即分數路出擊夾攻金艦隊。南宋水軍駕駛大型戰艦“乘風使蓬,往來如飛”,打得金艦隊潰不成軍,創造了以逸待勞,出敵不意,伏擊火攻,速戰速決,以少勝多的出色水戰戰例。但金艦隊擺脫黃天盪封鎖後,在舟中載土,加強了穩性,上鋪木板,兩舷鑿洞置掉槳,提高了航速,增強了防護,顯著改善了作戰條件。四月二十五日,金艦隊趁江上無風、宋艦大不便機動之機,令小船出擊,以火藥箭猛射帆蓬,大敗宋艦隊,遂得以渡江北返。金水軍以已之長擊敵之短,掌握戰機,實施火攻,水戰指揮藝術也十分巧妙。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軍再次南下攻宋。金艦隊水軍7萬、戰艦600餘艘駐泊密州(今山東諸城)膠西縣的陳家島(今膠州灣內),候風待發。宋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李寶駐紮平江(今江蘇蘇州),見事機緊迫,自請率領戰艦120艘、水兵3000人,北上遠航奔襲金艦隊。十月,進泊石臼山(今山東日照附近)。十月二十七日清晨,趁東南風驟,李寶下令按預定部署發起攻擊,迅猛衝人金艦隊,出敵不意,全殲金軍艦隊,創造了準確了解敵情、果斷掌握戰機、先發制人、火攻破敵、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海戰戰例。
紹興三十一年(正隆六年,1161年)十月,完顏亮率金軍主力進抵長江北岸,擬由採石渡江南下。宋廷為了挽救危局,派中書舍人虞允文為參謀軍事,到採石搞軍,他見事機緊迫,新任統帥尚未到任,遂即速部署江防。十一月初八日,虞允文布陣剛畢,金艦船數百艘就疾駛而來,前鋒70艘艦船已迫近南岸。虞允文急令部署在中流的海鰍船(車船)猛衝金艦隊,同時組織弓箭手沿江岸尾追齊射,水陸協同,激戰終日,大敗金軍。第二天清晨,虞允文又指揮戰艦上下夾擊,發射霹靂炮,艦隊預備隊也適時出擊,粉碎了金艦隊的反撲。金軍退卻,南宋轉危為安。采石之戰中,中國海軍最早使用了類似燃燒彈和煙幕彈的霹靂炮,要比歐洲早二三百年;虞允文還在水戰中採用了預備隊,更是水戰戰法的創舉。
蒙、元艦隊在攻滅南宋的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經過襄樊及陽邏堡、丁家洲和焦山水戰,殲滅了南宋水軍主力,為攻取臨安和最後滅宋奠定了基礎。雙方長江水戰,一次出動艦船數千艘乃至萬艘,實為中國古代海軍史上規模最大、爭戰最為激烈的江河水戰。臨安失陷後,宋帝趙禺於祥興元年(1278年)六月避於壓山(今廣東新會海中)。宋軍主帥張世傑錯誤地地採用大索聯結千艘戰艦、四周起樓槽、下鏇海中、列守海上堡壘的消極被動的防禦措施。次年正月,元將張弘范率海軍2萬,由福建沿海南下進抵壓山海域。他首先封鎖海口,切斷海上宋軍淡水和柴薪來源,並不斷增強兵力,緊縮包圍圈,使南宋海上堡壘陷人絕境。繼而於二月六日,元艦隊發起總攻,採用聲東擊西的戰法,突破宋軍海上堡壘,大敗宋軍。陸秀夫背負帝禺投海而死,南宋覆滅。
元朝大規模建設海軍,還用於發動海外戰爭。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動用艦船900艘、官兵2.5萬人,進攻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年),動用艦船達4400艘、官兵14萬人,再次進攻日本;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命史弼等率軍2萬、艦船千艘,遠涉重洋,進攻爪哇;還曾動用800艘艦船的大艦隊對占城、安南等國進行征伐。雖然由於不諳氣象、敵情等條件,這些遠洋作戰往往失利,但它說明了這支遠洋艦隊實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並“把中國在海上的統治範圍,從東中國海一直擴展到了南中國海”。
元末,朱元璋在削平南方割據勢力的戰爭中,曾多次大規模使用水軍,其中尤以朱陳鄱陽湖之戰最為激烈。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陳友諒趁朱元璋北上援救小明王之機,親率水陸大軍60萬、巨艦數十艘,圍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率水軍20萬迅急回援,雙方在鄱陽湖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決戰。初期在康郎山(今江西都陽湖內康山)水域的兩次水戰,雙方都動用了火藥箭、火炮等大量火器,互有勝敗,戰爭呈膠著狀態。第三次水戰,朱元璋在失利情況下,及時採納部將郭興的建議,決定改用火攻,於是令廖永忠、俞通海率勇猛水兵撐駕滿裝火藥和材薪的7隻漁船,乘風沖人陳軍艦群,鏇即縱火,風急火烈,煙焰滿天,湖水盡赤,焚毀陳艦船數百艘,斬殺2000餘人。八月二十六日,陳友諒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冒死突圍,湖口血戰10餘小時,無法衝出,復走徑江口,又遭伏擊,陳友諒中流矢死,艦隊全軍覆沒。朱元璋指揮得當,謀略過人,部署周密,及時搶占有利攻擊陣位,不失戰機地運用火攻,終於獲得全勝。在這次空前規模的湖泊水戰中,艦隊的編隊攻擊,水陸軍的戰略、戰役協同、各種火器的有機配合,對自然條件的掌握和利用,以及水戰戰法的靈活運用,都是極為出色的,創造了中國古代海軍史的光輝戰例。
2.明清時期—中國古代海軍從頂峰走向衰落
明清是中國古代海軍從頂峰走向衰落的時期。南宋開始大規模向海洋挺進,中國海軍艦隊控制了中國海東部;元代繼續發展,進而取得了南中國海的優勢;明國中國艦隊的遠航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巡航於印度洋海區,建立了馬六甲等海外基地,掌握了從日本到非洲東南岸、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控制權,無疑“中國在宋末、元、直到明初,曾是一個海軍強國”。
但到了15世紀下半葉後,中國古代海軍卻逐漸走向衰落。
明代,北起松花江,南達廣東沿海,西起怒江,東至黃海和東海,造船工場遍布全國。當時的南京龍江船場、淮南清江船場和山東北清河船場規模最大,其中龍江船場尤為著名。該船場長354丈,寬138丈,瀕臨長江,由“提舉司”管轄,分工較細,訂有嚴格的管理制度,並以建造大型海船(如大寶船等)著稱於世,同時也建造各類戰艦。永樂年間龍江船場年定額為131艘,宣德以後,增至319艘。永樂時,曾一次就令福建都司建造海艦達137艘之多;永樂最初的6年內,即建造艦船1700艘,足見明國中國造船規模和造船能力的強大。可是,從15世紀60年代以後(成化年間),興盛的造船業開始萎縮,龍江船廠的工匠到1531年竟被削減剩下不足100戶。明代中後期,造船業曾一度振興,但未能繼續下去。
明代造船技術高超,雄踞世界前列。鄭和第一次遠航的“寶船”,船長44丈,闊18丈,張12帆,錨重數千斤,排水量達千噸以上(一說1500噸),可載員千人。鄭和隨行人員鞏珍曾讚美說:鄭和“所乘之寶舟,體勢巍然,巨無與敵,蓬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1957年5月,在南京下關三漢河附近的中保村(寶船場故址),曾發掘出一個巨型舵桿,全長11.07米,有三四層樓高,舵葉高度也達6.35米,舵有如此之大,就可見寶船的雄偉。船越大,用料更加考究,各種設備更加複雜,工藝技術要求更高。鄭和艦隊各種艦船結構堅實,性能優良,航海技術高超,多次安全遠航,足見我國造船技術之先進。較鄭和遠航晚近一個世紀的哥倫布船隊僅3艘帆船、88名水手,最大的“聖·瑪利亞”號也僅250噸;1497年,達·伽馬遠航印度的船隻僅4艘,旗艦也不過300噸。
明代艦船型號齊全,種類繁多,大體可分為內河和海洋艦船兩大類。內河艦船基本因襲前代,但也有創新;海洋艦船則發展顯著,形制因地而異,種類極多。浙江有“蒼山”,福建有著名的“福船”,廣東則有更大的“廣船”。其中福船有六種型號,最利於海戰,不僅福建使用,浙江、廣東亦用。在北方則有吃水淺的“沙船”,在內河和狹窄港漢擊敵則有航行快捷的“鷹船”和“網船”。此外,還有以爆炸、燃燒火器進行攻擊的特種戰艦“連環舟”、“子母舟”、“火龍舟”等等。
清代沿襲明代造船技術和特點。除沿海、沿江設場造船外,海南島和台灣也建有船場,為抗擊沙俄的人侵,還在吉林烏拉(又名船廠,今吉林吉林市)設場造船。清代艦船種類也極繁雜,有趕增船、舫船、哨船、巡船、沙船、昵船、唬船等,以及內河各種型號的艦船,其中李長庚在福建督造的“霆船”,高大堅緻,配置火炮10餘門,火力很強。但從整體來說,仍遠遠落後於明代的水平。
中國古代海軍火器的發展,到了明代達到了高峰,拋射性、燃燒性爆炸性火器一應俱全。明朝中央政府設立“軍器局”、“兵仗局”,專門負責兵器(包括火器製造。明初,艦船上已裝備了碗口銑、火藥箭等火器。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銅鑄“大碗口筒”已配屬“水軍左衛”使用,這是現在世界最早的艦炮。明代中期之後,艦船裝備的各種火器大增,初步形成百步之內的火器殺傷系統。嘉靖年間,一隻福船上裝備的火器,即有重型火器大發煩1門,大佛郎機6座,碗口銑3個,輕型火器鳥嘴銑10枝、噴筒60個、煙罐100個、火藥箭300支、火磚100塊、火炮20個等,使用火器的人員已占戰鬥人員的50%。到萬曆年間,火器進一步增加,使用火器的水軍兵士已達70%。這個比例要比陸軍大得多,表明海戰已由從前的以冷兵器為主轉變到以火器為主的時代。這是劃時代的變化。明代海軍火器的發展,還表現在一些新型火器的創造。“水底雷”、“水底嗚雷”、“水底龍王炮”的發明和施用,當為近代水雷的雛形。而“水龍鴉”,這種以火炮發射在水中行進,自動鑽透敵艦的武器,則可視為近代水雷的先聲。那種以兩級火箭推動的、距離水面三四尺飛行的“火龍出水”,射程可達幾百步,則類似今日的艦對艦飛彈。這些新型火器的發明和創製,充分顯示了當時火器的發展水平。
火器普遍裝備艦隊,廣泛使用於海戰、水戰,必須引起海戰戰法的革新。由於艦炮裝備艦隻,原有的接舷、沖角、近距離的火攻戰法,開始向以艦炮等火器為主的、較遠距離的艦對艦攻擊戰法過渡,海戰面貌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而揭開了近代海戰的序幕。
朱元璋早在統一戰爭中,已經建立了一支相當規模的水軍。明朝甫即建立,樓寇即乘機侵掠沿海地區,為防範樓寇,明太祖和成祖十分重視海軍建設。當時的海軍可分為三部分:由中央直接管轄的擁有千餘艘戰艦的戰略機動艦隊;沿海衛所擁有的海軍,戰艦至少千艘以上;拱衛京師的長江水軍,約有戰船百餘艘。此外,還建立了龐大的運輸船隊,其中海上運輸船300餘只,內河運輸船1萬餘只。永樂十九年(1412年),明朝京城遷往北京後,山東登州也建立起一支直屬中央政府的強有力的戰略機動艦隊。正統之後,海軍一度衰弱,中央直屬海軍不復存在,沿海衛所海軍和長江水軍也大為減少。嘉靖之後,再度振興,特別是沿海衛所的海軍有較大加強,萬曆中期,僅浙江地區就有海軍官兵30152名,戰船1117艘,艦船的形制達20種。廣東、福建、南直隸以及北方的海軍也有所加強。這時的海軍已經不象明初那樣,平時在衛所,戰時登船作戰,而是地道的專業海軍了。
明代初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鄭和的遠洋艦隊。該艦隊組織嚴密,分工明確,武備先進,反映了明初海軍建設的成熟。現以第一次遠航艦隊為例,其中寶船62艘,連同其他艦船共317艘,官兵等共2.7萬多人。整個艦隊由正使太監鄭和和副使太監王景弘等統率,他們掌握外交、航行、作戰、貿易的決策權;海軍官兵和陸戰部隊由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等統領;財經貿易人員有“戶部郎中”、“買辦”、“書算手”等;航行保障人員有“火長”(領航員,掌管航海羅盤)、“舵手”、起落錨的“班鏇手”、“水手”和修理船的工匠等;還配有“通事”(翻譯)和醫官、醫士等。
整個艦隊各級指揮人員多達638名,醫務人員竟也達180人。鄭和艦隊的大艦配備千斤以上先進銅炮10門,以及火藥箭、火銑等海軍兵器。這支艦隊7次遠航印度洋,標誌著海軍力量達到中國古代海軍的頂峰。
然而好景不長。宋元以來,商品經濟雖然發展迅猛,但發育、成長不健全,往往受制於封建專制主義和“崇本抑末”的栓桔,海外貿易並未成為君主們廣泛和集中追求的目標,因而海上武裝力量的建設和不斷發展,缺乏經濟和持久的經濟動因,於是海軍建設呈現一種快慢不定,時高時低,甚至停滯不前的狀態。作為一個既是大陸國家又是海洋國家的中國,面臨著來自海上和陸上兩方面的外部危險,可是對於明政權的主要現實威脅,卻是來自北方瓦刺人的入侵。巧世紀下半期後北方告警,明政府的國家戰略決策隨之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特別是統治者視野狹窄,驕矜苟安的心態,缺乏對世界形勢和海洋戰略態勢的深刻理解和預見,加上政治腐敗和混亂,財政拮据,統治階級更加貪婪腐化,社會動盪不安,於是出現了海軍建設衰微的趨勢。
1463年,明英宗即位時即頒布旨令,不僅禁止建造遠洋船舶,而且削減戰艦和武器,結果各個海軍建制單位均進行裁減。此前,浙江原有700多艘海上艦船,到1440年被裁減過半;南京新江口的400艘艦船,到1474年只剩下140艘尚能適應海上作戰;山東登州的艦隊原有艦船100艘,到1448年僅留下18艘,其中4艘還被用於海上運輸,1503年又減為10艘,最後竟只剩下3艘戰艦了,可謂裁撤殆盡。1452年,海上基地撤回和例行中斷後,造船業受到沉重打擊,甚至這一行業已被人們所遺忘。。大型遠洋戰艦停造後,到16世紀初,明海軍擁有的最大艦船僅可載員百人,隨之海軍官兵薪傣銳減,士氣低落,逃亡現象嚴重,這種艦小、炮小、軍心浮動的艦隊,只能在近海海域抵抗樓寇和海盜的侵襲,由遠洋轉回近海,原來叱吒海洋的明初艦隊,從此失去了往日的光輝和銳氣,雖然一度振興,但從整體上講曾長期居於世界前列的中國古代海軍無可奈何地開始走向衰落。清代前期,仍然承襲了明代的海禁政策,海軍建設不僅停滯,甚至倒退,艦隊裝備陳舊,沿海設防廢弛,海軍戰鬥力虛弱,海防危機油然而生。18世紀中葉後,衰落趨勢明顯強烈。
明建國之後,曾多次與外敵進行海戰。洪武七年(1374年),靖海候吳禎率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舟師出海,於琉球大洋大敗倭寇,俘獲其人員和船隻。永樂七年(1409年),安遠伯柳升率領的舟師出海於靈山(今山東膠東南海中)大敗倭寇,斬溺甚多,然後追擊至金州(今遼寧金縣)的白山島,有一支艦隊甚至追擊到朝鮮義州界。鄭和艦隊在海外也曾三次用兵,均取得了勝利。這是有史以來中國古代海軍距離本土最遠的海外作戰,足見其兵威之盛。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後的十餘年間,中國古代海軍在近海打擊人侵倭寇的次數不勝枚舉,僅1552年一戰,俞大酞率領艦隊就曾焚敵船50艘。當時有人還提出“海上之戰,不過以大船勝小船,大銑勝小銑;多船勝寡船,多銑勝寡銑”的海戰理論。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明朝水軍都督陳磷、副將鄧芝龍與朝鮮海軍名將李舜臣率領聯合艦隊800艘戰艦與日艦隊500餘艘艦決戰於露梁海域,打得日艘隊司令島津義弘僅率50餘只戰船逃脫,其餘全部被殲。此次海戰是古代帆船艦隊在遠東海域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海上伏擊戰、殲滅戰,它充分顯示了中朝海軍將領的高超指揮藝術和強大的海戰實力。
清代的中國古代海軍可分為兩部分:沿海海軍和內河海軍。初期,海軍曾有一定的發展,主要表現在沿海建立了7支水師。以後又加以整頓,在江南、福建、廣東設立了水師提督,在旅順口、大沽口、吳淞口、廈門、台灣、虎門等海防要地設水師營等。
清代初期的重大海軍可分為兩部分:沿海海軍和內河海軍毛初期,海軍曾有一定的發展,主要表現在沿海建立了7支水師。以後又加以整頓,在江南、福建、廣東設立了水師提督,在旅口、大沽口、吳淞口、廈門、台灣、虎門等海防要地設水師營等。
清代初期的重大海戰大都是圍繞著台灣問題展開的。16世紀,西歐殖民者開始向東方擴張,同時入侵中國。1642年,荷蘭殖民者侵人台灣,並於1642年擊敗西班牙後獨占了台灣全島。永曆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1661年4月21日),民族英雄鄭成功率軍2.5萬人、戰艦數百艘,從金門島料羅灣啟航,先取澎湖,後於四月初二日拂曉趁漲潮和濃霧之機,突然從禾寮港登入,進而圍攻嵌城(今台灣台南市)。荷軍組織反擊,雙方展開了海戰。鄭成功令陳廣、陳冲率戰艦60艘包圍了荷蘭艦隊,靈活採用火攻、炮擊、接舷等戰術,擊沉荷蘭主力戰艦“赫克托”號,又燒毀荷艦一艘。此後,又在八月十二日的海戰,鄭成功率陳澤等用伏擊、接舷、炮擊、火攻戰術,擊敗考烏所率艦船10餘艘、水兵700餘人的支援艦隊,取得毀沉荷艦2艘、俘獲小艇3隻、殲敵480餘人的海戰勝利。由是,荷蘭總督挨一頑抗8個月後,不得不於1662年2月1日被迫在投降書上籤字,淪亡38年的台灣,終於重新回到祖國懷抱。鄭成功組建了強大艦隊,出色地指揮了海戰,為收復台灣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不愧為名垂青史的偉大民族英雄和傑出的海軍將領。
1681年統治台灣的鄭經病故後,鄭氏集團發生內亂,荷蘭殖民者企圖捲土重來,康熙帝正確決策,令水師提督施琅統領艦隊進軍台灣。鄭氏集團名將劉國軒率戰艦200餘艘、精兵2萬餘人,據守台灣門戶—澎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五日,施琅率戰艦230餘艘、官兵2.1萬人由銅山(今福建東山)啟航,先頭艦船於十六日駛抵澎湖海域。十七日,施琅艦隊齊集後,發起了第一次攻擊,結果不分勝負。二十二日,雙方展開決戰。施琅令陳蟒與董義等各率50艘戰艦,從東西兩個方向佯動,牽制和夾擊鄭氏艦隊,自率艦隊主力(大鳥船56艘)繼進,其餘80艘艦船為預備隊。海戰開始,清艦隊預先占據了上風上流的有利陣位,施琅率主力迅即突入劉國軒艦隊,以5艘合圍1艘,經過激烈炮戰,鄭氏艦隊難以抵擋,劉國軒被迫率殘兵敗將逃逸,澎湖鄭軍覆沒,施琅奪取了進攻台灣的前進基地。由於施琅的傑出指揮和正確部署,取得了澎湖決戰的勝利。此後不久,鄭克瑣降清,台灣復歸統一。
此外,清朝的東北水師於順治十五年(1658年)的庫爾乾河戰役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雅克薩戰役中,都曾大敗沙俄侵略軍;廣東水師於嘉慶十三年(1808年)在澳門擊退英國殖民者1J艘軍艦的進犯,為保衛祖國的領土、領海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道光、鹹豐年間,清軍水師曾英勇抗擊了英法侵略軍的海上人侵,但由於雙方武器裝備的明顯差距,清軍水師始終未有組織過一場真正的海上決戰。湘軍水師與太平軍水營的長江水戰爭奪劇烈,互有勝負,可是由於太平軍領導集團戰略指導思想的消極,喪失了戰機和主動,長江控制權逐漸易手,最終導致了敗局。
中國古代海軍建設的成就是巨大的,無論在艦船製造、航海技術,還是海軍建設、海戰藝術等方面,均長期居於世界前列;中國古代海軍長期以來一直是東方的主要海上武裝力量,矗立於世界海軍強國之林。中國人民和廣大海軍官兵以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創造了一部光輝燦爛的中國古代海軍史。
綜述
縱觀中國古代海軍的全部歷史,與世界古代海軍相比較,實頗具特色。其一為江河水戰頻繁並連綿不斷,且戰法精妙絕倫。雖然戰爭具有對外和對內兩種不同類型,可是中國古代內部爭奪權力的戰爭卻居於主導地位,因而江河水戰眾多,內河艦船種類齊全和先進,海軍兵器不斷推陳出新,戰法也隨之屢屢改進,整個古代世界唯有長江上呈現一連串精彩紛呈的水戰,實為世界海軍史所罕有。其二為海軍發展的曲折和往復。中國古代海軍誕生於長江,後由內河推進到海洋,長期主要活動於瀕海和近海海域,宋元明時期才發展到遠洋,以後又回到近海海域,這與歐洲海洋國家的海軍從近海到遠洋則不盡相同。其只為技術裝備的先進。無論艦船製造、航海技術、海軍兵器等方面,中國曾長期居於世界前列。其四,火攻為中國古代海軍戰法的優點和突出特點。針對古代艦船均為木質船體的特點,中國古代海軍在艦艦攻擊中,一貫重視和不斷採用火攻戰法,火箭、火船、沃油、火藥箭等燃燒性火器,在海戰和水戰中往往成為決定勝負的主要手段和因素,這與西方古代海軍主要採用沖角和接舷戰法有顯著差別。這些特色既是中國古代海軍的優點,也表明了它有著發展不甚完善的缺陷。
長期以後,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與西方不同,是一個相對獨立和隔絕的自然單元。中國的北、西、南三面大部以高山為屏障,東南瀕臨海洋,在工業、科技落後的年代實為天塹,面海方向始終未構成重大憂患。西方各國的封建經濟以莊園制經濟為基礎,商品經濟發展迅速而健全,君主們竭力追求財富和貴重金屬;中國的封建經濟是以家庭小農經濟為基礎,商品經濟受到種種制約,發展十分緩慢又具有深刻缺陷。歷代統治者還竭力倡導“崇本抑末”,除了形成農民的安土重遷的觀念外,更極大的阻滯了航海事業和海外貿易的拓展。在封閉的人文環境中,儒家思想長期以來成為整個社會道德規範,主宰著歷代社會思潮,加上傳統軍事思想某些缺陷的沉澱,這就不能不束縛著中國國防觀念和海洋觀念的更新和發展。雖然中華民族的文明曾持續地高速發展,但由於以上種種因素,一統天下的封建專制政權,就成為二千多年來中國各階級和各集團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於是就出現了一方面海軍技術裝備和海戰、水戰戰法的不斷創新,為世界古代海軍的發展作出了偉大貢獻,同時又呈現了江河水戰特別活躍和進軍海洋的艱難曲折局面。尤其令人磋嘆的是,從15世紀中葉開始,尤其是從18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海軍無可奈何地走向衰落,而西歐各國海軍卻迅速發展,馳騁海洋,進而於19世紀率先進人近代海軍發展階段,並對中國的海洋和海防構成了嚴重威脅。中國海疆從此進入了多事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