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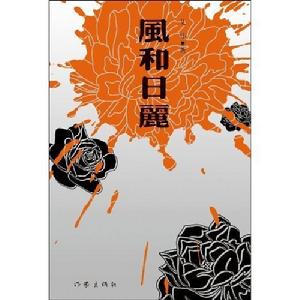
一位神秘將軍的風流韻事,一個女孩隱秘的身世,從楊小翼的悲劇一生中娓娓道來。楊小翼渴望父愛,但在媽媽那裡卻始終得不到滿意的答案,在劉伯伯的幫助下,她終於鼓起勇氣北上尋找父親。與楊小翼青梅竹馬的劉世軍在她走後與好朋友結了婚,曾經暗戀她的伍思岷因自尊心受傷而故意傷人,被迫遠走他鄉。愛情的遠去,更加重了楊小翼對父親的歸屬感。在北京,楊小翼不甘被動地等待,於是她有預謀地接近同父異母的弟弟尹南方,並如願地見到了父親,不料尹南方卻陰差陽錯地愛上了她。私生女楊小翼的出現使將軍家裡引起了軒然大波,並釀成了無法挽回的悲劇。在楊小翼彷徨無助的日子裡,劉世軍給了她最大的安慰和支持,那段兩小無猜的愛情於若干年後,在二人孤獨的心中瘋狂滋長……
作者介紹
 艾偉
艾偉艾偉,一九六六年出生。主要作品有:長篇《愛人同志》、《越野賽跑》,小說集《鄉村電影》、《水中花》、《小姐們》、《水上的聲音》等。其作品主要將“生命本質中的幽暗和卑微”作為敘事聚焦的對象,作為“存在的勘探者”,其作品充滿了人性關懷。曾獲得《當代》文學獎,全國大紅鷹文學獎,浙江省首屆文學之星獎等獎項。部分作品譯介到國外。
寫作札記
角度
終於敲定了《風和日麗》的寫作角度。小說從原來以母親為中心轉移到以楊小翼為中心。楊小翼將是這部小說的視角。這是一個很小的角度,但我希望寫出詩史的氣息,希望這部以楊小翼為主角的個人史時刻聯繫共和國的大歷史。我把這句話寫在了畫板上,時時提醒自己。
這是有可能的。楊小翼是一個革命的私生子,在某種程度上私生子這樣的身份是一把鋒利的匕首,它雖然在革命之外,但有可能刺入革命的核心地帶,刺探出革命的真相。
寫作是寧靜的工作
因為《風和日麗》的寫作,日子變得簡單而寧靜。對我來說,寫作帶來的綿長的充實感是任何工作都無法獲得的。
是,我喜歡呆在屋子裡。是,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是,他們現在還是孩子,馬上要談戀愛了。是,他們將伴我一年或更長。是,他們有的生活得好,但多半命運多舛。是,這是我的遊戲,我在黑暗中,和他們玩。
想起一部書
想起《靜靜的頓河》。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充滿了土地的氣息。它是如此遼闊,如此充滿了活力,就是在最日常的生活中,依舊可以見出人的偉大。它在處理革命時,是那么忠實於生活,忠實於人本身。我驚嘆於史達林時期居然可以誕生這樣的作品,他竟然把一個手上沾滿了紅軍鮮血的人塑造成了一個正直而善良的英雄。同時,他也不醜化革命,而是寫出歷史深處的那種真實,寫出革命的洪流下的個人行為。
革命作為主導中國20世紀最為關鍵的一種思潮,它的影響今天依舊複雜幽深地隱藏在我們的血液里,作用在我們生命的深處,聯繫著我們的情感反應。在革命被“告別”後,我們的情感和我們的理性全然不是合一的。我記得美國人占領巴格達時,我百味雜陳,一方面理性告訴我,薩達姆命該如此;另一方面我的情感卻是無比複雜,很難用高興或悲傷來形容。這種複雜性不是理性可以解決的,它連結著我們的經歷、我們的歷史。我們不能重新出生一次,變得像一個嬰兒。革命曾經是我們的父親,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革命的遺孤。
要寫出革命語境中這種人的複雜性,寫出革命對人性的塑造——這塑造有好有壞,有信仰帶來的幸福感也有人性的壓抑。很早以前我就說過,作家要做的工作不是為歷史注釋,它不追求“歷史正確”,也不追求“政治正確”,作家的立場就是人的立場,因此,惟有關心在歷史洪流中的人性的處境才是作家的職責。
公允地面對世界
哈金的《等待》無疑是一部批判體制戕害人性的小說,但哈金非常公正地對待體制,他寫出了體制專制的一面,同時也寫出了體制仁慈的一面——最後,是體制把男主人公遠在鄉下的老婆和孩子接到城裡來,成了受公家照顧的人。
某種意義上,哈金寫的是關於“閹割”的故事,他讓那對戀人在18年中沒有性生活。所有的細節都是在日常的經驗上展開,這對戀人在漫長的等待中倍受煎熬,他們的情感因時光流逝而慢慢變質、扭曲。
如果這個故事讓一個國內作家來寫會是什麼樣子?我想一定不會這么公允,一定會呈現如下兩種情形:一種把這對男女的愛情崇高化、悲劇化,從而達到批判體制的目的;另一種會迅速地極端化、寓言化。國內許多作家沒有耐心描述18年中一對正常的男女不發生性關係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的手裡,也許在這個關於“閹割”的故事中,主人公真的會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閹割”這一行為是多么有解讀的可能性啊,“文革”中人性不是很壓抑嗎?不是連思想也被閹割了嗎?這正對批評家們的胃口。
“先鋒”以來,中國小說在處理類似問題時,總是有一個概念放在那兒,往往用極端偏激的方式處理。這種方式迅速地掠過小說需要的物質層面,抵達某個形而上的目標,很少關心日常的貼著大地的人類活動。這種處理讓人物成為某個概念的符號,使人成為非人。
我們曾經把革命崇高化,後來把革命簡單化、妖魔化。我必須忠實於事實,公正地對待歷史,公正地對待小說中的每一個人。即使是一個壞蛋,也依舊需要懷著對生命的敬意來書寫。必須尊重你筆下的每一個人,用心傾聽他們的聲音。
長篇小說的基本價值元素
考察《紅與黑》的經典化過程是非常有意思的。《紅與黑》剛出來的時候,整個法國幾乎沒有人認為它是好小說,許多人認為這部小說做作、平庸,充滿了胡言亂語。司湯達實在沒辦法,他只好自己跳出來替《紅與黑》說話,當然,他是化名表揚自己的,他夸自己的作品寫出了“人類心靈的本質”。可是整個法國依舊對這部作品保持沉默。那是19世紀30年代,司湯達非常激憤,恨恨地說,他的作品是給20世紀的人看的。
後來,這部小說的經典性顯露出來,小說的命運幾乎印證了司湯達自己的預言。
《紅與黑》確有值得病詬之處,在一些地方,敘述顯得粗糙、匆忙,不夠考究,對上流社會及教會的描寫也充滿了偏見,有漫畫化的傾向,但依舊難掩它的熠熠光彩。這部小說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包含著長篇小說最基本的價值元素:複雜的人物、豐富的情感和令人喟嘆的命運感。
《紅與黑》里的於連,是小說人物畫廓中無法忽略的人物。於連是如此複雜,他在人類價值的兩極,是一個矛盾的產物:他是如此自私又是如此慷慨,如此自卑又是如此驕傲,如此膽怯又是如此勇敢,如此理智又是如此瘋狂,他是個既黑暗又光明的人物。
同時,這部小說中的情感處理相當獨到。如果說這部小說中於連更多地呈現出人類的黑暗,那么雷納爾夫人絕對是光明的,她是個善良的人,她對於連帶著母性的無私的愛,是小說中最打動讀者的一部分。雷納爾夫人的存在使這部小說的光亮與陰影得以平衡。
命運感應該是我們之所以寫長篇的一個理由之一。在《紅與黑》里,於連出場時是19歲,他上斷頭台只有23歲,小說的時間只是短短的四年,但讀完小說,我們感到像是過完了長長的一生。好的長篇莫不如此。
情感是小說的物質基礎
一部好的長篇小說,要被一代一代讀者喜歡,一定要有好的情感故事。《安娜·卡列妮娜》如此,《傲慢與偏見》如此,《日瓦戈醫生》也如此。
《傲慢與偏見》簡直是一個通俗的愛情故事,用今天先鋒式的解讀辦法大約很難對其闡釋出深意,但這絲毫無損於它的經典地位。《傲慢與偏見》講述的情感故事,令一代一代的讀者著迷。
“先鋒”以來,深度模式一直控制著中國作家,這種對所謂深刻的追求導致在小說里只有冰冷的理性。小說不是寫詩,不是靠幾個意象就可以完成。深度也不是靠結構、靠寓言即可以抵達。小說必須寫出人在歷史洪流中的歡欣和血淚,寫出命運的弔詭,寫出眾多力量作用在人性中的波瀾。
是的,小說里有作家的思想背景,但決不是思想,小說不是去說明什麼偉大的發現或對歷史重新書寫,小說永遠關注人在時代意志下的無以言說的複雜情感和處境。小說是用來感受的,不是用來分析的。我對好小說的評判標準是:閱讀完一部小說,像是重新活了一次,會百感交集,看待世界的目光會拉遠,對世界的看法在那一瞬改變。即使只是一剎那的改變,也夠了,因為這個堅硬的紋絲不動的世界終於有了柔軟的時刻。
小說的結構應該像一棵樹,自然生長
小說是語言的藝術,也是結構的藝術。小說的結構往往是作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但作家不能夠為了某個理念去設定一個結構,結構不能過分強勢。如果結構強勢,那一定會格式化生活的豐富性,格式化人物的複雜性。好的小說結構應該像生活本身,要像一棵自然生長的樹。
《風和日麗》的寫作終於抵達終點了。重新打量這部小說,我驚訝地發現,這部小說具有奇異的對稱性。在《風和日麗》這棵樹上最初萌生的眾多嫩芽,隨著時間的流逝,按自己的方式生長成了樹枝,向天空展示出它們各不相同的身姿。在小說結尾處,枯枝重現,開頭的元素一一浮現,小說結束在開始的地方。這種對稱性不是刻意為之,更像是自然造化塑造而成。
主題思想

《風和日麗》從尋父開始,到審父結束,其實是完成了由尋找並理解革命到全面審視革命的一個艱巨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楊小翼完成了自己尋父的心愿,同時也實現了自己審父的目的。艾偉認為,楊小翼的出生、成長、愛情、婚姻、傷逝,無一不與那個年代躁動不安的歷史相映照,她每一次的命運轉折都涵蓋著新中國曲折蛻變的絞痛,她那一代人對於父輩的尋找,又暗示著中國人理念中千百年來未曾改變的尋根意識。
小說充滿了人生的殘酷和無奈,可《風和日麗》這個書名聽起來卻非常陽光,兩者明顯矛盾。艾偉說,小說里雖然有很多悲劇性元素,但主人公卻是在用含淚倔強的微笑面對沉重的歷史。“在小說里,儘管歷史詭異,但人性總的來說是善的。我試圖寫出苦難人間的溫情時光,寫出愛、友誼、家庭的持久力量,寫出絕望中的希望。在這個意義上,我起了這么一個充滿希望的、溫暖的名字。另一方面,當然有反諷的含義在,小說的世界可以說是風雨雷電,但我用了一個完全相反的詞。”
人物塑造
小說塑造了多個人物,比如楊小翼、將軍、劉世軍、伍思岷等人。在這些人物中,艾偉自評將軍寫得最好,“他的無情和有情,很複雜很矛盾。將軍在這部小說中幾乎是主宰者,他出現不多,卻無處不在。當我寫到將軍埋葬天安,把早年的情詩‘願汝永遠天真,如屋頂之明月’獻給天安作為墓志銘時,我感到自己真正了解了他——他是一個孤獨的人。他可能是歷史悲劇的創造者,但也是歷史悲劇中的一分子。在這部小說里,我是在一種更廣大的時空背景上看待歷史。因此,將軍是歷史的勝利者,但同時也是歷史的犧牲者。人人如此。”
對於先後遭遇愛情夭折、婚姻失敗、痛失愛子、被父親遺棄等諸多傷痛事件的楊小翼,艾偉滿懷同情:“因為小說是從楊小翼的視角出發,在技術上她需要有足夠的彈性和包容性。楊小翼雖然是女性,某種程度上,她和作者是合二為一的。在小說里,她是這個世界的感受者,歷史的承擔者、批判者。她的內心感受就是我的內心感受。她是一個令人喜歡的人,我有一個朋友讀完這部小說後告訴我,如果楊小翼在現實生活中,他會愛上她。她寬容、倔強、沉靜、智慧,這是我想要的楊小翼。”
價值
對於這部構思多年才寫出來的小說,艾偉期待頗高,他希望讀者喜歡、認可這部小說。“我一直認為小說的生命不是文學界或批評界給予,而是由讀者賦予的。一部小說只有參與到和讀者的精神對話中,才有持久的生命。”艾偉說,在他的這部小說里,楊小翼和劉世軍艱難的浸入骨髓的情感,讀者會喜歡,“女性讀者會喜歡劉世軍這個人物。我希望讀者讀完《風和日麗》會有這樣的感受:一夜讀完,如過長長的一生。”
從目前收到的反饋來看,小說的確在情感上打動了人,這讓艾偉很滿足。他說:“在我看來,小說首先在情感上打動人,然後再判斷其別的價值。現代學理有那么多分析的方法,即使一部破綻百出的小說,依舊可以分析出偉大的意義。其實有時候,日常生活的廣闊中也有其深邃的精神性。我相信小說最深刻的東西就是情感。”
書評
60後作家艾偉創作的長篇小說《風和日麗》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推出單行本前,《風和日麗》曾因在《收穫》雜誌上連續兩期連載而廣被文學界關注,新書上市後也受到不少讀者的注意。文學評論家張莉認為,艾偉一直以來沉默而切實地寫作著,並不為純文學界之外的讀者廣為熟悉,但其實他應該獲得更多的關注,僅就《風和日麗》而言,他深切思索的努力使這部小說遠離了當下那種生活主義的寫作模式,非常難得。《風和日麗》寫的不是我們國家的革命史。它寫的是女人楊小翼從少女到老年生命中出現過的思念,美好,性慾,以及痛楚。其實楊小翼又與革命緊密相關,因為她出生於革命世家:她是私生女,父親是我們共和國的著名將軍,由此,她的一生注定隨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起伏。
儘管楊小翼與共和國共生共長的一切沉默如謎,但革命,傷痛,愛戀,生離,死別,都在她身上隱密鐫刻了。小說讓我想到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毫無表情的老年女性,你以為她們什麼也沒有經歷過,你以為她們身上只有簡單如水的日常,但非常有可能的是你錯了,在嚴肅的被歲月日益損毀的面容之下,有敏感多愁的神經,也有抵擋千鈞的堅韌。楊小翼就是這樣的女人,她看起來像其他薄命紅顏一樣離不開男人的支持,但內在里,她強大而豐富的心靈卻自有寶藏。
楊小翼經歷文革,經歷愛情的背叛,意外地與父親在流放之地四川重逢。年輕、勇敢、一腔熱愛的女兒偷偷放走了父親,之後,她結婚,生子,歷經世事滄桑。——小說中的愛情是綿長的和動人的,但是,我被打動的首先不是她的愛情,而是關於她的兒子。這個年輕人有主人翁責任感,渴望報效國家。你看,血緣在這裡發生了多么奇妙的又理所應當的作用,——楊小翼的兒子身上流著外祖父的革命熱血。“願汝永遠天真,如屋頂之明月”。這個青年死去後的碑文是尹將軍題寫,這也是當年將軍在法國留學時寫下的詩句。這詩句是不是很動人?它柔軟又堅硬,它深情款款又冰涼如水,它懵懂無知又洞若明火。你能從詩句中感受到將軍的深情,但是,你更能感受到的是作家艾偉對革命歷史的浪漫主義情懷。
這是故事的核心部分嗎?我堅定地認為它是。我以為,作家艾偉敏感地捕捉到了楊小翼身上那被隱藏著的意義:楊小翼連線了革命的父親和革命的孩子,最終,送走了兒子又送走父親,沉默地接受一個又一個發生在她身上的命運際遇。在日益現代化和物質化的今天,讀那些與革命理想有關的往事,回視、翻檢那些我們國家的革命史,怎么能沒有感慨?
《風和日麗》一路讀來有嘆息,老實說,這個故事很有被寫成通俗讀物賺足大眾眼淚的危險。好在小說家是謹慎的,他在閱讀快感和雅俗共賞方面尋找著某種平衡。當然,我也不得不說,艾偉書寫大院子女們的生活有些吃力,有些隔。而更大的閱讀障礙也不應迴避,即,作為讀者,你無法無視和克服自己的八卦心理,你無法不去猜想楊小翼到底有原型嗎諸如此類的問題。因為楊小翼的紙上生命中有一些與現實對應的地名和事件,比如顧城事件。而這樣的問題和閱讀心理,自《收穫》去年連載時就常在網路中被討論。看來,如我一樣的讀者也不在少數。我想表達一位讀者的理解:《風和日麗》雖以中國革命的真實歷史為依託,但是,它的故事不一定因為真實才有說服力,其實這個故事也是有超越國度的可能的,——小說中對革命的悖論講述難道不會發生在別的什麼時代,或者別的國家?
艾偉是一位出生於六十年代的作家,一直以來沉默而切實地寫作著,並不為純文學之外的讀者廣為熟悉。我認為他的工作應該獲得更多人的關注,僅就《風和日麗》而言,他深切思索的努力使這部小說遠離了當下那種生活主義的寫作模式,非常難得,你能感受到作家渴望穿透生活表層抵達內在肌理的努力,你能感受到他對社會、對人生、對歷史的深入認知。我想,《風和日麗》的意義在於小說家書寫了傳奇外殼之下的革命倫常,作家盡其所能地將那些日常中的“風和日麗”揭開來,使我們在這個白紙黑字的世界裡共同經歷那曾經的狂風呼號,電閃雷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