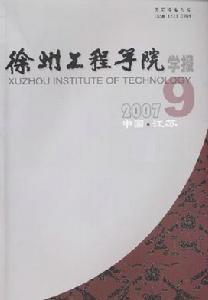 《徐州教育學院學報》
《徐州教育學院學報》期刊主辦
徐州工程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編輯委員會
主 任:劉延慶
委 員(按姓氏筆劃為序)
馮長君 劉延慶李 平 李蘇北 沈 超
宋農村 張仲謀陳宏偉 邵曉根 秦衛東
倪宏昕 徐德蘭殷惠光 唐 翔 黃傳輝
主 編:劉延慶
副主編:沈 超 宋農村
執行副主編:張 楠孔凡濤
主管單位:江蘇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徐州工程學院
編輯出版: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編輯部
刊期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2004年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1994年
詳細介紹
《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是徐州工程學院主辦的學術刊物,是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收錄期刊、萬方數據——數位化期刊群上網期刊、《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收錄期刊。主要刊載哲學、歷史學、文學、經濟學、新聞傳播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從2007年起,重點建設“瞿秋白研究”、“楚漢文化研究”、“金瓶梅研究”、“中國古典戲曲研究”、“經濟與管理研究”等欄目。
《徐州工程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主要刊載數理科學、建築科學、食品科學與工程、生物科學、機械製造、金屬材料學、自動控制、無線電、計算機技術、化學與環境工程、能源與動力工程、交通運輸等基礎研究和套用研究方面的學術論文及科研報告。
人員組成
編輯部現有人員14人。人員名單:
張楠、孔凡濤、梁化奎、徐永銘、蔣成德、何穎、劉自強、燕善俊、朱春花、崔思榮、鄒麗楊、曹晨、翟愛東
網站管理員
姓名:朱春花
主要欄目
政治與哲學研究 法律法制研究經濟學研究 中外文學研究
美學研究 語言文字研究
教育教學研究心理學研究
特色欄目
社會科學版特色欄目
自然科學版特色欄目
優秀文章
從《多餘的話》看瞿秋白的歷史貢獻和局限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瞿秋白曾經要求隨軍行動,毛澤東、張聞天也曾經請求中央讓瞿秋白隨軍行動。可是,中央最高三人團還是拒絕了瞿秋白的要求和毛、張二人的請求,將瞿秋白留在瑞金。中央紅軍剛剛撤離蘇區,國民黨即以1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實行血腥的“全面清剿”。次年2月24日,瞿秋白在轉移的途中,於長汀縣境內被國民黨保全14團2營俘獲。4月25日,瞿秋白的真實身份暴露,敵人如獲至寶,將他又移押在駐長汀中學的國民黨第36師師部監禁。瞿秋白身陷囹圄,十分清楚自己生命最後結局,他“願意乘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坦白的話”。從1935年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間,瞿秋白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自傳性的文章近兩萬字,分為“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主義路線”、“文人”和“告別”等七個部分。文章開頭以《詩經·離篇》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作為引言。這兩句詩表達了東周大夫出行至舊都鎬京,目睹宗廟宮室毀壞,盡為禾稼,感傷不已,所抒發的憂國之情。秋白同志在《多餘的話》中明確地說:“我願意趁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坦白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他希望人們了解呀,他說:“人往往喜歡談天,……能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通觀《多餘的話》秋白同志是以關切黨的事業,懷念同志戰友的真摯感情,認真地總結了一生,嚴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血淋淋的靈魂赤裸裸地放在顯微鏡下,坦然無私地自我審判,也留給後人去品評是非功過,“願意受歷史的最公開的裁判”。《多餘的話》也流露出了消沉、灰暗的情緒,不那么健康,不那么鼓舞人,但是這些消沉和灰暗掩蓋不了蘊涵在《多餘的話》中的光輝。
《多餘的話》的光輝之處,僅就其嚴格地剖析自己這一點來說,大體有兩層意思。一是秋白同志在《多餘的話》中對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以至文藝觀的剖析中,都有極其精闢的見解。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
瞿秋白同志,對政治是極端熱情的,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堅定不移的。他從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就“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都比較有興趣。”“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現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是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覺得很有趣。”秋白同志在《多餘的話》中明確地表示:“要說我自己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切的。”“我二十一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正是從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很快轉到了馬克思主義。”“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還應當指出,秋白同志在監獄中尖銳地批判過胡適、批評過三民主義,痛斥過蔣介石及其主子,並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級軍官進行過革命思想的宣傳。秋白同志對監獄醫生陳炎冰說: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土地革命,毛澤東的土地革命、農村割據主張是正確的。他在贈給陳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寫了這樣的兩句話:“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麼用處?”在秋白同志看來,有的人雖生已經死亡,因為他只有軀殼而無靈魂;有的人雖死猶生,因為他是一個不死的靈魂,與永恆的宇宙同在。
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明確地表示他堅信共產主義,主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事實上,秋白同志一生中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論述,文獻俱在,彪炳史冊,是無能、也無法抹殺的。作為我黨的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他是當之無愧的。為了參加1927年國共兩黨在廣州召開的重要會議,他不顧他的病重垂危的愛人王劍虹,在死前離開了他。在“八七”會議是,他勇敢地挑起了領導整個革命的重擔。他批評自己的思想深處是願意調和的,但是他與彭述之、陳獨秀做著堅決的路線鬥爭。他有自知之明,他是不願意當領袖的,連諸葛亮都想做,但是在革命最困難的嚴重關頭,他毅然走上黨的最高領導崗位,這完全是見義勇為,是他自稱的“韋護”的象徵。這那裡是像他自己講的“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自己又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哪裡像他自己講的”不但不足以鍛鍊成為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
二、挖掘自己內心深處的靈魂
在他就義前夕,在死囚牢里他像解剖自己患肺病的軀殼一樣,他用馬克思主義的利刀,在平靜中理智地、細緻地、深深地解剖著自己的靈魂,挖掘自己的矛盾,分析產生這些矛盾的根源,他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在《多餘的話》中,秋白同志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世界觀還未能脫淨“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即小資產階級意識,因而說自己是“弱的二元人物”,存在很多的弱點。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無產階級意識與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之間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矛盾。他說:“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練自己,要有非常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里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隊伍里站穩自己的腳步。”秋白明明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經臨近,不是以年、以月計算了,但是他仍然心懷坦白,舉起小刀自我解剖,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又當法官嚴格地審判自己,他為的是什麼?他不過是把自己當作一個完全的布爾塞維克來要求自己,並以此來品評自己的一生,這是一個真正布爾塞維克的品質。秋白同志通過對自己一生的總結所得到的教訓,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實事求是、坦蕩無私的崇高品質。他在《多餘的話》中告戒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指的就是不要保留“異己”的思想意識,不要做“二元人物”,而要脫胎換骨,做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所以,《多餘的話》全部都是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和自我譴責;全部是和自己計較。顯然,正是由於這一深刻反省與嚴格自責,所以瞿秋白才能在原來思想的基礎上,產生上述那樣的飛躍;超越了他原來的自我,達到了他原來思想也未曾達到的高度。
三、勇於承擔責任
在《多餘的話》找能夠,瞿秋白同志對於自己所犯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表示異常的痛心,作了誠懇地自我批評,並表示:“我應當負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待自己所犯的錯誤的正確態度。首先,他重點回顧並勇敢地正視了自己從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表現,那真是“慘不忍睹”:用他自己的話,則是“從那時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著怎樣說。說我說錯了就是機會主義好了。其次,正是這一軟弱退讓和違心屈從,造成了王明路線同志這一“後來的禍害。為此,他譴責自己:“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著2的正確路線奮鬥嗎?”並進而指出:“以前幾年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卻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相反,在共產黨的觀點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重了。”共產黨的觀點是歷史的、發展的;這也是說,他眼前王明路線這個“禍害”,正是“以前幾年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延續和發展。所以,自己這個軟弱退讓者同時還是個“始作俑者”,因此,加倍地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再次,在路線是非的重大問題上軟弱退讓,“優柔寡斷,隨波逐流”,“仁慈、禮讓、避免鬥爭”——當然是不可原諒的嚴重錯誤。為此,他將自己痛斥為“十足的市儈”、“最壞的黨員”、“半吊子文人”——直至“叛徒”和“叛徒的一種”並自請處分:堅決要求將自己開除出黨——他這些話強烈、認真,翻來覆去,決非偶然。
四、黨和革命事業,熱愛戰友和同志
在《多餘的話》中,秋白同志對黨和革命的事業以及對同志和戰友充滿感情。在“盲動主義和立三主義”一段,瞿秋白說:“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發展,——事後我曾經說,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實際上我也會走上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至於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的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如此寬大為懷、代人受過,表現了一種十分難得的高尚品德。能夠以這樣的姿態面對身邊的已被證明是犯有嚴重錯誤的同志的,哪怕就在我們黨內,也屬為數不多。別人且不說,就是這個李立三,在1930年12月初於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聽取了國際東方部所作的《關於中共中央關於三中全會和李立三同志的錯誤的報告》之後的討論會上,在瞿秋白缺席會議的情況下,先是把自己的錯誤推給瞿秋白:“現在我知道,我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在最近兩年在中國做的,是在秋白同志影響之下的。”然後又反過來誹謗瞿秋白:“我現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確用了兩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會上的行動,就可以表現出來。黨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集團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略加對照,兩個人品德的高下已經涇渭分明。時至今日,為了私利諉過與人,甚至對別人落井下石的人,並不罕見。在《多餘的話》最後,他說:“永別了,親愛的戰友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一次’。”“你們在鬥爭中勇猛前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我已經不能跟隨你們了。”他還說:“永別了美麗的世界!”“這個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比從前更光明了。”
秋白同志對於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同魯迅一起從事文化鬥爭所做的重要貢獻,無論在“口供”“筆供”,還是在《多餘的話》中,都一字不提,只是說他離開中央政治局以後“告了長假休養醫病”,“大病,時發時止,耗盡了三年時間,他被俘後寫給魯迅和周建人的信是化名、暗語,採取了周密的安全措施;他對國民黨的記者談話,說魯迅“只能算是為同路人”,有意為魯迅開脫。苦心孤詣,成功地保護了魯迅,保護了上海地下黨的組織和同志。
五、正確文藝觀點
秋白同志在《多餘的話》中也談到文藝方面的問題。他反對“霧裡看花”,主張考察“實際生活”。他說:“學著比較精細的考察人物,領會一切‘現象’。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地了解人生和社會,了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者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百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階級之中。我想,這也許是從‘文人’進到真正了解文藝的初步了”。
人,對於作家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的概念。文學藝術作品要塑造“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而不是用種種現成的模式去鑄造類似機器零部件那樣的簡單化、公式化的人物。這個在多年來被弄得混亂不堪的重大文藝理論問題,早在四十多年,就被秋白同志明白透徹的闡述清楚了。
秋白同志在《多餘的話》中所表現的思想光輝,還不僅在於《多餘的話》的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的真知灼見。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說常常使得一些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責的地方正是他寫的《多餘的話》這個出乎常規、驚世駭俗的行動本身。據說,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是不能有弱點、缺點和錯誤的,有了而又在敵人面前進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是的“假面具”,就給共產黨抹黑,丟了醜。
無產階級政黨要求自己的成員包括其領袖人物應該達到的品德、風格和行動的標準,無疑是根據無產階級固有的優點和特點規定的。但是,共產黨人及其領袖人物達到這個標準之前,必然有一個形成、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一般地說,由於社會、階級、自我改造等客觀和主觀因素的限制,即使是在偉大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身上,也難免不存在“異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至於人類所共有的七情六慾,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與平常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產黨人的力量不在於掩飾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於能夠勇於解剖自己,揚棄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而為了徹底揚棄,首先必須作到嚴格解剖。解剖自己,說起來不難,做起來其實很不容易,決沒有那些不預備作自我解剖的人所指責、所鄙視的那么輕而易舉。像《多餘的話》這樣徹底、嚴格的自我解剖,在我黨歷史上的領袖人物(例如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等等)中,不敢說鳳毛麟角,但是也確實不算很多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多餘的話》閃爍著不尋常的光輝,人們是可以從中汲取有益的啟示的。
能不能在敵人牢獄中進行自我解剖呢?我們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產黨人在敵人牢獄中直到臨終之際才做這樣的自我解剖。應該具體地分析瞿秋白同志何以在此時此刻進行自我解剖?瞿秋白同志身陷囹圄,他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隨時有被敵人處決的可能。他已經無法在黨組織面前進行一生的總結和最後的自我批評。他通過《多餘的話》把自己內心世界的一切都說出來,留待後人論定,這是應該允許的。把瞿秋白一直寫《多餘的話》曲解為“絕望的心情”所導致的結果,是不公正的。
《多餘的話》里確實流露了消沉的、不健康的情緒。
如何估計《多餘的話》中的灰暗情緒?第一,要看到這些灰暗情緒在《多餘的話》中,是非本質的、次要的,它不是《多餘的話》的主流。而寫《多餘的話》,在瞿秋白同志被捕以後的全部表現中又是一時一事,不是主流,無損於洋他的革命大節。我們聽慣了氣吞山河的豪言壯語和驚天動地的檄文,當你乍一接觸到《多餘的話》這些發自肺腑的真實話語時,不免回迷茫若失,不知所措,心理上自然產生一種無可名狀的牴觸情緒。不過,只要你細心研讀和體味,便不難發現,瞿秋白在寫這篇文章是,可謂是真心可憫,用心良苦。《多餘的話》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字句——“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文人結習未除”,“我潛伏的紳士意識”,“弱者的道德”,“一個戲子”等。透過這些尖刻自責的字句,我們難道沒有看到,他對自己違忤黨性原則的消沉頹喪的言行,所進行的嚴厲的道德靈魂的自我鞭笞嗎?當然,瞿秋白的身上確實有著一些“怯弱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意氣”,他“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他嚮往的“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地日子”。他對黨內無謂的鬥爭已經是“十分厭倦了”。王明等宗派主義集團已經剝奪了人們說話的權利,嚴酷的現實逼得他“對於政治問題”,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他已經“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思想為思想”;但是,他又時常忖度著,如此敷衍塞責,是與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宇宙觀和人生觀“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他常常想,如此下去,“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如此,尷尬的兩難的境地,必然塑造他的相互矛盾的人格。當我們理清了20世紀30年代黨內外鬥爭所處地位和境遇是,我們便會對《多餘的話》中迷一般的語句所表現出來的情緒,具有了認同和理解的理由。第二,要從歷史的特定環境,從秋白同志這樣一個具體的人,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例如,秋白同志在《多餘的話》中所說的“歷史的誤會”和“噩夢”,是僅就自己思想中存在著的“文人”與政治家的矛盾,及其釀成的後果而說的。秋白同志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獻給了黨的事業,並有著重大貢獻,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在於他的《多餘的話》中對於個人愛好、專長同黨的事業需要之間的矛盾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表現了不應該有的消沉情緒,說明秋白當時的心情還是帶有一些灰暗。矛盾是每個革命者都會遇到的,每個人都應該隨時隨地警惕自己改造自己,戰勝一切消極嚴肅,特別是在極端困苦之下,對人生、對革命要保持旺盛的朝氣。但是,他在這裡並沒有對黨和革命的惡意詛咒,更沒有“否定自己”,“推卸責任”,“悔過求寵”,以求倖免一死。這一點,《多餘的話》已經寫得清清楚楚了。
又如,秋白同志在《多餘的話》中寫了“我實際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這些話主要是由上述“歷史的誤會”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悶情緒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話還包含著秋白同志對王明路線的懷疑和不滿,以及他在王明一夥打擊下所產生的苦悶心情。秋白同志在《多餘的話》中多次說到他要“休息”,從時間上看,主要是指1939初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一夥把持黨中央領導權以後。他說“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神經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1931年1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又說:“1931年出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還說:“我當時覺得,不管宇宙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的休息’的機會。”對這些話,有人認為是對革命的動搖,是“否定自己”。從字面上看,也許可以這樣理解,但是要注意歷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環境。王明一夥把持黨中央,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動輒給反對者扣上“反黨”、“反革命”的帽子,置人於死地。在這種情況下,只好說“不假思索”了;但是並非真的沒有疑問與思索,只是在敵人面前不願意說出,所以只說“心中空無所有”,對黨的路線“懶得過問”等等。這些話,正好反映了那時黨內民主被扼殺,黨內生活窒息以及瞿同志深受打擊所產生的思想苦悶的狀況,而不是證明他對革命“動搖”,更說不上“叛徒投降”了。像秋白同志這樣的重要人物,如果對敵人有一點動搖乞降的表示,蔣介石是決不會放過利用他的機會而輕易地殺掉他的。相反,敵人正是從秋白同志監獄中革命言行和《多餘的話》中明顯地看出他決不會屈膝投降,才將他處死的。《多餘的話》最早摘錄發表及評價見國民黨中統局主辦的《社會新聞》1935年8月第13卷第1期,按語說“共魁瞿秋白已伏法於閩南,關於瞿之處死,這是近年來的剿滅共匪事件上是一大收穫。因中國共產黨之積極破壞中國革命,並發動各處暴動,甚至於流為土匪,其關鍵全在民十六之八七會議,而此會議之中心人物,及會議後之政治領導責任者,即為今日伏法之瞿秋白……”。“觀於此則瞿之狡猾惡毒,真可謂至死不變,進既無悔禍之決心,退亦包藏顛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處死,實屬毫無疑義。”由此可見,當時國民黨對《多餘的話》評價是“很高”的,既沒有讀出對共產黨的叛變,也沒有讀出對國民黨的乞憐求生。秋白同志在寫《多餘的話》以前不畏刑訊,謳歌蘇區;在寫《多餘的話》以後拒絕勸降,從容就義。這一系列行動說明,《多餘的話》是秋白同志在監獄中全部鬥爭實踐中同舊的傳統觀念決裂的一個環節。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同志專門寫了《告別》一章,一再向同志們親切地告別;一再說他寫的是“最後的話”,這都只能說明他決心捨身赴死,而沒有“在革命的生死關頭,消極動搖,叛變投敵”意圖。《多餘的話》的基本內容是自我解剖,這個行動說明他並非絕望地“消極等死”。他最後英勇犧牲同他就義前夕總結自己的一生,這兩者之間沒有無法解釋的根本矛盾,不是不可理解的。
秋白同志的一生是戰鬥的,而且戰鬥得很苦。在我們這個不夠健全的世界上,他薰染了還來不及完全蛻去的一絲淡淡的、孤獨的、蒼白的心情是可以同情的。他說了一些同時代和有同感的人們的話,他是比較突出的,比較典型的。他的《多餘的話》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是也有些遺憾,這篇文章還不是很鼓舞人的。
總之,《多餘的話》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乞求免死的念頭。相反,《多餘的話》中多處可以看出的倒是熱愛黨、熱愛戰友,堅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勇於承擔責任和嚴格解剖自己,這是《多餘的話》的主要傾向,也是它的基調。
相關詞條
教科文藝期刊大全(十七)
| 教科文藝期刊雜誌涵蓋了各國民俗文化、民間藝術、民間傳統手工藝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國際文化、藝術,且對其保護與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