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概要
 《大地》
《大地》一個名叫王龍的貧苦農民從地主黃家娶回一個丫頭做老婆。倆人辛勤積攢,漸有積蓄。他倆一心想拿這筆錢買田。黃家後代揮霍錢財,把田一塊塊賣出去,而王龍卻一塊塊地買進。不料來了荒年,災民搶劫了王龍的家。王龍只得逃到南方城市,靠拉洋車和乞討過活。此時的王龍一心望天下雨可以回到老家去種田,什麼革命都無濟於事。在一次貧民暴動中,王龍撈到了一筆錢財。於是他回到老家買了牛,買了田,學著地主的樣娶了姨大太,後來住進城裡的大宅,又娶了一個18歲的丫頭當小老婆......
作品評價
像這樣一個故事顯然是脫離了中國當時社會的本質,憑藉一些極個別事件杜撰出來的。然而,1938年的諾貝爾文學將卻授給了這樣一個作家。當時的諾貝爾委員會的主席霍爾斯陶穆,在評析賽珍珠的報告中還說:“這次頒獎決定,要比以前許多次決定來得恰當些。”瑞典文學學院還給予了這樣的評語:“由於她對中國農村生活所作的豐富而生動的史詩般的描繪,以及她的傳記性的傑作。”顯然,這般評價是極不公允的。
作者介紹
賽珍珠,原名珀爾-賽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年出生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父母親均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派到中國來的傳教士。賽珍珠從小隨父母來到中國,在江蘇鎮江長大,自小跟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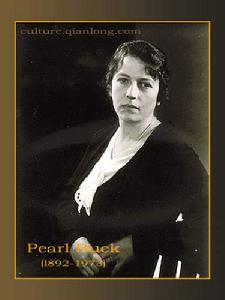 《大地》作者
《大地》作者教師學習經書。15歲時,她進上海英國人辦的寄宿學校念書。賽珍珠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賽金花”為自己起的中國名字。可見,名妓“賽金花”在她心目中有著特殊地位。
17歲時,賽珍珠回到美國進入維吉尼亞州倫道夫一梅康女子學院攻讀心理學,畢業後在美國過了一段短期的教書生活後又來到中國,在鎮江一所教會學校教英文。1917年,賽珍珠與傳教士約翰-洛辛-布克結婚,自己也從事傳教活動。爾後,她又在南京金陵大學和東南大學教英語和英國文學。
賽珍珠於1922年開始寫作,初次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作品。1925年她再度回國進康奈爾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又來到中國,並開始從事長篇小說的寫作。
1928年,中國爆發了舉世聞名的北伐戰爭。賽珍珠站在反動的立場上,仇視革命戰爭。因此等到北伐軍進入南京時,她擔心自己的生命沒有保障,匆匆離開了中國。
1931年,她的暢銷書《大地》在美國約翰一戴公司出版。這本書的發行使她成為名噪一時的暢銷書作家。《大地》也於第二年獲美國普利茲獎。這部小說系她的代表作品《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之一,其他兩部分別是寫於1932年的《兒子們》和1935年的《分家》。
賽珍珠一生共寫了85部作品,包括小說、傳記、兒童文學、政論等。1933年她用英文翻譯了《水滸》,改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魯迅對此舉表示了不滿。他說:“近布克夫人譯《水滸》,聞頗好,但其書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確,因為山泊中人,是並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待的。”(與克書,1934年3月24日)
1934年,賽珍珠與布克離婚,進入美國約翰一戴公司編輯部工作,第二年與公司老闆、《亞細亞》雜誌主編查一沃爾什結婚。晚年的作品《北京來信》、《梁太太的三個女兒》等,明顯地流露出對新中國的敵視態度。賽珍珠於1973年去世。
《大地》在中國的命運
《大地》原著在美國出版不久,中國《東方》雜誌便開始連載,以後幾年中,上海、北平等地的八個不同的書局先後出版了8種譯本,僅上海商務印書館就印刷了12次,這在中國的出版史上是不多的。
《大地》在中國受到了毀譽參半的命運。
莊心在的文章稱賽珍珠是我們民族的友人,作者認為,一個民族能否被人尊重,文學藝術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個國家的文學是無形而有力的,它能不必流血,就能消除他國的愚昧與無知。“雖然有時也不免有誇大失真之處,但大體上她至少已做到以誠懇客觀的態度把中國的情形給予西方以較正確的姿態,這一點,在復興民族過程中的中國人,是應當感謝的。”第二種看法是褒貶有加,如我國著名出版家趙家璧先生的《布克夫人與王龍》一文指出,賽珍珠的《大地》一文,大大改善了外國人對中國的偏見,從大體上講,此文簡直不像出自於西洋人的手筆。
但是趙先生同樣指出,儘管賽珍珠對王龍和小說中其他人物寄予了同情,但那個頭腦簡單的王龍正好符合了西方人把中國人看做是個文化落後民族的口味,它只會加深西方人對中國人所持的偏見。第三種看法從根本上否定了賽珍珠《大地》的藝術價值,第一個持這種觀點的人,恰巧也是該書最早的中譯者伍蠡甫先生,他在《譯者序》中發問:“這難道是中國的真實情況嗎?在作這些描寫時,作者難道沒有一點白人優越感嗎?難道小說不是要把中國表現成是對世界和平的一種威脅,表明黃禍將臨嗎?”《譯者序》在分析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和經濟關係後指出,是封建勢力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勾結才阻礙了中國農業的發展,而這些正是外國人不願意看到,或是看到了不願意承認的事實。
新中國成立後,《大地》一文受到了長年的批判,例如《美國反動文人賽珍珠剖析》一文就鋒利地指出,《大地》一文,是賽珍珠向中國人民射出的第一支暗箭,文章進而指出,賽珍珠“反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反對蘇聯,反對各國人民的解放,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殖民主義政策辯護,這都是貫穿在她的一切著作中的共同的主題。”
《大地》走紅的原因
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就是1937年以賽珍珠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大地》(The Good Earth)。
賽珍珠是美國最早以中國背景進行小說創作的一位美國作家。她的母親長期在中國傳教。塞珍珠本人雖然在美國出生,但下地三個月即被帶往中國,在那裡生活了近四十年。賽珍珠曾根據自己在中國的經歷,寫就數部描寫中國底層農民的小說,並為此而榮獲諾貝爾獎。塞珍珠的小說在三十年代的美國廣為流傳,是當時美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來源,其中尤以《大地》最受歡迎。該小說曾在美國先後發行兩百萬冊,而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也極為成功。據統計,在電影發行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大約有兩千三百萬美國人看過這部電影,而別的國家觀看此片的人數高達四千三百萬。
賽珍珠的小說所完成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在美國公眾心目中造就了中國底層人物的形象,向他們細緻刻劃了中國農民惡劣的生活狀況。她的小說的一大特點,就是力圖在描寫中國底層社會的過程中,避免捲入任何國家利益的糾紛。
電影《大地》在當時的美國取得轟動性成功,主演影片中的女主角阿蘭(O-Lan)的美國演員露伊絲·雷納為此而榮獲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
影片講述的是中國農民王龍(Wang Lung)和其妻阿蘭如何憑藉勤勞、堅韌,與貧窮和天災作鬥爭,從赤貧轉為富裕,創造一個四代同堂的幸福家庭的故事。影片試圖挖掘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農民與土地的深情和超驗性關係。
王龍是一個貧窮但勤勞、樂觀的農民。他自幼喪母,在一間茅草屋裡與父親相依為命。王龍生活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擊石取火,一年之中,只洗一回澡。但即便如此,影片中的王龍和四周鄰居都精神飽滿,對生活充滿信心。他們耕田種地,用自己的勤勞,謀求生存。影片以王龍去被稱為大宅院的富豪之家迎娶妻子阿蘭為開場。
王龍一開始進城迎親時雖不乏喜氣和活力,但卻一幅謙卑、畏縮的模樣,以至大宅院的門房把他誤當小販。王龍的未婚妻阿蘭原是大宅院廚房裡的下人,長年受盡欺凌虧待,王龍的到來對她來說是一個新生活的開端。在迎親回家的路上,阿蘭撿起王龍扔下的桃核,說桃核可以長成樹,由此第一次點明了賽珍珠試圖在阿蘭身上體現的主題:人與大地的關係。
王龍與阿蘭婚後過著樸素而幸福的生活。夫妻倆勤於農務,不久又喜得貴子。
阿蘭自豪地和王龍攜子重返大宅院,在眾僕人和大宅院主人面前大大榮光了一番。
大宅院家運不濟,不得不出賣田地,王龍用多年積攢的銀元購下數畝麥田,王龍一家呈現出興旺的面貌。但天災卻不期而臨,饑饉遍地,王龍用重金購置的麥田成了顆粒無收的廢地。好吃懶做的叔叔勸說王龍廉價拋售麥田,堅信土地對農民的重要,說服王龍寧肯南下逃荒,也不出賣土地。王龍聽取妻子的話,攜全家老少搭火車南下,尋求活路。
時值辛亥革命暴發,阿蘭在一次眾人對富豪之家的哄搶中,不期撿到一袋珍珠。這筆意外之財使王龍一家有足夠的資本回家,重振家業。回到舊家,王龍大量置地,併購下了現已破落的大宅院。面對財富,王龍開始萌生非分的念頭。在叔叔的誘使下,王龍娶來一名賣唱女子為妾,並終日懶散不堪,與小妾廝混。面對這一切,阿蘭則表現出典型中國女子的忍耐和大度,想方設法使王龍改邪歸正。
小兒子與二房偷情使王龍認清了自己的處境。他悔悟過錯,休掉二房,賣掉大宅院,重新回到土地上照料農務。蝗蟲襲擊麥地,王龍在學農的兒子的幫助下,招呼左鄰右舍,與鋪天蓋地的蝗蟲展開成功搏擊,使王龍更深切地認識到一個健康家庭的重要,並愈加珍視自家的田地。影片以阿蘭的死結尾,臨死前的阿蘭再次告誡王龍熱愛土地,王龍則深情地說“你就是土地。”
影片《大地》力求寫實,通片用的都是中國音樂。影片中王龍一家的曲折命運、主要人物自然率真、感情誠摯的表演,都給美國公眾提供了豐富的中國農民形象,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他們昔日對中國人籠統而模糊的認識。影片所展示的中國農民的堅毅、勤勞,在天災面前的無畏,以及在道德方面的分鑒力給當時的美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地》堪稱是好萊塢電影中一部表現人性美的傑作。它的可貴處,不僅在於提供了一個非西方民族和人民的真實可信的形象,而且在於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種族、族裔和文化的差異,來表現人類的生存困境和人類的意志與情感。
但是,賽珍珠的小說及電影也在無意中製造了新的刻板形象,那就是底層中國大眾的艱辛。他們始終掙扎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中,用原始的生存手段延續生命,土地是他們唯一的生命圈。
賽珍珠始終選取中國底層大眾的命運沉浮作為小說創作的題材,這中間不乏女作家對中國農民深深的同情與熱愛,但同時也滲透著她從家庭獲得的強烈的傳教士心態。在美國公眾看來,在遙遠的東方大地上與土地相依為命的中國普通百姓,始終是需要保護和拯救的對象。這很自然地會引導他們以救世主身份自居,飽含憐憫地看待這些在宗教信仰上未開化的人們。觀看鏡頭只對準活動在前現代原始落後環境中的底層人的電影,也同樣容易引導觀眾將其與統治他們的政府作尖銳對立。
事實上,賽珍珠的小說及後來改編的電影成為之後美國人想像共產黨治下中國百姓生存狀況的重要資源。
關於《大地》另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女主角的表演。露伊絲·雷娜的表演雖然非常出色,但這位西方演員顯然有刻意表現中國女子逆來順受、溫順馴良的傾向。將東方女子刻板化為低眉頜首、受盡欺凌而不知反抗的受難者形象,一直是西方人對東方女子的主導想像。我們在阿蘭這位角色身上能明顯地看到這一點。
但《大地》無論在藝術上還是在票房上,都是一個成功。
借著這種成功,好萊塢曾將賽珍珠的其它小說陸續搬上銀幕,如制於1944年的《龍種》(Dragon Seed)等。影片《大地》拍攝之前,好萊塢曾與中國政府接觸,徵求拍片意見。當時的中國政府希望影片的主角能由華人出演,但可惜的是,好萊塢最終未能答應這個要求。
賽珍珠的中國系列小說在當時的美國是一個文化時尚。
《大地》公演期間恰值中日戰爭,大量關於日軍在華暴行,如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的報導也紛紛傳回美國,激起美國人對侵略者的義憤和對反侵略者的同情。
隨後,美國與日本的軍事衝突也逐步升級,最終導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可以說,當時的政治氛圍,是象《大地》這樣的電影所以流行的重要原因。
作品中的農民形象
描寫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北方農民生活的巨著《大地》(TheGoodEarth)三部曲的問世,使賽珍珠(PearlS.Buck,1892-1973)享譽文壇。其中出版於1931年的《大地》又“因其對中國農民生活的豐富而真實的史詩般描寫”〔1〕而先後獲得美國普利茲小說獎、豪厄爾斯(HowellsMedal)最佳小說獎和諾貝爾文學獎。
但是,這部小說自問世之日起,對它的批評就始終存在。在美國文學界,批評家們認為雖然賽珍珠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她的《大地》僅僅是部通俗小說,其審美價值根本無法與海明威、福克納等人的文學成就相比。因此,一般的文學史專著對賽珍珠只是做簡單的介紹,往往幾筆帶過。還有一些評論家認為賽珍珠不能算是美國作家,因為她的作品多是以描寫中國為主的。
中國知識界對賽珍珠的作品也多有批評。這些批評文章見諸當時在美國和中國出版的報刊上。最早對《大地》提出質疑的是康永喜教授1931年7月1日發表在《新共和》雜誌上的文章,以後江康湖教授也撰文批評《大地》。他們認為賽珍珠筆下的農村生活是不真實的,並指出一些細節上的失真。在國內,魯迅、姚克也認為《大地》是不真實的。當然,中國學者中對《大地》也不乏首肯者,林語堂便是其中之一。
1949年以後,由於政治原因,海峽兩岸都把賽珍珠作為一個政治符號來加以利用。台灣一些人把賽珍珠說成是反共的人士而大加讚賞,另一些由於她對國民黨所持的批評態度,排斥她的作品;而大陸則把賽珍珠作為反共作家,禁止出版她的作品,以至於她的名字連同她的作品都在她熱戀的土地上消失了。直到近年,大陸學術界才開始對賽珍珠進行重新評價。
筆者認為,賽珍珠的《大地》就其審美價值而言,不能稱之為優秀的或經典的文學作品,它的確是一部通俗小說。而小說中對中國農村生活的描寫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真實。但這部小說的意義在於,當世人還不甚了解中國的時候,她用英文寫了這樣一些中國農民。通過這部作品,使西方人懂得,中國農民不僅僅是留辮子、抽鴉片、纏小腳的“東亞病夫”,他們也是人,他們也在為生存而搏鬥。和世界上的所有農民一樣,他們與土地也有著血與肉的關係。賽珍珠用自己的筆,架起了一座世人了解中國的橋梁,這便是小說的魅力之所在。賽珍珠是位十分複雜的作家。她不贊成共產黨,同時也批評蔣介石政府;她反對殖民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主張超越階級對立、民族矛盾的人道主義,不分是非,一笑泯恩仇。但是,她對中國的熱戀和對中國農民命運的關懷,已經遠遠超出了她的政治立場,具有豐富的人道主義內涵。
1931年,賽珍珠的《大地》一問世,立刻成為西方世界最暢銷的小說之一。它那特異的東方情調和濃郁的鄉土氣息,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古老中國的魅力,儘管貧窮、混亂、水深火熱,但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深深地打動了他們。這種超出時代、地域的人與土地的關係,使人聯想起那些原始的時代和古老的神話——人由泥土做成,人的生命源於大地,最終還要歸於大地。
賽珍珠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接觸過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但她所關注的首要對象是農民,這固然是受到她的丈夫、美國農業專家約翰·洛辛·巴克的影響,同時也不能不說明賽珍珠切入中國人生活的角度是獨特的、準確的、深刻的。因為儘管在本世紀30年代,中國已經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等一系列事件,中國開始走向擺脫封閉的農業文明之路,但是,中國社會的主體仍然是農民。賽珍珠緊緊抓住農民,通過農民與土地之間的永恆關係來表現時勢的變化和命運的興衰。過去,中國的古代文學一直給人展示那些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以至於人們只看到了中國文明中的士人文化和儒士雅興。在現代,儘管有許多作家關注農民的命運,特別是魯迅對農民的描寫深入骨髓,但都不是以農民與土地的關係為核心的。而賽珍珠則以一種樸素的、笨拙的、甚至是愚昧的農民文化來界定中國的傳統,那些臉朝黃土背朝天、汗水滲透著淚水的人們,祖祖輩輩生於土地、長於土地,與土地相伴而終。他們的土氣、愚笨恰恰是中國人另一種高尚情懷的表現。他們“乃是實實在在的人,他們緊貼著泥土,緊貼著生與死,緊貼著樂與悲。……在他們中間,我看到的是真而又真的人。”
圍繞著王龍與土地的關係,賽珍珠從家族的興衰和人性的變化這兩個層次揭示了農民的生命源於土地這一永恆的主題。
(一)土地與家族的興衰
從小說的結構上看,《大地》屬於傳統的家世故事,一個家族的興衰和在這個過程中的悲歡離合構成了作品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線索。但是在這個家族故事的深層,有一條主宰著人的命運的主線,那就是王龍一家與土地的關係。家族的興盛與衰敗、家庭的和諧與分裂繫於人與土地的離合。賽珍珠通過兩個家族的更替和一個家族的命運成功地揭示了人與土地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作品一開始,當王龍的家還一貧如洗的時候,作家描寫了黃大地主家族的全盛,他們靠手中的土地獨霸一方,生活在悠閒、奢華和糜爛之中。但是,由於黃家與土地的關係僅僅是一種功利性的財產關係,土地只為他們提供生活享樂所需的財富,他們只躺在土地上坐享其成,而沒有腳踏土地,把自己的血汗融入土地。在黃家,那種人與土地間的血肉關係已蕩然無存。為了維持奢華,他們不得不一塊塊地出賣土地。每出賣一次,黃家便衰敗一分。當所有的土地都出賣後,這個家族也隨之消失。
黃家的衰敗恰恰為王龍一家的興盛提供了最好的契機。王龍一家靠著他們與土地的血肉關係,靠著他們在土地上吃苦耐勞、忍辱負重,終於由普通的農民一躍而為顯赫一方的地主,取黃家而代之。這種家族的更替說明誰擁有土地、珍惜土地、耕作於土地,誰就會興盛。
王龍曾是個貧苦的農民,靠租種地主的土地過活,貧困得連娶媳婦也要靠有錢人家的開恩。小說的開篇,通過王龍簡樸的婚姻、破舊的房屋以及全家那寒酸的衣食,突現了王龍的貧困。但貧困並未壓垮他,更未泯滅他對土地的渴望,反而使他的生命格外昂揚,因為有一種古老而彌新的信念支撐著他——一定要擁有自己的土地。為此,他忍受貧困、飢餓和屈辱,與天災人禍搏鬥,終於實現了他的夢想。他購買了大量的土地,由寄人籬下的農民變成了顯貴的大地主。土地對王龍來說既是生命之本,又是他走向顯貴的標誌。
從王龍結婚、生子到他成為大地主,是小說中最樸素、最富於詩意的部分。為買到土地所付出的艱辛,買到土地時的興奮、豐收時的喜悅、遇災時的悲哀、逃荒時的窘迫,都與王龍和土地之間的渾然一體息息相關。就是在被迫離開土地之時,大城市的五光十色也一刻未能泯滅王龍對土地的一往情深。那時的王龍家,夫妻間的親密默契以土地之夢為根基,新生嬰兒的歡樂被土地的溫情所圍繞。王龍和妻子阿蘭共同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領著孩子玩耍在自己的土地上,儘管困頓、勞累,但他們的精神和親情使簡陋的茅屋熠熠生輝。一種只有紮根於土地之中才會有的充實、和諧構成了《大地》前半部的浪漫情調。對王龍來說,土地就是詩、就是畫、就是音樂、就是宗教。
然而,王龍家族的和諧因人與土地的分離而破碎。王龍富有了,不願再下地幹活,想過體面人的生活。當他脫下農裝、換上絲綢長衫在城鎮裡四處遊逛之時,當他只知道坐在土地坐享清福、不再嗅泥土的芳香時,當他拋下妻子阿蘭與妓女荷花歡悅之時,他的家庭開始走向分裂。儘管他的財富足以使他的家庭成為受人尊敬、甚至嫉恨的對象,但卻已開始了內在的糜爛。阿蘭與荷花之間的相互仇恨籠罩著這個家,王龍與兒子之間的親情不見了,代之以相互的不滿和怨恨,他的三兒子甚至離家出走。這種不和諧和分裂在王龍死後便演變成分崩離析——分家。分家時,兒子、兒媳們之間的相互算計,分家後大兒子的遊手好閒、二兒子的狡猾奸詐、三兒子的殺人嗜血,一一預示著王龍家族的衰敗。隨著王龍留下的土地被分割、被一塊塊賣掉,王龍家族也漸漸走向分裂和衰敗。在《兒子們》和《分家》中,這種衰敗表現得淋漓盡致。賽珍珠的這種描寫從反面揭示了同一個主題:農民一旦離開土地,便失去了和諧與生命,“當人們開始賣地時……那就是一個家庭的末日。”〔4〕
(二)土地與人性的變化
賽珍珠在《大地》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農民形象,這些人物的性格有的單純、有的複雜,特別是王龍,時而粗魯猥瑣,時而堅定執著;時而懦弱卑鄙,時而英勇善良;時而勤勤懇懇,時而遊手好閒、無所事事。但王龍的這種複雜性格始終與他與土地的關係相連,而性格中他對土地的熱愛則貫穿於一生。當王龍還沒有成為顯赫的大地主時,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占據著人物的核心,他吃苦耐勞、富於同情心,他的一舉手、一投足,都透露著土地給予他的信心和力量:
王龍開始踏踏實實地在土地上耕作,他甚至連回家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搭了進去。……如果白天活幹得實在太累了,他就躺在壟溝里,他的肉貼著自己的土地,感到暖洋洋的。〔5〕
這是肉貼著泥土的王龍,是中國農民純樸性格的逼真寫照。
但當他富有了,過上體面人的生活後,他開始用絲綢打扮自己,開始覺得阿蘭很醜,開始去城裡閒逛、喝酒、逛妓院,給叔叔和嬸子送鴉片,強行奪走阿蘭僅存的兩顆珍珠,終日和他的愛妾荷花“吃著、喝著、盡情地享樂著”。他變得油頭粉面、輕浮放蕩,昔日在田地里勞作的生命力消失了。他開始空虛、睏乏。而他的兒子們一個個離開土地後,就再也沒有人性的善良與純樸了。老大終日沉湎於酒色,老二唯利是圖,老三雖然有理想,但由於從土匪起家的軍閥本性,使他成為一個殺人如麻、魚肉百姓的劊子手。通過兒子們的所作所為,賽珍珠似乎在暗示:農民一旦離開土地,必定墮落。
但是,作家在王龍那種複雜多變的性格中始終突出著一種不變的個性——對土地執著的愛。當他沒有土地時,拚命幹活、攢錢,渴望有一天得到土地;當他得到土地後,他一頭扎向土地,辛勤勞作,不斷擴大自己的土地;當他被迫離開土地、逃荒在外的時候,他時時刻刻想著回歸土地;當他離開土地,遊手好閒的生活使他感到空虛、煩躁時,他傾聽到的是土地的召喚。他脫去長袍、絲絨鞋和白色襪子,挽起褲管,重新踏上黑油油的土地。土地給他力量和充實。特別是在他不久於人世之時,他對兒子說的那番話,更突現了王龍對土地的執著:
我們從土地上來的_……_我們還必須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們守得住土地,你們就能活下去……誰也不能把你們的土地搶走……〔6〕
王龍死了,但他對土地的熱戀永存。
賽珍珠對這種執著於土地的讚美,還可以從小說中二位女性人物的性格中見到。首先是阿蘭,這位女僕出身的農村婦女,有著不屈不撓的堅韌和近乎啞巴式的沉默,她對土地的執著體現在她言行的每一細枝末節上,懷孕不能中斷她去地里幹活,剛生完孩子又回到土地上勞作,即便在成為大戶人家的女主人之後,她仍保持著吃苦耐勞、樸實忠誠的品質。她是一個與土地渾然一體的人,寧可自己死去也不要丈夫給她花錢治病,因為那些錢能買好大一塊地。她說:我活不長,就要死了,但地在我死後還在。在這裡,賽珍珠對阿蘭充滿著同情和讚美,特別是對阿蘭那土地般純樸的性格給予了詩意化的描繪。
另一個女性形象是王龍的二妾梨花。作家突現她性格的純樸和忠誠是在王龍死以後。唯有她在分家時不去爭奪遺產,甘願遠離王家大院,回到鄉間的土屋裡;唯有她撫養著王龍的傻女兒,一個人守在王龍的墓邊,寄託哀思;更重要的是,這個平日與世無爭、百依百順的女人在聽到王龍的兒子們要賣地的訊息時,卻一反常態,變得激憤、尖刻,她全身顫抖,兩眼含淚,企圖阻止賣地,並用鬼魂報復來威脅王老大。這種對王龍的忠誠似乎是王龍對土地的忠誠在活人身上的延續。
從以上的分析中,賽珍珠把中國農民的生活理解為人與土地的離合。他們只有紮根於土地才會有希望、和諧、幸福,他們的生命才有意義,他們的人性才會純樸、善良。而農民一旦離開土地,他們就失落、迷茫、痛苦,他們的生命就空虛、萎縮,他們的人性就邪惡。
(三)對土地的浪漫情懷
賽珍珠還是個嬰兒時就被父母帶到中國,在這裡她度過了珍貴的童年時代,直到1934年返回美國,她前後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她既傳教又讀書,廣泛地接觸過社會各個階層。她幾乎像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經歷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系列風雲變幻。到本世紀30年代,中國仍然被內憂外患所威脅。軍閥混戰、日軍進犯、經濟衰敗、政治腐朽,中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賽珍珠目睹了這一切,便不能不在她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是,賽珍珠的筆一直處在理智與情感、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之中,並使她對土地、對農民的偏愛化為一種理想化的浪漫情調貫穿作品始終。當她能夠冷靜地觀察中國現實之時,她是那樣真實地描繪了風雲變幻、動盪不安、多災多難的中國,她寫到了下層民眾的貧困,寫到了自然災害、土匪、軍閥、稅賦給人民帶來的苦難,甚至無情地描繪了她鍾愛的農民身上的各種弱點:封閉、愚昧、自私以及百依百順的奴性,還有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算計、殘殺、坑害。但是只要一涉及到農民與土地這一主題之時,她那種博愛式的同情、浪漫式的理想主義便為嚴酷的現實抹上了一層絢麗的光彩,甚至會以寬容、理解的筆調描繪農民身上的弱點,把愚昧、順從和封閉作為一種美德加以讚揚,把原始的農業文明視為人性完美的標誌。她像法國的盧梭以及那些浪漫主義時代的文人,也像中國的老莊、陶淵明,把原始的刀耕火種和封閉、落後的農村升華到田園詩般的境界。她曾明確地表示過:“農村裡的生活才是中國底真實而原來的生活。這種生活欣幸地尚未沾染上駁雜的摩登習氣而能保持她純潔健全的天真。”〔7〕她把這種生活視為中國的基礎。
這種浪漫主義的理想也成為《大地》一書中城市和鄉村之間相互對比的準則。在作品中,只要一觸及到泥土,賽珍珠的筆就充滿了溫情,一涉及到城市,便冷酷、乾澀、挖苦。鄉間的樸素無華和大城市的燈紅酒綠,耕耘於土地上的充實和逛妓院、去賭場的空泛,腳踏土地的升華和在城市閒逛中的墮落……都在暗示作家這種回歸土地的理想主義。
同樣,這種浪漫主義也滲透在作家對中國農民、中國農村前途的理解中。作品中,王龍後代們,老大坐吃山空,不會有任何前途;老二狡猾奸詐的商人習氣只會導致世風日下;老三當上了一方軍閥,軍閥的本性吞噬了他的理想,其結果是國家分崩離析、百姓生靈塗炭。王龍的幾個孫子曾在城市中參加革命,但作家似乎是以開玩笑的態度來描繪這些毛頭小伙子的衝動,最後是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賽珍珠在以否定的筆調描繪了商業、武力、革命在現實中的失敗之後,向讀者獻上了一個理想的光環——王龍的孫子王源留學歸來,回到他祖父的土地上,知識與土地的結合便是中國農民的未來。至此,《大地》三部曲形成了一種人為封閉的循環:來自土地,歸於土地。作者似乎在暗示,只有土地和腳踏土地的農民才是中國的未來。
儘管《大地》中有許多現實主義的描寫,但整部小說的基調仍然是理想主義的。她似乎不願中國走出幾千年的農業文明,走出封閉愚昧的傳統生活方式,不願中國走向現代文明、工業化。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表明,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是以農民走出土地為標誌的,工業化和商業化是現代文明的支柱,原始的農業文明無論具有多么純樸的田園氣息,農民的生活方式無論多么率直,終將被現代文明的城市化、工業化所代替。
《大地》作為一部小說,那種田園詩般的樸素固然很美,但作為一種了解中國的資料,它的浪漫情調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中國嚴酷的現實。所以,賽珍珠筆下的中國農民,是加入了作家的主觀構想,而不完全是現實中的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浪漫情懷不能代替長期落後的農業文明所造就的落伍的中國和保守、愚昧的中國農民。
盤點賽珍珠作品
| 賽珍珠(Pearl S. Buck或Pearl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直譯珀爾·巴克,美國作家。1932年借其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成為第一位獲得普利茲小說獎的女性;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她也是唯一同時獲得普利茲獎和諾貝爾獎的女作家,作品流傳語種最多的美國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