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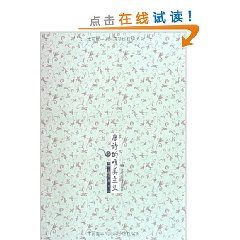 0
0外文書名:theaestheticismofpoetryoftheTangDynasty
平裝:173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9787805887845,7805887845
條形碼:9787805887845
商品尺寸:23.8x16.6x1.4cm
商品重量:358g
品牌:北京磨鐵圖書
ASIN:B002XISE7S
內容簡介
《唐詩的唯美門義》內容簡介:詩是通往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路,包括宇宙和心靈;世界上任何一條路最後都會歸於詩,包括生與死。在本書中,作者用綢緞般精緻細膩的文字,以超越常人的豐富想像,貫通中外,融合古今,用最通俗華麗的筆法解析了唐詩的美感。其文筆優雅靈動,其風格姿肆縱橫,其神韻悠遠綿長,其思想深邃博奧。
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什麼都不得也會有個閱讀快樂。詩用有限的文字表現無限的空間、時間與心靈。一次哭泣、一團雲煙、一枚手印皆因詩成為永恆的存在。於是你的閱讀,從觸碰卷首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
編輯推薦
《唐詩的唯美主義》:繼《納蘭詞》《人間詞話講評》之後,蘇纓又一嘔心之作。本書是一本唯美主義唐詩的解密書,是迄今為止唯美主義唐詩解析方面最權威、最通俗、最優美的著作,是一本以專業的深度,以通俗華麗的筆法,深入淺出講解唯美唐詩的普及通俗讀本。
專業書評
詩可以延伸出通向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路,包括宇宙和心靈,世界上任何一條路最後都會歸於詩,哪怕這條路一開始和詩南轅北轍。能夠看到這么精美的語句,這讓我激動不已,好書並不需要太多,一兩本這樣的經典就足夠了。
書到的之後當我打開包裝,就知道,自己這次買的書很值得收藏。印刷質量很好,插圖精美的我都想放大之後當成海報。文字精緻優雅,淡淡的,淡淡的感覺~
書如其名,當得起“唯美”二字~
內文的插圖超級漂亮,這個做插畫的“藍”真是非同一般啊,佩服
這樣精美的包裝設計,與蘇家小妹的美文珠聯璧合,可說是相互輝映。
能夠將唐詩解析得如此深入淺出,如此文辭優美,舍蘇纓其誰?
作者簡介
蘇纓著名詩詞研究點評家,著有《納蘭詞典評》《納蘭典評宋詞英華》等,均為暢銷之作,深受廣大讀者歡迎。其文華麗優美,精奧深微,輕靈流暢,堪稱當今頂級的詩詞研究點評美文。目錄
序言•小徑分岔的花園,與通向花園的所有小徑■專論•唐詩的唯美主義■
美將我們俘虜,更美將我們釋放——錦瑟(李商隱)
詩人把不同意象的疊加或並置,就如同音樂家把不同的音符組成和弦。意象派的創作方法其實就相當於編寫和弦。
感傷是一種終生不愈的殘疾——重過聖女祠(李商隱)
痛苦並不是撕心裂肺的,也不是排山倒海的,它就是那樣淡淡地存在著,亘古以前是這樣,現在是這樣,亘古以後也還將是這樣……
開滿秘密的花園——《碧城》三首(李商隱)
這是一場被禁止的戀愛,我們雖然距離很近,可以“對影聞聲”,但不能公開有所表示,只有見面時回頭示意,把萬千心事盡付不言中。
看不見的城市——天上謠(李賀)
在理性上,這是荒誕的;在感性上,這卻是相當逼真的。理性之荒誕塑造了感性之逼真,這正是歷代的李賀批評者們很難領會的道理。
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銅仙人辭漢歌(李賀)
李賀更像是現代詩人,像海子那樣的詩人,純真,孱弱,在幻想的世界裡旁若無人地癲狂著。
■隨筆•唐詩小札■
詩與帝國對峙——野望(王績)
詩與帝國對峙。帝國擁有法律、軍隊與財富,詩除卻光榮與夢想,一無所有。不過,時間早已將勝負揭曉,帝國灰飛煙滅,而詩歌占領的版圖至今仍在持續擴張。大唐帝國在現實的此岸,而王績和詩,在理想的彼岸。
離歌響起,不訴離傷——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
面對漫長的距離和更為漫長的時間,詩人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對將來滿懷信任的態度。他大膽地尾隨命運的行蹤,不猜度生活的軌道將延伸至何處,篩掉壞的可能。這絕不僅是風華正茂書生意氣的結果,這是現世安穩歲月靜好賦予他的野心。
於輪迴中開啟永恆之門——春江花月夜(張若虛)
第一次面對囚犯和獄警發表自己的創作時,梅湘向整個集中營驕傲地宣布:“我要終結的不是自己身為囚犯的期限,而是對過去和未來的觀念,也就是說,這部作品是為了開啟永恆而作。”而在東方的對應物中,《春江花月夜》就是終結了對過去及未來的觀念、只為開啟永恆而作的作品。
思念如蝴蝶般撲面而來——望月懷遠(張九齡)
不在同一國度或時區,沒關係,當月華從黑漆漆的天幕浩浩湯湯地傾瀉下來,我們在月光的同一流域。
善的乏力——讀張九齡《詠燕》
面對現實的滿目瘡痍,我欣賞張九齡“無心與物競”的超然與淡定,但我更敬重羅曼•羅蘭“不管人生的賭博是得是損,只要該賭的肉尚剩一磅,我就會賭它”那一往無前、所向披靡的勇氣。隱士們用激流勇退、置身事外的方式來堅持操守,表達拒絕同流合污的立場,我能夠理解;但我偏激地以為,放棄鬥爭是對自己的鄙薄,對信仰的出賣,並不值得頌揚。惡的勝利,並不是因為善的缺失,而是因為善的乏力。
人生是個蒼涼的手勢——讀王維《終南別業》
很多時候,豁達都不是一種你可以信手拈來、也可以恣意淘汰的選擇。更多的時候,那是現實留給你的唯一出口。豁達是窮途末路時對命運最後一次視死如歸的反抗。
時間永在,是我們飛逝——讀劉希夷《代悲白頭吟》
大多數的讀者卻被迫採取和詩人一樣的節奏踏上通向生命真相的螺鏇樓梯,持續下沉,直至觸底:公子王孫,宛轉蛾眉,無人打破時間的牢。一切企圖阻止時間飛逝的行為皆是徒勞,因為,時間永在,是我們飛逝。
不敢拆封的信——讀宋之問《渡漢江》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如若在這之上再添任意一字一句,詩就會死去,就在這危急的一刻,詩人靜靜擱筆。其實,詩人並沒有停止,他用沉默繼續說話。
母親是一個叫做“溫暖”的地方——讀孟郊《遊子吟》
保爾•艾呂雅在《公共的玫瑰》中說道:“男人只會變老不會成熟。”我相信,正是母親的柔軟懷抱和無限溫柔,使幼稚成為男人終生不會失去的權利。
目的地不明——讀錢起《省試湘靈鼓瑟》
這世界上有許多奇怪的加減法,比如想念和留白。想念,在心裡加上一個人,單數變雙數,卻更寂寥——如果我從未在生命中加上這個人,我就不會因為想念一個人而變得如此孤獨。留白,山水畫減去畫幅中段的筆墨,電影減去男女主角的對白,維納斯減去雙臂……意義的空白處延伸出分岔豐富的小路,向客群揭露無限的可能性,有人被引向命運交叉的城堡,有人被引向果殼中的宇宙,目的地不明。
悲觀主義的花朵是心的名勝——讀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離別使月光變得珍貴。月如砒霜,灑在離人心上,開出悲觀主義的花朵。月是夜的名勝,悲觀主義的花朵是心的名勝。
如果愛,請深愛——讀薛濤《牡丹》
薛濤對牡丹的心情,像初戀,像一根纖細而堅韌、由兩股擰作的繩,一股叫纏綿,牽引她從白晝到夜深,日復一日自醉;一股叫悱惻,捆綁她從去春到今春,年復一年輪迴。武則天有兩種選擇,愛或不愛;薛濤也有兩種選擇,愛或深愛。
獻給一個時代的情書——讀韓翃《寒食》
窗外是一座城池,一個春天,幾縷輕煙,芳菲翩躚。窗內的我,心情是一分春色,兩分香甜,三分怡然,四分安閒。宮中的燭火傳遍了長安豪貴的門庭,歲月又在新一輪的鐘鳴鼎食里重新開始,讓多少滄桑巨變轉眼間成為可以記住、也可以忘卻的故事。
沉默的犧牲——讀白居易《燕子樓》
還有一種隱性的殉情,安安靜靜,仿佛什麼都沒發生,好像誰也沒有犧牲,但在旁人窺不見的地方,當事人某些部分暗中死亡,毫不聲張地獻給愛人。比如息夫人固執的緘默、關盼盼十年的足不出戶,沒有死亡,但公道地講,她們向愛情進獻的祭品並不亞於死亡——她們進獻的,是餘生里幸福的可能。
時間如白晝之月,暗中運行——讀劉禹錫《金陵五題》
詩人是另一種獨裁者,他毋需頒布法令或建立軍隊,然而全世界都淪為詩歌的道具供其予取予求,由他安排角色和劇本。……無垠宇宙在詩人面前等待著,不言不語,而詩人終日思索的,是在其中挑選怎樣的演員,展開怎樣的情節,才能成功演出自己內心那部盪氣迴腸、永垂不朽的好戲。
家鄉,在那美的遠方——崔塗《春夕旅懷》
身在此處,卻生活在別處。家鄉,其實存在於他鄉,家裡永遠找不到關於家的蝴蝶夢。
月光再亮,終究冰涼——讀張泌《寄人》二首
李白一生賦詩1059篇,其中341篇與月有關,誇張點說,李白生命的三分之一交付給了月亮。但只一句,便讓我覺得張泌的一生都給了月亮。
繞過詩的守門人——讀張籍《節婦吟》
詩有一群守門人,比如“作者生平”和“創作背景”,如果同那個鄉下人一般一心取得他們的許可再進入詩,或許一生不得進入。如若張籍的“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讓你看到了愛情中的掙扎,就別管他的真實意圖是拒絕招募。我們探尋真實,也珍惜錯覺,錯覺和真實一樣重要,錯覺是彼時彼地心的真實。
鴛鴦蝴蝶夢未完待續——讀崔珏《和友人鴛鴦之什》三首
被人們當做白頭偕老象徵的鴛鴦並無不離不棄的習慣,也無莫失莫忘的約定,《本草綱目》中形容的“終日並游”只是交配期暫時的需要;看似終生戀花、與奼紫嫣紅相廝守的蝴蝶實屬色盲,從最低色階到最高色階,這變化之於它只是一條迂迴的線,它無力察覺其中的驚心動魄與旖旎風光。愛情的起點是憧憬,而我們從起點開始,就錯了。關於愛的期望都是誤會一場,當然免不了黯淡收場。
向記憶深處打聽一個人——讀杜牧《贈別》二首
關於揚州,我會告訴你許多。我將從一組雕花的光輝歲月講起,從壚邊女子如霜的手腕講起,從蘭橈入水的姿態講起,從青石板上馬蹄落下的節奏講起,從夜市燈火與星辰的差別講起,從楊花和雪的關係講起,從二十四橋某一晚淳厚的簫聲講起,從瘦西湖曲折與迴旋的角度講起……關於揚州,我會告訴你許多,但我不會告訴你它在東經119°、北緯32°。此刻,我不願意用數字說話,數字這種語言不適合描述揚州這樣的城市。
後記
序言序言
小徑分岔的花園,與通向花園的所有小徑
這篇文章的題目很怪,我知道。但我不打算改,它準確地表達了我對詩與世界的關係的理解:詩可以延伸出通向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路,包括宇宙和心靈;世界上任何一條路最後都會歸於詩,哪怕這條路一開始和詩南轅北轍。下面的章節,是我在詩中走過的某幾條路,我邀請你與我同行。不過請你注意,這是一次奇怪的旅行,同一條路並不一定通往同一個地方。
暗號•川端與“底”
我知道一個關於川端康成的秘密,這個秘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夜空下一片白茫茫。——這是《雪國》的開場白,它的日文原文是:“國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國であった。夜の底が白くなった。”(“底”在日文中是“底部”的意思)從開場白開始,川端就使用了“底”字,接著會發現,《雪國》中“底”出現的頻率高到不自然的地步,而且相當多的時候並沒有使用“底”字的必要。為什麼迷戀“底”字?背後隱藏著怎樣的訊息?
川端先生已離開人世三十餘年,為什麼會有那么多“底”已永遠成謎,即使川端先生仍在世也未必能解開這個謎,或許先生自己也沒有正確答案。有些暗號無人能解,無人知道那暗號所對應的真相,包括當事人。但正是因為沒有標準答案,或者說到處都是正確答案,這些暗號才顯得意味深長和引人入勝。
詩中藏匿著數量驚人的暗號,詩人都沒發現,你有沒有發現?讀這本書後,你能發現幾個?
捕捉•傅科擺
1851年,在巴黎,法國物理學家傅科為了推翻《聖經》中所說的“大地是靜止不動的”,製作了一個由67米的繩索和28千克的擺錘組成的擺。擺錘下方是巨型沙盤,用於記錄擺錘的運動軌跡。如果地球一動不動,那么擺應在沙上畫下唯一一條軌跡——但是,擺每過一個周期,就會偏離原來的軌跡一點,兩個軌跡之間相差約3毫米。這3毫米,正是地球以子彈速度不停鏇轉的證據。
地球自轉在傅科擺出現之前就存在,在傅科擺將來滅亡之後也會繼續存在,傅科擺和地球的生命比起來,可以忽略不計。但,生命短暫的傅科擺證明了地球自轉永恆的存在。詩與傅科擺是同類,詩用有限之文字表現無限之空間、時間與心靈。一次哭泣,一團雲煙,一枚手印,皆因詩成為永恆的存在。
科學家捕捉地球的脈搏,用傅科擺演示;詩人捕捉靈魂的顫動,用詩篇傳達。傅科擺讓人類了解地球,詩篇讓人類了解自己。傅科擺與詩的區別在於,傅科擺會死亡。
魔術•猶大之窗
《猶大之窗》是美國偵探小說家狄克森•卡爾最精彩的一次“不可能犯罪”:兩個人進入封死的房間後,其中一人陷入了15分鐘的昏迷狀態,不過15分鐘,罪惡——不,說是“魔術”更準確些——已發生。在這密閉的、反鎖的、與世界隔絕的房間裡,另一人已被謀殺,但昏迷者卻不是兇手。如果不是神乾的,那么這房間一定有著一扇只有兇手才看得見的猶大之窗。猶大之窗,不是一扇真的窗,是罪犯用靈活頭腦和縝密邏輯找出的常人的思維死角,是完成這齣不可能犯罪的最佳角度。是魔術,更是藝術。
詩人時時都在製造“不可能犯罪”,帶著詩般的殺意。他們在符號的海洋中尋找那朵能將讀者淹沒窒息的浪花,企圖用一句話、一個字甚至一個標點伏擊讀者,完成注入力量、抽去溫度、剝離思考、阻截血液流動等高難度動作。他們畢生都在尋找通向自身和他人心靈的猶大之窗,進入那棲息在身體裡的、上鎖的房間。
反射•羅氏墨跡測驗
羅氏墨跡測驗,是一種人格測驗方法。測驗者向被試者呈現各種由墨漬偶然形成的形狀,讓被試者在無拘束的環境中自由聯想。被試者的聯想,就是其個性的真實反映。聯想的順序及結果,即是其思想運行的軌跡。
詩如墨跡,顏色和形狀是固定不變的,是創作者賦予的。但從解讀開始,就已成為讀者的作品,是讀者與詩的化合物。一個人解讀一首詩,即是在照靈魂的鏡子,通過詩這一鏡面反射出靈魂的顏色與形狀。你對詩的解釋,就是一份靈魂診斷書。如果沒有做過羅氏墨跡測驗,不妨讀詩看看,效果一樣,且測驗品美得多。
征服•CS
詩人和讀者的關係並沒有想像中那么友好、和諧,甚至恰恰相反,他們好比CS遊戲中的反恐先鋒與武裝暴徒,上演著激烈的對抗。詩人是熱血澎湃的反恐先鋒,子彈是語言、結構、情感、思想和意象,每一發都瞄準讀者的心臟,等待他們投降;讀者是武裝暴徒,或左右躲閃,或坐以待斃,有時被子彈打穿了胸膛,有時安然無恙。奇怪的是,被打穿胸膛的從此愛上殺戮者,而安然無恙的,並不感激主的仁慈和攻擊者的手下留情。
被詩征服,大概是這世界上最美好的失敗方式。在詩的戰場上,我渴望這樣的失敗。
走過了通向花園的所有小徑,我們真的走進了小徑分岔的花園了嗎?末了,以卡爾維諾的話作結:“我對於文學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只有文學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給予我們的感受。”希望這本書給予你豐富的感受。
毛曉雯
2009年5月
後記
後記
1.
欣賞詩歌,其實和欣賞球賽的道理是一樣的。如果你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外行,不熟悉雙方球員的背景和特點,不了解球隊的戰鬥歷史,也不懂得比賽規則,那么即便是最頂級的比賽也無法讓你獲得多少樂趣。你對足球的熟悉程度越深,從球賽當中獲得的快感也就越大,這應該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欣賞詩歌,和玩電子遊戲的道理也是一樣:你參與的程度越深,獲得的樂趣也就越大。而要想參與得更深,自然就有必要精通遊戲的各種規則,熟悉遊戲的地圖和所有道具的特點和使用方法。這應該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很多人在欣賞詩歌的時候,卻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主張:擺脫注釋,擺脫一切背景知識,只憑“最直接的心靈的感悟”,因為“美是不可言說的”。
好吧,即便“美是不可言說的”,但我們不需要在理解詩意的基礎上領會詩歌之美嗎?而理解詩意就需要許多紮實的工作了。況且,美不一定就是不可言說的,只不過有人願意把它言說出來,而有人作了相反的選擇。這看上去應該屬於生活態度的問題,無論哪種選擇都無可厚非。
美如何可以被言說出來呢?道理其實非常簡單。人體為什麼看起來是順眼的,“大師”們可以說人體是得造化之妙,蘊宇宙之氣,法陰陽,合五行,有神鬼莫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但是,也可以有非常樸素的解釋:因為人體是中軸線對稱的。
於是有人會問,維納斯斷了臂,美在哪裡呢?其實這個雕像在斷臂之後依然是中軸線對稱的,並且給人以更多的發揮想像力的空間,這和詩歌的“歧義空間”正是同樣的道理。我們還可以反過來構想一下:如果斷臂維納斯的雕像只斷掉了一隻胳膊呢?
道理就是這樣簡單,以前我甚至沒想過這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我在《人間詞話講評》序言裡的一段話同樣適用於這裡:文藝理論的一大功能就是把所謂不可言說的東西言說出來。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這么做,也不是所有人都贊成這么做,甚至有人覺得似懂非懂的朦朦朧朧的感覺才是最好的,這也無可厚非。“禪客相逢唯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我尊重彈指派的深不可測,但我是講理派。
2.
人們的審美標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舊有的唐詩選本未必適合現在的時代了。《唐詩三百首》是清代的蒙學讀物,《唐詩選》也已經是幾十年前的選本了,帶著那時特有的時代烙印。而我這本書,選講的是一些風格上帶有唯美主義傾向的詩歌,是唐詩中最美麗的那些作品。這樣的選講標準如果放到過去,肯定是要受到批判的。
這本書的初衷,是要做一個古典詩詞的普及讀本,要有一些“暢銷書化”的寫法。我非常認可編輯的要求,也承認這比較符合市場需求。事實上我在以前也寫過這樣的作品,書也頗能為市場接受。但有些事,道理雖然想得明白,卻很難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棄自己想要做得更加專業一些的想法。一坐在電腦前邊,總是不自覺地想要寫得更好一些,會拿出一點暢銷書市場絕不需要的專業精神。但是,在一個連專家們都不斷跨出專業、犧牲專業精神以投身於轟轟烈烈的玩票事業的時代,我這一點點愚蠢的火花也不知道還會閃爍多久。
這本書,內容上我有時也會用上一些論文的筆法,對一些詩歌史上的疑難問題作出適度的辨析,得出自己的結論,希望這個通俗讀物也能有一點點的學術價值,但在形式上用的是散文的形式,希望讀者能獲得一種輕鬆愉快的閱讀體驗。
希望我做到了。
作者
2009年5月
文摘
美將我們俘虜,更美將我們釋放——錦瑟(李商隱)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李商隱(813—858),字義山,號玉谿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開成年間考中進士,歷任縣尉、秘書郎、東川節度使判官等低級職務。一生都受黨爭影響,飽受排擠,政治上很不得志。詩與杜牧齊名,人稱“小李杜”;又和溫庭筠齊名,人稱“溫李”。
如果問唐詩當中哪首詩堪稱第一,這是沒有答案的,但要問哪首詩最具唯美主義色彩,最迷離恍惚、費人猜想,那就非李商隱的《錦瑟》莫屬。
用“唯美主義”這個來自西方的現代標籤貼在李商隱的身上,其實從五十年前就有過了,只是那時候提倡現實主義和階級鬥爭,所以唯美主義這一路的詩人不是接受批判,就是遭到冷落。我們現在天經地義地認為李商隱是一位傑出的詩人,這個觀念的塑造其實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
愛好歷史的人往往會養成一種歷史觀念,正是這種觀念,使他們在看問題的時候和其他人迥然不同。比如我們說起“龍的傳人”,很多人都以為這是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其實也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從二十多年以前以至上古時代,人們並不這么理解問題,龍的形象也很複雜多變。李商隱也是這種情況,我們今天對他的認識大不同於前人對他的認識。從晚唐到清代,李商隱從詩歌到人品,一直都是主流社會批評的對象,儘管偶爾也有人對他標榜一下,但很快又會被時代大潮淹沒。尤其到了明代,文學圈打出了“詩必盛唐”的口號,李商隱作為晚唐詩人就更沒地位了。
李商隱的詩真正受到主流社會的重視一直晚到清朝,到新中國又受三十年的冷遇。我們動不動就說某某詩歌千百年來膾炙人口,有些確實是這樣,但也有不少其實只有很短的膾炙人口的歷史。
李商隱的詩歌為什麼一度飽受冷落呢?原因很多:一是不合儒家正統,正人君子們覺得他的很多作品太淒淒婉婉了,太沉溺於男女之情了,不健康;二是根據以人品論詩品的傳統,人們覺得李商隱人品不好,屬於文人無行的那種,所以連帶著鄙薄他的詩;三是李商隱的一些詩寫得太前衛了,所以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很難被主流社會接受。要說第三點,這首《錦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清朝末年,知識分子們有一個瘋狂地接受西方文化的時期,除了政治哲學和科學技術之外,西方的文學批評、美學理論也被拿過來重新闡釋中國的古典文學,大家都很熟悉的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就是這樣的一部典型之作,還有一些如今名氣沒有那么大的,比如梁啓超也有過一系列這樣的文章,其中講到李商隱,說《錦瑟》、《碧城》、《聖女祠》這些詩,我也看不懂講的是什麼。拆開來一句一句地讓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釋不出來。但我就是覺得美,讀起來感覺很愉快。要知道美是多方面的,是含有神秘性的。(《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
我們經歷過1980年代朦朧詩大潮的人都很容易領會梁啓超的這番話,但對古人來講,這就是前衛。“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只是一些朦朧而美麗的意象堆砌在一起,到底說的是什麼意思呢,很難把握。
在進入具體的闡釋之前,我們不妨先看幾首現代意象派的詩歌。ThomasErnestHulme(1883-1917)是英國意象派的先驅人物,他畢業於劍橋大學數學系,對柏格森的哲學頗有研究,這樣的學術訓練似乎很難使他成為一名詩人,但他寫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詩,比如這首TheSunset:
Acoryphee,covetousofapplause,
Lothtoleavethestage,
Withfinaldiablerie,poiseshighhertoe,
Displaysscarletlingerieofcarmin?蒺dclouds,
Amidthehostilemurmursofthestalls.
詩題是《日落》,但內容和日落毫無關係,只是寫一位芭蕾舞女演員遲遲不願走下舞台,在觀眾不友好的交頭接耳的聲音里高高踮起腳尖,露出了嫣紅的內衣。能和詩題發生關聯的一是這位女演員表演的結束,二是這最後的一點努力、一點留戀和一抹嫣紅。詩歌只傳達了這些意象,但它到底要表達什麼呢?是要表達某種情緒嗎?似乎有一點什麼,卻難以鑿實,字裡行間更不帶一丁點的情緒。
再看他的AbovetheDock:
Abovethequietdockinmidnight,
Tangledinthetallmast?蒺scordedheight,
Hangsthemoon.Whatseemedsofaraway
Isbutachild?蒺sballoon,forgottenafterplay.
這首詩的內容更加簡單,不過是說半夜的甲板上,月亮被桅桿和繩索纏住了,高高地掛著。它看上去遙不可及,其實只是個被孩子玩過之後丟棄的氣球。詩人不動聲色,不動感情,只是平靜地編織意象而已,但他要表達什麼意思呢?如果按照中國小語文教育的套路,給這兩首詩總結中心思想,恐怕誰都會感到無能為力。
我們仔細看看這兩首詩的手法,TheSunset標題里的“日落”和正文裡女演員在走下舞台之前最後的努力,這兩個意象構成一種比喻的關係;AbovetheDock詩中月亮和氣球這兩個意象也構成一種比喻的關係,這叫做意象的疊印(superposition)。我們再來看看意象派最著名的一首詩,EzraPound(1885-1972)的InaStationoftheMetro:
TheApparitionofthesefacesinthecrowd;
petalsonawet,blackbough
捷運車站裡,人群中幻影般閃過的幾張美麗的臉孔,濕漉漉的黑樹枝上的幾片段預告瓣,這兩個意象似乎構成了某種比喻關係,卻很難說清,也許超越了比喻的範圍,詩人只是把這兩個意象並列在一起,如何解釋它們的關係就是讀者的事了。這種手法,叫做意象的並置(juxtaposition)。T.E.Hulme本人作過一個比喻,說詩人把不同意象的疊加或並置,就如同音樂家把不同的音符組成和弦。意象派的創作方法其實就相當於編寫和弦。
再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是美國詩人WilliamCarlosWilliams(1883-1963)的TheRedwheelbarrow:
Somuchdepends
upon
aredwheel
barrow
glazedwithrain
water
besidethewhite
chickens.
整首詩別看分了四節,其實只是一句話,無非描繪了一輛被雨淋過的紅色手推車,旁邊有幾隻白色的小雞。這首詩如果隨隨便便地拿出來,很多人肯定會說“這不就是梨花體么”,但這是意象派的一首經典名作,W.C.Williams之所以得享大名,主要就靠這首詩。詩里看似純客觀地描繪了一個不起眼的場景,詩人卻以“Somuchdependsupon”(這個短語很難被翻譯出來)開頭。像這種極端脫離大眾的詩,只能在詩歌史中某個特定的時期里,由特定的人群欣賞。如果以大眾的、傳統的眼光,用諸如語言是否漂亮、意義是否深刻、比喻是否巧妙,還有抒情性、想像力、象徵主義等等標準來判斷詩歌的好壞,這種詩無疑會被嘲諷為梨花體。在很多古人的眼裡,李商隱的《錦瑟》就屬於極盡字面漂亮、帶有不確定的抒情涵義的梨花體。我們如果把詩歌史和詩歌闡釋史梳理一遍的話,真能生出很多撫今追昔的感嘆來。
1980年代,中國的朦朧詩人們向西方學習現代詩歌的表現手法,英美印象派成了他們最大的素材庫。所以很快地,北島和舒婷他們就算不上“朦朧”了,真正“朦朧”的詩漸漸浮出水面,比如顧城寫了一首極受爭議的詩,叫做《弧線》:
鳥兒在疾風中
迅速轉向
少年去撿拾
一枚分幣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觸絲
海浪因退縮
而聳起的背脊
這首詩之所以飽受爭議,因為無論是北島的《回答》,還是舒婷的《致橡樹》,意思都很明確,都是可以總結出中心思想的,而顧城這首《弧線》僅僅是把四種帶有弧線畫面的意象並置在一起,誰也不知道這首詩到底要說明什麼。意義!意義在哪裡呢?
1980年代的人還無法接受一首沒有“意義”的詩,一首總結不出中心思想的詩。現在回頭看看,《回答》和《致橡樹》那樣的口號體新詩之所以能被寫進詩歌史,主要是因為時代,以詩藝的角度來看並不出彩,而顧城的《弧線》能被寫進詩歌史,卻是因為詩藝。
好了,說到這裡,我們就可以翻回頭去,用現代眼光重新欣賞一下古典詩歌了。我在《人間詞話講評》里介紹過康熙朝的詩壇正宗王士禎,他寫過一組《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以詩論詩,對《錦瑟》下過一句著名的評語:“一篇《錦瑟》解人難。”說明了從唐朝到清朝,這么多年大家也沒弄清楚《錦瑟》到底是什麼意思。也許按照傳統的歸納中心思想的思路,《錦瑟》確實很難解釋,但像“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這樣或許無解的、沒有意義的句子,難道不就是意象派手法中的“意象的並置”嗎?難道不可以和T.E.Hulme的TheSunset、AbovetheDock、顧城的《弧線》一起來理解嗎?
這個想法一點都不前衛,因為中國古典詩歌本來就很有意象派的風格。1980年代的朦朧詩人們紛紛向英美意象派學習,而英美意象派卻熱衷於學習中國古典詩歌。和李商隱齊名的溫庭筠就寫過極具意象派風格的、甚至連英美意象派大師們都無法企及的句子:“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分別是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六個意象並置在一起,純粹的名詞表達,沒有一個形容詞,沒有一個動詞,沒有一個虛詞,不帶作者任何的主觀情緒,現代所謂“零度詩”的最高境界也不過如此了。(當然這只是把句子孤立來看。古典詩歌和意象派最大的不同就是“帶情緒”。)
接下來我們要作一件或許會令梁啓超前輩不快的工作:把《錦瑟》拆開來一句一句地解釋。這就是說,如果遇到意象並置的地方,就把這些意象一個個地講明白。
先看詩題,李商隱寫詩,常有一些有題目的無題詩,就是把首句的前兩個字當做題目,並沒有特殊的意思。這首詩的首句是“錦瑟無端五十弦”,所以拈出“錦瑟”二字作為詩題很合乎李商隱的一貫作風。但是,事情也不好一概而論,我們看一下這類無題詩的例子:《為有》的首句是“為有雲屏無限嬌”,拈出來作為詩題的“為有”二字獨立來看並不構成什麼意思,和詩的內容也沒有任何關係。但《錦瑟》就不同了,首句是“錦瑟無端五十弦”,就是在描寫錦瑟,從這個角度看,它不應該屬於無題詩,倒更像是詠物詩。
蘇軾就說過《錦瑟》是一首詠物詩。宋人筆記里記載過這樣一則故事:就連素來以淵博著稱的黃庭堅也看不懂《錦瑟》的意思,於是去請教蘇軾。蘇軾說:《古今樂志》上說,錦瑟這種樂器有五十根弦,也有五十個弦柱,奏出的音樂有“適、怨、清、和”四調,這就是《錦瑟》一詩的出處。
記載這個故事的黃朝英還對蘇軾的說法作了進一步的解釋:“莊生曉夢迷蝴蝶”,是為“適”;“望帝春心托杜鵑”,是為“怨”;“滄海月明珠有淚”,是為“清”;“藍田日暖玉生煙”,是為“和”。(《靖康緗素雜記》)這就是說,首聯“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主要描寫錦瑟的外形特徵,頷聯和項聯的四句分別描寫了錦瑟“適、怨、清、和”四調。至此,有典故出處,有專家鑑定,意思也能講通,詠物詩的說法看來是可以成立的。但麻煩就在尾聯的兩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這和詠物詩好像搭不上界。
在蘇軾之前還存在過一種推測,認為“錦瑟”或許是一個人名,而這個人就是令狐楚家的一名侍女。(劉攽《中山詩話》)令狐家和李商隱有很多的恩怨糾葛,這裡不作細表,只看這個推測,多少還是有幾分合理性的:“錦瑟”確實很像是侍女或歌伎的名字,這首詩看上去也與男女之情有關。但證據實在太薄弱了,這倒很好地反映出了讀者們的一種困境:極力想要貫通這首詩的意思,要總結一個中心思想出來,最終也只能找出一個連自己都未必相信的解釋。
那么,這首詩要么是懷人的,要么是詠物的,總不可能兩者都是。宋朝的讀者們據此各選陣營,伸張各自的解釋。啟蒙主義時代的歐洲流行過一句諺語:如果有兩種觀點爭執不下,則真理必在其中。懷人說和詠物說爭執不下,真理到底在哪裡呢?
這正是黑格爾的辯證法發揮闡釋力的時候,懷人說為“正”,詠物說為“反”,交戰一段時間之後就該出現一個“合”了。許彥周頗合時宜地提出了一個折衷之見:“令狐楚的侍女”不假,“適、怨、清、和”也沒錯,如果說令狐楚的侍女能用錦瑟彈奏出適、怨、清、和的曲調,問題不就結了么!(《許彥周詩話》)儘管缺乏足夠的依據,這卻稱得上是一個自洽的解釋。明代的屠隆更有意思,說令狐楚有個侍妾名錦,擅長鼓瑟,演奏起來盡得“適、怨、清、和”之妙。(《唐詩選脈會通評林》引)
諺語並不總是對的,兩種意見爭執不下的時候,真理也許遠在別處。到了金代,元好問提出了一個新的解釋,說《錦瑟》是詩人自傷年華之作。這是我們最熟悉的說法,不少初階詩詞愛好者甚至以為這就是《錦瑟》的唯一解釋或標準解釋,因為現代的唐詩注本基本都採用這個說法。
元好問以詩論詩,寫過一組《論詩》絕句,對李商隱的評價就在這裡:
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這首詩並不是專論《錦瑟》,而是綜論李商隱和宋代效仿李商隱的西崑體,前兩句是直接從《錦瑟》化用來的。元好問一面感嘆李商隱這種詩風晦澀難懂,一面借《錦瑟》的句子點出了李商隱詩歌的核心內容:“望帝春心托杜鵑”是說春恨,“佳人錦瑟怨華年”是說自傷年華,兩者都是一個意思,李商隱的很多作品都脫不出這個類型。李商隱有一首《朱槿花》:
勇多侵路去,恨有礙燈還。
嗅自微微白,看成沓沓殷。
坐疑忘物外,歸去有簾間。
君問傷春句,千辭不可刪。
槿花的特點是朝開暮落,詩人清早出門才看到花開,晚上歸途就看見花落,難免悵然,吟詠嘆息不能自已,所以是“君問傷春句,千辭不可刪”。這一句不但是為本詩作結,更刻意說是為自己的一生創作作結。
李商隱還有一首《杜司勛》,是寫給當時就任司勛員外郎的杜牧的: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勛。
這首詩非常推崇杜牧的創作,還把杜牧引為同道,最後兩句概括出了杜牧詩歌的與眾不同之處:著力抒寫傷春和傷別的題材。
以上這兩首詩,尤其是後一首,我以為應當是解讀《錦瑟》乃至李商隱整體創作的關鍵。《杜司勛》在現在的唐詩選本里比較常見,但注家往往忽視了詩中一處具有點明主旨之功的用典,即“高樓風雨感斯文”一句中的“斯文”。
這個詞之所以易被忽略,因為它實在不像用典,字面意思很簡單,無非是說那些文字,即杜牧的創作。但這裡的“斯文”是個雙關語,既有字面的意思,也有典故上的出處,即《論語》里的“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地的人曾經遭受魯國陽貨的迫害,偏巧孔子長得和陽貨很像,結果在路過匡地的時候被當地人誤認為陽貨,受到了拘禁。孔子看自己大有性命之虞,也許是很自信,也許是自我安慰地說了這樣一番話:“周文王死後,傳續文化的重任不都在我的肩上嗎?天若要滅絕這種文化,我也沒辦法;但天若不想使這種文化斷絕,匡人能拿我怎么樣呢?”
我這裡用“這種文化”來翻譯“斯文”,不很準確。“斯”是代詞,可以翻譯成“這”或“那”;“文”在這裡是指周禮,也就是周代開國元勛們制定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孔子主張“克己復禮”,所謂“復禮”就是要在春秋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恢復周初的典章制度。所以,自從《論語》成為經典之後,“斯文”這個本來很普通的詞就有了特殊的涵義,成了歷代儒家知識分子所追尋的“道”。
美國漢學家包弼德有過一部研究唐宋思想史的名作,書名就叫“ThisCultureofOurs”:IntellectualTransitionsinT?蒺angandSungChina,被加了引號的“ThisCul?鄄tureofOurs”就是《論語》里的“斯文”。他對這個詞在唐代的涵義有如下的解釋:“降及唐代(618—907),斯文開始首先指稱源於上古的典籍傳統。聖人將天道(thepatternsofHeaven)就是現在所說的‘天地’或自然秩序,轉化成社會制度。由此引申,斯文包括了諸如寫作、統治和行為方面適宜的方式和傳統。人們認為,這些傳統源於上古三代,由孔子保存於儒家經典,並有所損益。”(《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這就是李商隱的時代觀念中的“斯文”。現在我們還有一個常用詞,叫做“有辱斯文”,源頭也在這裡。
所以李商隱為什麼要在“高樓風雨”里去“感斯文”,引申的涵義是在晚唐那個風雨飄搖的政局當中,深感於堅守斯文的不易,那么“短翼差池不及群”也就不再是現在許多注本解釋的那樣,自謙才力淺薄,不如杜牧,而是明說杜牧,暗含著自傷身世,說你我這樣有政治抱負的人卻被朝中當權的兗兗諸公們遠遠拋在身後,寂寞無依。(為什麼說那些注本解錯了,還有一個證據:所謂“不及群”,既然是“群”,就不可能是說杜牧這一個人。)
政治抱負無法施展,這才“刻意傷春復傷別”,把一肚子的悲憤、希望與委屈都寫在傷春和傷別這樣看似風花雪月的詩作里。——我們要知道,傷春和傷別是歷代詩歌的兩大主題,寫的人很多,那么為什麼李商隱說“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勛”呢?因為杜牧的傷春和傷別是別有寄託的,不是普通的風花雪月。李商隱說出這兩句來,暗含有兩個意思:一是“我是你的知音”,二是“你是我的同道”。為什麼我說這首詩是我們理解《錦瑟》乃至理解李商隱全部作品的關鍵呢,答案就在這裡。
以下逐句來看。“錦瑟無端五十弦”,所謂錦瑟,其實就是瑟,加一個“錦”字一是為了字面漂亮,給人一種高貴華美的感覺,二是為了湊成雙音節詞,這都是詩文當中常見的手法。我在《納蘭詞典評》里講過一個“玉笛”的例子:同樣描寫一支笛子,如果你想表達君子情懷,就說“玉笛”;如果你想表達鄉野之情,就說“竹笛”;如果你想表達豪客滄桑,就說“鐵笛”。只有笛子是真的,那些玉、竹、金、鐵一般都只是詩人為塑造意境而主觀加上的修飾,不可當真。就詩人們而言,這些修飾都是意象符號,是一種傳統的詩歌語言。
據說瑟這種樂器本來有五十根弦,有次太帝讓素女鼓瑟,覺得音調過於悲傷,就改了瑟的形制,變五十弦為二十五弦。(《史記•封禪書》)李商隱說錦瑟“五十弦”,說的是傳說中的瑟的古制。
問題馬上就出現了:通行的瑟,主要就是二十五弦的,五十弦的瑟僅見於傳說,那么詩人為什麼不說“錦瑟無端廿五弦”呢,這也完全合乎七律的音律呀?——最常見的解釋是:詩人寫作這首詩的時候,正值五十歲左右,所以從錦瑟的五十弦聯想到自己所度過的歲月。持此論的學者當中,最權威的要算錢鍾書了。但如果採信《年譜》,李商隱寫這首詩的時候當在大中二年,那時他不過三十五歲。(葉蔥奇《李商隱詩集疏注•年譜》)看來數字不能指實,否則的話,在三十五歲緬懷年華就一定要用含有三十五這個數字的東西來起興,詩就沒法寫了。
面對這種問題,現代人比前人優越的地方就是可以電腦檢索。檢索一番,例證就羅列出來了,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李賀詩有“五十弦瑟海上聞”,有“清弦五十為君彈”,鮑溶詩有“寄哀雲和五十絲”,有“娥皇五十弦”,吳融詩有“五十弦從波上來”,李商隱自己的詩里也有“雨打湘靈五十弦”,有“因令五十絲,中道分宮徵”。所以詩人好古,“五十弦”可以代指瑟這種樂器,這就是唐代的一個詩歌套語,並沒有什麼深刻的涵義。但是,太帝破五十弦為二十五弦的傳說給瑟這種樂器定下了一個悲慟的調子,給這首《錦瑟》也定下了一個悲慟的調子。
解決掉了這個問題,就該琢磨“無端”的涵義了。葉蔥奇把《錦瑟》解釋為客中思家的詩,從詩人當年的處境出發,認為首句是感嘆自己為衣食所迫,遠去外地,不能和家人團聚,所以“無端”的用法和杜甫詩中的“邂逅無端出餞遲”相同。(《李商隱詩集疏注》)這也是一個自洽的解釋,但我們有兩個問題要說:一是杜詩這樣用“無端”一詞是比較特殊的,這個詞在唐代最普遍的意思和在現代一樣,表示“沒來由”、“無緣無故”;二是清代的屈復提出過一個具有普適性的讀詩方法:一首詩如果沒有作者自序,讀者也就不必費力索隱詩歌背後的實事了,就詩論詩也就是了。《錦瑟》正屬於背景極難考索的情況,太多地聯繫實事未必是一種恰當的解讀方式。
至此我們知道,“錦瑟無端五十弦”,是一種很“無理”的說辭。錦瑟為什麼會有五十根弦呢?這是“無端”的,沒來由的。雖然沒有來由,卻真切地以一弦一柱勾起詩人對年華往事的思緒。——“一弦一柱思華年”,所謂“柱”,是琴瑟上系弦、調弦的小木棍,和提琴、吉他上的鏇鈕是一類的。如果把“柱”用膠黏住,弦就不能調了,這就是所謂“膠柱鼓瑟”。這句詩有兩種解釋:一是比較實在的,聯繫上句,詩人從錦瑟沒來由的五十弦里想到自己行年五十;二是以“一弦一柱”指代一音一節,是說詩人從錦瑟奏響的鏇律里勾起對青春往事的浮想聯翩。
第一種解釋在現在的注本里比較常見,但第二種解釋才是合理的,原因除了前邊提到的那些之外,還有詩句中“華年”的意思。“華年”並不等於現代漢語裡的“年華”,它其實是“花年”,因為“花”就是“華”。漢字里本來沒有“花”字,“花”是後起的俗字,後來約定俗成,才在“花”這個義項上取代了“華”。所以“華年”用在人的身上,特指青春年少的美好時光,四五十歲就不能再算“華年”了。我們從宋詞里看到對《錦瑟》的化用,宋人就是這樣理解的,比如“錦瑟華年誰與度。暮雨瀟瀟郎不歸”、“追念舊遊何在,嘆佳期虛度,錦瑟華年”、“家本鳳樓高處住,錦瑟華年”、“紫燕紅樓歌斷,錦瑟華年一箭”。
首聯的意思至此就比較明確了:詩人聽到錦瑟的鏇律,想到了逝去的青春。這一聯里最關鍵的是“無端”一詞——年輕人的喜怒哀樂往往比較簡單,高興是因為什麼,傷心是因為什麼,都有一一對應的關係,說得清,道得明,但人一旦上了年紀,經歷得多了,坎坷得多了,情緒和事情就沒有那么清晰的對應關係了。當一種愁緒泛起的時候,你不再說得清到底因為什麼,就像杜牧登上九峰樓,聽到角聲響起,寫下“百感衷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角聲到底傳達了什麼意思呢,其實沒有任何意思,但一下子便觸發了詩人的萬千感受。所以說有些作品需要用歲月去體會,年輕人很難理解得了。
《錦瑟》的“無端”營造出了比杜牧那句詩更為廣闊的歧義空間,會讓讀者想到很多很多。錦瑟為什麼是五十弦,為什麼不是三十弦或者六十弦,這是問不出所以然的,無緣無故的。中年心事濃如酒,多少悲歡離合、酸甜苦辣,糾結在一起,或被一聲畫角勾出百感,或被一曲錦瑟惹動衷腸,似乎也是無緣無故的,找不出任何明確的因果。
再看頷聯兩句:“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我在《納蘭詞典評》的序言裡簡單講過律詩的讀法,就用這首《錦瑟》作的例子。我們讀律詩,不能像讀散文一樣,而要像讀八股文一樣才行。律詩有一套嚴謹的結構,一共八句話,每兩句為一聯,構成首聯、頷聯、項聯、尾聯四組,這四組構成了“起、承、轉、合”的關係,也就是說:首聯要給全文開頭,頷聯要承接上文,也就是承接首聯,順勢下筆,項聯要轉折,尾聯作總結。一首律詩就像一篇小型八股文,我們得知道如何從它的結構規則來讀。
像《錦瑟》的頷聯“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在結構上要起到“承”的功能,所以它是上承“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而來的,既然首聯的意思是詩人聽到錦瑟的鏇律,想到了逝去的青春,頷聯便應該進入回憶才對。
“莊生”一句,用到一個廣為人知的典故,即《莊子•齊物論》里夢蝶的故事:莊周回憶自己曾經夢為蝴蝶,悠然暢快地飛舞,完全忘記自己是誰了,忽然醒覺之後,驚奇地發現自己還是莊周。這一刻真是令人恍惚,不知道是莊周夢為蝴蝶呢,還是蝴蝶夢為莊周?
莊子講述夢蝶的故事,本是為了說明“物化”這個哲學觀念,但詩人不搞得那么深刻,只是用它來形容一種似夢似真、疑真疑幻的感覺。此刻沉浸在錦瑟的音樂聲中,水樣流去的錦樣年華在眼前依稀看見,是青春的自己夢到中年聽琴,還是中年的自己夢到青春往事,如同莊周夢蝶,恍惚間無從分辨。
我這樣講,有點把詩句鑿得實了,我們不妨把夢蝶當做詩人營造出來的一個意象,一個處處似實、落腳皆虛的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