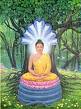 《三彌底部論》
《三彌底部論》簡介
【正量部】
(梵Sammiti^ya、Sammati^ya、Sammr!ti、A^rya-sammr!ti-nika^ya,巴Sammitiya、Sammiti,藏Kun-gyis bkur-ba、Man%-bkur-ba)
小乘二十部之一。佛滅第三百年,與法上部、賢胄部、密林山部同時自犢子部分出的學派。音譯三彌底、沙摩帝、三眉底與、三密栗底、三摩提、式摩、彌離底、彌離、阿離耶三密栗底尼迦耶。又譯作聖正量部、正量弟子部、一切所貴部。
關於此部名稱之由來,《異部宗輪論述記》(卍續83·439下)︰‘正量部者,權衡刊定,名之為量,量無邪謬,故言正也。此部所立,甚深法義,刊定無邪,目稱正量,從所立法,以彰部名。’即以宗義立名。另依《三論玄義》載(大正45·9c)︰‘正量弟子部,有大正量羅漢,其是弟子,故名正量弟子部。’又,西藏所傳清辨(Bhavya)之《教團分裂詳說》(Sde-pa tha-dad-par-byed-pa dan^rnam-par-bs/ad-pa)中,謂此部之祖為Sam-mata,故部名稱為Sammati^ya。此為因人立名。西藏所傳另有一說。謂此部由其所住之地得名,故又有Avantaka與Kurukulaka兩種梵名。
此部之起源,諸傳雖多主張出自犢子部,然《文殊師利問經》則謂出自賢部(即賢胄部)。《出三藏記集》卷三謂此部與僧伽提部(即說轉部),均由迦葉維部所旁出。清辨以此部為屬於上座部十部之一。《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藏文《比丘婆樓沙具羅問論》、《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等謂,此部與大眾部、有部、上座部共為根本四分派。
依《大唐西域記》所載,七世紀中葉玄奘入印度時,正量部之傳布僅次於說一切有部,盛行於北印外之十九國,僧徒合計六萬多人。又載玄奘歸國時也攜回此部之經律論十五部。今此十五部已佚失。《南海寄歸內法傳》載,正量部三藏有三十萬頌,當時盛行於西印度之羅荼、信度等地。
此部主要學說,大多篤守犢子部本宗舊說。此外,亦有依舊說而作進一步推論的;也有正與大乘學說相對峙的。此部主張由於身口業起滅無常,不能久住,故業之存在並不是業法本身。業之能招致果報,乃由於業之薰習積聚之力量。對於心色二法的性質,此部以為心法剎那滅,而色法有時暫住,故色心分離,各自獨立。此說與瑜伽系學說相反。
演變
正量部是從早期佛教犢子部分化出來的,爾後成為本宗的代表,活躍在西印和西南印。據7世紀上半葉玄奘記述,除北印以外,正量部已遍及全門19個國家,僧眾6萬人,中心在摩臘婆。西南摩臘婆①與東北摩揭陀,並列為五印的兩大學術重鎮,其時,正量部有寺數百座,僧徒兩萬餘人。但關於此部的具體歷史狀況,所知很少。
正量部是與大乘思想聯繫密切的小乘派別,特別接受了菩薩行的入世和救世思想。但對與其同時興起的瑜伽唯識學說,則取批判態度。傳說南印老婆羅門般若毱多(智護)以正量部的觀點作《破大乘論》,可能就是針對瑜伽學派的。正量部強調境在心外,心外有境;心之取境,是直線式的反映,不經過任何中介。這種說法,同瑜伽學派全力主張唯識無境和“帶相”緣境之說,全然對立。顯然,正量部的說法是符合常識的,但失之於粗糙。
正量部堅持犢子部的補特伽羅有“我”說,同時發展了“業力不失”的宗教觀念。它認為,在“業”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不是有部所主張的那種“意業”,而是表現為語言行為的“表業”,也就是說,它不贊成動機論,而是把直接造成實際後果的言論和行動放在第一位。
相關內容
正量部梵名三彌底耶(Sam-mitiya)原系創派的人名,所以從前也譯作‘正量弟子部’。另外,舊譯和西藏譯作‘一切所貴部’,這是部名原文轉作娑摩底耶(Sammati^ya)的緣故。這一部乃從犢子部分裂出來,各家傳說差不多一致。至於分裂的原因,據《異部宗輪論》說,是為了解釋‘已解脫更墮’云云的一個頌,各家的意見不同,犢子部一時分成四派,正量便是其中之一。又據真諦所傳,犢子部原來推崇《舍利弗阿毗曇》,後來各家感覺毗曇所說還不完備,便各自造釋補充,如是意見紛歧,因而分派。照此一說,那有問題的頌文應該和《舍利弗阿毗曇》有關,但在漢文譯本里還找不出來。並且頌文簡略,意義也不易明了。窺基的《異部宗輪論述記》採取舊說,舉出四家不同的解釋,大體上是談阿羅漢退墮不退墮的問題。我們另從南方所傳敘述部執的《論事》一書看,犢子部本宗和正量部都主張阿羅漢有退(見《論事》第一品第二章),而這一主張在各部派的異執里還占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論事》特別將它列為二一六種異執的第二種。對於退墮的解釋不同,當然可以成為分派的原因。不過四部中正量和犢子本宗關係比較密切,正量所有的新主張最初都被看作犢子變化之說,並不用正量的名義出場。因此在《大毗婆沙論》編纂的時代(西元二世紀),犢子部的主張只有和一切有部不同的六、七條(見《大毗婆沙論》卷二),到了龍樹著作《中論》時(西元三世紀)便說犢子更有‘生生’等十四種俱生法和‘不失法’之說(見《中論》的〈觀三相品〉、〈觀業品〉),這些都是正量部分出以後的新說仍舊歸之於犢子名下的。
正量部的名目到安慧、清辨時代(西元六世紀)才十分顯著。所以有這一變化,大概是正量部關於業一方面的理論得到發展的緣故。此後勢力日盛,像玄奘在《大唐西域記》所載,當時(西元七世紀)印度除了北印以外,都有正量部的傳播,明文列舉了十九國,僧徒合計六萬多人。摩臘婆國是西印度佛學的中心地,而正量部僧眾就有兩萬人,可見它在各部派中如何的占有勢力。因此,像《慈恩法師傳》卷四所說,當時南印度老婆羅門般若■多(智護)發揮正量部的說法,作了《破大乘論》七百頌,不但為各派小乘師所一致推崇,而且使那爛陀寺答應戒日王的請求去參加辯論的各位印度大德都喪失了自信,這也可說明正量部的議論在當時發生如何的影響。其後雖然經過玄奘《制惡見論》的破斥,又有過曲女城無遮大會的擴大宣傳,但它的勢力依然存在,三十年後義淨到印度之時,還相當盛行,一直維持到波羅王朝的時代(西元八世紀以後)。
次談典籍。正量部後來既成為一大宗,便和其餘上座部等大宗一樣,也具備著它獨有的經律論三藏,這從《慈恩法師傳》卷六說玄奘曾由印度帶回正量部的經律論十五部,可以證明。不過那些經律早已散失,詳細內容現無可考。只有關於經藏即四阿含裡面的重要義類,可以從和正量部淵源最近的賢胄派(犢子部分出的四派之一)著述《三法度論》(東晉譯)見得一斑。另外律藏也有《明了論》(正量部律師所造,陳譯)略攝大義。至於論藏,以《舍利弗阿毗曇》為根本,漢譯有其書,但不完全。此外還有些解釋毗曇的論著,現存的《三彌底部論》(失譯,今勘應附梁陳錄)就是一種。又《慈恩法師傳》卷四說玄奘在北印度缽伐多國所學的《攝正法論》、《教實論》,也都是有關正量部的書。《攝正法論》或者即是宋譯的《諸法集要經》,原系觀無畏尊者從《正法念處經》所說集成頌文,闡明罪福業報,正是正量部的中心主張,而《正法念處經》唐人也認為是正量部所宗的。《教實論》也就是《聖教真實論》,瞿沙所造,沒有譯本,相傳是發揮‘有我’的道理,為犢子部根本典據。玄奘在缽底多國學習正量部的根本毗曇,同時兼學這一書,可見也是正量部所重視的。
再談正量部的主要學說。這裡面有篤守犢子部本宗舊說的,有依據舊說作進一步推論的,也有正和大乘學說對峙的。最先,守舊之說,即是犢子部獨有的‘有我論’。‘我’這一名詞,系‘補特伽羅’的旁譯,因為說‘補特伽羅’(正翻‘數取趣’),說‘我’,說‘有情’,說‘命者’,都指的一種事實,而這些名目原來是作同義語看待的。所謂‘有我’,即是這一種法體在諦義上(實有的意義)、勝義上(究竟的意義)是可得的,存在的。犢子部這種主張對於正統佛學無異是叛逆之說,佛學根本發呶我道理,而犢子偏偏主張有我,豈非背道而馳?但這只是表面的。實際它和佛家以外的學派所說‘有我’並不全同,而對佛家余義也取得一些調和,所以儘管不絕地受到批評、破斥,但它依舊流行,並還影響到其他部派,為他們暗地裡採用著,像大眾部的根本識、化地部的窮生死蘊,乃至說一切有部的同隨得,都不妨看作變相的有我說。
正量部對於這種理論有比較詳盡的解說,見於《三彌底部論》。據論所說,犢子部有我學說的建立乃是經過料簡了內外各種異論而後完成的。這些異論,像佛家部派中的無我說、片面的有我說(或者離蘊、或者即蘊、或者是常、或者無常等),以及有我無我不定說,還有餘宗的實有我論(一異斷常等等說法)都是的。離開種種不正確的說法,所建立的我便和五蘊的關係不得說一,也不得說異,它的性質也是非斷、非常而推論的結果,它是歸於五種所知法(即對象)裡面的不可說法的。
另外,佛之說我可以看它是施設的假說,分成三類,一依假,二度假,三滅假(這三類名稱在《三法度論》的譯文中作受施設、過去施設、滅施設)。佛說有時指現在有執受的內蘊等(如有情血肉的色蘊等)為我,這屬於依假。譬如火之依薪,我對所依蘊等是一是異,都不可說。佛說有時又通三世來作假設,比方在種種本生上說,今我(佛自稱)即是過去頂生王等;又比方作種種授記說,汝慈氏未來當作佛等。這些各有自體,相續不亂,屬於度假(度即三世轉移之義)。佛說還有時在有餘的暫時滅(但舍此身)和無餘的永久滅(不受後有)方面也用我作自體來區別,但一異斷常都不可膠執,這就是滅假。即由三類假說,不妨承認有我,歸在不可說的一類法中。正量部對有我說作這些解釋,不用說是含有補充的意味的。
其次,推闡的新說,這是關於業報的理論。本來犢子本宗主張有我用意在於成立生死解脫的不落空,但推究怎樣才有生死或解脫,這就會牽涉到業力的一方面,因此,有我論的骨幹必然是業論。正量部闡明此義,很多新解。比方說業的存在並不是業法的本身,因為身口意業起滅無常,都是不能久住的。業之能招致果報,乃由於它薰習積聚的力量。那種積聚是不相應行,和心一道起滅,卻不相應;它既無所緣對象,又是無記性質(這些都是和業自身顯然有別的。詳見《論事》第十五品第十一章)。還有業的積聚可以總分四類,欲界的業和它的習氣以類積為一聚,其餘色界、無色界、無漏也同樣的各以其類各為一聚。這些業積相續存在,不是一期生死即了,必須相隨到了修道或入涅槃方才消滅。佛所常說的‘不失法’便是指此而言。這很像借債人所立的券契,憑著它就需還欠。正量部以此解釋業的決定,比較周到,《中論》的〈觀業品〉引了他們的主張,有這么一個頌︰‘雖空而不斷,雖有而不常,諸業不失法,此法佛所說。’(此頌在青目的註解里變成了正面文章,好像是龍樹所答,但依清辨的《般若燈論》看,這明明是正量部的主張。)即由於有不失的業券說法,便進一步對於業的性質得著種種闡明。第一,表色不妨看成業的一類;第二,表色可以認作律儀;第三,色法也有善惡性的區別(這些詳見《論事》第八品第九章、第十品第十章、第十六品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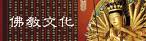 《三彌底部論》
《三彌底部論》最後,對破大乘之說,主要是破瑜伽學系關於所緣緣的說法。正量部分析心色二法的性質,以為心法剎那滅,而色法有時暫住,這便使色心分離,各自獨立,對於瑜伽系學說根本相反。像無著所著《顯揚聖教論》成立色法念念滅即是以色隨心而說的(見論卷十四〈成無常品〉)。正量部又主張心之緣境可以直取,不待另變相分,這更和瑜伽學說大為逕庭。瑜伽學說流行之時正量部也勢力全盛,它們中間曾發生正面的激烈衝突,像《慈恩法師傳》卷四所載玄奘痛破般若■多之說並引起曲女城無遮大會裡擴大宣傳的那一番因緣,可算是勢所必至的。可惜般若■多破大乘的原作和玄奘反破他的著述都已失傳,彼此往返的議論,不得其詳,只有唐人留下一些傳說,以為正量部師般若■多所破的是大乘所緣緣帶相義,玄奘在無遮大會上也針對此破予以反駁(見《成唯識論述記》卷四十四)。又說,無遮大會上玄奘所提出的是一個成立唯識道理的比量(見《因明入正理論述記》卷五),依據這些傳說,正量部破瑜伽學說乃是集中在所緣緣的一點,可以無疑。
相關詞條
參考
1 中華佛教 http://www.cnbuddhism.com/cid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265
2 http://tieba.baidu.com/f?kz=1457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