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簡介
徐晃不聽王平意見,被黃忠,趙雲打敗,王平降玄德。
操被劉備打敗,回到南鄭,魏延、張飛已得南鄭,操走陽平關。亮以疑兵勝操。
操親領兵戰,備兵大敗曹兵,操棄陽平關而逃至斜谷界口,進退兩難,殺了楊修,次日出兵大敗回京兆。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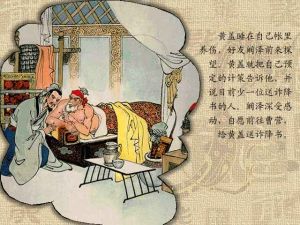 《三國演義》第七十二回
《三國演義》第七十二回卻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聽,渡過漢水紥營。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云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教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夾攻,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敗。”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為偏將軍,領嚮導使。卻說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降劉備矣!”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恐孤軍難立,遂退於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人;乃回到營中,喚趙雲分付:“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我營中炮響:炮響一番,擂鼓一番。只不要出戰。”子龍受計去了。孔明卻在高山上暗窺。次日,曹兵到來搦戰,蜀營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發。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炮。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方才回營欲歇,號炮又響,鼓角又鳴,吶喊震地,山谷應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闊處紥營。孔明笑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
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擂鼓三通,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並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上弒母后,自立為王,僭用天子鑾輿,非反而何?”操怒,命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迎。交戰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為西川之主。”大軍齊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皆爭取。操急鳴金收軍。眾將曰:“某等正待捉劉備,大王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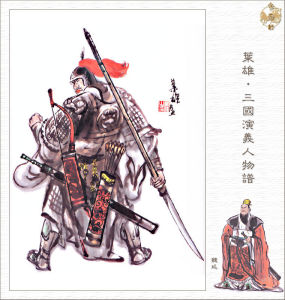 魏延
魏延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閬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此來,何敗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為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四路軍將,各引嚮導官軍去了。
卻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報曰:“今蜀兵將遠近小路,盡皆塞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操正疑惑間,又報張飛、魏延分兵劫糧。操問曰:“誰敢敵張飛?”許褚曰:“某願往!”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草。解糧官接著,喜曰:“若非將軍到此,糧不得到陽平矣。”遂將車上的酒肉,獻與許褚。褚痛飲,不覺大醉,便乘酒興,催糧車行。解糧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去。”褚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哉!今夜乘著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許褚當先,橫刀縱馬,引軍前進。二更已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至半路,忽山凹里鼓角震天,一枝軍當住。為首大將,乃張飛也,挺矛縱馬,直取許褚。褚舞刀來迎,卻因酒醉,敵不住張飛;戰不數合,被飛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馬;軍士急忙救起,退後便走。張飛盡奪糧草車輛而回。卻說眾將保著許褚,回見曹操。操令醫士療治金瘡,一面親自提兵來與蜀兵決戰。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須兒來,汝假子為肉泥矣!”劉封大怒,挺槍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炮響,鼓角齊鳴。操恐有伏兵,急教退軍。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多,奔回陽平關,方才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蜀兵從後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操大敗。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一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能手格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夫之勇,何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眾,縱橫天下;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為將。”操問:“為將何如?”彰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因聞操在陽平敗陣,故來助戰。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須兒來,破劉備必矣!”遂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原來馬超、吳蘭兩軍殺來,曹兵驚動。孟達引兵夾攻。馬超士卒,蓄銳日久,到此耀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曹彰正遇吳蘭,兩個交鋒,不數合,曹彰一戟刺吳蘭於馬下。三軍混戰。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紥住。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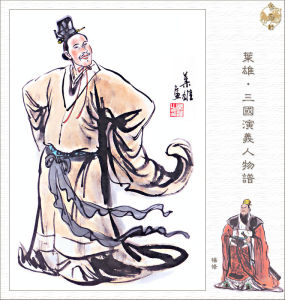 楊修
楊修適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因而有感於懷。正沉吟間,夏侯惇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眾官,都稱“雞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報知夏侯惇。惇大驚,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得臨行慌亂。”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於是寨中諸將,無不準備歸計。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手提鋼斧,繞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原來楊修為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闊字也。丞相嫌園門闊耳。”於是再築牆圍,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眾分食訖。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操雖喜笑,而心惡之。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著,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晝寢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床睡;半晌而起,佯驚問:“何人殺吾近侍?”眾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為操果夢中殺人;惟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嘆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與眾商議,欲立植為世子,曹丕知之,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簏藏吳質於中,只說是絹匹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徑來告操。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丕慌告吳質,質曰:“無憂也:明日用大簏裝絹再入以惑之。”丕如其言,以大簏載絹入。使者搜看簏中,果絹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譖害曹丕,愈惡之。操欲試曹丕、曹植之才幹。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卻密使人分付門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門吏阻之,丕只得退回。植聞之,問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為能。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修又嘗為曹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即依條答之。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修死年三十四歲。後人有詩曰:“聰明楊德祖,世代繼簪纓。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繡成。開談驚四座,捷對冠群英。身死因才誤,非關欲退兵。”
曹操既殺楊修,佯怒夏侯惇,亦欲斬之。眾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來日進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為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大罵。操令龐德出戰。二將正斗間,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斬!”眾將努力向前,魏延詐敗而走。操方麾軍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刺斜里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視之,乃龐德也。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馬超已退。操帶傷歸寨:原來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卻門牙兩個,急令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卻教龐德斷後。操臥於氈車之中,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趕來。曹兵人人驚恐。正是:依稀昔日潼關厄,仿佛當年赤壁危。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賞析
本回演義的前半章說到曹操被諸葛亮的計謀弄的焦頭爛額,此事在上一章便已經解釋過了,絕無可能,漢中戰役中諸葛亮一直在後方負責後勤,根本不可能來到前方指揮戰事,這只是演義為了神話諸葛亮的又一做法而已。演義的後半章則有一件事頗引人注目,便是楊修之死。
楊修,漢太尉楊彪之子,以才思敏捷著稱,與曹植交好,為其出謀劃策以奪取世子之位,不過史書中說起他的功績則遠不如曹魏中的諸多大臣,然而在諸多小說筆記中談到了他與曹操鬥智的諸多事,而他與曹操的關係則頗為後人所津津樂道,有一部京劇《曹操與楊修》便是戲說此事。
演義中在談到楊修之死提到了兩點曹操要置於楊修死地的原因,其一是楊修是曹植心腹,曹操在定下曹丕為世子後,惟恐他日後生事而將其處死,以斷絕曹植羽翼;而其二則是楊修才思敏捷,在鬥智上屢屢超出曹操,並能猜出其心思,曹操厭惡之,而藉機將其處死,這一點也是後人最為關注的,因為這一點關係一個問題,便是領袖與其部屬應當如何相處。
楊修的死之所以能引起後人的關注,很大程度便是因為歷史上的諸多文人將自己代入楊修的角色,深哀自己才高八斗,卻被君王所忌,這一事例不單只是楊修而已,韓信,文種諸多等人都是如此,那么,領袖是否真的忌憚其部屬呢?
說到這點,我們不能不先說一下領袖的能力。在評書中,在演義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君主無善戰之本領,無謀劃之能力,只靠舉著一張“仁義”大旗便引得眾人來歸,為其所用,其中之典型莫過於三國之劉備,水滸之宋江,說唐之李世民。好似領袖人物只需仁義和會用人便可成就霸業,而無須自己有能力一般。當真如此嗎?
“仁義”是歷代文人對主公的要求,我們先放在一邊不談,那用人說呢?用人是不是那么神奇,只需要會識人用人,即便自己能力一般也可以成就霸業呢?假如真如此的話,那歷代皇帝便肯定多是相士了。
事實上,歷代皇帝尤其是開國皇帝,能從群雄之中脫穎而出,其能力都是首屈一指,亂世之中,以強者為先,很難想像一個不會帶兵不會打仗的人卻能統御遠超自己能力之上的人,而那些人都甘願為其下而不動反心。且不說李世民朱元璋劉裕劉秀這一些用兵如神的開國帝王,我們只說這三國時期,曹操劉備這兩人便都是一等一的沙場高手,每奉大戰便親率其部出征。曹操就不說了,自起兵起,可說每年都率領大軍出征,可說是無戰不歡,而劉備自起兵起,實力從弱到強,所有大戰都是自己親歷親為。(劉備實力比曹操確實是略顯不足,但是與曹操和自己的那一乾手下相比,就顯得高超許多了。)而其他諸侯也都是自己親征,少有自己不打仗卻委任於部下者。(真是委任於部下時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實力已經雄厚無比,剩下的地區只需要一偏師足以,如劉秀討蜀,朱元璋北伐;還有一種是繼承長輩之位,江山不是自己打下來的,沒有經歷過大戰的考驗,如孫權,在作戰上便明顯有缺陷,自己親征的效果遠不如委任於部下。)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依賴別人,所謂只需用人便能成事,那肯定是不現實的。
就說那常被用人說作為一大證據的劉邦吧,劉邦將自己成就天下歸咎於自己能用漢初三傑,並盛讚蕭何張良韓信,但是這並非是說劉邦便需依賴這三傑了,就以韓信來說,其軍事才能確實無人可及,劉邦也認為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可雖不如韓信和項羽,比之他人來說,劉邦之軍事才能又遠過之了,韓信說劉邦不善將兵,只善將將,可他說的不善只是相對於自己而言,相對他人來說,劉邦之才足以,何況,世間豈有不善將兵卻善將將之人,不知兵又何以知將?其他也是如此,對一個行業一竅不通的外行又何以知道選拔和使用內行呢?
歸根究底,用人說是建立在領袖本身便擁有一定的能力之上,若是迷信所謂的用人而無視自己的能力,那更大的可能是被人所出賣欺騙。(俗話說隔行如隔山,歷代皇帝多有被大臣所矇騙者,即便大事也被其推卸過去,非其寵信之,而是能力有限,不明其理,而大臣則有專門的知識來推脫責任。)
而在這個問題上看領袖是否忌憚有能力部屬這個問題之上,我們就能或多或少了解一些。
首先:大部分部屬往往能力在領袖之下。開國領袖往往能力出類拔萃,絕大部分下屬都非其對手而心甘情願為其驅使,如朱元璋劉秀李世民,他們的能力遠超越其下屬,從他們個人來說,根本無須畏懼之。(楊修者,才思敏捷和文學才華或許出眾,但是軍事政治能力都非曹操敵手,這樣的能力曹操無須畏懼。)
其次:下屬在一些能力之上超越領袖,但是他們無力對領袖產生威脅,或被其遏制,如直接限制其權力,手中無兵,能力再強也無用;或以制度方式分權,這往往是後世皇帝能以遠不及開國皇帝能力經驗的情況下卻能統治的原因;或其能力不能對自己的統治產生威脅,如宋朝文臣大都比武將寵信重用,便是文臣能力再強也不能象武將一樣能產生直接的威脅。(這點上楊修自己也不搭邊。)
其三:下屬能力過之,又有實權,能產生直接威脅;這便是最糟糕的。如韓信最終慘死便是因為這個緣故,其將才遠超劉邦,又受封為王,有自己的獨立武裝,不將其處死如何能安心?(楊修自然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威脅。)
其四:下屬對自己的做法不贊同,而且是強烈反對,成了自己前進的絆腳石。假如是如此,則無關能力高低,都需除去之,而且能力越高則越要儘早解決,荀彧為曹操首席謀士,才能卓越,但是在受九錫為公一事上站在了曹操的反面,立刻受到冷遇。(這點上楊修是個問題,他是漢太尉楊彪之子,楊彪與曹操不善,而他又是袁氏之甥,雖然為曹操所用,但是在政治立場上更和被曹操所殺的孔融相近。在這點上,對於楊修被殺有部分關係。)
其五:下屬能力對自己毫無威脅,能被自己遏制,但是自己的繼承人不能控制這些有能力的下屬,所以要除去之。典型例子便是朱元璋,朱元璋晚年之所以殺戮功臣很大程度便是因為自己雖能統御之,但是自己的兒子則未必能,而之後朱標死,皇孫即位,其擔心又加上了幾分。(楊修的死很大程度便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對於曹操或許影響不大,但是若曹操死後,他支持曹植與曹丕抗之,則麻煩多多,這便是楊修被殺的一大原因。)
其六:下屬能知其心思,而領袖又多疑。對於能猜到自己心思的部下,領袖往往是且喜且憂,喜者,能知心思為其解憂,可謂之知音也,憂者,成了自己肚子的蛔蟲,對自己的喜怒哀樂知曉的清清楚楚,便可以被之利用了,而多疑的領袖則更傾向於憂了,如勾踐殺文種便是這個緣故。(楊修被殺在這方面吃虧很多,他一方面知曉曹操的心思,但是卻不用在為其解憂上,總是給曹操難堪,如此一來,曹操不恨才怪呢。)
想來日後大家做領袖者少,做下屬者多,那可要注意這么幾點,其一:若其能力在領袖之上者,要不乘早回家,要不自立門戶,不然被其遏制便麻煩了;其二:若自己的能力對領袖來說只是增添光彩而非威脅者,則可以放心大膽的做下去;其三:若與領袖意見不同,或自立門戶,或順從之,若是不走又不從,那便要被放逐了;其四:能力不在領袖之上,這種情況想來最多,那要在換班的時候注意了,繼承人的能力如何,與自己的關係如何,直接影響現在的地位;其五:若是知曉領袖之心思,切不可隨意說出,須知:悶聲大發財最好了。
領袖與下屬之關係,實在太過微妙,又太過複雜,人心的難測又更加劇之,過一分便是不及。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劉關張,諸葛亮和劉備的關係才會被後人如此崇敬甚至神化吧。
回評
毛宗崗批語
曹操善疑,而孔明即以疑兵勝操。此非孔明之疑操,而操之自疑也。然雖操之自疑,而非孔明則不能疑之也。燒於博望、挫於新野、困於烏林、窮於華容,操之畏孔明久矣。見他人之疑兵未必疑,惟見孔明之疑兵而不敢不疑。故善用疑兵者,必度其人之可以疑而疑之,又必度我之可以用疑兵而後用之耳。即如韓信以背水勝,徐晃以背水敗,同一法而今昔之勢異;徐晃以背水敗,孔明以背水勝,同一時而彼此之勢又異。兵之善用,豈不視乎其人哉!
操之不能守漢中,猶備之不能守徐州也。操既取兗州,則徐州為操之所必取;備既取西川,則漢中亦為備之必取。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操欲跋涉山川,以與備爭此土,吾知其難矣。
漢高之破項王,賴有彭越以擾其後;先主之破曹操,亦有馬超以擾其後:前後殆如一轍也。五虎將中,關公既守荊州,而張飛、趙雲、黃忠之建功又備寫於前回,獨於馬超未有及焉。今觀此回,則超之功不在四人之下。
孔融、荀彧、楊修皆為忤操而死,而修則不如融,並不如彧。何也?不事操而以正直忤操者,孔融也;先以不正不直事操,而後以正直忤操者,荀彧也;既以不正不直事操,又以不正不直忤操者,楊修也。修為楊彪之子,而屈身事操,既有愧於家門;復為曹植之故而使操心疑,又不善處人骨肉。夫以正直忤操,則罪在操;以不正不直忤操,則罪在修。故修之死,君子於操無責焉。
或疑操以才忌楊修者,非也。士之才有二:一曰謀士之才,一曰文士之才。以謀士之才而為操用者,如郭嘉、程昱、荀彧、荀攸、賈詡、劉曄等是也;以文士之才而為操用者,如楊修、陳琳、王粲、阮瑀等是也。文士之才,不若謀士之才之為足忌。而操之忌荀彧但以阻九錫之故,前此未之忌焉,其餘謀士亦曾未之忌焉。其視謀士之才且然,而何忌於文士哉?故雖罵操如陳琳,而操不以為罪,蓋才而不為我用則忌之,才而為我用則不忌耳。使修非黨植以欺曹操,則操可以不怒,而修可以不死。彼謂修之以才見忌者,殆未為篤論矣。
曹操於定軍之南,折其一股,又於漢川之東,折其二齒。股之折非真,而齒之落則真矣。於潼關之役,割須數莖,又於漢中之役,落齒兩個,須之割不痛,而齒之落則痛矣。弟既死,身又傷,其兆大凶,恨不再令管輅卜之;須既短,齒又缺,其相已破,恨不再令管輅相之。
此回敘事之法,有倒生在前者:其人將來,而先有一語以啟之,如操之稱黃須是也。有補敘在後者,其人既死,而舉其未死之前追敘之,如操之惡楊修是也。有橫間在中者:正敘此一事,而忽引他事以夾之,如兩軍交戰之時,而雜以曹彰、楊修兩人之生平是也。至於曹操之平代北,則因曹彰而及焉;曹丕之忌曹植,則又因楊修而及焉。其它正文之中,張、趙、馬、魏、孟達、劉封諸將,或於彼忽伏,或於此忽現,參差斷續,縱橫出奇,令人心驚目眩。作者用筆,直與孔明用兵相去不遠。
李贄總評
操殺楊修,忌才也,固為可恨,但楊德祖處人父子兄弟骨肉之間,敢於任怨,安有不敗之理?即非疑忌如老瞞,亦未有不敗者,況疑忌如老瞞者乎?凡有聰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殺其身也,以楊德祖為前車可也。德祖、子建諸人再無有成事之理,輕浮操露,無所不有,適足以殺其身而已.凡有大智慧者,必如張子房諸人,迫而後應,感而後起也,安有不叩而鳴,而樣者耶?
鍾敬伯總評
楊修好露聰明,曹操忌而殺之。操固媾嫉可恨,修亦驕吝自取也。凡成大事者,必有大智,寧以小才殺其軀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