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兄逼弟曹植賦詩 侄陷叔劉封伏法
簡介
獻帝在華歆、曹洪、曹休等威逼下讓帝位於曹丕,國號大魏,丕自許昌幸洛陽。
孔明設計使劉備為帝。備欲起傾國之兵伐吳,趙雲諫曰不可。
正文
 《三國演義》第七十九回
《三國演義》第七十九回卻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眾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眾視其人,乃諫議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即命賈逵前往。逵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璽綬安在?”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侯之所宜問也。”彰默然無語,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逵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彰曰:“吾來奔喪,別無異心。”逵曰:“既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鄢陵自守,彰拜辭而去。
於是曹丕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封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升賞。謚曹操曰武王,葬於鄴郡高陵,令于禁董治陵事。禁奉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畫關雲長水淹七軍擒獲于禁之事:畫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為人,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當下於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病,不久而死。後人有詩嘆曰:“三十年來說舊交,可憐臨難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識,畫虎今從骨里描。”
卻說華歆奏曹丕曰:“鄢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蕭懷侯熊,二人竟不來奔喪,理當問罪,丕從之,即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不一日,蕭懷使者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丕令厚葬之,追贈蕭懷王。又過了一日,臨淄使者回報,說:“臨淄侯日與丁儀、丁廙兄弟二人酣飲,悖慢無禮,聞使命至,臨淄侯端坐不動;丁儀罵曰:昔者先王本欲立吾主為世子,被讒臣所阻;今王喪未遠,便問罪於骨肉,何也?丁廙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自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廟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臨淄侯因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
丕聞之,大怒,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千人來。褚奉命,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之,直入城中,無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褚皆縛之,載於車上,並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拿解鄴郡,聽候曹丕發落。丕下令,先將丁儀、丁廙等盡行誅戳。丁儀字正禮,丁廙字敬禮,沛郡人,乃一時文士;及其被殺,人多惜之。
卻說曹丕之母卞氏,聽得曹熊縊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丁儀等已殺,大驚。急出殿,召曹丕相見。丕見母出殿,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疏狂,蓋因自恃胸中之才,故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也。”丕曰:“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
卞氏灑淚而入,丕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為後患。”丕曰:“母命不可違。”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若果能,則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丕從之。須臾,曹植入見,惶恐伏拜請罪。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禮?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誇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姑恕!”植曰:“願乞題目。”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著兩隻牛,斗於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畫曰:“即以此畫為題。詩中不許犯著‘二牛斗牆下,一牛墜井死’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凹骨。相遇塊山下,郯起相搪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泄畢。”曹丕及群臣皆驚。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為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植曰:“願即命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為題。亦不許犯著‘兄弟’字樣。”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其母卞氏,從殿後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為安鄉侯。植拜辭上馬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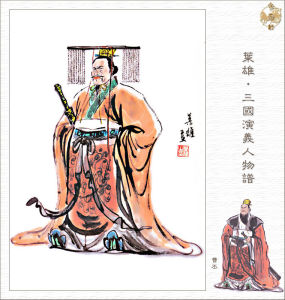 曹丕
曹丕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漢中王聞之,大驚,即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威逼天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仇;次討中原,以除亂賊。”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乞誅此二賊。”玄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可升此二人為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玄德從之,遂遣使升劉封去守綿竹。
原來彭羕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馳報孟達。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即往見彭羕。羕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羕因酒醉,恨罵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羕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為外合,某領川兵為內應,大事可圖也。”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
超辭了彭羕,即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擒彭羕下獄,拷問其情。羕在獄中,悔之無及。玄德問孔明曰:“彭羕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羕雖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玄德賜彭羕死於獄。
羕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舉止失措。忽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為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丕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
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覽其表曰:“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望風歸順。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足自愧!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勛,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悼!邇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即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卻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為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準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單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準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即修書一封,使人齎赴蜀寨招降劉封。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誤吾叔侄之義,又間吾父子之親,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
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上,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腳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颭,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漢中王既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
且說魏王曹丕,自即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升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丕即還鄴郡。時惇已卒,丕為掛孝,以厚禮殯葬。
是歲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於是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種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於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廙、劉曄、陳矯、陳群、桓階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正是:魏家社稷今將建,漢代江山忽已移。
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賞析
曹操死後,曹丕繼位,曹丕此人文學佳,又有一身武藝,可稱得上文武全才,當了多年世子,還破獲了魏諷謀反一案,也算得上是政治經驗豐富了。不過就是有一點不好,心眼小,說來這也是遺傳自老爸曹操,不過曹丕比起曹操來說又更厲害了,曹操多年打下來的江山,知道過程的不易,能忍就忍,曹丕就不同了,或許也是沒繼位之前太忍的關係,上台之後對於當年沒給他好眼色看的一群人都來了一個打擊報復,就連叔父曹洪也沒逃過,(說起來曹洪也是過於吝嗇了,身為侄子還是世子身份的曹丕向他借點錢也不肯,只是就為了這些小事曹丕就一直懷恨甚至到要殺曹洪的地步也太過頭了。)險些被殺,最後在太后的介入之下,改判為罷官,日後曹丕兒子魏明帝上台才重新可以起用。
對付功勳卓著的叔父如此,對於親兄弟自然也不會放過,本回演義中曹植賦詩一事便是出自《世說新語》中的故事,“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詩流傳的版本不同,也有傳說並非曹植所作,但是其中的比喻確實將當時曹丕對兄弟的威逼表現出來了。
曹植是當年與曹丕爭奪繼承權的主要對手,曹丕對之忌憚三分,雖然沒有殺他,但是仍將其遣之封國,派遣監國使者監視,並屢次找藉口遷削改封,這一政策直到魏明帝即位也沒有改變,曹植屢次上書求用都不成功,最後鬱鬱而終。
不過相對曹植來說,其實曹丕更多擔心的是曹彰,曹植能力上佳,但是畢竟不掌兵權,他的權力來源於曹操的寵信,曹操死後,他的權力基礎消失,而一些黨羽都被剷除,他的封國又被嚴密控制,所領兵不過幾百老弱,只要不給其機會,曹植就翻不起浪。但是曹彰不同,他本是大將之才,上陣多有勝績,領有大軍,且有異志,《魏略》中便記載他對曹植說:“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魏氏春秋》記載曹彰問先王璽綬一事,此事在賈逵傳中也有記載,便是本章開頭的一段,曹彰比起曹植來更有奪位的實力,所以曹丕對其最不放心,黃初四年,曹彰暴死。對於其死,三國志注中談到曹彰問璽綬一事,稱“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
說到這裡,我們先把曹魏兄弟的恩怨放在一邊,先說說這個皇族宗室如何處置的問題。在周朝時期,皇族是分封到各地,作為朝廷羽翼的,但是明顯效果不好,秦朝建立後,郡縣制就取代了分封制,那是否以後分封制就不存在了呢?那自然不是,漢朝依舊存在分封制,不過劉邦死前的白馬盟誓從而將周代的分封制度做了一個極大的改變,便是異姓不得封王,也就是說周代時期那些異姓大諸侯是不可能出現了。(雖然異姓可以封侯,但是待遇與王有這天壤之別。)雖然之後還有多種變革,至此,皇族處置的大方向基本定位了,便是分封到各地去和在中樞輔政,前者都漢晉明,後者如李唐,總體的目的都是一樣的,便是維護皇族利益。
現在我們談到分封制總說他們的不好,維護一家一姓的利益有什麼對的,歷代非皇族之人自然也不喜歡皇族占據重要位置,這樣自己便沒了機會。然而若站在皇家的角度之上,以分封制度與皇族捍衛自己的利益到是也不能說他們的考慮錯了。而且分封制度也並非一無是處,各路諸侯王雖然有兵權,但是糾集在一起的力量總敵不過中央朝廷,若想作亂馬上便是覆滅的命運。而若是中央朝廷被權臣奪權,中央肯定會一度混亂,則諸侯王便可高舉大義之名進軍中央,以保皇姓,這樣一來等於兩者在朝野形成了雙保險,皇位就算變換也就是在自家一姓之中。以宗親子孫在中樞輔政也是一樣的道理,上陣不離父子兵,以宗親輔政總是比外姓姓得過。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都是難得的名帝,卻不約而同的採取了諸子分封制度,並不是他們昏庸,而是為了他們皇族的利益,這是必要的措施。
應該說,這種措施在皇朝初期是很有效的,西漢初年劉姓能在呂后死後奪回政權,在外的諸侯王出力不少,李唐開國到安史之亂的這段時期,能在多次變亂中屢屢奪回政權,李唐宗室在內外的力量極其重要。
在這樣的一個措施中,中央朝廷占據著一個極其重要的地位,地方諸侯王實力再強,合力也不是中央朝廷的對手,只有當中央朝廷至少有一部分力量站在皇族一邊的時候,地方諸侯王才有成事的機會,如呂后死後,如不是周勃等人乘虛奪得了兵權,單單依靠劉姓諸侯王的那些兵力是根本不足以與中央朝廷對抗的。也只有當中央朝廷混亂不堪,屢屢走錯棋的時候,才會發生外地藩王入京的事,比如那著名的八王之亂被當作分封制不妥的例子,但是要不是晉惠帝太過白痴,控制不住下面的明爭暗鬥,賈后引狼入室,就憑那幾王的聲望兵力,(所謂的八王之亂,亂子是夠大的,但是八王的實力遠比不上西漢七國之亂時的吳王等人的實力)根本不夠對抗中央的力量,八王之亂的根源還是在於選了一個白痴做皇帝。至於靖難要不是建文帝屢屢走錯棋,就以朱棣的實力,根本翻不了船。(建文輸的真叫冤枉,要不是他總是下莫名其妙的詔書,和運氣實在太糟糕,朱棣連一年都挺不過去。在總結靖難時總說朱元璋殺了那些名將是建文失敗的因素,其實在我看來,根本一點關係也沒,靖難之役雙方都湧現出了大批傑出的將領,換那些老將來了也未必討的了好,何況就建文這搞法和運氣,徐達再多活幾十年也不行。不過最後政權倒也算是落在一家人手裡吧。)
不過無論是分封制度還是宗親在中樞的地位都只是在初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而已,隨著時間的推移,皇朝的地位漸漸穩固,不再需要分封制度為之保駕護航,反而因為內外皇族對皇位的窺視,後幾代皇帝們開始漸漸採取了排擠皇族的作法。這也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後幾任皇帝再也不能有如前代皇帝一般對著皇族中那些甚至是自己長輩的同姓有著足夠的控制力。(資歷在時代中還是很有用的,若說第一代皇帝對於那些皇族不是弟弟就是兒子侄子有著絕對的威望,第二代皇帝有著長子還能控制著絕大多數人的話,從第三代皇帝開始,祖父父親為之帶來的威望就幾乎消失為無了。建文帝的一大弱點便是他的輩分比許多藩王起來太低,外地藩王不服,建文自己也感覺到壓力,若是他父親朱標在世,便不會有這么多麻煩了。)而隨著絕大多數的異姓臣子的支持,諸如削藩的辦法便接連到來了。
這在各代往往有標誌性的轉折點,如西漢之七國之亂,(從此開始漢代諸侯王勢力越來越弱,到了武帝推行推恩令更是無力繼續。)唐朝肅代兩宗,(肅宗為控制大權,一方面收回李唐諸王的權力,一方面又寵信宦官,不料從此之後權力便收不回來了。)明朝之靖難,(外姓藩王上台的成祖上台後自然對外姓藩王不放心,之後明代諸王基本上是空架子了,沒有什麼兵權。)
在這之後,權力便集中到中央朝廷手中,但是這往往引起的又是中央權力過大,皇帝又不能信賴那些皇族宗親,權力就向著外戚宦官權臣中一點點倒去,這對於天下未必是壞事,但是對於一姓之皇朝肯定是壞事了。
回評
毛宗崗批語
劉、曹之相形,何厚薄之懸殊乎!玄德以異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則痛義弟之死,而不顧其養子之恩;一則欲親弟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於此,有天倫之感焉。
甚矣,名之不可竊,而實之不可誣也!操以武王之事遺其子,而自比於文王;丕則不以文王之事目其父,而仍謚之曰武王。是父欲避改革之名而讓之後人,子又避改革之實而歸之先世也。歸之先世,而魏之篡漢非丕篡之,實操篡之耳。操將欺人,而子先不能欺;操欲自掩,而子不為之掩。嗚呼!奸雄之奸,亦復何用哉?
文章足以殺身,而有時乎亦足以救死;文章足以取忌,而有時乎亦足以動人。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楊惲種豆之歌,適觸君王之怒,不若子建煮豆之詠,能發兄弟之悲;朱虛耕田之吟,但寒異姓之心,不若子建燃豆之詩,能解同氣之怨;劉勝聞樂之對,自述涕泣之情,又不若子建釜中之辭,能隕他人之淚。此豈獨當時為然哉?凡今之人有與兄弟而相煎者,觀於其文,亦宜為之泣然矣。
曹子建亦嘗倩人代筆矣,楊修手教數十條是也。然子建倩人代筆,面試卻不出醜;不似今人倩人代筆,面試即便出醜。面試不出醜,連平日之代筆者,亦信其自作;面試一出醜,連平日之自作者,亦疑其代筆。故惟才如子建,可不倩人;亦惟才如子建,可以偶一倩人。
觀曹氏之得免於內亂,而知天之不欲祚漢也。懦若曹熊不足論耳,曹彰以勇略自矜,而驅雄兵於鄴郡;曹植以才名自恃,而集文士於臨淄:岌岌乎幾不免內亂之作矣。使亦如譚與尚之相爭,琦與琮之相惡,而漢中王得乘隙以攻之,豈不大快事哉!乃熊既死,彰既歸,而曹植亦束手而受縛,君子以為魏之幸而漢之不幸雲。
劉封之拒孟達,與糜芳之從傅士仁則有異矣。然既然拒之於終,何不拒之於始;既能斬孟獲之使而不降曹操,何以聽孟達之譖而不救關公乎?南郡之救樊城也難,糜芳不聽士仁則必死;上庸之援麥城也易,封不聽孟達則未必至於死。惜其見之不早耳。
劉封雖有罪,而先主殺之亦未得其當也。其不救關公也,可罪;其不降曹氏也,可原;其拒孟達於後也,可嘉;則其悔聽孟於前也,亦可諒。而喪一義弟,又殺一義兒,誠計之左矣。且既欲殺之,不即召而殺之,而使喪師失地以重其辜,則先主有三失焉:彼自知獲戾,而將兵於外,安保其無降魏之心?其失算者一。以一劉封當徐晃、夏侯尚、孟達之師,明知其非敵,而故遣焉,是棄劉封並棄五萬人,其失算者二。孟達已去,不更令別將以守上庸,而至有申耽,申儀之叛,使劉封進退無路,是棄劉封並棄上庸之地,其失算者三。有此三失,宜先主之終悔歟?
張松、法正、孟達、彭羕四人皆賣國,而各有不同:初欲投曹操,而繼乃向先主者,張松也。既歸先主,而又欲叛先主者,彭羕也。事劉而復降曹,降曹而其後又欲歸劉者,孟達也。其背劉璋之後,始終事先主者,惟法正一人而已。雖然,法正、孟達功同一體,孟達有罪,法正必不自安,幸其時正已死耳。若正而在,安保其不為彭羕乎?苟曰始終無二,吾於法正未之敢信。
李贄總評
諸葛亮真狗彘也,真奴才也,真千萬世之罪人也。彼何嘗為蜀,渠若真心為蜀,自不勸殺劉封矣;即其勸殺劉封,乃知藉手剪蜀爪牙,實陰有所圖也。蠢哉!玄德何足以知此。
劉封忠義,玄德不知而殺之,罪猶可原;孔明知而殺之,罪不容誅矣。更將言語文飾,真是小人之過也必文。
鍾敬伯總評
子建七步成章,聰明賈禍,非生才之意,乃小才之過,不可以以此致憾造物。
劉封忠義,玄德不知而殺之也。孔明必欲殺之,更將言語文飾,何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