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簡介
鍾會約鄧艾伐蜀。
後主聽信黃皓讒言,不準姜維出兵拒魏之奏,瞎信師婆虛妄之說,只在宮中飲宴歡樂。
鍾會軍所到之處,秋毫無犯,漢中人民,出城拜迎。
姜維等大敗,奔劍閣。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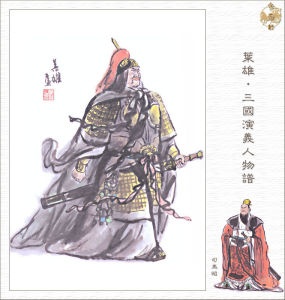 司馬昭
司馬昭卻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蜀人心膽已裂;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即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此言乃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
卻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瓘,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爰青彡、丘建、夏侯鹹、王買、皇甫闓、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為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眾皆曰:“非此人不可為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班之將。父子有名;今眾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逕取漢中。兵分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左軍出駱谷;右軍出子午谷。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令軍填平道路,修理橋樑,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眾,星夜起程。
卻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遏羌人,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比及軍馬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漢中,忽於腳下迸出一泉,水勢上涌。須臾驚覺,渾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護衛爰邵問之。邵素明《周易》,艾備言其夢,邵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將軍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滯不能還。”艾聞言,愀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頎,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中;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邀姜維之後。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卻說鍾會出師之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凜然。人皆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寔,微笑不語。太尉王祥見寔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王祥問其故,劉寔但笑而不答。祥遂不復問。
卻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安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這二處最為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時後主改景耀六年為炎興元年,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即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床之上。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鏇於案上。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師婆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陛下欣樂太平,何為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國疆土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勿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蘇。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誤了大事。卻說鍾會大軍,迤邐望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即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眾將領命,一齊併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將到,先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鍾會。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塌,陷住馬蹄,爭些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馬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槍刺來,卻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麾眾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即以荀愷為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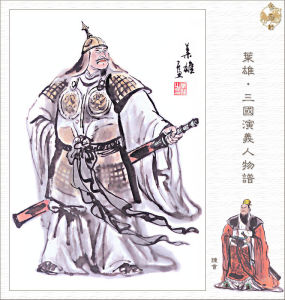 鍾會
鍾會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汝為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樑道路,以便行軍。吾方才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橋;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汝既違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眾?”遂令斬首示眾。諸將無不駭然。時蜀將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軍取陽安關。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眾,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為上。”僉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睏,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傅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眾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升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魏兵複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僉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僉圍在垓心。僉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嘆曰:“吾生為蜀臣,死亦當為蜀鬼!”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槍,血盈袍鎧;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後人有詩嘆曰:“一日抒忠憤,千秋仰義名。寧為傅僉死,不作蔣舒生。”
鍾會得了陽安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犒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鍾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三更,西南上喊聲又起。鍾會驚疑,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並無一人。”會驚疑不定,乃自引數百騎,俱全裝慣帶,望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會勒住馬,問嚮導官曰:“此何山也?”答曰:“此乃定軍山,昔日夏侯淵歿於此處。”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會大驚,引眾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安關時,不曾折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卻不傷人,只是一陣鏇風而已。”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吾當親往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宰太牢,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祭畢,狂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鶴氅,素履皂絛,面如冠玉,唇若抹朱,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其人步入帳中,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見顧。吾有片言相告: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罹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後,萬勿妄殺生靈。”言訖,拂袖而去。會欲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是武侯之靈,不勝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於是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會一一撫慰,秋毫無犯。後人有詩讚曰:“數萬陰兵繞定軍,致令鍾會拜靈神。生能決策扶劉氏,死尚遺言保蜀民。”
卻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迎之。魏陣中為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頎也。頎出馬大呼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槍縱馬,直取王頎。戰不三合,頎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卻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神,與艾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毀了。”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撤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岩下,岩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將姜維圍住。
維引眾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然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安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維大驚,即傳令拔寨。
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為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槍趕來。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楊欣撥回馬來殺姜維。維躍起身,一槍刺去,正中楊欣馬腦。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從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維乃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嘆曰:“天喪我也!”副將寧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頭,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卻引兵奔劍閣守之,則漢中可復矣。”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守之地,倘有疏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橋,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卻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安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前赴白水關。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起,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正是:漢中險峻已無有,劍閣風波又忽生。
未知何處之兵,且看下文分解。
賞析
公元262年,司馬昭力排眾議,決定征伐蜀漢。在當時,諸多朝臣多反對冒然攻打蜀漢,即便征西將軍,與蜀漢多年征戰的鄧艾,也屢次上表提出異議,反對此時攻打蜀漢。鄧艾乃當時名將,多年統領西線曹魏之軍與姜維作戰,為天下之名將,司馬昭攻打蜀漢一定得依賴他不可,而他的傾向對於這次戰役舉足輕重。
鄧艾的反對除了他上表中已經提到的內容確實反對攻打蜀漢外,很可能與他並非此次戰役的主將有關,當時,司馬昭是選擇了他的親信,支持他此次攻伐計畫的司隸校尉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若是如此,鄧艾便要在鍾會指揮之下。然而從日後鄧艾在戰役中的表現看,他很不願意在鍾會麾下作戰,試圖自己帶軍。為此,司馬昭派遣主簿師纂為鄧艾司馬,並解釋司馬昭的意圖,這其中便有可能說明了日後攻打蜀漢的戰役部署,並對鄧艾進行拉攏,(日後攻打蜀漢一戰,鄧艾自領一路,有著極大的自主權。)此外,師纂此行很可能不單有拉攏解釋的意思,更有若鄧艾再行勸阻,就剝奪其兵權,令其回京的意思。所謂恩威並施。鄧艾隨後便表示支持司馬昭的征伐計畫,鄧艾的轉變對於這次戰役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司馬昭這次攻打蜀漢並非純粹是以蜀漢為目的,而是統一天下的第一步而已,在司馬昭一次對於群臣的解釋中便可以看出。
“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在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並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眾以屠城,散銳卒以略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暗,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
很顯然,司馬昭最終的目的是消滅東吳和蜀漢,統一天下,然而,東吳屢伐不克,不如先消滅蜀漢,三年之後,再由蜀漢順流而下,進攻東吳,這也是日後北方南征的常用戰略,便是迂迴作戰。
司馬昭選擇蜀漢為第一個目標不是沒有原因的,在他看來,東吳疆域廣大,而且地處南方,曹魏之軍多是北地之人,要破東吳水軍,攻克長江天險,取東吳並非易事,而且東吳蜀漢同為盟友,尤其蜀漢每每乘東面有事,屢次出擊,不若先平定蜀漢,一來若得蜀漢,長江天險可同為其有,再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奪東吳事半功倍,二來蜀漢雖小,但是屢屢出征牽制曹魏兵力,不如先滅之解決後顧之憂。(司馬昭對於姜維的屢屢興兵也是很頭疼的,一度要招募刺客暗殺之,後來被勸阻。)
而且正如他所說的,蜀漢戰士不過九萬,(這和日後蜀漢滅亡後所獻戶口軍吏統計中軍士十萬相差無幾。)在成都,南中,防禦東吳,各處總和至少要四萬上下,真正能在前線應對曹魏軍隊的五萬人至多。而曹魏興兵十多萬,以多戰少,勝算是很大的。
確實,司馬昭所說的很有道理,但是若真是那么簡單,蜀漢早就在多年之前便滅亡了,然而蜀漢卻沒有滅亡,反而曹真曹爽當年兩次出征,十多萬大軍勞師不克,慘敗而回。尤其曹爽一次,司馬昭跟隨出征,對於那次出征的結果自然清楚。蜀漢雖然兵少,但是擁有天險,大軍出征,不說蜀道難行,就說大軍的後勤保障,就很成問題,這也是那些大臣反對出征的主要原因。司馬昭故意忽略了難處,自然是為了那句話,戰略上藐視敵人,就好象荀彧說袁紹的四勝四敗說一樣,勝敗本是常事,但是若只是只說敗,不談勝,只說不做,那永遠也不會勝利。
雖然戰略上藐視敵人,但是戰術上還是要重視敵人,為了麻痹蜀漢,也是為了防止東吳乘機出兵,司馬昭下令“青、徐、兗、豫、荊、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吸引東吳的注意力,而實際上徵集四方之兵,由鍾會在關中訓練軍事。
此計被姜維看穿了,他便建議由廖化張翼帶兵率軍分守陽安關口與陰平橋頭,以防備之,然而劉禪寵信黃皓,而黃皓相信鬼巫之說,認為曹魏不可能進攻。(好象好幾次國家亡國時總有幾個巫師或者文人站出來信誓旦旦的說不可能,比如這次,再比如陳後主那次,真不知他們的信心從哪裡來的。)這次姜維的上表群臣都不知曉,這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後來的兵敗。
另一方面,司馬昭定下了三路進軍的戰略部署,其一路,由鎮西將軍鍾會率領主力由各處徵集而來的十多萬軍隊,從斜谷,駱谷,子午谷進軍漢中;其二路,由征西將軍鄧艾率軍三萬多眾,由狄道進攻沓中的姜維,而第三路由雍州刺史諸葛緒率三萬餘人,出祁山進軍武街橋頭,斷絕姜維歸路。
雖然為三路進軍,但是實際上稱之為二路更為確切,鍾會這一路十多萬兵力進軍漢中,而鄧艾和諸葛緒兩路合起來六萬多人的目的其實都是一樣的,限制姜維軍的行動,讓其不能回援並尋機消滅。
曹魏景元四年,蜀漢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夏,曹魏下令攻打蜀漢。
也就是此時,蜀漢得到了曹唯進犯的訊息後開始回應,劉禪拿起姜維當初提議的計策,派遣廖化帶兵增援姜維,而張翼董厥帶領到陽安關駐守,然則,兩軍都未及時趕上。
我們先說東路,鍾會部分三路進軍,令許儀在前修道,結果修出的道路可說是豆腐渣工程,橋穿,馬足陷,鍾會下令斬首許儀,許儀為曹魏功臣許褚之子,他的被殺立刻震驚了整個魏軍,一方面對於進軍修路再也不敢鬆懈,另一方面鍾會也樹立了自己在大軍中的威信。
此時漢軍的計畫部署是借外圍,守漢樂兩城與關頭,這是當初姜維制訂的計畫,所以鍾會大軍迅速進入漢中,開始攻打漢樂兩城,並派遣護軍胡濟進攻陽安關。
應當說,在這個時候,曹魏和蜀漢的計畫都順利實施了,曹魏進入了漢中,而蜀漢則只要據險防守,等待魏軍糧盡退兵就可以了。
但是,戰爭的天平開始向曹魏或者說司馬家這邊傾斜了,鍾會進入漢中,令部將圍漢樂兩城,而率軍攻打陽安關,陽安關為天險,易守難攻,即便鍾會大軍親到也未必能克,可此時發生的一件事改變了一切。
陽安關守將蔣舒開城投降,主將傅僉力戰而死。(演義中把故事倒過來了,變成了傅僉出擊,其實是相反。)本來陽安關乃天險,易守難攻,鍾會主力到了也未必能短時拿下,(鍾會攻打樂城就失敗了。)但是蔣舒的行為使魏軍前鋒胡濟就將陽安關拿下了,尤其重要的是,若是防守不濟被攻破,陽安關守軍可以將那些糧草燒盡,可此時陽安關的糧草補給盡數落入魏軍手中。陽安關的糧草是為了防備魏軍圍攻而為大軍長期準備的,收藏頗豐,這一收穫使得鍾會大軍在日後可以堅持的更長一些,對最終的結局也起了極其關鍵性的作用。
以鍾會日後在劍閣與姜維對峙時還發生糧草危機這一情況看來,若是陽安關未破,鍾會大軍的糧草危機會出現的更早,那這對另一路魏軍也會產生重大影響。
攻破陽安關,鍾會得以補充,而再進一步進軍時,鍾會卻發現本是由另兩路軍隊牽制的姜維卻出現在劍閣阻擋住自己的去路,這是怎么回事?
這就要說到西路戰事,西路鄧艾由狄道進攻姜維,此時姜維已得知鍾會主力進攻漢中一事,於是無心與鄧艾糾纏,且戰且退,準備到關口阻敵。然而諸葛緒率軍由祁山到陰平橋頭,擋住了姜維的退路,這一切似乎已在曹魏掌握之中,姜維或者被兩軍夾擊,或者來不及趕赴救援,那之後鍾會可以長驅直入了。
為了對付諸葛緒的擋路魏軍,姜維帶軍從孔函關繞北,準備出諸葛緒之後,而諸葛緒聞知,擔心後路被截斷,趕緊後退三十里,此時姜維已經由北道進軍三十里,得知諸葛緒的行動後,馬上回軍再度由橋頭進軍,而諸葛緒此時再試圖攔截,已經來不及了。
從這次機動作戰的情況看,姜維這一招聲東擊西,實北實南的計策遠在諸葛緒之上,尤其是姜維軍的情報與機動能力遠遠超過了諸葛緒,這才使其擺脫了兩路圍攻的被動局面,就好象圍棋中的一條大龍,眼看就要被全殲,卻衝出重圍,走活了。
姜維軍的這次突圍,使得曹魏三路進軍的其中二路的主要目的:圍殲牽制姜維軍的目標沒有完全達到,這也是前期或者說全部戰役中漢軍最大的亮點。
不過,曹魏主力衝破陽安關,使得這一路的目的基本達到,這也就是多路進軍的好處。
姜維率軍到陰平,合集士眾,準備趕赴關城,卻得到了已經被破城的訊息,只好退軍,與廖化,張翼,董厥合兵守衛劍閣。(張翼廖化兩路的行軍有些奇怪,從記載上看,廖化很可能是在陰平附近和姜維回師,而張翼所部和姜維會師應該是漢壽附近,但是這是趕往陽安關的途中呢,還是赴援陽安關得知已經被破而回師的途中呢?也有張翼軍曾經在陰平等待防禦諸葛緒的說法,不過最終的結局是一樣的,三部漢軍回師守衛劍閣)
至此,前期作戰中,魏軍奪得大片領土,捷報頻傳,但是,這次作戰最終的目的是消滅蜀漢,這一目標要實現,前面還有一個攔路虎,漢大將軍姜維率領漢軍守衛劍閣,而姜維本應該被西部兩路魏軍限制才對。也就是說,儘管魏軍總體大勝,但是西路魏軍的戰果不及東路主力輝煌,目標沒有達到。
而現在的局面便是,三路大軍是否要會合作戰呢,這取決於三路魏軍統帥的意見,而這意見決定了整個戰役的結果。
這就是下一章的故事了。
回評
毛宗崗批語
此回記魏取蜀之事也,而司馬昭主其事,則非魏之能取之,而晉之取之也。魏之滅,尚在蜀滅之後,然曹芳已廢而曹髦已弒,雖奐之一息尚存,而已全乎其為晉也。全乎其為晉,則不得復以魏目之。猶之起兵徐州,乃備之討曹,而非備之犯漢;兵敗當陽,乃魏之攻備,而非漢之伐備也。前乎此者,魏之攻蜀有二:一發於曹丕,而五路之兵不戰而自解;再發於曹睿,而陳倉之兵遇雨而引歸:是天意之不欲以魏滅漢也明矣。天不欲興漢,而又不欲以魏滅漢,於是滅之以滅魏之晉焉。而漢之滅,庶可以無憾云爾。
鍾會將取蜀,而佯作取吳之勢,其謀是詐;乃未取蜀而先為取吳之地,其謀仍是真。斯伏線之最奇者矣。而猶未也,邵悌於會之未行,而預知其必勝,預知其必叛,則更奇;司馬昭於會之未勝,而預知其勝後之必叛,又知其叛之必無成,則尤奇。以數回之線,於一回伏之,天然有此一氣呼應之文。近之作稗官者,雖欲執筆而效焉,豈可得耶?
黃巾以妖邪惑眾,此第一回中之事也,而師婆之妄托神言似之;張讓隱匿黃巾之亂以欺靈帝,亦第一回中之事也,而黃皓隱匿姜維之表又似之。前有男妖,後有女妖,而女甚於男;前有十常侍,後有一常侍,而一可當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應尾,尾必應首。讀《三國》至此篇,是一部大書前後大關合處。
以死諸葛走生仲達,而武侯不死;以死諸葛嚇生鍾會,而武侯又不死。然武侯能顯聖以諭魏將,而不顯聖以教後主;能顯聖以護百姓,而不顯聖以助姜維,則何也?曰:此天之不可強也。自非然者,武侯之前,關公亦嘗顯聖矣。關公能顯聖以追呂蒙,豈不能顯聖以追陸遜;能顯聖以解鐵車之圍,豈不能顯聖以救猇亭之敗哉?
鄧艾未入川時,先得一夢;鍾會於定軍山前,亦得一夢。人但知艾與會之夢為夢,而不知艾之以夢告卜者亦夢也。會之祭武侯,與武侯之託夢於會亦夢也。不獨兩人之事業以成夢,即三分之割據皆成夢。先主、孫權、曹操,皆夢中之人;西蜀、東吳、北魏,盡夢中之境。誰是誰非,誰強誰弱,盡夢中之事。讀《三國》者,讀此回述夢之文,凡三國以前、三國以後,總當作如是觀。
李贄總評
後主信師婆,諸葛武侯之教也。客問何故。曰:武侯所為禳星祈命,皆師巫之術也,如何怪得師婆也r客大笑。
鍾敬伯總評
蟊賊內訌,戎馬生郊。後主不自為計,而聽信於惑亂之師婆,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者,此其一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