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詮釋學
中國詮釋學起源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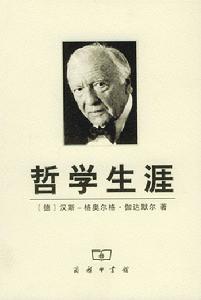 伽達默爾
伽達默爾從詮釋學這種詞源學意義出發,伽達默爾曾把詮釋學解釋為語言的一種普遍的中介活動,是“一切思想的使節”(NuntiusfuerallesGedachte)。所謂使節,就是指兩國進行交往的使者。伽達默爾曾把詮釋學與法國人文主義者安東尼•孔德(AntoineConte)所說的法國經紀人事務加以比較,他說“它涉及的是最廣義上的一種通譯工作和中介工作,但這種通譯的作用並非僅限於技術語言的翻譯,也並不限於對含糊不清的東西的闡明,而是表現一種包含一切的理解手段,它能在各方利益之間進行中介”,並說這與柏拉圖《伊庇諾米篇》把詮釋學理解為一種從符號象徵中猜出神意和未來的占卜術完全一樣,“涉及的是一種普遍的中介活動,這種活動不僅存在於科學的聯繫之中,而且更存在於實際生活過程中”。
從赫爾默斯發展而來的詮釋學還有另一層意思,即它是傳達諸神的旨意,而這種旨意人們是必須絕對服從的,也就是說,人們必須把它的要求當作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從的藝術。正是這種具有規範性的職能,長久以來成為獨斷論詮釋學(神學詮釋和法學詮釋學)的基礎,其中套用這一要素得到普遍強調。什麼叫套用呢?就是把普遍的原則、道理或觀點運用於當前具體情況,或者說,在普遍真理與具體情況之間進行中介,伽達默爾說:“研討某個傳承物的解釋者就是試圖把這種傳承物套用於自身……為了理解這種東西,解釋者一定不能無視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處的具體的詮釋學境遇。如果他想根本理解的話,他必須把本文與這種境遇聯繫起來。”
綜上所述,詮釋學傳統從詞源上至少包含三個要素,即理解、解釋(含翻譯)和套用,傳統詮釋學把三個要素稱之為技巧,即理解的技巧(subtilitasintelligendi)、解釋的技巧(subtilitasexplicandi)和套用的技巧(subtilitasapplicandi),這裡所謂技巧,就是說它們與其說是我們可以支配的方法,不如說是一種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實踐。總之,對於詮釋一詞,至少要把握它的四個方面的意義,即理解、解釋、套用和實踐能力,而最後一方面的意義說明它主要不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實踐智慧。
三大轉向
 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第一次轉向是從特殊詮釋學到普遍詮釋學的轉向,或者說,從局部詮釋學到一般詮釋學的轉向。這一轉向一方面指詮釋學的對象從聖經和羅馬法這樣的特殊卓越的文體到一般世俗文本轉向,即所謂從神聖作者到世俗作者的轉向,另一方面指詮釋學從那種個別片斷解釋規則的收集到作為解釋科學和藝術的解釋規則體系的轉向。這次轉向的主要代表是施萊爾馬赫。施萊爾馬赫把詮釋學從獨斷論的教條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一種解釋規則體系的普遍詮釋學。但這一轉向的消極結果,使詮釋學失去了本來與真理內容的聯繫,使對真理內容的理解淪為對作者意圖的理解,從而原先詮釋學的三種技巧(理解的技巧、解釋的技巧和套用的技巧)在浪漫主義詮釋學裡只剩下理解和解釋兩種技巧,詮釋學本有的第三個要素即套用(application)則與詮釋學不發生關係。
第二次轉向是從方法論詮釋學到本體論詮釋學的轉向,或者說,從認識論到哲學的轉向。狄爾泰以詮釋學為精神科學奠定了認識論基礎這一嘗試,使詮釋學成為精神科學(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論,但在海德格爾對此在進行生存論分析的基礎本體論里,詮釋學的對象不再單純是文本或人的其他精神客觀化物,而是人的此在本身,理解不再是對文本的外在解釋,而是對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因而詮釋學不再被認為是對深藏於文本里的作者心理意向的探究,而是被規定為對文本所展示的存在世界的闡釋。這一轉向的完成則是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詮釋學哲學就是這樣一門關於人的歷史性的學說:人作為“在世存在”總是已經處於某種理解境遇之中,而這種理解境遇,人必須在某種歷史的理解過程中加以解釋和修正。伽達默爾說:“理解從來就不是一種對於某個所與對象的主觀行為,而是屬於效果歷史,這就是,理解屬於被理解東西的存在。”
第三次轉向是從單純作為本體論哲學的詮釋學到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的轉向,或者說,從單純作為理論哲學的詮釋學到作為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詮釋學的轉向。這可以說是20世紀哲學詮釋的最高發展。與以往的實踐哲學不同,這種作為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詮釋學在於重新恢復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Phronesis)概念。正是這一概念,使我們不再以客觀性、而是以實踐參與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真理最高評判標準。伽達默爾說:“詮釋學作為哲學,就是實踐哲學”,這表示詮釋學既不是一種單純哲理性的理論知識,也不是一種單純套用的技術知識,而是綜合理論與實踐雙重任務的一門人文基礎學科,這門學科本身就包含批判和反思。
當代狀況
 詮釋學
詮釋學今天詮釋學可以說進入了作為實踐哲學的更深層次的發展階段。在當代科學技術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對社會進行全面統治而造成人文精神相對日益衰退的時候,詮釋學再次強調古希臘的那種與純粹科學和技術相區別的“實踐智慧”德行(phronesis),無疑會對當代人們熱衷於經濟和技術發展的狂熱帶來一種清醒劑。亞里士多德曾把人類的活動和行為區分為兩類:一類是指向活動和行為之外的目的的或本身不完成目的的活動和行為;一類是本身即是目的的或包含完成目的的在內的活動和行為。例如生產這種活動,其目的在於產品而不是生產,它是本身不完成目的的活動,反之,政治或道德這類行為,如果它是真正的政治或道德行為,其本身就應當是目的即善的活動。目的是在活動之外的,活動就變成了手段,因而會造成不擇手段地去追求它之外的目的,反之,目的是在活動之內的,活動本身也就是目的,因而活動就不會超出目的而不擇手段。詮釋學作為哲學,就是實踐哲學,它研討的問題就是所有那些決定人類存在和活動的問題,那些決定人之為人以及對善的選擇極為緊要的最偉大的問題。
詮釋學由於自身的實踐性、多元性和開放性,往往與後現代思潮相聯繫。但詮釋學作為後現代思潮,只能是一種積極的後現代思潮。現代與後現代的區分是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絕對性與相對性、理性與超理性的區分,與消極的後現代思潮不同,詮釋學並不把非確定性視為不可能性。按照詮釋學觀點,非確定性只表現為解釋的相對性、意義的開放性和真理的多元性,而不表現為解釋的不可能性、意義的不可能性和真理的不可能性。詮釋學主張解釋的相對性,但並不是主張什麼都行的相對主義;詮釋學主張意義的多元性,但並不是否認客觀真理的主觀主義。相對性表明真理的開放性,多元性表明真理的創造性。無論是開放性還是創造性,都表明詮釋學的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中國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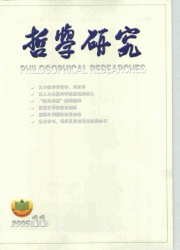 哲學研究
哲學研究就國內研究來說,詮釋學基本上在四個領域拉開了中國化的研究序幕:西方哲學研究界關於西方詮釋學的研究和介紹;中國哲學研究界關於詮釋學與中國經典注釋結合的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對實踐詮釋學的研究以及探討如何建構馬克思主義詮釋學問題;詮釋學向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滲透。
西方哲學研究學者首先在翻譯方面下了苦功,他們不僅翻譯了《存在與時間》(三聯,1987)、 《真理與方法》(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1999)等經典著作,還翻譯了西方重要詮釋學文獻,如利科的《詮釋學與人文科學》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姚斯與霍拉斯的《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赫施的《解釋的有效性》(三聯,1991)、洪漢鼎編的《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東方出版社,2001)等。其次,在深入理解的基礎上也出了一些詮釋學研究專著,如張汝倫的《意義的探究——當代西方釋義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殷鼎的《理解的命運——解釋學初論》(三聯,1989),嚴平的《走向解釋學的真理——伽達默爾哲學述評》(東方出版社,1998),洪漢鼎的《理解的真理——真理與方法解讀》(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詮釋學——它的歷史與當代的發展》(人民出版社,2001)以及章啟群的《意義的本體論——哲學詮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中國哲學研究學者試圖運用西方詮釋學的觀念與方法,重構中國自己的詮釋學傳統,以完成傳統注釋理論的當代轉化。湯一介先生早在1998年就發表了一篇題為“能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的論文,繼後於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上又發表了“再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無疑推動了詮釋學在中國哲學研究中發展。隨後還有劉耘華的《詮釋學與先秦儒家之意義生成——<論語>、<孟子>、<荀子>對古代傳統的解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李清良的《中國闡釋學》(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對詮釋學的重視來源於詮釋學的實踐性,詮釋學作為哲學,就是實踐哲學。繼曹可建在《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發表“解釋學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1990,第3期)後,上海《學術月刊》編輯部在1991年舉行了一次題為“馬克思主義與現代西方哲學”的學術討論會。會上有些學者提出,儘管馬克思只有一次而且只是在貶義上說過“法學上的詮釋學習慣”,但他的哲學思想“卻包含一種可深化詮釋學研究的批判性的與建設性的見解,同時,詮釋學的特殊的研究角度也為我們全面地理解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提供了新的途徑”。俞吾金甚至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解為實踐詮釋學”。
馬克思不僅通過革命的實踐活動來改造整個現存世界,而且也主張以人的實踐活動為出發點來解釋我們現在用文本這個概念所指稱的所有對象。以後《哲學研究》發表了朱士群的《現代釋義學原理及其合理重建》(1992,第9期)和潘德榮的《現代詮釋學及其重建之我見》(1993,第3期),《光明日報》在1997年還發表俞吾金的論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詮釋學》。作為專著的有俞吾金的《實踐詮釋學》(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和何偉平的《通向詮釋學之途》。
詮釋學對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滲透,首先表現在文學與法學方面的一些專著上:金元浦的《文學解釋學》(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梁慧星的《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梁治平的《法律解釋問題》(法律出版社,1998)、陳金釗的《法律解釋的哲理》(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彭公亮的《審美理論的現代詮釋——通向澄明之境》(武漢出版社,2002)。特別要提出的是洪漢鼎主編的“詮釋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叢書”,現已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7本,深入到文學、歷史學、神學、法學、自然科學各個領域:李建盛的《理解事件與文本意義——文學詮釋學》、韓震、孟鳴歧的《歷史、理解、意義——歷史詮釋學》、楊慧林的《聖言、人言——神學詮釋學》、謝暉、陳金釗的《法律:詮釋與套用——法律詮釋學》以及黃小寒的《自然之書讀解——科學詮釋學》等。
海外情況
 真理與方法
真理與方法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試圖把方法與本體結合起來,即通過本體將方法規範化,又通過方法將本體條理化,他想通過他的這一本體詮釋學,對歐洲的詮釋學思想進行批判性地綜合,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一種融會貫通中西方哲學的“世界整體哲學”。反之,傅偉勛的創造詮釋學則試圖根據我國儒道佛的漫長解釋經驗,在方法論上重整或重建中國哲學思想,他試圖通過五個層次(“實謂”、“意謂”、“范謂”、“當謂”、“必謂”)建立中國詮釋學的方法論。
黃俊傑教授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系台灣教育系統所推動的“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之一,也是他自己早先提出的建立中國特色的詮釋學計畫的繼續(他所謂中國詮釋學,是指“中國學術史上源遠流長的經典註疏傳統中所呈現的、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詮釋學”),參與者來自台灣大學、台灣清華大學、中央大學。該課題包括兩個領域:東亞思想史和東亞之經典詮釋學。該計畫曾在國內外多次舉行學術研討會,其研究成果是《儒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現已出版《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 (黃俊傑著)、《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李明輝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二)》(李明輝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三)》(楊儒賓編)和《日本漢學研究論集》(張寶三、楊儒賓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