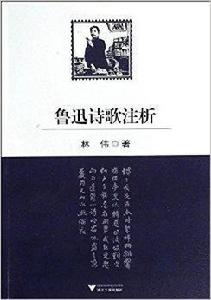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編集了魯迅的所有詩歌,並進行必要的注釋和賞析,兼及魯迅的文集中的有關詩歌的論述的收輯和必要的注釋。本書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收錄魯迅的舊體詩,第二部分收錄魯迅的新詩和政治諷刺詩,第三部分收錄了魯迅的殘句、斷句,第四部分則收輯了魯迅的論詩和文學創作的文章和片斷。本書特點如下:1、關於魯迅詩歌有關的資料收集完整,資料豐富,條理清晰;2、有關魯迅詩歌的解析有自己的新見,多有創新之處,且提出的新看法又是切合魯迅的;3、全面地總結評價了魯迅的詩歌創作成就;4、以賞析的角度來詮釋魯迅詩歌,貼近普通讀者。
作者簡介
林偉,字心齋,男,1969年11月20日出生;浙江省寧波市北侖人。199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現在寧波市鎮海區建設局所屬的基層單位從事管理工作。業餘喜歡學習《魯迅全集》、《郁達夫全集》、《紅樓夢》、《金瓶梅》和先秦漢魏晉南北朝文學
圖書目錄
第一部分舊體詩
別諸弟三首(庚子二月)(1900年)
蓮蓬人(1900年)
庚子送灶即事(1901年2月11日)
祭書神文(1901年2月18日)
別諸弟三首(辛丑二月)並跋(1901年4月2日)
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園主人元韻)(1901年4月)
自題小像(1901年)
哀范君三章(1912年7月22日)
我的失戀——擬古的新打油詩(1924年10月3日)
替豆萁伸冤(1925年6月5日)
哈哈愛兮歌三首(1927年4月3日)
無題(大夜彌天)(1927年9月10日)
吊盧騷(1928年4月10日)
題贈馮蕙熹(1930年9月1日)
送O.E.君攜蘭歸國(1931年2月12日)
無題(慣於長夜過春時)(1931年2月)
贈鄔其山(1931年春)
贈日本歌人(1931年3月5日)
無題(大野多鉤棘)(1931年3月5日)
湘靈歌(1931年3月5日)
無題二首(大江日夜向東流雨花台邊埋斷戟)(1931年6月14日)
送增田涉君歸國(1931年12月2日)
無題(血沃中原肥勁草)(1932年1月23日)
偶成(1932年3月31日)
贈蓬子(1932年3月31日)
一二八戰後作(1932年7月11日)
自嘲(1932年10月12日)
教授雜詠四首(1932年底)
所聞(1932年12月31日)
無題二首(故鄉黯黯鎖玄雲皓齒吳娃唱柳枝)(1932年12月31日)
無題(洞庭木落楚天高)(1932年12月31日)
答客誚(1932年12月31日)
二十二年元旦(1933年1月26日)
贈畫師(1933年1月26日)
學生和玉佛(1933年1月30日)
吊大學生(1933年1月31日)
題《吶喊》(1933年3月2日)
題《彷徨》(1933年3月2日)
悼楊銓(1933年6月20日)
題三義塔(1933年6月21日)
無題(禹域多飛將)(1933年6月28日)
悼丁君(1933年6月28日)
贈人(1933年7月21日)
無題(一枝清采妥湘靈)(1933年11月27日)
阻郁達夫移家杭州(1933年12月30日)
無題(煙水尋常事)(1933年12月30日)
報載患腦炎戲作(1934年3月15日)
無題(萬家墨面沒蒿萊)(1934年5月30日)
秋夜有感(1934年9月29日)
題《芥子園畫譜三集》贈許廣平(1934年12月9日)
亥年殘秋偶作(1935年12月5日)
第二部分新詩和政治諷刺詩
寶塔詩(1903年春夏之間)
夢(1918年5月15日)
愛之神(1918年5月15日)
桃花(1918年5月15日)
他們的花園(1918年7月15日)
人與時(1918年7月15日)
他(1919年4月15日)
贈川島(1923年12月13日)
《而已集》題辭(1926年10月14日)
好東西歌(1931年12月11日)
公民科歌(1931年12月11日)
南京民謠(1931年12月25日)
“言詞爭執”歌(1932年1月5日)
第三部分佚詩殘句
佚詩殘句一(1898年5月)
挽丁耀卿(1902年1月12日)
嘲王惕齋(1903年春夏之間)
嘲蔣觀雲(1907年7月)
《新秋雜識》附詩句(1933年9月14日)
科學史教篇片段(1907年)
摩羅詩力說(1907年)
娜拉走後怎樣片段(1923年12月26日)
詩歌之敵(1925年1月17日)
忽然想到片段(1925年6月18日)
《兩地書》第32封信片段(1925年6月28日)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片段(1927年23、26日)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1932年12月15日)
書信集·330628·致臺靜農片段(1933年6月28日)
漫與片段(1933年9月27日)
準風月談·詩和豫言片段(1933年7月20日)
書信集·340220·致姚克片段(1934年2月20日)
書信集·341101·致竇隱夫片段(1934年11月1日)
書信集·350920·致蔡斐君片段(1935年9月)
主要參考書目
主要人名索引
後記
後記
2013年3月30日中午12時30分,當我寫完這本小書的最後一個字後,一種如釋重負的、喜悅的感覺滿溢全身:真的寫完了!
我提筆寫作此書,雖是受了有些方面的刺激,但是想寫一本書的念頭,卻是從我於1988年8月踏入浙江大學中文系學習的時候就已經有了的。四年的大學生活,面對浩瀚的典籍,也有過痛苦的迷茫,有人們常說的那種“上窮碧落下黃泉,兩頭茫茫皆不見”之感。經過痛苦的找尋,我終於找到了讀書要“博學守約”和精讀泛讀相結合的方法,這方法似乎對我很有用。但最終,我的大學四年還是在追尋和平淡無奇的感覺之中過去了。
1992年7月畢業後,為了謀生,我參加了工作,但寫作的念頭愈益熾烈。而想寫作嗎,談何容易?!此後,我只能是延續了大學時期買書、讀書的興趣,並開始了尋找課題和積累資料的漫長過程。讀書是快樂的,但買書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這是因為我對好書的強烈的占有欲,和工資收入有限的激烈矛盾,常使自己有“阮囊羞澀”的感覺,使我自己只得量入為出。在書店看到好書,而袋中又有盈餘時,我就跑書店,這成為我除讀書之外的又一樂趣。買書時,遇到除了錢的問題之外,我也常常有這樣的疑惑,就是紙質書和電子書的優劣問題。在現在,如果我不買書而想在電腦中讀遍世上所有感興趣的書,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有時我想,這世上的好書太多,而我的資金有限,我還是不買任何書,就在網上看吧。但這不過是想想而已,因為我覺得電子書究竟無法替代紙質書,其中不僅僅在於紙質書有讓人捧著書讀的踏實的感覺。
於是,這書是一天天多起來,看書的時間也愈益緊張,終至於因來不及看而積壓下來。這樣下來,我家中的書競達到了三四千冊的規模,並也得到了我所在的小城的“藏書家庭”的稱號。有了這個稱號,我就想:難道自己就只會蒐集書和“藏書”嗎,我就不能用書、寫書嗎?!於是,我又強烈地感到自己也要來寫本書。終於,在2012年“十一”長假過後,我確定了要寫這本小書。
我的與《魯迅全集》的結緣,是從大學二年級開始的。因為我在大學期間主要的興趣是在古典文學和文字、音韻、訓詁學,而對於現當代文學,除了儘可能廣泛閱讀經典的現當代文學作品外,我沒有深入的興趣。但我知道魯迅的偉大,和他的作品在這個社會存在的現實意義,於是開始選修時為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的黃健老師開設的《魯迅研究》課程。當一學期末了的時候,老師要求寫一篇關於魯迅的論文,於是我根據自己對魯迅的理解,寫了一篇論文,竟得到了黃老師的讚揚,並被評為優秀,這大大地激勵了我。這激勵的結果是使我勒緊褲帶,花了近兩個月的生活費,去杭州的解放路新華書店買了一套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當這一套全集沉甸甸地背在我的身上,坐上16路公車回玉泉校區的路上,我想,這一個月,我得常吃三分錢一碗的綠豆粥和兩分錢一個的大饅頭了。
儘管饅頭和綠豆粥吃得使我的胃常泛酸,且有一段日子,我一看到饅頭和綠豆粥就怕,但《魯迅全集》卻是放在床頭手不釋捲地看完了一遍。此後,在工作後至今,我又一共看了五遍。當這套書被我翻得怕散架的時候,聽說新版《魯迅全集》又出版了,我毅然又跑去書店把它背回來了。
因為感覺到自己對魯迅的理解的自信,又感到自己僻居小城可使用的資料的缺乏,以及自己未受過更專門的專業研究訓練,所以我決定想以註解和賞析的角度來闡釋魯迅的所有詩歌,以期能接近這位孤獨的思想家、文學家的思想和心靈,於是就有了這本書。這本書在史料上較多的參考了倪墨炎先生的《魯迅舊詩探解》,在理解上儘量地以魯迅先生自己在雜文、小說中所表現的思想和觀點來闡釋,書中有註解,有賞析,也有對各注家就某一問題的分歧的辨析。為便於讀者的理解,並使這種理解能切合現在這個社會的實際,我從魯迅的雜文、小說中,以摘錄和存目的方式,增加了“延伸閱讀”的部分,以幫助讀者對某些詩歌的理解。這裡摘錄的內容,其中有的是魯迅在當時社會狀況和語境下,對國民性和民族劣根性的剖析和論斷。我覺得這種剖析和論斷,即使在21世紀的中國,仍有積極的警醒作用,畢竟國民性和民族劣根性的形成並存在至今,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積澱的過程,不可能因為政黨的更替、意識形態的轉換而瞬間消失。因此,魯迅的思想還有長期存在的必要,並可以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而提供思想的源泉。也就是說,我的這種“延伸閱讀”的摘錄和存目的方式,一方面是為了便於讀者的檢索和閱讀;一方面是因為覺得這些內容與本詩所表達的意思有關聯,可供讀者加深對本詩的理解;另一方面則是我個人的理解,認為這些摘錄所揭示的民族劣根性和國民性的特徵,確實在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在今天有繼續重提的必要,我認為,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魯迅、需要魯迅的現實意義。
書的第四部分摘錄了魯迅關於詩歌創作的觀點,這應該是本書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可供理解魯迅詩歌的創作思想,故從全集中摘錄出來,並作必要的詮釋,其中對《科學史教篇》的節錄部分、《摩羅詩力說》的文言文進行了譯釋,注釋大體採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對《魯迅全集》的注釋,以幫助讀者進一步加深理解。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的老師,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黃健先生繼續給我以熱忱的關心和支持,並答應為我的這本小書作序,這使我非常感激。因為為別人的書作序,的確也算是一種冒險。對於作序者來說,別人索序,而己心不願,又盛情難卻,則實在是委屈自己;既答應了作序,而索序者所寫的東西實在不能令作序者恭維,恭維之則實在是委屈自己,不恭維之則面子上又過不去,這是很為難的。再進一步地說,如果著者所寫的東西是抄襲和拼湊之作,是劣品和贗貨,則又掉了作序者的價,正如明星為某些產品作代言廣告而發生的尷尬一樣。所以,為別人的書作序是一個冒險的工作,這使我對黃健教授的慨然應允,再次表示由衷的感激,謝謝老師的提攜的熱忱!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的妻、女給予我極大的支持。我的妻子方海波從未對我的買書提出過反對的意見,我的女兒林敬儀的優秀的學習表現,給了我很大的動力和寫作的餘暇,這都是我很感欣慰的。
書成之後,我的外甥女楊靜波、鄭賽麗,我的同事蔣艷、李傑、胡斌、管旭鳳、陳達周等,都各個為我的書的早日出版而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我的同事、寧波市鎮海區園林綠化養護中心主任王義軍同志給予我精神上的巨大鼓舞和大力支持,都使我非常感謝。這本書的出版,也算是對大家的報答吧。
本書的編輯、校對,承浙江大學出版社宋旭華先生、本書的責任編輯包靈靈先生認真負責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著者
2013年5月20日記
2013年12月9日校訖
序言
前言
關於魯迅的研究,從1913年4月25日《小說月報》第4卷第l號發表主編惲鐵樵對署名“周追”(周樹人的筆名)的小說《懷舊》的點評文章“焦木附志”以來,到今天已經走過整整一百年的歷史。然而,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問“魯迅是誰?”這個看似簡單,而實際上又難以回答的問題,一直都纏繞著20世紀的中國社會。不論他曾經是如何被推上神壇,後來又怎樣地走下神壇,也不論曾經他頭上戴有何種桂冠,他的多重身份,他的思想的多樣性,心靈世界的複雜性,性格表現上的矛盾性,尤其是深藏在他內心深處的那種難以“直說”的苦楚,那種揮之不去的多疑、憂鬱和孤獨,那種被靈魂的“毒氣”和“鬼氣”糾纏而產生的苦痛,都使他成為20世紀中國始終無法“說清楚”而又“說不盡”的“異端”,並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中國,同時,這也是他成為現代中國最為獨特,也是最為傑出的文學家和思想家的內在緣由。
李澤厚在《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一文中,曾高度評價魯迅“是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無與倫比的文學家兼思想家,他培育了無數青年。……他的作品是當之無愧的中國近代社會的百科全書”。的確,在現代中國處於激烈動盪的社會和文化轉型過程中,魯迅所有的創作都是指向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的。對於他來說,他要做的就是要衝破這種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的精神束縛,雖然他也認識到“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但他始終相信“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於是,他總是自覺地選擇“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一點缺陷”的方式,向舊世界“宣戰”,如在小說《狂人日記》里,他就借狂人之口,對有著“四千年文明”的歷史,發出大膽的質疑:“從來如此,就對么?”並將歷史負面的根性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形象地比喻為“吃人”。這是迄今為止,通過文學文本所展示出來的對歷史和傳統人生的解讀,最為深刻、最為形象的藝術比喻和認識結論。通過文學創作,魯迅把他深藏在內心深處,經過反覆思考和生命體驗的思想認識,化為一個個鮮活的文學形象,由此展現中國人的生存境況、心理性格和歷史命運,並深刻地揭示出“病態社會”和“病態人們”的疾苦,希望能夠引起社會“療救的注意”,達到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魂靈的目的。
魯迅之所以能夠用與舊傳統徹底決裂的方式,來進行大無畏的質疑、批判和反省,最主要的還是源白乾他對傳統根底所具有的深刻認識、把握和體悟。在《墳·寫在後面》一文中,他曾宣稱:“孔孟的書我讀的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正是置身於傳統與現代、東方和西方的兩種不同文化的交匯、;中突和融合的特定語境中,魯迅的文學創作達到了一種新的思想高度。他給自己文學創作規定的任務是:以文學為點燃“國民精神的火花”,通過文學“畫出沉默的、現代的國民魂靈”,並以此為橋樑,溝通國民彼此隔膜的心靈,喚醒仍在“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里昏睡的國民,促進民族的自我反省與批判。可以說,居於魯迅文學創作觀念中心的,不是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動及其對人的影響,其意義重構的中心指向是展現身為國民的“人”,如何獲得精神的解放、心靈的解放,如何擺脫長期的封建倫理道德束縛而進入精神自由、心靈自由的境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文學創作集中地體現了他作為20世紀中國最傑出的思想家,通過文學而展示出來的關注人的生存境況、心理發展和前途命運,尋找人的精神歸宿,建構人的精神家園的思想激情和精神風采。
魯迅一生的文學創作成就,多集中表現在小說、散文(包括雜文)創作上,而對於在他那個時代興起的白話新詩創作,他幾乎沒有涉足,故也有人說魯迅不是一個詩人。其實,魯迅是不是詩人,具不具有詩人的名分,戴不戴詩人的桂冠,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究竟具不具有詩人的氣質、詩人的才智、詩人的胸襟,以及詩人那特有的詩性情思,詩性境界和詩性品格。魯迅雖然在白話新詩創作方面建樹不多,但人們只要認真地讀他的舊體詩,就不難發現,他本質上就是一個詩人,具有濃郁的詩人氣質。他的舊體詩創作,不僅展現出了他的深厚的古典文學的功底和修養,而且更是展現出了他作為一個詩人所獨有的稟賦、才華、胸襟、品格、情思和境界。從魯迅創作舊體詩的情境和心境上來看,他的這種獨有的詩意情懷、詩性精神,毫無疑問是貫穿他整個文學創作活動之中的,這也是他的文學創作極具藝術魅力的根本原因,如同李澤厚所指出的那樣:“魯迅卻始終是那樣獨特地閃爍著光輝,至今仍然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裡呢:除了他對舊中國和傳統文化的鞭撻入里、沁人心脾之外,我以為最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一貫具有的孤獨和悲涼所展示的現代內涵和人生意義。”因此,在文學創作中,魯迅也總是能夠將“極強烈的情感包裹沉澱在極嚴峻冷靜的寫實中,出之以中國氣派的簡潔凝練”,從而構成他極具詩意和詩性精神的“特有美學風格”。顯然,魯迅這種“特有美學風格”的形式,與深蘊在他內心的那種詩意情懷、詩性精神是分不開的。
林偉是我的學生,他入浙江大學時學的是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我當年是他的任課老師,主講專業基礎課“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同時還開了一門“魯迅研究”的專業選修課。當年的浙大還是一所理工科大學,文科專業並不多,尤其是像中文這種基礎性文科專業,在理工科大學更是“少數派”,不像我當年上大學時,中文系通常是數一數二的大系,特別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制度後,像我這樣在農村“廣闊天地”插隊落戶的知青,由於沒有受到良好的基礎性教育訓練,往往數理化都比較差,故選文科而學中文的比較多。我是恢復高考制度首批考上大學的1977級大學生,當年我所在的一個班就有108位學生,與《水滸傳》里所描寫的梁山108位好漢的人數一模一樣。浙大的文科氛圍並不是太好。儘管早在1928年,國立浙江大學就設立了中文系,但中文學科並不是浙大的強項學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文科從浙大分出,浙大成為一所單科性的工科大學,後又陸續恢復理科,成為以理工科為主的多科性大學。恢復文科建制,則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我是1985年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浙大工作的。我到浙大時還沒有中文系,我先是到臨時掛靠在教務處下設立的“文學藝術教研組”,不久該教研組被併入當時的語言系(實際上是外語系),改名為“漢語教研室”。後來準備成立中文系,又改名為“中文教研室”。我也就隨之先後到這兩個教研室工作,學校成立恢復“中文系籌備小組”時,我也是其中的成員,在教學科研之餘,主要負責恢復建制和專業論證報告的起草和外聯工作。1986年浙大正式恢復中文系建制,開始招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批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本科生。
林偉是1988年入學的,儘管文科在浙大的地位不如理工科高,但作為全國知名的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考入浙大的分數仍然是很高的。可以想像,林偉在中學時學習成績是很優秀的,各方面的表現也是非常優秀的,否則也進不了浙大。林偉的個頭不高。但學習很勤奮。刻苦鑽研,為人也非常樸實、忠厚、誠懇。他在學校時就對魯迅研究非常有興趣,所以與我接觸比較多。他知道我對魯迅的研究比較用心,所以他在課後也常到我家,就學習中的問題,特別是有關魯迅研究的問題,與我一道探討,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畢業後,他回到寧波老家工作,與我也偶爾有些聯繫,但我去香港進修,後來又留在香港工作了幾年,就逐漸地失去了聯繫。我重新回校任教後,浙大已經是“四校”(即原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合併後的大學,被稱為新浙江大學。我原先任教的老浙大中文系,也就是林偉在浙大學習時的中文系,已改名為國際文化學系。一段時間與中文系一道被納入新組建的人文學院內,不久則與新聞系一道。組建成為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屬於該院下屬的一個系。我回校任教後,雖然是在中文系工作,但此時的中文系,實際上就是原先的杭帥l大學中文系。故在後來編撰出版《浙江大學中文系系史》時,原先老浙大中文系的系友並沒有被編入,只是在大事記里作了說明,並將當時老浙大中文系的情況和人員作為附錄附在系史後面。我後來與林偉重新恢復了聯繫後,曾開玩笑地說,你現在不屬於中文系的系友了,升格了,屬於國際文化學系的系友了。他當時看著我,似乎有些驚訝,然而只是苦笑一番,並沒有說些什麼。是啊,歷史有時就是這么弔詭,人生有時也就是這么無常。能說些什麼呢?就像魯迅當年所自嘲的那樣:“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與林偉恢復了聯繫後,有一天,他鄭重地告訴我說,他一直都在研究魯迅,特別是他對魯迅的詩歌創作非常感興趣。他對我說,他不滿意目前對魯迅詩歌的註解,決心要用自己的研究心得,重新對魯迅的詩歌進行注釋。我就對他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表示了高度的讚賞,並希望能夠早日看到他的研究成果。今年暑假期間,他將魯迅詩歌注釋的文稿電子版發給我,並囑我寫序,我認真地拜讀了他的文稿。看得出來,他是用了心的,如同他在代自序中所說的那樣:“毋庸置疑,魯迅的偉大的思想和作品,在今天仍有閱讀、研究,以期達到繼續療救這幾千年來受中國傳統文化及思想積澱、遺傳影響的國民的靈魂的必要。本書所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就魯迅先生的全部詩歌進行闡釋,以期接近魯迅的思想,並以此拋磚引玉。能就教於專家、學者。對筆者來說,即使使大方之家哂笑,亦無暇考慮會使自己汗顏的可能。故筆者不揣冒昧,懷著這樣的堅決的心情,抱著欲接近這位偉大的、孤獨的思想家的魂靈的目的,試圖對魯迅的詩歌進行粗淺的探討。”
關於魯迅研究的論文和著作,可謂是汗牛充棟。我開始還擔心,僅憑他個人之力,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來“啃”這塊“硬骨頭”,是否真的能夠如願?即便如願,又是否具有學術價值?能否展開他對魯迅詩歌創作的學理性分析、闡述和邏輯論述?讀完他對魯迅詩歌的注釋和研究,我心裡的這份擔憂,可以說是解除了。儘管我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地贊同他的注析,以及從中所表現出來的他對魯迅的創作,特別是對魯迅詩歌創作的研究結論,但我還是要為他這種鍥而不捨的鑽研精神,給予熱烈的掌聲和喝彩,對他獨到的魯迅研究視角、分析、闡釋和論述。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讚賞。在代自序中,林偉全面地闡述了他對魯迅詩歌創作的認識,重點從五個方面,闡述了魯迅詩歌創作的價值和意義,是一篇具有自己獨到學術見地的論文,從中可以看到他對魯迅思想情感和心路歷程的整體認識和把握。同時,也正是基於這種整體的高度,他對魯迅詩歌的注析,也就避免了一般民間學者研究習慣於就事論事,緊扣字面分析而微言大義的弊端,顯示出基於民間研究立場的獨立性特點和學術精神。
國外有“說不盡的莎士比亞”之說,同樣,在中國也有“說不盡的魯迅”之說,正如李澤厚所說的那樣:“有兩部散文文學可以百讀不厭,這就是《紅樓夢》和魯迅文集。《紅樓夢》是封建社會的沒落輓歌,魯迅的文章則是指向它的戰鬥號角。”無疑,作為一種精神生命,魯迅在現代中國將是長存的。他“特立獨行”的人生方式,“遺世獨立”的人生精神,他疾惡如仇的性格特徵,作為文化的一種“集體無意識”,也已深深地沉積在古老民族的心靈深處,並為現代中國人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在現代中國的發展歷程中,這種人生精神煥發的光芒是永不磨滅的。我想,林偉對魯迅詩歌的注析,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學術研究,而是從中寄寓了他通過對魯迅詩歌創作的研究,表達出的他對於魯迅精神的深刻領悟和繼承弘揚。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他也是魯迅的傳人。
是為序。
黃健
於杭州西子湖畔
2013年10月10日
後記
2013年3月30日中午12時30分,當我寫完這本小書的最後一個字後,一種如釋重負的、喜悅的感覺滿溢全身:真的寫完了!
我提筆寫作此書,雖是受了有些方面的刺激,但是想寫一本書的念頭,卻是從我於1988年8月踏入浙江大學中文系學習的時候就已經有了的。四年的大學生活,面對浩瀚的典籍,也有過痛苦的迷茫,有人們常說的那種“上窮碧落下黃泉,兩頭茫茫皆不見”之感。經過痛苦的找尋,我終於找到了讀書要“博學守約”和精讀泛讀相結合的方法,這方法似乎對我很有用。但最終,我的大學四年還是在追尋和平淡無奇的感覺之中過去了。
1992年7月畢業後,為了謀生,我參加了工作,但寫作的念頭愈益熾烈。而想寫作嗎,談何容易?!此後,我只能是延續了大學時期買書、讀書的興趣,並開始了尋找課題和積累資料的漫長過程。讀書是快樂的,但買書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這是因為我對好書的強烈的占有欲,和工資收入有限的激烈矛盾,常使自己有“阮囊羞澀”的感覺,使我自己只得量入為出。在書店看到好書,而袋中又有盈餘時,我就跑書店,這成為我除讀書之外的又一樂趣。買書時,遇到除了錢的問題之外,我也常常有這樣的疑惑,就是紙質書和電子書的優劣問題。在現在,如果我不買書而想在電腦中讀遍世上所有感興趣的書,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有時我想,這世上的好書太多,而我的資金有限,我還是不買任何書,就在網上看吧。但這不過是想想而已,因為我覺得電子書究竟無法替代紙質書,其中不僅僅在於紙質書有讓人捧著書讀的踏實的感覺。
於是,這書是一天天多起來,看書的時間也愈益緊張,終至於因來不及看而積壓下來。這樣下來,我家中的書競達到了三四千冊的規模,並也得到了我所在的小城的“藏書家庭”的稱號。有了這個稱號,我就想:難道自己就只會蒐集書和“藏書”嗎,我就不能用書、寫書嗎?!於是,我又強烈地感到自己也要來寫本書。終於,在2012年“十一”長假過後,我確定了要寫這本小書。
我的與《魯迅全集》的結緣,是從大學二年級開始的。因為我在大學期間主要的興趣是在古典文學和文字、音韻、訓詁學,而對於現當代文學,除了儘可能廣泛閱讀經典的現當代文學作品外,我沒有深入的興趣。但我知道魯迅的偉大,和他的作品在這個社會存在的現實意義,於是開始選修時為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的黃健老師開設的《魯迅研究》課程。當一學期末了的時候,老師要求寫一篇關於魯迅的論文,於是我根據自己對魯迅的理解,寫了一篇論文,竟得到了黃老師的讚揚,並被評為優秀,這大大地激勵了我。這激勵的結果是使我勒緊褲帶,花了近兩個月的生活費,去杭州的解放路新華書店買了一套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當這一套全集沉甸甸地背在我的身上,坐上16路公車回玉泉校區的路上,我想,這一個月,我得常吃三分錢一碗的綠豆粥和兩分錢一個的大饅頭了。 儘管饅頭和綠豆粥吃得使我的胃常泛酸,且有一段日子,我一看到饅頭和綠豆粥就怕,但《魯迅全集》卻是放在床頭手不釋捲地看完了一遍。此後,在工作後至今,我又一共看了五遍。當這套書被我翻得怕散架的時候,聽說新版《魯迅全集》又出版了,我毅然又跑去書店把它背回來了。 因為感覺到自己對魯迅的理解的自信,又感到自己僻居小城可使用的資料的缺乏,以及自己未受過更專門的專業研究訓練,所以我決定想以註解和賞析的角度來闡釋魯迅的所有詩歌,以期能接近這位孤獨的思想家、文學家的思想和心靈,於是就有了這本書。這本書在史料上較多的參考了倪墨炎先生的《魯迅舊詩探解》,在理解上儘量地以魯迅先生自己在雜文、小說中所表現的思想和觀點來闡釋,書中有註解,有賞析,也有對各注家就某一問題的分歧的辨析。為便於讀者的理解,並使這種理解能切合現在這個社會的實際,我從魯迅的雜文、小說中,以摘錄和存目的方式,增加了“延伸閱讀”的部分,以幫助讀者對某些詩歌的理解。這裡摘錄的內容,其中有的是魯迅在當時社會狀況和語境下,對國民性和民族劣根性的剖析和論斷。我覺得這種剖析和論斷,即使在21世紀的中國,仍有積極的警醒作用,畢竟國民性和民族劣根性的形成並存在至今,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積澱的過程,不可能因為政黨的更替、意識形態的轉換而瞬間消失。因此,魯迅的思想還有長期存在的必要,並可以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而提供思想的源泉。也就是說,我的這種“延伸閱讀”的摘錄和存目的方式,一方面是為了便於讀者的檢索和閱讀;一方面是因為覺得這些內容與本詩所表達的意思有關聯,可供讀者加深對本詩的理解;另一方面則是我個人的理解,認為這些摘錄所揭示的民族劣根性和國民性的特徵,確實在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在今天有繼續重提的必要,我認為,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魯迅、需要魯迅的現實意義。 書的第四部分摘錄了魯迅關於詩歌創作的觀點,這應該是本書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可供理解魯迅詩歌的創作思想,故從全集中摘錄出來,並作必要的詮釋,其中對《科學史教篇》的節錄部分、《摩羅詩力說》的文言文進行了譯釋,注釋大體採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對《魯迅全集》的注釋,以幫助讀者進一步加深理解。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的老師,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黃健先生繼續給我以熱忱的關心和支持,並答應為我的這本小書作序,這使我非常感激。因為為別人的書作序,的確也算是一種冒險。對於作序者來說,別人索序,而己心不願,又盛情難卻,則實在是委屈自己;既答應了作序,而索序者所寫的東西實在不能令作序者恭維,恭維之則實在是委屈自己,不恭維之則面子上又過不去,這是很為難的。再進一步地說,如果著者所寫的東西是抄襲和拼湊之作,是劣品和贗貨,則又掉了作序者的價,正如明星為某些產品作代言廣告而發生的尷尬一樣。所以,為別人的書作序是一個冒險的工作,這使我對黃健教授的慨然應允,再次表示由衷的感激,謝謝老師的提攜的熱忱!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的妻、女給予我極大的支持。我的妻子方海波從未對我的買書提出過反對的意見,我的女兒林敬儀的優秀的學習表現,給了我很大的動力和寫作的餘暇,這都是我很感欣慰的。 書成之後,我的外甥女楊靜波、鄭賽麗,我的同事蔣艷、李傑、胡斌、管旭鳳、陳達周等,都各個為我的書的早日出版而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我的同事、寧波市鎮海區園林綠化養護中心主任王義軍同志給予我精神上的巨大鼓舞和大力支持,都使我非常感謝。這本書的出版,也算是對大家的報答吧。 本書的編輯、校對,承浙江大學出版社宋旭華先生、本書的責任編輯包靈靈先生認真負責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著者 2013年5月20日記 2013年12月9日校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