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靡非斯特是聖經中大天使盧佛斯的本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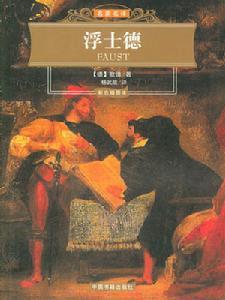
引言
一、簡介
歌德的《浮士德》是一部耗時作者60年之久的詩劇,是他整個生命的完整表白,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深遠影響。全劇描寫主人公浮士德不斷追求、不斷探索人生理想的道路,寫他的思想發展的歷程。歌德把浮士德塑造成在不斷克服自身弱點的同時,不斷追求豐富知識、追求美好事物,追求崇高理想,生無所息、堅韌頑強、有著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品格的積極進取精神的代表,向人們指出了一條精神淨化的道路。而靡非斯特與浮士德自始至終處於矛盾對比之中。浮士德作為善的象徵,他是美的,積極樂觀、入世進取、熱愛人類、追求真理是其個性特徵;靡非斯特是惡的代表,他是醜的,其悲觀厭世、否定人生、仇恨人類、蔑視理智、冷酷無情恰與浮士德形成鮮明對比。
作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浮士德》在思想內容上是“說不盡的”在形式上也是豐富複雜的。這種博大精深和豐富複雜性無疑增加了文本解讀的難度,不免語義叢生,歧義迭出,因此歷代學者對於《浮士德》的研究也是眾說紛紜。而對於魔鬼形象的評論也是各抒己見。但終其一點可以肯定,魔鬼靡非斯特與《聖經》中“蛇”這個意象母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本文試圖從魔鬼靡非斯特這個原型意象及其發展演變過程來分析這一人物,並試圖從更深層次挖掘其產生變化的歷史原因。
二、《浮士德》中魔鬼靡非斯特意象解讀
(一)魔鬼靡非斯特主要代表否定精神和“惡”
靡非斯特是作品中的重要形象,他在詩劇中是作為浮士德的對立面出現的。靡非斯特有各種化身,扮演各種角色:他扮成獅子狗從而達到接近浮士德並與其訂立契約的目的;他打扮成浪蕩學生,企圖用形上學與好高騖遠的智力誘惑浮士德;在拯救瑪甘淚時,他幻化成一團黑煙而活動;在古羅馬帝國他又成為容克貴族,通過發行紙幣維持日漸衰退的封建王朝;而在唯美的古希臘,他又成為福耳庫阿斯,充滿著辯證思維;諸如此類等等。
魔鬼靡非斯特主要代表否定精神和“惡”,正如他自我解釋說:“犯罪、毀滅,更簡單一個“惡”字,這便是我的本質。”[1] 靡非斯特的形象充滿著有意的矛盾:一方面,他肯定人的物質性及其“生物——物質”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肯定“生物——人”的虛無意義的過度勞碌,籍以給一切超出純感覺範圍以外的生產性的東西以否定的批判。因此,碩爾茨根據歷史哲學的解釋,認為靡非斯特體現歷史哲學的虛無主義。靡非斯特自稱是“黑暗的一部分”[2],又稱是“混沌的寵兒”[3]光明是與大自然的創造塑性同源的,而代表黑暗的靡非斯特卻使虛無、無形、永恆空虛與之對立。雷德爾說:作為否定的化身,靡非斯特的職能在與使一切東西貶值和衰落,這同樣表現在破壞形式和維持僵化上。他在太古的寂寞中,只有自身成為朋友、夥伴和誘惑者;他毫不停頓地需求絕對的靜止;他在美麗假象的諷刺戲中,以滑稽形式表演虛無的嚴肅;他縱然千變萬化。其本質始終不變。[4]
(二)魔鬼靡非斯特體現“積極性的惡”
從另一個角度審視魔鬼靡非斯特這一意象可以發現,他並非代表純粹的否定而更兼具積極作用,即體現“積極性的惡”。詩劇中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構成一對善惡矛盾,體現辯證統一關係。
“我是經常否定的精神,
原本合理;一切事物有成
就終歸有毀;
所以倒不如一事無成。
因此你們叫作罪惡、毀滅,
簡單說來,這個“惡”字,
便是我的本質。”[5]
靡非斯特的做惡,激勵和促進浮士德的向善,浮士德的向善又反襯出靡非斯特的做惡,靡非斯特自稱是“作惡造善力之一體”。[6]又如《浮士德》第一部“書齋”一場中,靡非斯特說:“我是經常否定的精神”,“我是那種力量的一體,它常常想的是惡而常常做的是善。”[7]浮士德和靡非斯特的矛盾是人間的矛盾,有其具體的現實內容,是現實的形而下的善惡衝突,與第一層的形而上的善惡矛盾相比,這對矛盾的構成由冥冥的宇宙走向了現實的人間,由至善至惡變成了具體的善惡。在悲劇中,浮士德五個階段的追求,靡非斯特始終作為具體的惡的不同化身,作為“至惡”的具體行動的承載者,具有推動力,作為惡的載體的靡非斯特在浮士德的追求中設定障礙,激勵和促進浮士德不能滿足、不斷地向著更高的境界奮進。詩劇開篇描寫浮士德早已厭倦枯燥無聊的學者生活,於是,在愛情生活中,靡非斯特試圖用愛情蒙蔽浮士德的雙眼,但浮士德最終克服熱情的衝動,在拯救無望下擺脫愛情的羈絆;在政治生活中,靡非斯特試圖用封建王朝高官厚祿的幻景引誘浮士德,但僵化腐朽的封建制度無法滿足浮士德的政治抱負,使其轉而走向對古典美的追求;浮士德意識到古典希臘的美無法成為當前的現實,隨著海倫的幻滅,靡非斯特所設定的這一誘惑的詭計再次付諸東流;在改造大自然的過程中,浮士德最終犧牲,但他理解到這種犧牲的必要,即人類達到人道生存的更高境界的必要犧牲,最終浮士德戰勝靡非斯特得到瑪甘淚的接引向上飛升。他對浮士德所做的種種誘惑都是從惡的動機出發,企圖使浮士德走向沉淪和毀滅,但卻使浮士德從迷誤和錯誤中接受教訓,提高認識,不斷地向更高的境界追求,更加接近所追求的“至善”的境地。
魔鬼靡非斯特與浮士德訂立契約,以僕人的身份跟隨其左右,並用盡一切方法滿足浮士德的要求以達到最終目的。伯姆聲言靡非斯特是“浮士德的壞的自我”。[8] 浮士德的內心是充滿激烈的矛盾的,在與靡非斯特相遇之前,他攻讀中世紀的各門學問多年卻一無所得,內心十分痛苦以至企圖自殺,直到聽到復活節的鐘聲,聽到天使們的合唱,才使其重獲生之力量。因此,浮士德甘願有靡非斯特式的麻木不仁,好讓自己解脫那浮士德式的渴望的苦痛。他要求瞬間的享受,以便忘記永無休止的追求,這是浮士德內心深處的矛盾。因而,魔鬼靡非斯特就承擔了浮士德內心深處對立雙方一方的特質,成為浮士德本身中的否定精神。在作者的心目中,實際上這是人的一分為二,所以二者是合二而一,浮士德是人的積極的或肯定的一面,靡非斯特是人的消極的和否定的一面。這一人一魔,一主一仆,相生相剋,相反相成,如影隨形,如呼如吸,如問如答。
三、魔鬼靡非斯特源於《聖經》中的撒旦,即“蛇”這個意象
(一)“蛇”原型的變形與置換
魔鬼靡非斯特是一個來自北歐傳說和基督教傳說的形象,即《聖經》中的撒旦。民間傳說只給了他身份卻限制了他的發展。浮士德的使命不斷變化,靡非斯特卻始終堅持唯一的目標:誘惑他,讓他墮落,常常淪為一個程式化的人物,履行引誘的義務,承擔失敗的命運。而魔鬼靡非斯特這一形象正是源於《聖經》中的蛇這個原形。原形按弗萊的定義是指:“一種在文學中反覆運用並因此而成為約定性的文學象徵或象徵群”。原形批評理論認為,反覆的生活經歷會在人們心靈上留下心理殘餘,即所謂“原始的偶像”,他們被人類的集體無意識世代傳承,並在神話、宗教、夢境、個人想像和文學作品裡得到描繪,形成各種“原形”。而《聖經》中的許多比喻、母題和象徵也演化成具有普遍適應性的跨文化的原型模式和符號。在《舊約·創世紀》中,蛇是作為一種邪惡的象徵符號出現的。
耶和華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上帝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上帝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也就明亮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善惡。”於是女人見那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他們的眼睛就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體的,便拿無花果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9]
它引誘夏娃偷吃禁果,違背上帝意旨,從而導致了人類的墮落,開始了人間的苦難歷程。蛇也被給予了重懲:一方面詛咒蛇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另一方面,蛇將與女人及其後裔世代結仇。正因為蛇在西方宗教文化里背負著“原罪”思想,被詛咒與人類世代結仇,而且在現實生活里,蛇在與人類雜處的過程中也對人類構成威脅,蛇在文學作品裡往往被視為邪惡的象徵。因此蛇的意象旨意是誘惑、欺騙與背叛。這個意象凝聚了人類從遠古以來長期積累的巨大心理能量,因而具有人類感覺與聯想的共通性,在後世的文學作品中不斷出現,形成了一種固定的原型。這個原型在《聖經》的其它地方演變成了撒旦和魔鬼。
但西方文明里的蛇也並非從一開始就是魔鬼撒旦般的邪惡形象。古埃及的先民以蛇和鷹作為本族群的圖騰物,但經過歷史的演變,北部埃及奉蛇為保護神,南部埃及奉鷹為保護神。北部埃及被南部埃及征服,鷹就被尊為唯一的保護神
蛇才逐漸被視為邪惡之物。大約公元前1700年前,古希伯來人受到乾旱的威脅,逃到埃及生活了四百餘年,所以也就接受了蛇是邪惡的觀點,《聖經·舊約》里蛇成為誘惑、欺騙、背叛的代言者也是由此演變而來。撒旦是“敵對者” 的意思,即“魔鬼”與“上帝”對立之意,早期在編撰舊約聖經的時候,猶太教還沒有惡魔的概念,當時的撒旦比較接近試驗者的意味,後來衍生出一種版本,認為撒旦是嚴格追求真理的天使,無法容忍違背真理的行為。 《聖經新約-啟示錄》中寫到:
……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墮,七頭上戴七個冠冕。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落在地上。......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也同他的使者去爭戰。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10]
在講到雙方戰鬥結束後,《啟示錄》的作者特意加上一句:大紅龍就是那“古時的蟒蛇”,這一簡要的補充十分重要,它把蟒蛇與魔鬼間的同等關係勾勒了出來。此後,在新約中出現的蟒蛇,往往就是魔鬼的代用詞。在《馬太福音》中,耶穌曾有兩次斥責法力賽人,而且兩次均把法力賽人比作蛇。
“你們這些蛇,既然你們屬於邪惡的種類,怎麽會說出好話來呢?”
“你們這些蛇和蛇的子孫,你們如何能夠逃脫地獄的懲罰呢?” [11] ????
耶穌在這裡所說的蛇與引誘夏娃的“古時的蟒蛇”,顯然具有同質性。 撒旦在與上帝的交往中因對上帝的作為心懷不滿而鼓動諸神起來造反,失敗後被打入地獄,但他也未能改悔,圖謀誘惑人類之祖——亞當和夏娃,結果化身為蛇。
16世紀德國馬丁·路德進行了宗教改革,城市得以發展,導致民間文學極為繁榮。路德為了使人們可以直接領悟上帝的語言,推廣普及新教教義,1521年,他第一個將基督教經典《聖經》譯為德文。在翻譯過程中,他不斷徵求意見,貼近百姓的習慣,儘量讓廣大民眾能夠看懂聽懂《聖經》,這些做法促進了路德新教教義的推廣,使路德的教義深入人心,也使《聖經》突破貴族文化壟斷,從而具有大眾化和流通性。獨特的宗教背景與文化背景對歌德創作《浮士德》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有明確的語言說明魔鬼靡非斯特正是源於《聖經》中撒旦:
《浮士德》第一部《女巫的丹房》一節中
女巫????? (手舞足蹈)我簡直昏頭昏腦,在這裡又見到撒旦公
子真想不到!
靡非斯特?? 婆子,不準叫我這個名字!
女巫?????? 為什麽?它怎麽了你?
靡非斯特?? 它早已進了稗官野史;可人們並沒有好過起來:他
們擺脫了一個惡,更多的惡依然存在。…… [12]
女巫的一席話點出了魔鬼靡非斯特正是《聖經》中的撒旦,他的所作所為與撒旦的行徑並無二致。
又如《浮士德》第一部《天堂序曲》一節中:
靡非斯特? 好吧!是非分明不會拖得很久。我毫不為我的賭賽發
愁。如果我達到目的,就請您允許我鼓起胸膛把凱歌高奏。讓他
一輩子去啃塵土,而且甘心情願,象那條大名鼎鼎的蛇,我的同
族。[13]
由此可見,教唆人犯罪的蟒蛇成為魔鬼,正突出了魔鬼的一大特性——誘惑,正是由於蟒蛇的誘惑才是一切罪惡的淵源。而靡非斯特為了贏得與上帝的賭局,使浮士德說出滿足之意,它採取各種手段,而這諸種手段的核心本質就是誘惑。蛇成為魔鬼的化身,因為它身上也兼具有魔鬼的第二大特性——淫慾。女人經不起蟒蛇的誘惑,因此遭到上帝的懲罰,蛇成為女性邪惡情慾的象徵也是從這裡衍生的。在《浮士德》中,魔鬼靡非斯特誘惑浮士德愛上少女瑪甘淚,正是想通過淫慾的手段使其墮落,最終獲得滿足。由此可見,靡非斯特正是蛇的演化與再生。
魔鬼靡菲斯特源於《聖經》中的撒旦,即“蛇”這個意象,撤旦的意向旨意成了誘惑、欺騙和背叛,成了一種邪惡的象徵符號。由於這個意象凝聚了人類從遠古以來長期積澱的巨大的心理能量,具有人類感覺和聯想的共通性,使之具有了一種跨文化的語義普遍性,得以成為世界性的文學原型,在以後的文學中不斷出現,繁衍出一個龐大的惡魔家族,使世界文學形象畫廊異彩獨放。
(二)“蛇”成為“惡”的代言人
作為魔鬼靡非斯特的原型——蛇與其有許多共通之處。夏娃、亞當經不起蛇的誘惑而偷吃禁果,違背上帝的旨意,犯下了原罪。蛇攪亂了幻想世界的和諧與寧靜,破壞了理想生活中的夢境,打破了“樂園”中均衡的美。蛇成為這一切後果的始作俑者,是一切罪惡產生的淵源,因此也成為“惡”的代言人。而當蛇蛻化成撒旦和魔鬼時也是“惡形”累累:它企圖引誘義人約伯和救世主耶穌反抗上帝,對他們進行各種各樣的考驗和折磨。施洗者約翰曾多次將那些刁難和仇視耶穌的法利塞人和撒都該人稱為“毒蛇的種類”。因此,在文學史上,蛇便演化為一種邪惡的象徵符號。
(三)“蛇”體現“造善”功能
靡非斯特在作惡的同時又兼具造善功能,蛇亦是如此。蛇作為藝術的原型和母題,它並非完全是醜的而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是一朵色彩繁雜的惡之花。在《聖經》中,它引誘人類的始祖違背了上帝的禁令,導致了惡的誕生。然而這是人類歷史長河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它使人類邁開了進化的第一步,使他們從沉睡中睜開了惺忪的眼睛。在這裡“惡”也成為一個辯證的概念。從一般意義說,“惡”是作為“善”的對立面存在的,壞事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變為好事,即“惡”也可為“善”發展的條件。因此,黑格爾並不把“惡”看作絕對的壞事。在“蛇”這一母題意象所概括的“惡”的涵義中包含了肯定和發展的精神,它作為“惡”同“善”構成了一對矛盾,從而成為自然和社會發展的根源。
魔鬼靡非斯特承擔浮士德內心矛盾中否定精神的特質,作為魔鬼,它的本質卻體現了人類社會和人自身的另一方面,這正是“存在之真”。當涉及到人的心靈深處時,外在的魔鬼便常常內化為心中的不良念頭。在追求古典美的過程中,浮士德與海倫結合併生下歐福良,但當這一切最終都幻化成為虛影時,浮士德也隨之崩潰。然而在追求古典美的過程中雖然有靡非斯特的幫助,但浮士德卻是因為初見海倫時為其傾倒而下定決心尋找她的。可見,正是由於浮士德內心的焦灼,靡非斯特才得以實施他的詭計,從而進一步誘惑他。同樣,蛇也具有相同的價值內涵。蛇對始祖夏娃的耳語正是寫在太陽神阿波羅神殿的大門上的箴言:“了解你自己”。蛇成為推動人類不斷地克服人自身內外在矛盾的直接動力,在否定之否定中揚棄人性中的弱點與局限,不斷地走向人性的美好至善。恩格斯曾說:“凡是現存的,都是應當滅亡的”,在本質上說明了伊甸園般的樂土生活並不能永恆存在,蛇所代表的“否定”與“惡”恰好與人內心的焦灼情緒吻合,從而成為其走向文明進步的源泉和動力。人類要有所進步,就要有所行動,有所變化,有所努力,有所鬥爭,而蛇正是充當了人類內心矛盾中否定精神的物質,成為人類向文明進化的“使者”。
《聖經》中的原型“蛇”在《浮士德》中置換變形成為魔鬼靡非斯特,二者在象徵“邪惡”,作“惡”同時兼具造“善”功能以及代表主人公內心矛盾的否定特質等方面具有共通的特性。《聖經》對西方近代和現代文藝作家的影響是一言難盡的,在第一流作家的代表作中往往交織著希臘神話和聖經的故事、名句、原型等。歌德是大作家中最反對宗教迷信的,卻在塑造魔鬼靡非斯特時“借用”了源於《聖經》中的“蛇”這一原型。但歌德的“借用”並不是一味的沿襲蠻幹卻是充滿智慧與時代氣息的。因此,在歌德的妙筆下,魔鬼靡非斯特對於《聖經》中“蛇”這一原型是有所發展與超越的。
四、魔鬼靡非斯特的發展與超越
浮士德是德國16世紀民間傳說中的一個人物。據說他用自己的血和魔鬼訂約,出賣靈魂給魔鬼,以換取世間的權力、知識和享受。歌德童年時候就通過傀儡戲接觸到浮士德的故事。1587年施皮斯在萊茵河畔法蘭克福出版《約翰·浮士德博士的生平》。1599年,維德曼在漢堡出版浮士德的故事書。1674年,普非策爾將這本書加以改編。歌德在寫“天上序幕”時,曾在魏瑪圖書館借閱過。英國劇作家馬洛以德國民間故事為藍本於1588年寫出《浮士德博士的悲劇故事》。
這是零散的民間傳說第一次以正統文學的形式——戲劇表現出來,這無疑是飛躍。馬洛使主角浮士德的形象更加豐滿有致,情節設定曲折動人,人物對話形象逼真。在中世紀宗教統治的背景下,馬洛站在宗教立場上反對浮士德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浮士德言行反映出文藝復興時期知識分子熱衷探索宇宙奧秘、追求知識的冒險精神,引起人們廣泛的興趣,馬洛從這個角度進行創作加工,將人文精神貫穿的更加徹底,為浮士德母題做了一次整理和提升,也為歌德的進一步完善該主題提供了範本。馬洛的劇作講述了浮士德把靈魂賣給魔鬼,魔鬼供他驅使二十四年,到期他的靈魂被魔鬼劫往地獄的故事。魔鬼在這裡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位“敵對者”,他為嘗試“終極知識”的浮士德提供“魔法”,最終使浮士德成為傷害他人的“魔鬼”並受到最終的懲罰。而這正是《聖經》中撒旦形象的變形和置換。
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劇》是個新舊結合的產物,形式上仍可以看出道德劇的印痕,其中一些人物是擬人化的善惡的代表,魔鬼靡非斯特亦是如此。魔鬼靡非斯特只是單純的代表“惡”的簡單符號並沒有可挖掘的深層內涵。而在該劇中馬洛揭開了宗教的薄薄的外衣,講述一顆靈魂的悲劇,所有的情節都以浮士德為中心展開,而魔鬼靡非斯特只是推動情節得以順利展開的一顆“棋子”。
德國狂飆運動的一位知名的作家克林威爾,於1791 年寫有“浮士德的生平、事業及下地獄”的長篇小說。書中的浮士德同魔鬼訂約,是為了藉助超人的魔力以控制或剷除世界上不公平的現象。
與之前魔鬼靡非斯特不同,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兩位主要人物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靡非斯特的基本職能不變,但他參與全部事件的進程,他非但不愚蠢,而且充滿哲學家的氣質,深刻而睿智,完全有能力和浮士德針風作對。靡非斯特仍然是誘惑者,但歌德賦予他的含義已經遠遠超出了基督教文化的容器。
歌德是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德國最偉大的詩人和作家,而《浮士德》的創作時間持續60年之久,貫穿於歌德的全部寫作生活。在這60年間,世界上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性巨變,這對於魔鬼靡非斯特的形象塑造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浮士德》中靡非斯特並不是一個“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他更樂於付諸實踐。又如它對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奚落嘲笑,成為創造力的對立面。這樣的靡非斯特不僅僅限於宗教領域,更樂於活躍在人道領域與自然科學領域。在相對於《聖經》中的原型“蛇”,靡非斯特跳動在一個更為廣泛的舞台形象中,因而他也更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歌德將近代歐洲時代精神注入新的魔鬼形象中,使其迸發出更強烈的時代脈搏。
此外,歌德在對魔鬼形象的再塑造中,集中地表現了資產階級原始積累時期個人主義冒險家的罪惡本性。他將浮士德對少女瑪甘淚的愛戀演化為赤裸裸的性愛;他發行紙幣,使金錢成為政治生活的重心;他用最殘忍的方式燒死了木屋裡的老人,表現出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欲望。諸如此類反映出歐洲新興資產階級人生追求的歷史內容。此外在詩劇第二部第五幕中魔鬼靡非斯特利用戰爭、海盜和貿易三位一體的方法,也就是早期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方法發展致富。歌德揭露著資本主義罪惡的同時,也宣告了靡非斯特雖然無德無道,但沒有喪失其存在權力而帶有歷史必然性。靡非斯特雖然圍繞著一個單項惡質而展開,但其深刻的社會和心理內涵卻使惡帶有兩重性,令人回味無窮。
從作者歌德的文藝思想和世界觀角度看,魔鬼靡非斯特成為其代言人及對現實的揭露者。歌德在歐洲啟蒙運動的薰染下開始創作《浮士德》,而啟蒙運動的首要問題是人道主義,因此人道主義成為歌德創作思想的重要的一環。浮士德作為啟蒙時期,即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思想代表人物,必然是反封建、反教會的。但作者往往通過代表“惡”的魔鬼靡非斯特之口揭露教會的貪得無厭,愚弄人民,諷刺教士詐欺財物的醜態。
“母親請來一位教士,
教士還沒有把話聽畢,
一見寶物便滿心歡喜。
他說:這種想法真是不錯!
誰能克制,才能收穫,
教堂的胃口很強,
雖然吃遍了十方,
從不曾因過量而患食傷;
信女們功德無量,
能消化不義之才的只有教堂。”[14]
作者痛恨教會貪得無厭,借靡非斯特的口更能將這一人道思想強有力的表現出來。正是因為魔鬼靡非斯特目光敏銳,世故極深,對現實的觀察頗能擊中要害,說話做事毫無顧忌,一眼能看穿別人的心思,所以沒有了“惡”,也就沒有了人間地獄,救贖也就失去了意義。魔鬼靡非斯特對於醜惡黑暗現實的揭露是直白與露骨的,然而卻可以使人們從另一個側面認清現實的實質從而覺醒悔悟。
靡非斯特是歌德在新的兩面神思維方式和審美原則指導下寫成的藝術形象。歌德深受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的影響,康德的“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等二律背反的論點,以及康德對於人的內心宇宙全部複雜性的探索強烈地吸引歌德。而歌德本人就是一個性格豐富到了難以捉摸程度的天才。他“既感情豐富又十分理智,既瘋狂又智慧超群,既兇惡陰險又幼稚天真,既過於自信又逆來順受”。他在設計浮士德和靡非斯特兩個對立形象時,則體現了康德的二律背反,以及人的主體性的辯證法。
而莫姆森在靡非斯特是否惡魔的問題上的解釋中,特別說明靡非斯特具有積極的創造力量。她認為在《海倫》那幕中,靡非斯特不光是作為搭檔的夥伴出現,而且通過劇中對魔法的敘述,他自己在這裡好象成了詩人。他本著事態進程者的資格,才創造性的使事件得以發生。這種能力是基於他洞察詩歌的本質,這在《古典瓦卜吉司之夜》和《海倫》那幕中充分表現出來了。靡非斯特已經超越了《聖經》中“蛇”這一原型已初步具有了人化與詩化特質。
歌德用18、19世紀的時代精神,激活古老的原型,圍繞詩劇的主題對原型進行了創造性的置換和變形,賦予原型以嶄新的意義,實現了古老原型的價值意義的近代轉換,使其所塑造的魔鬼靡非斯特帶有鮮明的時代氣息。
五、結語
《浮士德》是偉大詩人歌德傾其一生的心血寫成的詩體悲劇,其藝術構思宏偉,結構龐大。而在《聖經》原型“蛇”的基礎上塑造出的魔鬼靡非斯特形象更是耐人尋味。靡非斯特擁有原型“蛇”的一切特質並在此基礎上更兼具鮮明的時代特徵,使其成為歷史長河中經久不衰的文學形象。
注釋:
[1][2][3][5] [6][7] 歌德:《歌德文集》,綠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4][8] 董問樵:《〈浮士德〉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83頁,第179頁。
[9] [10][11]《舊約·創世紀》第3章,《馬太福音》第12章第34節,第12章第33節。
《聖經》,《新約全書-啟示錄》第12章,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第445頁。
?[12] [13] [14] [15] 歌德:《歌德文集》,綠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頁,第10-11頁,第85頁。
《浮士德》靡非斯特情節縮寫:
在廣闊的天庭,上帝正在召見群臣,仙官侍立左右。三仙長出位,以宇宙的浩瀚,變化的無窮景象,頌揚上帝造化萬物的豐功偉績。 惡魔靡非斯特和往常一樣來到這裡,口中無一句稱頌的話,反而大發一通議論,說什麼世界是一片苦海,而且永遠不會變;人只能終身受苦,像蟲魚一樣,任何追求都不可能有什麼成就。

參考文獻:
[1]歌德:《歌德文集》,綠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
[2]歌德:《世界文學名著寶庫—浮士德》,張文竹、葛子健改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董問樵:《〈浮士德〉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4]《聖經》,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
[5] 何其莘:《英國戲劇選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6] 劉欣、吳守鳳:《在天界和地界的惡魔—靡非斯特和伏脫冷之比較》,《泰安師專學報》。2001年7月第23卷第4期。
[7]孫斌、宗成河:《虛無與創造—從〈舊約〉看〈浮士德〉》,《浙江學刊》,1999年第5期。
[8]劉欣:《世析〈浮士德〉潛藏的〈聖經〉原型》,《泰安師專學報》,2000年1月第22卷第1期,。
[9]朱文利:《浮士德:人類精神的隱喻》,《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6卷第10期。
[10]林丹華:《〈浮士德〉與〈聖經〉》,《福建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10期。
[11]趙萍:《從靡非斯特看〈浮士德〉的辨證思想》,《無錫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9月第4卷第3期。
[12]王淑君:《〈浮士德〉的人物原型》,《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13] 宋德偉、方傑《向極限挑戰的悲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復仇悲劇及其動因》,《鄭州大學學報》。1999年7月第32卷第4期。
[14]陳雪蓮:《浮士德:幻想的綻放與壓制》,《合肥工業大學學報》。2006年6月第20卷第3期。
[15] 葉舒憲:《〈浮士德〉的辯證思想——文學與思想史研究片論》,《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16]朱維之:《聖經文學的地位和特質》,《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4期。
[17] 劉秀玉:《評馬洛與〈浮士德博士的悲劇〉》,《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3月第23卷第3期。[18]鄧亞雄:《西方文學中的神話傳統與〈浮士德博士的悲劇〉》,《重慶交通學院學報》。2006年9月第6卷第3期。
[19]林燕:《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對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影響》,《山西師大學報》。2003年1月第30卷第1期。
[20]郭明:《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意義》,《安陽工學院學報》。2005年5月第2期。
[21]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9月第1版。
[22]歌德:《浮士德》董問樵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