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曹利民的“蘭香”與“山泉”
曹利民作品的最大特點是溫婉和美,讀之有縷縷蘭花香——這源自利民對於傳統文字的承接與把握——她的文字有一種可貴的真誠品質與自由情愫,從生活的細節和體驗出發,讓我們閱讀之後感到某種摯愛和關懷。
曹利民的寫作,無論是散文隨筆還是詩篇,都是基於個人真實情感經驗和內心情愫的溫婉述說,始終能給人以積極、慰貼、純淨的閱讀感受。
曹利民的作品不是大氣磅礴的那種,而是一曲令人流連忘返的山泉,一路清澈,一路花香,哪怕就你一個人行走也不會覺得孤單,依然感覺自己在人世的繁華里真實可靠。
作者簡介
曹利民。江蘇女作家。江蘇省江都市人,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九十年代起寫作散文、詩歌,在縣(市)級以上報刊發表詩文作品多篇,已出版詩文集《那些繽紛的聲音》(江蘇文藝出版社),作品散見於《揚子江詩刊》、《星河詩叢》、《上海詩報》、《文藝家》、《揚州詩歌》等報刊,有作品入選《中國微型文學1000篇》,希望能以一顆純粹的心,耕耘出一片純淨的精神家園。現在江都市某政府部門供職。
 江蘇作家曹利民
江蘇作家曹利民內容簡介
《那些繽紛的聲音》是江蘇女作家曹利民的第一部作品集。
曹利民生長於江都。江都古稱龍川,利民的網名就取名龍川曲日、小橋流水,都與水有關,讀利民的文字,感覺身邊儘是暗香疏影和水靈靈的氣息。她的文字樸素、透徹,呈現出生活的質感。
《那些繽紛的聲音》,可以看作是曹利民的一種心靈記錄,一種對生命歷程片段式的展現與描摹。她的文字並不很多,但幾乎每一篇都來自她的生命經驗和內心情感。她以詩人敏銳的感受力,揭示和發現了被熟識所遮蔽的日常生活,情感內斂而強烈,她把個人體驗與大眾經驗在充滿情感的書寫中得到很好的融合,從而讓我們在人世的風雨長夜或與晴暖短日,都能感受到人性的溫暖與撫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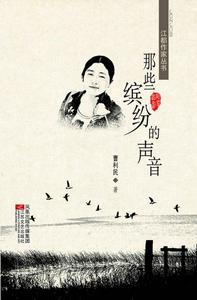 曹利民作品封面
曹利民作品封面作品目錄
第一輯:那時花開春天花會開
再見青松
草一樣的花
無助的草花
蝴蝶花開
心靈的花園
看荷
有一種樹
秋風中的合歡花
夢裡除夕
無名花
小鳥的童話
那些繽紛的聲音
銘記那一刻
帶著夢想一起飛
水色黃昏
行程的目的
一道小學生作業題
兩種場面
當甲流成為騙局
工作難度
鉛筆友誼
誰是陳浩南
紅燈
慢步
損耗
依賴
若不是秋雨
誰能封喉
對手
友誼三章
關於愛情
孩子,請你不要“吹燈”
同類的天空,另類的天堂
感受寂寞
請你亮起那張像
身體語言悄悄說
古運河岸邊的遐想
貼近邵伯湖
錦繡龍川
飛回夏天
越過千年
傾聽天涯
紅藝人與變性人
雨游呀諾達
十月的雨,六月的天
從懷疑開始
被遺忘的一首詩
周圍的一切在走動
心景相宜
水流的恣意,花開的落寞
搭著地氣生長的植株
一葉不系之舟
滑進瞳孔的陰影
走在你身邊
晨歸
懸在白髮上的愛情
生日
我是秧草的孩子
一次又一次
姑姑,你好
杯中的老爸
桂花香落
野菊花在綻放
桂子
植物在開放
我不是一條魚
陽光傷痕
幻想的茉莉花
梅雨時節
初夏
陷於六月
一個人的長途
追隨一首詩
你一定落下了什麼
冬天的形容詞
銅符
如果可以
醉夜
心事
回鄉
秋雨鑰匙
你掌心的雪花
我想看荷花
做一朵荷花多不容易
悼念
瞬間的天堂
我看的月亮
拎著沮喪的自己
在一棵青豆前駐足
馬路
托起一隻飛鳥
一首詩
一棵樹,一隻鳥
你說的小巷
第三個我
最後的石榴
在你伸手的剎那
第一場寒流
鐵柵欄
作品選讀
五百八十米的巍峨作者:曹利民
人與風景的緣份,就像人與人之間的相遇,有命中注定,有機緣巧合,有擦肩而過, 也有一別之後永無相見。在齊雲山,如霞如霧亦真亦幻的山水,與古往今來紛至沓來的人流之間,存在著種種可能的緣份。
齊雲山的山峰海拔在580米左右,但山奇、石怪、水秀、洞絕,引來奇人異士駐足,是偶然之必然。比如,道士龔棲霞,遊走到此心有所觸,於是辟穀修煉,羽化飛升,引來眾多道士進山清修,齊雲山名氣漸大,成為“天下無雙勝境,江南第一名山”。
加上道教的衣冠後,齊雲山與帝王將相、高官巨賈、文人雅士的相遇,有偶然,也有必然,有心嚮往之,也有興致突發靈感所至。比如徐霞客,比如乾隆,比如唐伯虎,比如朱煮,比如郁達夫等。而作為徽州第一大姓的汪氏族人,與皖南名山的相遇,無論怎么算,都是必然,是命中注定。
第一位是徽州汪姓的老祖宗汪華。在隋唐交替時,他保護了當地百姓,也被百姓們把塑像供奉在龔棲霞的身畔不遠處,他的子孫在徽州繁珩生息,遍布古徽州一府六邑。第二位是汪華的後人汪宏,一天早朝,嘉靖皇帝突發奇想要找風水寶地求子,身兼組織部長兼國防部長的汪宏,不失時機地推薦了齊雲山。於是,皇帝封汪宏為天官,代為上山許願。嘉靖得子後,齊雲山受到了禮遇,興建了玄天太素官,香火更加鼎盛了。汪宏本身以文入仕,身居要職,並給齊雲山帶來了皇恩帝澤,他的部分族人也得以入住齊雲山,守衛著天官府,他的名字注定是要被刻齊雲山上。
人生如同道家名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存在著諸多可能,不是所有的汪姓人都能像汪宏這樣占盡天機人緣。多數汪姓人,要么科舉入仕,要么經營起家,要么明哲入道,實在不行,只能安守薄田安穩度日。也有一種人,連普通平常的安穩生活也過不下去,比如汪士慎。
汪士慎是揚州八怪之第一怪,也是徽州汪姓人的另類。他是安徽休寧富溪人,從史料上看,他三十七歲來揚州,七十四歲在揚州去世,休寧與揚州分占他生命的兩半,他詩、書、畫、刻俱精,卻對家鄉歲月絕口不提,在畫作中也從不落款休寧。這就使得汪士慎的過去,變得撲朔迷離。我不是揚州八怪的痴迷者,對汪士慎知之不多,但在齊雲山,我一次次地聯想到他,感悟到他的年青歲月。
“文人入仕”是我在皖南之行中聽到的頻率最高的詞,是古代讀書人的夢,更是重禮重教的徽州人的最高理想。據說古代的休寧人家,生下了男孩都會栽一棵櫸樹,希望孩子將來金榜題名,光宗耀祖。在齊雲山的夢真橋上,導遊介紹,休寧所有讀書人未中舉之前都來祭拜文昌公,好多人夢想成真,這個縣出了十九位狀元,是狀元之縣。這樣的環境下,作為讀書人的汪士慎,雖有多才多藝的天性,卻沒有金榜題名過。古徽州人的眼光,多數投向那些少年得志衣錦還鄉者,或是自十二三歲就出外經商而成為大賈,進而修橋築路為鄉鄰造福的胡貫三們身上,而汪士慎這樣仕途不取、商路也不通的人,誰會放在眼裡呢?
祭拜過文昌公的汪士慎,沒有中舉,也沒有棄文經商,在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壓力下,他走出了齊雲山,選擇了繁華之地揚州城,希望以書畫之長讓家人過上好日子。但命運並沒有眷顧這位徽州才子,他投奔的馬氏兄弟,雖是商界成功人士,卻不懂得今人炒作之道,只能以同鄉之情,給他提供棲身之地和衣食補貼之類,沒能將他推向大眾視線。他賣畫多年,才靠微薄積蓄購置了一處民房,直至左眼失明,直至右眼失明,直至在默默無聞中去世,也沒有回歸故鄉。
悲苦一生的汪士慎,直到生命的最終,都自感庸常,羞於自稱休寧人。遍布齊雲山的摩崖碑刻中,我看不到汪士慎的遺蹟,只看到三三兩兩的畫院學生和畫家們在寫生,不知道他們是否學習過汪士慎?當年的汪士慎,崇尚師法自然,不肯臨摹他人,在好長一段時間內打不開市場,也正為如此,他的作品具備了臨摹者們所沒有的生命力。活著時,他謙卑,他渺茫,甚至沒有勇氣像唐伯虎那樣在齊雲山題字作詩。而他離世後,在休寧狀元們煙消雲散之後,他卻作為文化大師,為後人永遠敬仰。這是命運的公正,也是人生的玄妙。
接待我們的導游姓汪,土生土長的汪氏後裔,說起汪華與汪宏,如數家珍。說起汪士慎,他也滿臉自豪,汪士慎也是休寧的驕傲,是徽州人的驕傲,是齊雲山的驕傲。一路上,汪導遊細細解說每一處景物的典故與由來,熱情倍至,讓我們深感前所未有的禮遇,因為我們來自揚州,因為揚州與徽州,因為徽商與鹽商,也因為汪士慎。
告別齊雲山時,風雲突變,天空響起轟隆隆的雷聲。下山的索道被關閉,認真嚴謹的工作人員,關照我們要耐心等候。齊雲山有意挽留我們多停片刻,多感受一些它的風光與滄桑。
雨過去,坐上索道看天地,似乎自己正貼著漫山遍野的綠樹青草,凌空而飛。掠過視野的一簇簇映山紅和紫藤,燦爛,自然,直抵心扉。曲曲折折的橫江,清晰地呈現出太杉圖中的陰陽分割線,真實,玄妙,讓人驚奇,也讓人感嘆。
我慶幸自己走進了齊雲山,感受到另一種巍峨,一種五百八十米的巍峨。
作者:曹利民
有些東西是沒有緣由的,比如自然界的天敵,又比如我性格里的植物天性,內向,安穩,每到一處都巴望紮下根來不再挪窩。也因此,對花草樹木多了些偏愛,不論春夏秋冬,不論晴陰雨雪,有空就喜歡看窗外或路邊的靜默身影。特別是陽春三月,草長花開,好風景能讓我忘卻許多繁擾。
這種無欲無求的喜好,竟也煩惱不盡。那年清明前夕,在借用的單位準備資料的空隙,開窗欣賞春花,感覺眼瞼發氧,抓了撓了也不解事,同事說,大概使用電腦過度。所以揣了瓶眼藥水,跟他們去小紀檢查,一路上,陽光燦爛,桃紅李白,而我的雙眼火燒似的難受,人像霜打過的秋葉提不起精神。捱過兩天,眼睛好了,呼吸不暢了,先打噴嚏,後咳嗽,再後來是哮喘,不得不去了醫院,吃藥吊水地折騰了十多天。
第二年開春,我因為不能解決工作性質問題離開借用單位,應聘到《江都日報》,成天學寫新聞稿件,採訪不同層次的人物,深入社會表象分析成因背景等等,身心卻是前所未有的健康。然而,好景不長,我的記者生涯漸有起色時,縣級黨報分流,我再次換了單位。
又到了春天,為編寫工作簡報,跟新領導到幾個大鎮檢查。沿途感受著風光明媚,桃李爭艷,卻渾然不知,危機正向我襲來。老毛病又犯了,先眼瞼、後鼻子、再後是氣管,症狀、順序都跟以前一模一樣。拖到最後又到了醫院,說是感冒引起支氣管發炎。我姨媽有氣管炎,每到開春就咳喘不停,嗓子裡堵著咳不完的老痰,時不時的隨地就吐。我還沒老,怎么也染上這令人討厭的毛病呢?日夜咳喘之際,感覺自己一下子跨過好多歲月,直接活到了姨媽的狀態,蒼老、孤獨、無助。
連掛三天水,咳喘並不見好轉。換過醫生,說藥輕了,換了“左克”。一周過去,醫生納悶,別人兩瓶下去就見效,就算氣管炎也抑制住了,怎么到你就失效了呢?
醫生這么沒底氣,我心裡更是一團暗黑。醫保卡上的餘額早已用光,搭進了一個多月工資,還沒弄清病因,莫非是不治之症纏身了吧?多年來,事與願違,一而再、再而三的變換工作,總是剛剛生根發芽,就要連根拔起挪移到另一處,不停地傷筋動骨,再怎么努力也長不出枝繁葉茂的姿態,反倒像只行走在生活邊緣的弱小動物。那陣子,孩子剛上一年級,為了在新單位立足,每天拖著有氣無力的身體完成本職工作,還要幫新同事完成任務,要去醫院輸液,加上不明病因,心中倍感淒涼。我還沒活到中年,人生也還沒有安定,為何命運這么捉弄我呢?
我聳拉著腦袋去輸液,路過小區醫務室,小張醫生跟我打招呼,上哪去啊?他跟我婆婆熟悉,婆婆有什麼頭痛腦熱的,愛往他這兒跑。我從沒把他當回事,這么間小門臉,每天接觸的就是大媽大嬸們,水平能高到哪裡?既然人家問了,不回有些不禮貌。於是停步,告訴他我得了氣管炎。說著話,連打了幾個噴嚏。
小張吃驚地問,你一直這樣嗎?我說三年前這個時候得過。小張嚴肅地說,你的病不在氣管在鼻子,可能是季節性過敏鼻炎。
不會吧?我沒有任何過敏史,從小到大用青毒素,從沒有過有異常。小張說,跟那個兩碼事,我沒有工具,你去市人醫五官科檢查一下就能確診。
我半信半疑,把自己當成一匹死馬,求診五官科。檢查後,醫生跟小張的說法一致,清明時季花兒綻放,最有可能是花粉過敏。重配了藥物,用藥後竟是渾身清爽,我這棵枯枝爛葉的植物似乎正在返青、發芽。我陰霾許久的心空,豁然開朗之餘不禁嘆息,再高級的醫生,再高檔的藥物,不查清病源,不對症下藥,怎么能治得了病呢?
回頭告訴小張。他笑笑,只要一盒消炎藥加一盒抗過敏藥,二三十塊錢可解決問題,如果找到了過敏源,這些也可以免了。
受了小張啟發,我到小區花園找罪魁禍首。按小張的說法,那種花應該比較普遍,我原先的借用單位有,兩次赴鎮檢查的路途中有,現在的生活圈也應該有。春風蕩漾,花香陣陣,我的鼻子卻不堪承受,又打起了噴嚏。於絢麗燦爛的迎春花、紅葉李、杏花、櫻花、茶花、梨花叢中,我看到了桃花。這些紅艷艷、嬌柔柔的桃花,這幾年被大批種植推廣,成為城市風景里明艷奪目的粉紅佳人,就是我苦思不得其解的隱藏敵人啊!我求醫問藥這么多天,我迷迷糊糊問東問西,卻不知道解密的鑰匙就是自身!
說起這些,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同事說,這哪是命犯桃花啊,科班出生的醫生怎么這么差勁,這么多人查不出個小病?朋友們開玩笑,若交了桃花運還可能避免,桃花病要怎么才能治好?總不能讓桃花不開吧。
父母也詫異。桃木可以避邪,小孩子身佩桃木可以抵擋穢氣。家門口就栽著兩棵桃樹,左鄰右居們的家前屋後幾乎都有,我從未犯過什麼過敏症。怎么進城生活了多年,避邪物反倒成了邪物了呢?
我當然不能放下案頭成堆的工作,去找醫院理論,我也回不到童年的故鄉,更不能讓桃花不開。我生活的城市,市區面積越擴越大,景觀綠化越來越美,小區、河堤、路欄,隨處可見桃花、桃葉、桃枝。它們關係著我的視線、呼吸、心情,我不能愛,也不能恨。它們與我息息相關,上班下班、出差開會、旅遊散心,桃花會、桃花節、桃花詩,比比皆是。它們不屬於我,它們屬於大眾,桃之夭夭,桃李芬芳,桃花流水三千尺,桃花依舊笑春風,欲將人淚比桃花,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
沒有桃花的春天不是完整的春天。我不能為自己的感受,抱怨桃花的美麗,或是春天的完整。我能做的,是用口罩眼鏡把自己捂緊、再捂緊,或者乾脆不出門。每遇聚會,說起桃花病犯了,請師友們理解,讓自己窩在家裡,隔窗看風景。
有趣的是,這種撕不爛又甩不掉的桃花劫,也有人羨慕。詩人莊曉明說,別人生病大了不說,就算小病免不了發燒疼痛,你生這種病多幸福啊,看看燦爛的桃花,心懷小小的鬱悶,再寫寫小詩,很詩意呢。
事實上,春光越爛漫,我就越狼狽。昨日回鄉,我又捂緊了自己,像傷兵敗將一樣貓在車裡。道路兩邊,那些鮮艷的明媚的春天的寵兒,在別人眼裡是桃花,在我而言,是試圖擾亂視線與呼吸的烈焰和風暴。
後來,跟老媽說過一通話後,老媽驚喜地叫了起來,你的桃花病好啦?她青筋突兀的手,帶點顫動地伸了過來,撫過我的臉,掂起落在髮際的一朵桃花。我們站在桃樹下,桃花綻滿了枝頭。從我這邊看過去,桃花的粉白,與老媽頭髮的花白,對起來很是醒目。老家的桃花,還是那么純樸,還是那么自然,像親人一樣與我為善。
老媽不知道,並非所有的桃花都讓我反應強烈,我所敏感的,是城鎮風景線上那種嫁接改良後的觀賞型桃花。而老家的桃花,或許因地質,或許因水流,也或許因四周的青草與野花,具備了某種天然的抗過敏元素,就像土生土生的鄉親一樣,讓我可以卸下所有的偽裝與防備。
我不能說很多。我怕告訴她緣由了,她又要挽留我在家住一陣子,我工作生活安排滿滿,不得不回絕,她陡然明亮又陡然黯淡的眼神,將她希望變失望的心境一覽無餘。我也怕真住下來了,又像以前一樣不想動身,直到她催著上路……
或許,我跟桃花同類,我也是一棵植物,一棵生在故鄉,不服城市水土的植物。
詩歌欣賞
作者:曹利民
逆流的浪花離水越近,我越能感受光芒
在於江心的那些字句,高過了
潮頭上的尖叫
它們年輕、氣盛,一路叛逆
像飛禽,像走獸,像天使與魔鬼,大起大落
湧現出千萬種可能
它們沒有像我這樣散落在人群
沒有人到中年,沒有歷經世情西下、前途落山
成為一粒被時光濾乾的細砂
比如現在,我只想再次讀一條江
興奮、驚嘆、濕潤
回到年輕歲月
此前,我居住在蘇北小城
此前,我性別為女,年齡未知,屬相空白
此前,我網名叫小橋流水
此前,我像別人一樣,上北下南,左西右東
此前,我看到江水從高到低
像眾多遊客遠道而來,彬彬有禮
而潮水,不用謹慎 矜持 精心修飾
素麵朝天地來了
每一滴心思都情緒化
每一次尖叫,都類似於一種表達
我的同伴們擠來擠去,擠掉了表面謙和
沒有人發現,我臉上的那一滴
已經歸位
它翻騰過,破碎過,也沒能學會成熟
也還是樸素的旅程者
為了短暫體驗,就從壯闊奔向了狹隘
就像我剛剛回顧的一千里旅程
起於靈感,滅於傷感
在錢塘江,我清楚看到了自己
我一波一波地逆著人流,一群一群地守著潮水
偶然想起,我的未來與現實
全部湧向了過去
我並不想寫流水,寫小橋。江南
到了我筆下,遠不如在別人夢裡美好
我也不想退思園。退,思,任蘭生東山再起
不過是掛在嘴邊的幾句話
不想珍珠塔,小姐,書生,金榜題名
穿上二十一世紀的戲服,像影視劇一樣喜慶
我不想的還有,白天 黑頭髮 藍眼睛
海內外一撥一撥的人流
還有昨晚,醉倒在三橋邊的一群揚州柳葉
它們東拉西扯,還把張若虛當成了一碟下酒菜
也沒能醉成一棵老香樟
清麗少女是江南,婉約少婦也是江南
白頭髮的阿婆,放下竹籃,問我從哪裡來
也是江南。現在,鳥鳴把晨曦從綠枝里銜出
水影映著吳儂軟語,老屋,舊檐,東溪街,施家弄
明洪武、明宏治、清道光,洗衣,炊煙
青石板輕輕讀著一雙異鄉布鞋
輕得沒有聲音
臨近大門時,手中的鑰匙
讓我感覺生疏
它似是而非的樣子,像一扇門
倒在我手心
它單薄、老舊、昏昏沉沉
我難以進入。住在裡面的十年時光
似乎也不夠掂量
搬家後的三個月,我每天拿捏著新鑰匙
開門,或關門。反覆辯認
試圖把日子過得嚴實
它只在一旁晃蕩
這一次,它用鎖孔提示我:
舊衣櫥的幾件舊衣服有多么珍貴
漏洞百出的
是我時時幻想更新的生活
請不要談傳統,談楚辭
談屈原,汩羅江現在是我面前的一個名詞
裝不下二千多年的憾恨
也不要用雄黃灑、白娘子
痴情書生的故事早已長滿青苔
丟進了記憶角落
也不要棕子、艾草、布老虎、鴨蛋兜
這個日子,在檯曆上
與其它吃飯穿衣上班下班的日子
一樣淡薄
只因,在夜深人靜面對它時
有憂傷散開,故鄉與童年匆匆遠去
有感動湧起,母親在油燈下替我繫上紅繩
讓我至今滿懷溫馨
(以上五首詩,發表在《揚子江》詩刊2011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