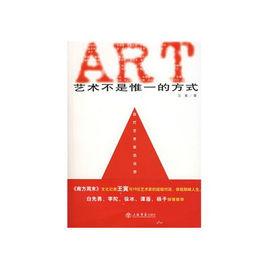圖書信息
圖書編號:2340652
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5-01
版次: 1
開本:16開
簡介
這本書完全有資格成為那些剛出道的文化記者的教科書。它將教會他們如何提問,如何從一大堆雜亂的印象中提煉出最傳神的細節嵌在報導裡邊,如何將一個高深的、現代或者後現代的學者或藝術家的思想和觀念神采飛揚地、通俗易懂地傳遞給普通讀者,而且,我相信,它也會讓那些書齋里的“ 專家型”讀者感到大快朵頤.發出類似於“深得我心“的感嘆。
王寅奠定他在詩歌界的江湖地位.差不多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現在他是《南方周末》的資深記者,採訪過一大堆中外藝術界的頂級人物,此前他是上海電視台的編導,參與製作過多集紀錄片《長征》和有關老上海的專題片。
王寅剛到《南方周末》,便以一篇霍金觀察記令大家震驚。在一次別說專訪,就連拋出一個問題都不可能的“採訪”中,他刀鋒般犀利的現場觀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採訪台灣現代藝術家蔣勛的時候.王寅的提問顯然是有備而來.蔣熏力也就很容易滔滔不絕。
王寅:有資料上說,你每年大概要作300次講座,這個數字確切嗎?…… 很多像今天這樣公益性、普及性的講座,我注意到下面有些學生在打嗑睡。
看到這種情況,你覺得還有必要和他們這樣聊嗎? 蔣勛:美這個東西,她有時候就是剎那間顯現一些東西給你,其實我不覺得美一定是一種知識。從你的講座裡面,他(她)會在隻言片語裡面得到一個什麼啟發,很難估量。……以前我們在故宮上課,沒有窗戶,在暗暗的房間裡看幻燈片,其實也打瞌睡的,可是我常常覺得忽然驚醒的那一瞬間看到的東西會變成我後來限重要的東西。如果迷信地講的話,你好像會在最重要的東西到了的時候醒來。
一個實際的提問,被訪者的回答卻帶有一些神秘的形而上的色彩。這是意外的收穫。一個記者在採訪中,意外越多,驚喜也越多。
王寅又問:“我看到張曉風在一篇文章中說你過著神仙樣的日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指你比較脫俗?” 蔣勛的回答很精彩:“台北是個很混亂的城市,髒、亂,幾平沒有人覺得自己居住的環境好。我是住在淡水河的河口,當初我那個房子買得便宜得不得了,70萬台幣。12扇窗往外推就看見河口,我有時跟人家講說也不輸西湖的景。別人已經覺得像神仙了,你怎么可以過這樣的日子?可是,有次,我看到唐伯虎50歲給自己寫的詩,他說:“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日問眠。漫老海內傳名字,誰信腰、司沒酒錢?”大家都會覺得他過得像神仙,可是他前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他沒有權,也沒有財富,但是他可以過得像神仙。我想張曉風講的神仙本質上就是自由。他常常羨慕我可以到處亂走,聽說日本的米園大雪,我就帶著川端康城的《雪國》去住上兩天。” 我們身邊不大看得到這種為了米園的大雪帶上川端康成的《雪國》專程飛一趟日本的浪漫怪人的,我們的媒體上宣揚得更多的倒是一些所謂成功人士為了招搖天下而實行的苦肉計式的折騰,和小資們的標榜另類實際已經很例牌的生活道具——法國悶片,村上春樹的小說,布拉格的城市景觀,諸如此類。但是我們仔細讀完蔣勤的這篇專訪,便可以知道.在我們是行頭和飾品的東西,在他那兒大概已經修行得天然去雕飾.成為他生活中像空氣一樣自然的東西。即便造作,也造作得底氣十足。
那些挑剔的被訪者往往只對那些了解他的記者開口。碰到傻瓜記者的時候,他寧可把嘴巴閉上。某報曾經發過張某大明星接受記者採訪的照片,照片上大明星的目光隨著身子轉向另 邊,完全背對記者。這個記者對如此不堪的待遇當然會感到慪氣,但他也不妨想想,他的採訪提綱里到底是些什麼問題,他有沒有做過充分的準備,他是不是動了腦筋,他是不是除了報紙雜誌,不讀任何別的東西。
中國有句說濫了的古話,“酒逢知己乾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這句話用在採訪上,倒是極其貼切的。提起被訪者的興致,是記者的一大學問,這就是為什麼有的採訪剛剛開始就已經結束,有的採訪原定半個小時,聊了兩個小時、三個小時,還意猶未盡。
林懷民的採訪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王寅的提問都是從他的觀察中生髮出來的。“我看見在彩排的時候,你一直在做筆記,只有過一次提示。我很好奇,你當時記的是什麼?”“在謝幕的時候.我才看到演員是高矮不齊的,在演出的時候。卻一點也看不出來。”“我注意到《竹夢》里個別片斷舞蹈和音樂編織得不是很緊密,比如第二段的雙人舞和三人舞。”“從風扇搬上舞台,就開始有了諧謔的成分,直到最後的穿幫。”“台上的竹子是真的嗎?”“《竹夢》用的是愛沙尼亞作曲家佩爾特的音樂。” 有了前邊的愉快的鋪墊,當王寅問出最後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雲門的下一個作品是什麼?“時,林懷民的回答是一大段話(任何一個記者都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但林懷民很可能只是報一個劇目給他) 兩年前在印度,恆河岸邊,我看見乳白色的煙從焚屍場升起,喪家的男子從頭到腳裹著白的棉衣,鬍子颳得非常乾淨,我想到我重病的父親……於是有了《煙》。
……在台灣沒有春天的感覺。這太像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中的場景:家族長老死去的時候,板栗樹上的落花像雪片一樣,狗被窒息死了。
後來在布拉格找音樂,我找了很久。音樂用的是許尼特克,我喜歡他的音樂喜歡得不得了,他是我嚴重的初戀。他的音樂很難弄,非常現代,又十分浪漫。他是猶太人,有德國血統,生長在俄羅斯。你看。多么複雜。布拉格路上的石板像有靈魂一樣,安靜得不得了。從旅館的窗戶可以看見卡夫卡墓地,綠色的樹,綠色的苔蘚,綠,全是綠色的,綠到讓你昏倒。你可以想像那裡冬天綠成什麼樣子。我回不到恆河了。
後來還是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中的一句話讓我找到了一塊跳板, “有時,會忽然想起某個春天所聽到的一個名字……”。
大樹落下細細的白色的花,沒有葉子的樹想起它的春天。我用的是真的玫瑰花瓣,曬乾了,是淡黃色的,在燈光下,是白的,很漂亮。現在,雲門的門外就曬滿了待用的玫瑰花瓣。
舞台上有一棵要幾人才能環抱的大樹,樹上有20多片樹葉。樹下有一個小水池,一個小女孩死在裡面,不穿衣服。水池裡放的是真的水,是燒好的水,我們反覆測試溫度,要維持三分鐘,不能太熱,也不能還沒有演完就冷了。你看,從出發點到終點,其實是不相干的。
如果是一家娛樂小報的記者去採訪林懷民,用一大堆傻瓜問題令他瞠目結舌,他就絕對不會說出這么一段特別緊貼他的“身段”的話來:他不會說到印度與恆河,不會說到馬爾克斯和《百年孤獨》,不會說到許尼特克,不會說到布拉格的石板路和卡夫卡的墓地。不會說到普魯斯特和《追憶逝水年華》,不會說到舞台上那棵有20多片葉子的樹,更不會說那句幾乎沒頭沒腦的話:“你看,從出發到終點,其實是不相干的。“不能緊貼身段.便不能活畫出他的本相。
當然,王寅完成最漂亮的採訪的一大前提便是,他自己也得有盎然的興致。被訪者越精彩,越合他的胃口,他的興致越高,他甚至可以一次,兩次,三次地和他們深談,話題從核心彌散開去.直到一些“民眾喜聞樂見”的細節也成群結隊地湧現出來。
人們已習慣於對詩人的文字存有某種迷信.但僅僅有漂亮的文字很難保證一個人可以成為好的記者。王寅早在大學時代就已經將他的文字錘鍊得很漂亮,但他的採訪最有價值的部分,倒並不在於他的文體.而是他從被訪者那裡挖掘出的思想的金子、經驗的白銀。我相信,一個舞蹈工作者會從林懷民的專訪中領會到很多深意.一個建築師會從庫爾哈斯和黑川紀章的專訪中獲得很多啟發,一個熱愛日本電影的讀者會對那篇佐藤忠男的專訪著迷,而我們普通讀者,除了獲得很多教益之外,還可以領略到一篇新聞報導可以好看到什麼程度。
前不久,我在一本書中看到一個法國人所做的對於塞尚的虛擬的採訪,當我知道這篇對話是虛擬的以後.便把它放下了。我當然更願意聽塞尚的親口說話,而不是一個自認為了解塞尚的人所做的“過度闡釋”。王寅這本書的最大價值,便是對於當代眾多藝術家的思想和觀念的原聲呈現。
目錄
序言:藝術家思想和觀念的原聲呈現
林懷民:舞蹈只是兩個小時的開心而已
蔣勛:美不一定是一種知識
朱德庸:我其實是在浪費才華跟浪費生命之間來回矛盾
賀友直:我成為一個連環畫家適得其所
佐藤忠男:小津的東京已經不在了
許鞍華:電影不是惟一的表達方式
賈樟柯:我的電影恰好背離了傳統
鄭鈞:我出賣我的痛苦
何訓田:所有的聲音對我來說都是圖案
溫普林:我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佛教徒
黑川紀章:我不能把我做的妥協寫在牆上
庫哈斯:建築是需要爭議的
朱天文:命名的喜悅是最大的回饋
馬原:我們每天活在西藏的傳奇裡面
葉兆言:等待馬不停蹄的到達
山崎朋友:《朝陽門外的彩虹》
後記: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變得如此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