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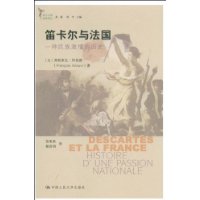
在法國,關於笛卡爾,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哲學家們有看法很正常,但作家、政治人士、教士、建築師或學者們竟然也是如此。這已經成為法蘭西民族的真實情況之一:笛卡爾代表法國,而法國人具有笛卡爾精神。笛卡爾,他把自己的名字賦予一個國家。打造了它的身份認同。 我們不禁要問:這種情況是如何形成的?這位1650年逝世於異國他鄉的哲學家怎么就終於代表起整個民族來了?對這個兼具象徵性和爭辯性的人物,天主教徒和無神論者、左派與右派、民族主義者和共和派,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意見分歧?笛卡爾的哲學到底蘊含了什麼東西,以至造就了三個半世紀的不休爭論,並最終譜寫了一個笛卡爾式的法國神話? 笛卡爾與法國的關係史,幾乎就是從1650年到我們當下時代的一整部法國政治和學術史。為了理解這位哲學家謎一樣的獨特命運,作者帶著我們重訪漫長歲月。
目錄
介紹
第一部分路易十四的世紀
第一章被列入禁令的笛卡爾
最後的旅行
最初的審禁令
《永久列禁書目》
第二章對笛卡爾主義的迫害
笛卡爾主義在法圍的際遇
出版和宣傳
“好天主教徒”和“好法國人
揚森派的標籤
加爾文主義的指控
第三章笛卡爾的世紀
笛卡爾在統治
現代派的保障
婦女的事業
第二部分啟蒙和反啟蒙
第四章混亂景象(1680—1730)
萊布尼茲的戰略
被牛頓的陰影壓得喘不過氣來
笛卡爾派和反笛卡爾派:一條變動著的
分界線
接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和《光論》
聲勢微弱的洛克
耶穌會士們的復盟
無處可覓的共識
笛卡爾:真正的法國人
第五章伏爾泰的效應
第一批宣判
1734,連結的一年
《哲學通信》的論戰
沒有笛卡爾的笛卡爾主義精神
學者信譽的喪失,哲學家的辯護
布拉德神父事件
偉人笛卡爾
科學院頌揚的時代
第三部分大革命時期(1789一1848)
第六章民族英雄
“笛卡爾被蟲蛀的骨頭
決定性的十年
第七章極端分子重讀笛卡爾
從反對大革命到拉梅內
《論麻木不仁》的衝擊
笛卡爾,敗壞教會的人?
僧侶們抵抗極右反笛卡爾主義
第八章實證主義者與空論者
笛卡爾,文證主義時代的先驅者
清談派據他為己有
第九章維克多?庫辛和他的對手們
維克多?庫辛的措施
一種天主教意味太少的折中主義
一種革命性不足的折巾主義
托克維爾
基內
米切雷
孔德
勒胡
維克多?庫辛的反擊
第四部分第二帝國或對抗時期
第十章共和國和科學的宗教
笛卡爾,科學主義之父
自由派和共和派的笛卡爾
第十一章天主教世界
1851年
托馬斯主義的復活
現代主義的異端邪說
第十二章反笛卡爾主義的理性主義者
右派:聖一貝夫、勒南、丹納
還有左派:蒲魯東
第五部分第三共和國笛卡爾的女兒
第十三章各個左派
來自社會主義者與激進分子的致敬
笛卡爾誕辰300周年
涂爾幹:一個相反的例子?
革命的工會運動
第十四章民族主義鏡子裡的笛卡爾
布爾熱,布倫地耶爾,巴雷斯
法蘭西行動組織
改宗者
佩吉孤獨的聲音
第十五章從一場世界大戰到另一場大戰
戰爭的年代
在馬利坦和托馬斯主義者周圍
世俗者
反對資產階級的起義
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最後的大轉變
人名對照表
譯後記
……
文摘
在1657年,人們為什麼會極力強調這位偉大哲學家的天主教式的臨終場景呢?毫無疑問,首先是因為這符合那些17世紀盛行的對死亡的鋪陳描述:一個“高尚的臨終”,或是一個“非常天主教式的臨終”,就像人們提及的路易十三的臨終那樣,二者如出一轍。但還有一些出於當時具體背景的理由。各種閒言碎語立即圍繞著笛卡爾的臨終散播開來:他不是被悄悄地葬在未受洗就夭折的兒童墓地里了嗎?因為那是沙尼的意願,他可是個誰都覺得怪異的人。不是有人說笛卡爾本要皈依他去世的那個國家的宗教嗎?還沒說他原來是無神論者呢!好幾個人說他是,他們也許想起了吉斯伯爾·沃埃在這位哲學家生前控告他的話。
另外,他去世後沒幾年第一批責難就來了,這些責難預兆著1663年羅馬的裁決。1658年,魯汶大學藝術系的一位醫學教授普朗要求他的同事們禁止接觸“危害國家”和有害病人健康的笛卡爾哲學,儘管笛卡爾曾與他通過信,一直把他視為朋友。1654年以後,普朗在他的《基礎醫學》第三版中增加了一篇附錄,裡面提到有三名神學教授提出要禁止笛卡爾哲學,他們指責它與聖事的聖禮完全牴觸。同時,沃爾格神父寫信給笛卡爾的遺囑執行人克洛德·克萊爾色列,要求後者對笛卡爾哲學中關於變體的論點進行解釋。笛卡爾的論點在當時極有爭議,沃爾格向克萊爾色列道出了自己的懷疑:“在廣延是物體的本質的設論中,為什麼連路德甚至加爾文的看法都正確的呢?”對笛卡爾主義的步步緊逼開始了,是關於聖事的問題啟動了它。
1654年出現的這個問題並非無因而起。早在1641年,安托萬·阿諾德在對笛卡爾的反駁中就已經把問題擺上了桌面。年方29歲的神學學士阿諾德剛畢業,很快又成為索邦大學的博士,正初踏職業之途,這讓他恰好置身於世紀後半期所有神學與哲學爭論的中心:還有誰能有朝一日自詡曾和當時最偉大的三位哲學家——笛卡爾、萊布尼茨、馬勒伯朗士——都交換過大量信件呢?他們在王港修道院的繁盛期可都是最著名的角色啊。在給笛卡爾的《反駁》中,阿諾德特別指出,在很可能會激怒神學者們的那些觀點上,廣延物體的理論攻破了教會的教導,觸動了在聖體餅中真有耶穌存在的奧義。如果真像《形上學的沉思》的作者認定的那樣,那些可感知屬性——第二性質——只能在與它們所定性的物體本身分離後才能理解,如果廣延的確是物體的本質,那么又怎么能夠“麵包已經不在某地,另一種物體已取而代之,而麵包所有的第二性質卻依然停留在原地呢”?阿諾德並不懷疑笛卡爾的天主教信仰,只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