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攔海歸報效祖國的中國教育
海歸戴靜怡帶著一雙兒女告別老公回美國了。在機場,她的心一直突突跳。畢竟,這是他們結婚20年來第一次長期分別。曾經這兩夫妻的底線是無論多苦多難都要廝守在一起,因為一旦牛郎織女,婚姻的質量和安全都無法保障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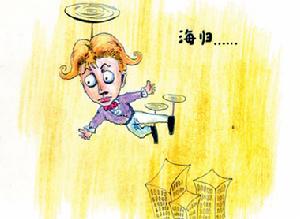 示意圖
示意圖讓戴女士下定決心回美國的是她還有兩年上高中的兒子豆豆。
豆豆在美國出生,國小三年級時才跟著歸國工作的父母回到上海。中國的教育模式讓他們全家傷透腦筋。兒子個性的變化和老師的冷言冷語,更令這對夫婦忍無可忍。
不止豆豆,很多海歸子女對中國的教育體系都相當不適應,特別是在國外出生的孩子。甚至有人稱“中國現行教育是阻攔海歸報效祖國的馬奇諾防線”。
對於海外歸鴻來說,能回來獨挑一個項目的人,一般都在35歲以上,拖家帶口,在海外發展已經很不錯了,要拋棄的東西非常多,家庭是其中最重要一環。
“引進人才重要,維護人才更重要。”有專家指出,“吸引‘海歸’的物質支持不可少,精神支柱更加不可或缺,一個是支架,一個是靈魂。歸國人員的家庭安置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
子女教育是海歸心中最大的痛
在國外的時候,這些留學生覺得孩子太輕鬆太放縱,說要管教孩子趕緊回國;到了祖國,他們又受不了教師對孩子的過分嚴厲和教育體系的刻板。一位從溫哥華回來的父親說,他孩子上學的地方,為了不把操場上的草坪踩壞,老師不讓孩子跑不讓孩子跳,只可以在操場上慢慢走,對孩子來說太壓抑了。他們不僅經歷了入學難入學貴,公辦教育中教師的兇悍,更讓很多海歸父母不能接受。
“現在的國小好可怕,一次我去給女兒送東西,站在學校的走廊里,幾乎每個教室里都有罵聲。”戴女士覺得,由於孩子的語文不太好,從國小至今,孩子們幾乎得不到表揚,承受的壓力太大了。老師動不動說“你們班年級最差,就是你拖後腿。怎么那么笨。”老師太兇,所以孩子對整個大人群體都沒好感。
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戴女士這幾年發現,兒子由於自卑從不跟同學交往,回家後臉上沒表情,父母跟他說話沒反應,眼神直直的。客人來家,他連招呼都不打。
兒子與在美國的時候判若兩人,曾經的鋼琴小童星,同學中的小頭目,是典型的優秀生。去年暑假戴女士陪孩子回美國辦理房產轉讓的時候,兒子的眼睛都放光,話也變多了,不停地央求媽媽,別回上海好不好。
戴女士明白,兒子糟糕的表現是在抗拒自己,抗拒回到國內的教育中。雖然現在美國經濟很差,但為了兒子,戴女士還是決定離開,“工作差點不要緊,只要能供兩個孩子生活就行了”。
從英國回來的周先生反問:“語文數學成績不好,難道就不得翻身了?”他的孩子在英國時是學校的灌籃高手,被很多女生愛慕和崇拜,但回來後因為學習成績差語言結結巴巴,重點中學的同學都躲著他。
與海外留學人員打交道30年的中關村前副主任夏穎奇說,子女教育問題,超越了多次出入境、辦簽證、外匯划進劃出、買一個免稅汽車、創業園的各種補貼等問題。如果子女教育耽誤了,扔在國外沒人管,帶回國內又跟不上,將來國內考不上大學,國外也上不了學,他就不是一個成功的人。“即使成了億萬富翁,他也不幸福。”
夏穎奇與一位科學家曾經開過一個玩笑:“你回來可能辦出一個上市公司,但你孩子中學念得一塌糊塗,大學上不了,中途說不定還學壞,你願意回來嗎?”對方的回答斬釘截鐵:“我不會做這樣的交換。”
“人在中國,家在矽谷”的海鷗族
一位海歸人才的離去讓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遺憾至今。幾年前,一位海外優秀的幹細胞科學家,聽說了北京生命所特有的機制,想要回來。接洽之後,雙方都很滿意。
然而,這位科學家到所時間不長,還在國外的太太提出如果再不回到身邊就要自殺,只好抱憾離開,“畢竟,回國是一家人的問題。”
事實上,在海歸回國的障礙中,除了子女教育,也有配偶的因素:願不願意換工作、願不願意搬家、是否支持另一半換工作等等。
不少人選擇了以犧牲家庭團聚為代價。老婆孩子常住國外,一個人國內外來回跑。回到國內,房子就像旅店,只是個晚上睡覺的地方;午餐晚餐往往都是便當解決。人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忙完這邊的事情再飛走。
有矽谷三劍客之稱的鄧峰和兩位好友一手打造的公司Netscreen,在美國創造了40億美元的併購神話。2005年,鄧鋒帶著妻兒和在美國得到的“第一桶金”悄然回國,在北京清華科技園科技大廈這座剛剛落成的寫字樓里做風險投資。
開始,鄧峰的孩子被送到位於順義區的國際學校上學,由於距離鄧峰上班地太遠,親情交流困難,又轉學到中關村四小,因為孩子難以適應國內教育模式,最終回到美國。
而今鄧峰只能“海鷗式”的中國、美國兩邊跑。
千人計畫入選者宋磊認為,現在大規模回來的海外留學人員剛好是這樣一代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出去,年齡在35歲到50歲之間,小孩正好在國小到高中階段。
宋磊所在公司里30多位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員工,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時間在美國,而且沒有一個人將自己入學年齡的孩子帶到國內就讀,太太也就留在了國外。
曾在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過十幾年的宋磊也被家庭羈絆,現在北京、矽谷兩邊跑。也經常移動辦公,在加州的家中只好從晚上7點工作到第二天三四點,那時正是中國的白天,因為他要與國內的同事一起同步研究、討論技術問題。
宋磊認為,要使海歸真正安心地回國,需要解決好配套措施,“時間和家庭是我目前考慮得最多的。”
像宋磊那樣50%%時間花在國內,剩下50%%時間花在國外的人不在少數,時間如何分配,成了他們每天生活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位歸國人士惋惜地說,“一些老‘海歸’雖然自己回國了,但家還沒有完全回來,老婆孩子都在國外,形單影隻的孤獨導致他們面對困難和挫折時更容易打退堂鼓。”
事實上,幾年來,他也目睹了身邊的朋友,有的中途打了退堂鼓,有的因為長期兩地分居最終離婚。
因為家庭等原因不能全職回來,也必將影響人才引進效果。
千人計畫入選者羅永章教授以科研舉例,實驗室的工作是要連續的,科研經費也該是連續的。實驗室良好的風氣沒形成起來的時候,老闆常常不在,是個空中飛人,那這個實驗室的士氣一定不旺盛,這個團隊也就帶不起來。
軟環境跟不上,海歸就會不歸或者歸海
其實,還在國內堅守的海歸對那些離開的人充滿了同情。來了四五年,剛剛搭建了一個課題組就跑了,對單位對本人的損失都很大。中科院的嚴老師說:“不到迫不得已,誰也不會拆爛污,然後拍屁股跑了。”而一些海歸心走了比人走了更可怕。中科院一位姓汪的老師指出,做科研做到最頂尖,必須心無旁騖,就像劉翔在最後衝刺的時候,腦子裡有一點雜念都不行。
但不可否認的是,有人就是離開了。網上一位出走的海歸這樣發問:“我那么愛祖國,可祖國愛我嗎?”
美國肯塔基大學的老師一到寒暑假就往回跑,雖然在國外有教職,但內心不安定,幹不了事業。可回來也只能去個三流大學上上國小期,像箇中學教師差不多。他說:“‘海鷗’再怎么不好,但家庭穩定,我孩子的教育可以保證。”
一位姓鄭的老師說,我們回國其實沒有什麼大道理可講,一是可以和父母團聚,享受天倫之樂。二是10多年在美國,現在忽然能用母語表達,感覺太好了。我們可以在食堂吃著晚飯就把想法談了,有什麼創意,馬上可以輕鬆準確地告訴學生。在國外我們說英語是劣勢,回到國內就成了優勢。“其實,說實在話,在國外,華裔還是有玻璃天花板的,也沒哪裡像中國這樣渴求創新渴求成果,那么捨得在科研技術上花錢。”
幾位海歸說,無論是“千人計畫”還是“百人計畫”,引進人來國家都要投入很大的資本、資源。個人的投入也很大,大家都是40多歲的人了,想的就是回饋祖國,畢竟這些年他們比一般人多讀書多研究新技術多走了些地方。引進時,國家開出了那么高的條件,如果不盡心維護,人才不流失也會變成廢才。人才進來了,給他一個平台你就不管其他了,很容易變成狗熊掰棒子。維護人才其實就是維護他的家庭穩定性。
“中國的人才到底是多還是少?”嚴老師問,“認真一盤點,一個領域內你怎么算,真正有水平的就那么幾個。在科技領域裡,三個臭皮匠可頂不了一個諸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