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陽郡王
 汾陽郡王
汾陽郡王汾陽郡王郭子儀生於陝西華縣,因功封代國公,後進封汾陽郡王,尊為尚父,官封太尉(一品),自唐代以來享有很高的聲譽。稱號雖多,但人們喜歡用汾陽王代稱郭子儀,有人乾脆稱他為郭汾陽,“汾陽王”稱號代表著郭子儀的特殊榮譽。郭子儀因功封汾陽郡王,其子孫以汾陽為堂號,然而因史書上沒有明確交待汾陽郡王封王稱謂的依據而其封地所在又沒有專門記載,引發了郭子儀研究中關於唐汾陽封地所在的爭論。對郭子儀汾陽封號封地的認定,有陽曲說、泛指說(意即汾陽泛指汾河西北的廣大區域)和現汾陽說。細讀《舊唐書》 ,從中找到一些信息,再結合唐代文獻《因話錄》的記載,可以清楚地說明:汾陽郡王的封地就在汾陽,郭子儀汾陽封號是依汾州封地而得名。
汾陽郡王依封地得名的依據
《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上元三年(公元762元)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使鄧景山亦為部下所殺,恐其合縱連賊,朝廷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使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郭子儀辭赴鎮……子儀至絳,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伏法。”
以上清楚地記載了郭子儀的進封與戰績,然而對汾陽郡王封號的依據沒有明確,於是有了各種猜測。讀以下兩道詔書,即可破解歷史難題。
貞觀十一年,太宗《功臣世襲刺史詔書》曰:“但今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齊國公無忌等宜委以藩鎮,改賜土字。無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魏國公玄齡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共十六人)——余官食邑並如故,即令子孫奕葉承襲。”
此詔說明“貞觀舊制”是——名為刺史實為諸侯,也意味著唐代功臣改封、進封的封地、封號、食邑是有內在聯繫的,封號來自於封地,封地的特定區有其食邑。
那么,到郭子儀封王的肅宗時期,是否仍是這樣?
乾元二年肅宗下《授彭王饉等節度大使詔》曰:“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內封子弟,外建藩維——歷考前載,率由舊章,彭王饉等委以臨戎。彭王饉可河西節度大使;……必能輯和戎律,慎守封疆。”共封七人。顯然這一名為刺使實為諸侯的“貞觀舊制”深深的影響著整個唐代。
不久,肅宗分別加封功臣李光弼為臨淮郡王、郭子儀為汾陽郡王。
李光弼的情況是最有力的時證。李光弼祖籍遼東人,安史之亂後與郭子儀齊名,先封鄭國公,因河南亂出任河南、淮南節度使,進封臨淮郡王,實封一千五百戶,可以肯定其封邑也在淮河邊,後來李便“收江淮賦租以自給"。李光弼臨淮郡王封號依封地得名。
從上面文獻和史例可以得出結論,汾陽郡王依封地得名,以汾陽代稱的古汾州為其食邑之地。
汾陽郡王食邑汾州的依據
首先解決汾陽王有沒有封地的疑問,回答是肯定的。《舊唐書·郭子儀傳》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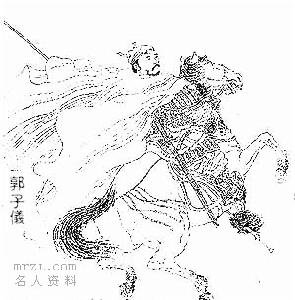 汾陽郡王
汾陽郡王《全唐文》中《優恤郭子儀諸子詔》內容如下:故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功格上元,道光下土。積其善慶,垂裕無窮。雖嫡長雲殂,支宗斯盛,汾陽舊邑,盍有丕承。其男前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食實封五百戶曖,夙稟義方,居忠履孝,儷崇銀榜,攄美金章,繼撫先封,允宜聽復。曖兄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 、並弟右金吾將軍祁國公食實封二百五十戶曙、太子左諭德映等,並休有令名,保其先業,宜允推恩之典,以明延嗣之誠。其實封二千戶,宜準式減半,餘可分襲。曖可襲代國公,仍通前襲三百戶, 可二百五十戶,曙可五十戶,通前三百七十戶,映可二百三十五戶。
“汾陽舊邑”在哪裡呢?
(一)有兩則唐宋文獻明確說明郭子儀的封地就是汾州。
一則是唐代趙粼名著《因話錄》中有一段話:“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敕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勛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寮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
另一則是宋代洪邁的《容齋隨筆》中有一則《北人重甘蔗》的短文: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
此兩則文獻出自唐宋,當應引起大家的重視。趙粼系唐人,而《舊唐書》成書於五代,《新唐書》成書於宋代。洪邁所說的汾上就是汾州,唐宋以來文獻多以汾上代指汾州。代宗登基後贈郭子儀為尚父,郭子儀一度在家閒居。這兩則歷史故事根據情理推斷,應該是郭子儀在家閒居時發生的事,對考證其封地有特殊的意義。兩則文獻與汾陽民間傳說郭令公曾帶領鄉民退敵並有郭太尉莊以及民間傳說與愛子村毗鄰文水馬村系郭子儀的養馬地相吻合。
(二)懷疑汾陽與郭子儀有關的人認為唐代現汾陽不叫汾陽,以下諸多記載和事實可以說明郭子儀進封汾陽郡主的前前後後汾陽就叫汾陽,汾陽還代稱汾州。
唐代名碑山西臨汾浮山縣玄宗所撰《慶唐觀紀聖銘》碑文中“汾陽之龍角山”的汾陽二字即指汾州,龍角山則指北龍角山暨今日介休的龍脊山。
現汾陽市收藏有在汾陽城周圍發現的《大唐故宋府君墓志銘並序》(公元735年),《唐故趙夫人墓志銘並序》(公元852年)。兩碑文中寫有“葬於汾陽城西"及“逝於汾陽私邸”字樣,說明唐代汾州城就叫汾陽城。(後又出土兩塊,也為唐代,均載明時稱汾陽)。另外唐代史籍中汾州多稱“汾上”,汾上也是汾陽的代稱。唐代中期改西河郡為汾州,汾州就是事實上的汾陽郡,郭子儀時代稱汾陽 的只有汾州。
另外古人寫詩以記經歷,唐代的遊歷詩中不乏用汾陽指代汾州的事例,如唐代詩人徐安貞在《奉和聖制答二相出雀鼠谷》詩中寫道:“還望汾陽近,宸游自奮然。”雀鼠谷在今介休一帶,南出雀鼠回望汾州叫“還望汾陽”,二相指張九齡和張說都是唐玄宗時期的名相。再如岑參在送友人歸太原(今晉源鎮或意指太原盆地)時寫下了“卻投晉山老,愁看汾陽花”的詩句,這句詩想像了友人落榜回家路上的悽苦心情,唐代北上太原的古道是蒲州——晉州——汾州——并州,由此可以確定岑參這裡用“晉山”代臨汾地區(唐晉州),用“汾陽”代汾州地區。可見汾州在當時叫汾陽,唐文中汾州還有汾上、汾隰、汾湄等名稱或簡稱汾,當時汾人即特指汾州人。
北宋太平興國四年在汾州設立汾陽軍。金代依舊設汾陽軍於汾州。金代詩人參觀汾州狄青廟後吟詩讚“汾陽留壯跡”。宋代名僧善昭本太原人,長期主持汾州太子院(大中寺),備受海內外佛教界推崇,其代號有汾州、汾陽、西河獅子等,可見在唐宋時代汾州、汾阻西河是同一個地方。
(三)郭子儀後人的家譜記載、郭曖封地汾陽遺蹟。
其一,汾陽王后裔珍藏的郭氏家譜,大都明確寫著汾陽是遷出地和世居地區,汾陽有許多關於郭氏的記載。(詳見郭裕懷主編的《汾陽王郭子儀譜傳》、李吉、馬志超合著的《郭氏史略》和郭世科主編的《汾陽郭氏郭村支譜》、《郭氏源流考》)。
其二,從唐代開始,汾陽先後建過三座汾陽王廟,歷代汾州官民還有修繕感謝汾陽王恩澤,這在全國也是唯一的。(詳見張海瀛先生《郭子儀與山西》一文)。
其三,郭曖食邑在今汾陽愛子村。舊唐書記載,“汾陽”(指郭子儀)去逝以後,“汾陽舊邑,盍有丕承”。二千戶食邑,一半歸公,一半分給了兒孫們,這在唐代是最高待遇。其中郭曖繼承的最多,“襲封地三百戶”,這就是現汾陽愛子村的起源,現村民留有古家譜。
這一史跡值得信賴的理由是:郭曖的第四子郭韋容娶了公主後,公主改封西河公主,汾州西河即今汾陽;郭曖夫人後封虢國夫人,而汾州有其先人聚居的大小虢城,又是古瓜(虢)衍縣邑在地。由此說明郭曖的封邑確在汾州。陝西師大唐史專家杜文玉指出“宦官之妻的封號通常以其得姓之地取名,如鄧某之妻王氏其先琅砑人也,故封琅砑郡君。”雖然杜文玉考證的只是宦官,但這一看法與杜甫詩“國與大名新”是吻合的。《打金枝》的故事,史籍早有提及,但只是作為汾陽王家事在汾州世代相傳。清代被時人搬上舞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又由孝義的劇作家整理並推向全國,使汾陽王與唐代宗君臣之間處理國事、家事的美好範例家喻戶曉,交口相贊。
(四)汾陽食邑,還有理論上的依據。
首先、《唐會要》和《新唐書》都記載唐代“名山、大川畿內之地皆不以封”。唐代太原稱北京,到唐玄宗又加封晉陽為赤縣,陽曲為畿縣。正由此因,這些地方是絕對不會封給功臣的。
第二、郭子儀封的是汾陽郡王,而非縣王。汾陽自三國以來,就一直為郡州在地,而陽曲縣歷史上從未有過郡州建置;何況陽曲稱汾陽,在隋末9年、唐初4年,總共只13年,時間上早於郭子儀進封汾陽郡王138年。
第三、郭子儀的後人封為太原公、祁國公、清源男等,也不能否定汾陽的食邑地位。舉幾個例子:并州祁人溫彥博,封的是西河郡公;薛仁貴絳州人,封的是平陽郡公;裴度是聞喜人,封在晉州晉國公(今臨汾)——皆以鄰郡為封,而且是只有封號沒有食邑封地的虛封;除承襲之外,郭子儀後人封號也多是虛封,只是大功臣才有實封食邑的。
綜上所述,今汾陽是郭子儀封地無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