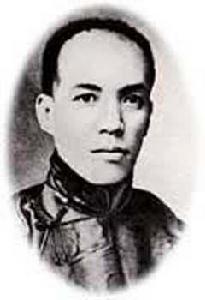歷史
中國具有悠久的史學傳統。1840年鴉片戰爭後,古老而悠久的中國史學開始向近代形態轉變。這一轉變過程,初期以龔自珍、魏源、徐繼畲為代表,中期以王韜、鄭觀應、黃遵憲為代表,最後於20世紀初年形成以梁啓超為代表的所謂“新史學”。
“新史學”
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封建舊史學基礎上的一種全新的史學樣式,是舊民主主義時期資產階級史學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新史學”的領軍人物雖然以資產階級改良派(如梁啓超、夏曾佑)為主,但資產階級革命派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等),也做出了很大貢獻。所以,“新史學”代表了晚清時期的整個資產階級學術陣營。新史學的意義,從根本上說,在於它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誕生奠定了學術的基礎。如果沒有“新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就要直接面對封建舊史學,就會付出更多艱苦的工作。有了“新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就可以直接超越封建舊史學,在資產階級所建立的學術與思想起點上,實現更高程度的超越。
梁啓超與“新史學”
1901年,1902年,梁啓超先後發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兩篇文章,對中國傳統史學做了激烈批評。他認為,傳統史學與國家,人民的事業毫無關係,不過充當了帝王的“政治教科書”;所以中國古代的史學雖然發達,但國民卻未能從中受到教益。他呼籲進行一場“史界革命”,倡議建立新史學,重寫中國史。梁啓超的這兩篇文章被稱為“新史學的宣言書”,對當時的史學變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新史學在歷史觀念,治史目的,對象等方面,都與傳統史學有著根本的不同:新史學持歷史進化論觀點,區別於傳統史學復古,循環的觀念;新史學以國民群體為歷史重心,區別於傳統史學以皇族王朝為歷史中心;新史學以以全體國民為讀者對象,區別於傳統史學為帝王個人提供借鑑。總之,新史學的宗旨是為全體國民寫史,寫全體國民的歷史。
第一
新史學”已經具備晚清時期最完備的世界眼光,這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強調世界統一性和規律性的特徵相銜接。從龔自珍、魏源、徐繼畲等人開始,進步的中國史家即開始以一種世界的眼光來審視中國歷史。其後,從世界性的眼光出發,成為王韜、鄭觀應、黃遵憲等人著作的共同特點。他們改變了兩千多年來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念,開始將中國視為世界的一部分,最早開創了中國近代的世界史研究。康有為、梁啓超、夏曾佑、嚴復、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登上歷史舞台後,更是竭盡全力地吸收世界歷史知識,總是將中國放在世界歷史發展和全球大勢變動的格局中予以思考和觀察。從此,在史學觀念上,中國與世界無法再分離。這種全球性和世界化的眼光,是史學觀念上的一場革命,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一致。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是一種立足於全球化和具有世界性目光的史學。
第二
“新史學”是以“經世”為價值取向的致用史學,是與時代脈搏息息相關的實踐性史學,這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實踐性與革命性的品格相銜接。從產生根源上說,“新史學”乃出於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相逼相迫”,而不是從書齋中自發地生長出來的。所以,“經世致用”、愛國圖強是自龔自珍到梁啓超一以貫之的主題。“新史學”家們深刻思考國家民族命運,嘗試著從歷史中尋找使祖國走上富強之路的努力,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繼承的重要遺產,具有重要的思想啟蒙、啟示和方法意義。馬克思主義史學,同樣是一種經世致用的史學,是應時而起的史學,是將歷史與現實打通的史學。
第三
“新史學”家所尊奉的進化史觀,雖然與唯物史觀具有本質上的區別,但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相信人類進步、追求人類進步、構建歷史分階段演進模式的屬性相銜接。當然,在不同的新史學家身上,對進化史觀的尊奉程度是不同的,進化史觀本身也頗多缺陷(如單線一元性、簡單化等等)。還有一些新史學家最後放棄了進化史觀。但是,總體上看,在一定的時間段內(主要是在晚清時期),進化史觀,是新史學家們整體上的價值取向。進化史觀以進化、進步的理念為前提,而馬克思主義史學所遵奉的唯物史觀,同樣是一種進步史觀。
第四
“新史學”對封建舊史學所展開的猛烈批判,與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品格相銜接。“新史學”的代表人物梁啓超等人曾經提出“史學革命”口號,並且與當時的今文經學思潮、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相配合,匯合成晚清思想解放與啟蒙運動的巨大潮流。馬克思主義史學正是在此基礎上繼續前進,在前人“革命”的基礎上繼續“革命”,在封建史學日益沒落和邊緣化的基礎上使其愈加沒落和邊緣化,在中國史學近代化轉向不可逆轉的基礎上使其繼續前行,實現超越。
第五
“新史學”家“伸民權”、“寫民史”、“去君史”,鼓動史學通俗化、強調多學科綜合研究的一系列主張和實踐,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強調人民民眾歷史作用、打破王朝體系、以社會經濟形態理論治史的特性相銜接。“新史學”從“歷史哲學”到編撰理論,都增加了許多舊史學不具備的內容,許多西方的歷史著作、歷史理念、歷史話語,被介紹引進到中國的歷史學當中。這些理念與話語,既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批判對象,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得以建立的平台和基礎。
所以,就學術流變而言,“新史學”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邏輯準備階段,是學術傳承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誕生清掃了道路,做了邏輯的、思想的以及學術資料上的準備。不消說,梁啓超等人在建構“新史學”的過程中,不僅曾經提到馬克思,而且還對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學說有所認識和介紹,已經接觸到唯物史觀。
但是,“新史學”無法自發地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歸根到底,它是一種唯心主義史學,還是一種形式主義史學,其思想源流龐雜而多元,許多見解也偏激、錯謬。由於它不懂得社會經濟形態理論,不懂得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作用的角度去闡釋歷史,因此,它“沒有摸到社會關係體系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係的根源”;對歷史主體背後的諸多“奧秘”,只能觸及,無法揭示。這樣,它雖然已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卻只能徘徊於門外,進而牴觸與抵制,非但不能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而且還會與馬克思主義日行日遠,愈加背離。因此,輝煌期過後,當更大的社會變局到來時,“新史學”立即與時代脫鉤,成為明日黃花,落在了時代後面:一方面,在史觀上逐步走向相對主義,直至與唯物史觀直接衝突;一方面,在研究領域上逐步向歷史考據及所謂“純學術”的方向退縮,不復當年的宏大氣魄與氣象。故爾,就連新興的資產階級史家,都開始瞧不起它。新史學被更新形態與樣式的史學所代替,也就成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