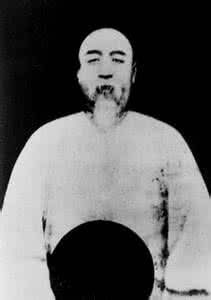張汝梅
張汝梅,高級工程師。浙江平湖人。1937年畢業於吳淞商船學校輪機科。1939年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院機械系。1942年回國。曾任貴州大定發動機製造廠工務處處長、上海中國油輪公司、吳淞商船學校輪機科主任兼教授。建國後,歷任上海招商局船務修建科科長,上海海運局設計科科長,上海船舶修造廠副廠長,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交通部上海船舶運輸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高級工程師。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對內燃機和金屬熱處理有較深研究,為我國內燃機和船舶機械製造工藝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生平
張汝梅(?—?) 清河南密縣人,字翰仙。歷任山西右江道,山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光緒 二十三年(1897年)山東巨野教案
後,繼李秉衡任山東巡撫。清政府令其加緊鎮壓濟寧、單縣、壽張等地的大刀會。抵任後,奏報“查明義民會即義和
團,並未滋事”,並將各鄉義和團編列保甲團防內,義和團在山東繼續發展,清政府責其彈壓無力,遂革職。
義和團運動之所以能夠席捲北方,震撼世界,固然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原因,但是,清政府的決策的誘導也起著關鍵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已成史界共識。然而,在對此進行分析時,人們往往重視中央統治集團,忽視地方督撫對義和團運動的影響。其實,在枝強幹弱的晚清時代,直隸、山東督撫對義和團的態度、政策不僅始終直接影響著義和團運動的發生、發展,而且也影響了清中央統治集團對義和團的決策。筆者由此入手,一抒淺見,以期深入說明義和團運動的興起,並就正於學界師友。
李秉衡、張汝梅首先轉變內外政策
甲午戰後,山東巡撫開始改變了以往在民教糾紛中的袒教抑民政策,轉而對外強硬。其轉變的背景除了以往一再強調的此間列強侵略的加深外,還應考慮到兩個容易被忽視的因素:
首先,1895年8月,李鴻章被解除直隸總督職務堪稱是這一轉變的政治因素。
自1870年起,李鴻章在此職位上盤踞達25年之久。此間,他通過管理通商、籌辦海防、興辦洋務而將山東納入到其勢力範圍,“坐鎮北洋,遙執朝政,凡內政外交,樞府常倚為主,在漢臣中權勢為最巨”[①]。但甲午戰敗及《馬關條約》的簽定,使之一時身敗名裂,直隸總督由以圓滑素稱的王文韶接任。李鴻章的去職深刻影響了當時北方的政局,不僅削弱了清廷在外交上的彈性和軍事上的應變能力,還標誌著洋務派在北方的失勢和頑固派的崛起,這可能導致對外政策的調整。於是,作為對李鴻章時代妥協、軟弱的外交政策的一種反動,甲午戰後不再仰直隸總督鼻息的幾屆山東巡撫首先表現出了強硬的對外立場。
其次,甲午戰後,頑固派開始得勢,頑固派的思想主張是山東巡撫對外政策轉變的思想因素。
在洋務運動中,頑固派提出過一個頗有影響的口號:“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如果拋開其反對自強新政的別有用心,則應承認其在立論上是無懈可擊的。而且,隨著清王朝的日見沉淪,“人心”的重要性愈發顯得突出起來。甲午戰後,頑固派得勢,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中有人重新強調“人心”,並獲回響。從李秉衡開始的幾屆山東巡撫多次強調要“固結人心”、“固結民心”[②],並把護民抑教作為改變“民氣遏抑太久”[③]的局面的途徑,以期為這個沒落的王朝拓寬一些社會基礎。加之他們本來就對西方的政治、文化持反感態度,於是,持一種強硬的對外立場也就是自然的了。
在這種情況下,1896年,李秉衡在令人困擾的民教糾紛的處理中,首先大膽地將糾紛歸咎於教會方面,他指出:
自西教傳入中國,習其教者率皆無業莠民,借洋教為護符,包攬詞訟,凌轢鄉里,又或犯案懼罪,藉為逋逃之藪,而教士則倚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為間說,甚己多方恫嚇;地方官恐以開釁取戾,每多遷就了結,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飲恨吞聲,教民愈志得意滿。久之,民氣遏抑太甚,積不能忍,以為官府不足恃,惟私鬥尚可泄其憤。於是有聚眾尋釁、焚拆教堂之事,雖至身罹法網,罪應駢誅,而不暇恤,是愚民敢於為亂,不啻教民有以驅之也[④]。
1898年,東撫張汝梅上奏朝廷,分析了反洋教的原因,雖然語句較上折委婉一些,但同樣表現出了強烈的感情色彩和強硬的對外立場:
竊以教士遠涉重洋,其傳教原是勸人為善。惟入教之始,不細加選擇,入教之後,遇事多所偏袒。於是搶劫之犯人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人入教者有之,負欠避債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訟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傳訊者有之。一經入教,遂以教士為護符,凌轢鄉黨,欺侮平民,睚眥之仇輒尋報復,往往造言傾陷,或謂某人毀謗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會匪,教士不察虛實,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勢愈張,則平民之憤愈甚。民氣遏抑太久,川壅則潰,傷人必多,其患有不可勝言者[⑤]。
對此,張汝梅提出了兩個辦法:其一是希望總理衙門據情照會外國公使,並“轉飭各教士,嗣後務須慎收教徒,嚴加禁約,毋得始終袒護莠民”[⑥]。其二是利用當時清政府興辦團聯的號召,企圖將山東反洋教的主要勢力——義和拳、梅花拳等組織納入團聯之列。這樣一來,既可將該組織納入政府控制範圍內,也可最大限度地消除來自教會的對這些組織的迫害和迫害的藉口,從而達到“調和民教”的目的。
針對中央對義和拳的疑慮,張汝梅進一步做了解釋:義和拳、梅花拳等本系鄉團,創辦於尚無教堂的鹹同年間,並非是與教會為難的組織,原為保衛身家、防禦盜賊起見,“臣現正檄行各屬,辦理保甲團防,謹當督飭地方官吏剴切勸諭,嚴密禁查,將拳民列諸鄉團之內,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不準懷挾私忿,稍滋事端,以杜流弊而消亂萌”[⑦]。
但是,應該指出,這一主張的實際結果遠不會如此簡單。義和拳一類組織由於與白蓮教有著說不清、道不白的歷史關係而長期被嚴禁,該組織有著較大的社會破壞性,其特殊的活動方式和組織形式也決定其很難接受政府改造並朝著有利於秩序的方向發展。張汝梅欲用其加強基層政權力量豈非緣木求魚,其構想除了在客觀上解除了對該組織的禁令,為其釋放力量提供了渠道,結果恰恰是反洋教力量的加強,“調和民教”根本無從談起。
同時,山東巡撫已經開始在實際工作中護民抑教,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世紀末山東民教糾紛不斷,當與此有一定關係。山東的教民感到了壓力,但這種壓力通過外國駐華公使又轉變成了對清中央政府的壓力。軍機處、總理衙門對張汝梅以及後來的毓賢發出了告誡:
疆臣辦事,總須為國家通籌全局,期無後患,不宜顧一時毀譽,率意逕行,是為至要。[⑧]
不必因其習教,故存嫉惡之心,庶彼此相安無事,遇有詞訟,無論教不教,地方官總應一律持平辦理,毋得稍涉歧視。[⑨]
我們找不到任何材料說明中央的旨意對山東巡撫產生了多少影響,更何況中央在這一問題上也存在著分歧,加之晚清時代中央對地方的影響本就有限,所以,山東巡撫們有著充分的理由漠視中央的指示。
筆者認為,山東巡撫對民教糾紛的分析和認識反映了當時列強侵略的事實,對日益尖銳的民教矛盾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結果在客觀上有利於義和團運動的發生、發展。
那兩篇引用率頗高的奏摺堪稱是反洋教運動中的“經典”性檔案,其中關於民教糾紛責任的歸屬,兩折都缺乏具體的列舉和量化的分析,即使僅從字面上看,就給人以絕對化和“一刀切”的印象。誠然,帝國主義的侵略及教士、教民的蠻橫不容否定,但這是當時中國社會面臨的普遍問題,為何偏偏在山東引發了如此嚴重的事態?這不能不令人深思。再者,也不能忽視這樣兩個問題:1、在19世紀末的山東,信教的中國人只是社會上的少數,而凌轢鄉黨、欺侮平民者又是教徒中的少數;2、中國教徒多為平民,而反洋教的領導、組織者則往往是地方紳士。這樣一來,就應承認山東巡撫的分析難免階級和文化上的偏見。
當時,中國人民一旦入教,即面臨著來自鄉里的歧視[⑩],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外國教士,還是中國縉紳,都起了挑撥民教關係的作用。李秉衡、張汝梅的這種認識的結果也只能是如此。
如果用這種認識來指導工作,就會出現偏差。其實,無論民教,均為清朝臣民,民教衝突,也不完全是一方的責任。李秉衡、張汝梅將人民與教民的關係視作水火不容,甚至要求外國勢力嚴格約束中國教民,只能產生不利於國家的結果。在洋教入中國已近半個世紀的情況下,作為一省督撫,不去探討如何緩和民教關係,而將責任一股腦推到教會和教民身上,這能說是對王朝負責任的行為嗎?在反洋教運動中,很多“口角細故”之所以最終“致釀巨案”,就在於士大夫和地方官對民教糾紛不但不加調解,反而火上澆油,推波助瀾。根據李秉衡、張汝梅的態度,聯想到這一歷史,就可信義和團運動的到來只是個時間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