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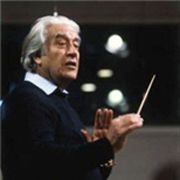 塞爾吉烏·切利比達凱
塞爾吉烏·切利比達凱塞爾吉烏·切利比達凱(1912——1996)生於羅曼離拉茲不遠,屬於羅馬尼亞的摩爾達維地區。幼年就表現了音樂、舞蹈的天才以及對文化學習的追求。
1936年他取道巴黎到柏林,在這裡他隨赫因茲·蒂埃森學習作曲,與瓦爾特·格門德爾學習指揮以及雨果·蒂斯特勒學習合唱指揮。蒂爾森後來成為他的音樂導師,馬丁·斯坦克是他的精神導師,而他的更多的指揮造詣是他自己觀摩富特文格勒的經驗得來的。當富特文格勒在戰爭結束時被列入黑名單時,他的指定的繼承人里奧·伯查德不幸被槍殺,一夜間,切利比達凱被任命掌管了柏林愛樂樂團。他很快重組樂團的餘部,使之成為一流的樂團,重新喚起柏林人對它痴迷的喜愛。當富特文格勒回到樂團時,由他們兩個人分擔首席指揮的職責。
1954年11月29日切利比達凱最後一次指揮柏林愛樂樂團,富特文格勒在翌日去世,12月13日首席指揮的位置安排給被認為有極富市場潛力的卡拉揚。相反的,切利比達凱在1953年發行了他與依達·哈恩黛爾合作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之後便停止了商業錄音,作為一位樂隊指揮,他更多地處在探詢、擔憂的十字路口上。
他一直未去居在美國直到1984年,他轟動性地出現在費城科蒂斯音樂學院的學生樂團的指揮台上。多年來,他都在與瑞士、丹麥、德國南部的廣播樂團合作,並使他們提高到從未達到過的高水準。
1979年,他再次成為慕尼黑愛樂樂團的首席指揮,並承諾要把這個樂團塑造成舉世無雙和世界級的樂團,他留在這裡直至逝世。
生平簡介
在布加勒斯特讀書時,切利比達克學習的是哲學與數學。在1936年,他又到柏林繼續他的學業,雖然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無線電,但切利比達克的音樂學習從未中斷過。他的博士論文的是十五,十六世紀的音樂家《若斯坎·德普雷》(JosquindesPres)。
1939年至1945年間,他在柏林音樂學院學習,並師從FritzStein,KurtTomas和WalterGmeindl。由於富爾特文格勒因被指控投靠納粹而不能帶領柏林愛樂演出,切利比達克一畢業便有機會與柏林愛樂合作。三年來,切利比達克擔任這個世界頂級樂團大部分演出場次的指揮,並籍此展現出他過人的天分與特有的風采。然而,當富爾特文格勒作為首席指揮重新回到柏林愛樂後,切利比達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只擔任客席指揮,而沒再固定負責某一樂團了。這主要因為他的苛刻要求往往讓樂團無法接受,而固執的他又絕不肯妥協。
一開始,切利比達克主要在柏林的交響樂團擔任客席指揮——包括柏林愛樂和RIAS柏林廣播交響樂團。但自從柏林愛樂任命卡拉揚為首席指揮後,切利比達克在往後的37年間就再也沒指揮過這個樂團。
1947年,切利比達凱繼大指揮家富爾特文格勒之後,擔任了五年這個偉大樂團的常任指揮。
1948年,他首次在倫敦登台,其後又不時在義大利擔任指揮。1959年起,他經常受斯圖加特廣播交響樂團邀請。
在1960至1962間,他在錫耶納的基賈納音樂學院(AccademiaMusicaleChigiana)開辦大師班,那是一個年輕指揮家夢寐以求可以進入學習的地方。在1962年,切利比達克擔任斯特哥爾摩廣播交響樂團的藝術總監,在他九年時間的指導下,樂團的面貌煥然一新。
1963年,切利比達凱將自己的藝術生涯和精力轉到了北歐國家,這一年,他受聘擔任了瑞典國家廣播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同時還兼任了丹麥廣播交響樂團的常任指揮。
從1973年至1975年他擔任法國國家交響樂團的終身首席客席指揮。1979年,切利比達克擔任慕尼黑愛樂樂團的藝術總監,並帶領其成為世界一流的交響樂團。在慕尼黑期間,他也開辦了指揮大師班。
1976年到1977年,他又接過了德國南部廣播交響樂團常任指揮的職務。
1979年又擔任了著名的慕尼黑愛樂樂團的首席指揮,此後他便經常以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國家為中心,廣泛地開展他的指揮活動。進入到八、九十年代以後,他又將他的指揮活動擴大到了世界的範圍內,在這十幾年裡,他先後在中美洲的一些國家的交響樂團以及美國的許多交響樂團中擔任客席指揮,獲得了人們的一致好評,並且還贏得了“著名樂隊訓練家”的美譽。
在切里比達克臨死前的幾個月里,嚴重的病痛並沒使他停止他的指揮工作。他擔任了許多作品首演的指揮,包括作曲家GuntherBialas’的"LamentodiOrlando”(1986),HaraldGenzmer’s的《第三交響曲》("SymphonyNo.3”)(1986),PeterMichaelHamel’s的(《三部分交響曲》("Symphonyinthreeparts”)(1988)和"undine”,還有亨策的“JeuxdesTritons”。切利比達克也有作曲,但他拒絕他的作品在音樂會上被演奏。
20世紀偉大指揮家
“在他充滿創造力的狂熱里,他的表演並非是想讓觀眾傾倒而自己離開站在一旁觀望。在他的精神世界裡找不到排除所有障礙的理由,但就在這些障礙自身之中。……我們花費了多少努力想與他並駕齊趨,但望塵莫及,當他跨越世俗的每一個偏見時就像一匹奮蹄飛奔的小馬駒,他的白熱化的激烈、無盡的發展、創造的、想像又一次使我們所認識的真理陷入置疑和毀滅。”切利比達凱對德國偉大舞台指導約爾根·菲靈如此大加讚賞。這些話可能正好是他自己的寫照。
 切利比達凱明
切利比達凱明切利比達凱明智地開拓理智來探索音樂同時音樂本身又迴避理智。
在蒂埃森的現代音樂研究的預言(«新音樂的歷史»,1928)里,他說:“創造形式就是藝術創造自身,它們每時都各有不同,與其說它是在我們工作的開始,不如說是在結束。借用保爾的簡短的格言:藝術不是模仿自然,而它必須就是自然,不管你是一個作曲家,一個演奏者,一個聽眾,不僅內容也是形式,藝術的組織結構必須成為你的一種直接經驗的感覺。它正好類似觀察自然的組織形式(比如說一棵樹,你可從內心用一種幾乎自然創造的移情來感受它),從它開始生長到樹幹長成以及綻開枝葉和開出花朵。”
切利比達凱指揮了蒂埃森的幾個優美的小型作品。1957年10月7日他回到柏林指揮廣播交響樂團,在慶祝作曲家70歲生日音樂會中的一個曲目就是《哈姆雷特》組曲(作於1919—1922年),它使用了密集的織體以及活躍的戲劇性的第一樂章。這裡,作品首先使用了一個齊唱,打算設計出“像海上暴風雨的聲音”的音響。
1948年小型的《G小調交響曲》是為DECCA的錄音,已經顯露了一些切利比達凱個性突出的成熟的莫差特作品特徵——它的嚴格,它的鮮于感傷,它的睿智,雕琢的形式——少見的柔順以及內部持續的律動成為與眾不同的標誌。他的柴科夫斯基的《胡桃夾子》於倫敦同時錄音,我們現在選擇的是最好的收藏版本。著名的EMI普羅科菲耶夫的D小調第一《古典交響曲與傳奇的孟德爾頌《義大利》交響曲的現場錄音,是首次在這裡正式發行,毋庸置疑,切利比達凱在自己的樂隊柏林愛樂樂團面前顯示了更多的個性。
在他掌管柏林愛樂期間,切利比達凱常常認為他自己作為一個臨時的領導,只是代替真正的主要指揮富特文格勒。在富特文格勒由於“清除納粹”的原因暫離樂團時期,切利比達凱無條件地擁戴他,主要目的是讓這位偉大的指揮家將來有可能在最好的條件下接手“他的樂團”。年輕的切利比達凱充滿對富特文格勒讚譽,我們選擇的錄音發現了具有懸殊的不同:節奏更輝煌、全體的控制、明亮的音色。儘管他已是一位成熟的指揮家,切利比達凱一直顯出他自己是個探索者。他的讚賞不只是對富特文格勒也包括其他管弦樂的統領,像維科多·薩巴塔、利奧波德·斯托科夫斯基、卡爾·舒希特、埃里克·克萊伯,對他們有許多讚美也有不滿之處。
最鮮為人知但充滿色彩的章節在切利比達凱的履歷里續寫著,曾經25年的漫遊經歷,從他斷然離開柏林愛樂(但他總是保留了一個柏林市民的身份,柏林的護照一直保留到德國統一)到17年間執掌慕尼黑愛樂。他在水平不等的各個樂團出現的次數很多,不管是在義大利、斯堪的那維亞、英國、法蘭西、西班牙、羅馬尼亞、以色列、拉丁美洲、日本,每一次都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通過保爾·克萊斯基的介紹,他長期與瑞典廣播交響樂團合作,10年間留下了他深刻的印記。
在那裡他指揮了大量的瑞典音樂,特別是當代作曲家的作品,尤其是“星期一組合”,集中了領導摩登潮流、扛起先鋒派大旗的卡爾伯格·布洛姆得赫爾、斯芬-埃里科·巴克與因格瓦·里德赫爾姆(10年以後他向巴克推薦了與他們志同道合的亨利·杜提魯克斯與波爾·那加德歸入於這個時代的重要作曲家)。1962年10月他在斯德哥爾莫最初演奏的曲目,是瑞典現代派的老將希爾丁·羅森伯格的《馬里奧耐特序曲》,這是一個優美的小曲。遺憾的是,他從來沒有演奏過羅森伯格的學生安得斯·埃里亞申的作品,切利比達凱在仔細研讀埃里亞申的《第一交響曲》總譜以後,他發現了他的未來“有極偉大的成就”。沒有遇到誰像切利比達凱那樣全盤接受了埃里亞申的藝術信條:“我僅僅嘗試遵循音樂的精神,這是一個完全客觀的過程。開始和結束緊緊聯繫在一起。我不是一個將音樂從開始帶向結束的人。音樂在做它自己的事情,我試圖置身事外。”
引領切利比達凱在這個管弦樂團成就的頂峰的明顯是在弗蘭茨·貝爾瓦爾德的第三交響曲《離奇》,斯德哥爾莫音樂學院的錄音場地有些迴響。大概沒有一個指揮家把這個作品表現的如此精確和雅致,活躍和激烈。引證斯坦克的話說:“強烈的個性,多么輕鬆地讓地球和宇宙在他的棒下跳舞。”僅此一次,貝爾瓦爾德自己特殊的10分鍾柔板,效果是正確的。所有意味著這個演奏技巧困難而且危險的作品在此都安然無恙了。
切利比達凱不只是在哥本哈根指揮了卡爾·尼爾森詼諧辛辣的喜歌劇《假面舞會》序曲。他認為尼爾森是一個“調性音樂無限潛力的復興者”,他保持了對偉大的丹麥作曲家高度的尊重,同時也意識到尼爾森的交響曲艱澀的管弦樂配器,要特別小心與精道地排練。在演奏中聽不到一絲不自然的舉措,是一瓶徹頭徹尾“純正的香檳酒”,我們品賞著充滿音樂奇想的系列,從北歐的羅西尼風格到地中海的雷神斧頭的閃電雷鳴。最後,切利比達凱自己無限的潛力又表現在1970年與丹麥國家交響樂團讓人愉悅充滿活力的約翰·施特勞斯作品現場錄音他的演奏遠離戰後維也納的虛情假意自我嬌縱和可能可以用來推翻一些陳詞濫調式的演奏風格。
用切利比達凱自己的話說:“如果是自由的人類,你將直接的創造,而不是在傳統、習慣和知識的基礎上。‘自由’是什麼?它的意思是察覺事物的功能並允許按客觀規律去做事。最終的自由不存在於我們製造音樂的過程之中,我們僅僅是製造條件允許音樂表現出來。音樂是無法被控制或強制的。”
晚年
晚年在慕尼黑,切利比達凱主要被認為是詮釋布魯克納、勃拉姆斯、施特勞斯、柴科夫斯基的大師。
 切利比達凱明
切利比達凱明1970年,當他在斯圖加特和巴黎指揮時,他特別讚賞德彪西、拉威爾、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羅科菲耶夫作品中無可比擬的細緻、豐富的色彩與結構和激動人心的力量。上世紀60年代在斯德哥爾摩,他最顯著成就是演繹介紹了許多陌生的當代大師的傑出作品。
他在晚年指揮的慕尼黑愛樂樂團表現出極端的“緩慢美學”。特別是,像大海一樣波瀾壯闊的布魯克納交響曲的《Adagio》樂章將冥想氣氛和崇高的美麗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常說:“終點就在起點裡。”他深深陶醉於西藏佛教和東方禪學思想。他用這句富含哲理的話解釋了音樂的同時性和剎那性。
切利比達凱從來不是一個專門家。他的古典、早期浪漫作品的詮釋,帶著它們的內斂、活躍、優美與深奧,但從來不固執和自負或熟視無睹,完全沒有表面的敷衍,是極少有人真正的理解。
曲目系列
本套唱片便是這些珍貴史料中精華部分。收錄了柴科夫斯基《胡桃夾子組曲》、普羅科菲耶夫《第一交響曲“古典”》、施特勞斯《拉德茨基進行曲》、孟德爾頌《第四交響曲“義大利”》等膾炙人口的古典音樂篇章。CD 1
尼爾森
1《假面舞會》序曲貝爾瓦爾德
2-4C大調第3交響曲《離奇》孟德爾頌
5-8A大調第4交響曲《義大利》柴科可斯基
9-12《胡桃夾子》組曲特性舞曲
CD 2
羅森伯格
1《馬里奧耐特》序曲蒂爾森
2-4哈姆雷特-組曲莫扎特
5-8G小調第25交響曲普羅科菲耶夫
9-12D大調第1交響曲《古典》施特功斯(二世)
13《蝙蝠》序曲
14《安娜》波爾卡
15《閒聊》波爾卡施特勞斯(一世)
16《拉德斯基》進行曲
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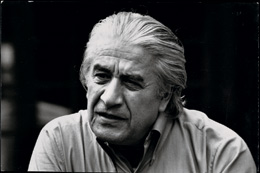 切利比達凱明
切利比達凱明切利比達凱訓練樂隊是以極其嚴格的態度而聞名的,在當今世界上的指揮家中,他是屬於在音樂會前排練次數最多、且對音樂處理要求最細緻的指揮家。他一般指揮一個樂隊開一場音樂會要排練20次左右,在排練過程中,他極其嚴格地訓導著樂隊隊員們來達到他的藝術要求,並且從不放過總譜上的任何細節,他的聽力是敏銳和超群的,任何細微的疏漏都逃不過他那雙如同機器般精確的耳朵。然而他那出奇嚴格的訓練方法和對藝術質量上的過高要求,也曾使他的指揮活動向更大範圍的發展受到過一些影響,許多歐美的大樂團都懼怕他那不留情面的嚴厲原則,故而不敢聘任他擔任常任指揮,這樣一來,便使得他由此失去了一些擴大名聲的良好時機,這大概也是他的名字鮮為人知的一個重要原因。
切利比達凱是一位以細膩、深刻和完美見長的指揮大師。他在指揮作品時,對於音色、表情和力度等方面的變化,處理得極其微妙和細膩。對於這一切,日本音樂評論家小石忠男曾說過這樣的話:“當我聽了切利比達凱指揮日本讀賣交響樂團演奏的音樂會後,的確感到那是一場令人感嘆不已的演奏會,切利比達凱的指揮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大師處理出的最弱音,可以說幾乎是在靜中將音響的幅度展開到空間的。在這裡,各聲部都有著自己明確的規律性,音樂的結構被毫無矯飾地揭示了出來,並以此製造出了聽眾與樂隊隊員同樣強度的緊張感覺。”
切利比達凱在指揮作品時十分注重於音樂內容的體現,他忠實於總譜上的每一個音符和記號,無論是在排練還是在演出中,他都從不任意地生硬賣弄和牽強附會,他所追求的是一種在極其自然的狀況和心態下的演奏。而真正做到寓表情於節拍中,在音樂中達到自己理想主義的要求,也就變成了他在藝術上的一個信念。此外,在他的藝術觀中,還努力地去追求在有限的空間裡與聽眾達到共同感受的目的,用小石忠男的話說,這表明了一種“在感情的表現上應具備的超脫的自由精神的哲學上的認識”。而這種觀點和認識,恐怕就是他極力否定錄製唱片的真正原因。
切利比達凱在演釋音樂作品時有著極為罕見的深刻性,並且每種演釋方法都有著包含哲理性的邏輯思維,這種特點是與他在年輕時代努力學習哲學課程的原因分不開的,他在排練時,經常教導樂隊隊員要學會用辯證的方法來對待作品,比如理解和分析音樂時,往往觀察的角度不同,就會產生出各自不一的看法與結論,而對於樂曲的分句法他是這樣理解的“當你們的腦海中像孩子那樣沒有任何困難的概念時,你們就會處理分句了。”
切利比達凱是一位異常嚴格的指揮大師,然而他卻不是一位粗暴的大師,他的排練雖然十分艱苦而漫長,但他卻非常善於誘導樂隊隊員的創造力和積極性。他曾對自己的指揮信念解釋到:“不能把意志強加給樂隊隊員,如果這樣做,充其量他們只會模仿你,而不可能有任何創造性的奇蹟出現。樂隊隊員從來不會問你為什麼要讓他們這樣做,那樣做,如果作為指揮家不是在他們的心田間播下藝術的種子的話,那么他只能盲目地跟著你走。”正是基於這樣的觀點,切利比達凱對於托斯卡尼尼的作法頗不以為然,他不贊成托斯卡尼尼在樂隊隊員面前的武斷做法,因此在他的眼裡,托斯卡尼尼雖然是一位偉大的指揮家,但卻不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