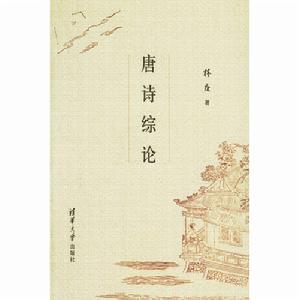版權資訊
作者:林庚著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7-1
版次:1
頁數:260
開本:16
定價:28.00元
I S B N:9787302123026
導讀
中國是詩的國度,詩國的高潮是唐詩,深入淺出而富於生氣的唐詩,給後人以無盡的新鮮啟示,並為今天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藝術借鑑。這是林庚先生對於唐詩的基本看法,也是他為什麼特別喜歡並潛心研究唐詩的根本原因。《唐詩綜論》是林先生數十年唐詩研究的主要成果,是有關唐詩研究文章的結集。文章分三組:唐詩高潮、唐詩遠音和談詩稿。後兩組文章所談詩篇和詩人,唐之前溯源《詩經》及屈原,唐之後涉及宋代詞賦和蘇軾,以此經之緯之,縱橫交錯,從而更凸顯唐詩的立體形象。所以,本書雖是文章的組合,卻有專著的效果。
林先生是詩人,又是學者,因而形成自己詩性學術的獨特品格。在唐詩研究中,始終以詩歌創作為指歸,意在“溝通新舊文學”,而“心在創作”,他說:“唐詩因此正如一切美好的古典藝術創作,它啟發著歷代一切的人們。”(《我為什麼特別喜愛唐詩》)為什麼而研究,決定怎么去研究,為了創作詩歌的借鑑,必然選擇創作主體的視角。回顧二十世紀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術史,學者多數選擇客觀批評的視角,對文學的歷史進行研究和評價;以創作主體的視角研究古典文學的學者並不多,所可舉者,聞一多、朱自清二先賢曾經嘗試過,而成就最高影響最大者,當推林庚先生。他的這部《唐詩綜論》如同他的《中國文學簡史》,都是選擇這一視角,因而在學術界獨樹一幟。
選擇創作主體的視角,自然要把握詩的文學本位,自然會貫徹詩的演進史觀,自然常採用詩的感性筆法,我們在閱讀《唐詩綜論》時,要特別注意這三個方面。
一、詩的文學本位 文學觀念是隨著時世的推移而改變的,即《文心雕龍》之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魏晉文學觀念的變革,擺脫了經學的束縛,確立了詩文正宗;近代文學觀念的更新,突破了正統的範疇,接納了戲曲小說。這裡所說的文學本位,自然是建立在這新的文學觀念基礎之上的。
林先生對於古代文學的研究,特別重視這種文學本位,著力於文學自身內在規律的探索,而外部社會條件對於文學發展的影響則相對地加以弱化。在唐詩的研究中,對於唐詩之所以發達,一般都要提到諸如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民族融合、大眾喜愛、帝王提倡、科舉賦詩等等外部條件,而林先生則不然,並不在歷史條件方面花太多的功夫,而且像科舉賦詩的作用,即便提到,也是極力加以否定。先生是位詩人,對於詩歌情有獨鍾,因而敏銳地發現,在這詩的國度里,詩成了整個文化的靈魂。他說:“詩簡直成了生活中的憑證,語言中的根據,它無處不在,它的特徵滲透到整個文化之中去。中國的文化就是以詩歌傳統為中心的文化,因此才真正成為詩的國度。”(《漫談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借鑑》)這無疑是很有見地的論斷。他以富於詩人個性的獨特視角直切詩歌的文學本位,因而在創作主體中偏重於寒士詩人,在創作方法中偏重於浪漫主義,在作家流派中偏重於山水詩派和邊塞詩派,在詩歌形式中偏重於語彙和格律。
林先生的唐詩研究,不同於一般批評者把目光投向詩歌所反映的具體社會現實,而是把握住創作主體的精神,提出了“少年精神”。唐代的創作主體是誰呢?是“寒士”。林先生認為中國古代作家大都屬於“士”這一階層,是中下層知識分子,出身寒微,生活困苦,通稱為“寒士”。他說:“中國古代的正統文學主要是代表著封建社會上升階段的文學,也就是以士為代表,以開明政治為中心的寒士文學。”(《中國文學簡史·導言》)唐代正是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曾推行開明政治,是寒士積極進取揚眉吐氣的時代,因而表現出一種“少年精神”。“少年精神”是積極的、進取的、“開朗的、解放的”,充滿“青春的氣息”、“樂觀的奔放鏇律”和“浪漫豪情”。李白是最富於“布衣感”的“寒士”,也是最富於“少年精神”的詩人,他“即便是悲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敗,也不失為英雄”,“他以布衣取卿相的豪情,他對權貴的抨擊和蔑視,都表現了這一集中的特徵,因而也就將寒士文學推向了高潮”(《唐代四大詩人》)。盛唐詩人詩作類皆具有“少年精神”,即便是發牢騷的詩,也是樂觀向上的,是對於權貴的蔑視;即便是寫空寂的境界,“也流露著與宇宙息息相通的無限生意”。正是這種充滿“少年精神”的詩人詩作,展現出“盛唐氣象”。林先生與“漢魏風骨”對舉,提出“盛唐氣象”,認為“盛唐氣象所指的是詩歌中蓬勃的氣象”,是“盛唐時代精神面貌的反映”,“蓬勃的朝氣,青春的鏇律,這就是‘盛唐氣象’與‘盛唐之音’的本質”,李白詩歌是“盛唐氣象的典型”(《盛唐氣象》)。林先生就是這樣,從寒士文學本位去把握唐詩表現出來的主體精神和時代風貌。
林先生認為敘事並非中國詩歌的主流,抒情才是中國詩歌的傳統。他說:“上古的神話——故事的淵泉——的佚亡,便加深了中國詩歌抒情的傳統。”(《中國文學簡史》)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最適合於抒情,最能體現這一傳統,所以林先生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浪漫主義作家,如對於屈原和李白的研究,就花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時間,晚年致力於《西遊記》的研究,也因為它是一部浪漫主義小說。他說:“從屈原到李白,中國詩歌中浪漫主義的優良傳統,從來是集中的表現了政治鬥爭的;愛國主義的精神,反抗權貴的品質,舉賢授能的開明政治理想,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上升發展中詩歌的中心主題”。(《陳子昂與建安風骨——古代詩歌中的浪漫主義傳統》)又說:“李白的詩歌氣質是浪漫的。這浪漫是意味著更高的解放要求,是帶著不可抑制的力量,是鼓舞著更為高漲的熱情的,這就是積極的樂觀的浪漫主義”, “那豐富的想像,解放的個性,通俗而飛動的歌唱,青春與浪漫的氣質,無一不是屬於那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這些表現為太陽般鮮明的形象,感染了無數的人們,這就是屬於李白的光輝的成就。” (《詩人李白》)一般人認為誇張是浪漫主義的主要特徵,而林先生則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種通用的表現手法,並非浪漫主義所特有。他說:“如果說夸張與浪漫主義之間也存在著某些特殊緣分的話,那只能說誇張的手法到了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中,似乎可以盡情發揮到完全不合理的程度。這並不是由於誇張手法有什麼特別之處,而是由於本質上浪漫主義乃是一種近於‘巨觀’的創作方法;正如現實主義乃是一種近於‘微觀’的創作方法;並由此自成不同的局面。”(《漫談李白詩歌中的誇張》)在他看來,現實主義表現的是現實,是存在,是形而下的,近於“微觀”,而浪漫主義表現的則是感情,是精神,是形而上的,近於“巨觀”。在社會上強調典型說的現實主義理論,把許多詩人詩作裝進現實主義大籮筐之時,林先生卻根據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更多地闡發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特性,並肯定其積極意義,這也反映出他那不同流俗的學術品性。
林先生對異彩紛呈流派眾多的唐代詩壇,尤其關注山水詩派和邊塞詩派。山水景物之進入詩中,早在《詩經》時代就存在了,只不過那時常作為民歌的起興,並沒有構成一種獨立的形象。魏晉六朝之後,詩中的山水景物,漸次削弱比興的象徵性,而取得相對獨立的品格,並成為感情的載體,於是山水詩也就應運而生了。這就是林先生所說的:“最初作為詩歌內容的起興,之後形成更廣泛的結合,最後在大量的作品中才出現一些單純寫山水景物的詩篇。而這些山水詩篇即使表面上並不直接道出具體的生活內容,實際上生活的氣息,思想的背景,時代的精神面貌是宛然可見的。”(《山水詩是怎樣產生的》)他認為山水詩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而不是由於士大夫的雅好園林,也不是由於隱士們的遁跡岩穴,所以說:“在山水詩廣泛的天地里,園林或隱逸並不占什麼重要地位,優秀的山水詩極少出現在那裡。”山水不是逃避現實的避風港,而是與生活息息相通的,唐代的山水詩,已成為熱愛生活熱愛祖國的真摯感情的表現形式,因此說:“真正把山水詩進一步的提高和發展,這是到了唐代。”他舉了王維、李白、杜甫等大詩人的山水詩作,說明山水詩“乃是封建經濟發展更為成熟的階段上自然的產物”。(同上)唯其如此,所以唐代的山水詩類皆積極向上,充滿對於理想的追求,在這一點上,和唐代邊塞詩有異曲同工之妙。先生說:“唐人的邊塞詩因此基本上乃是長城線上的邊防歌;以保衛邊疆的愛國熱情、昂揚飽滿的基調,豐富了一代的歌唱。”(《邊塞詩隨筆》)又說,唐人的邊塞詩,“並不在於寫戰爭,而是一種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充滿著豪邁精神的邊防歌”(《略談唐詩高潮中的一些標誌》)。邊塞詩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信心和盛唐時代豪情之上的,因此說,“沒有生活中的無往不在的蓬勃朝氣,所謂邊塞風光也早被那荒涼單調的風沙所淹沒”(同上)。林先生之所以特別關注山水詩和邊塞詩,是因為這兩個詩派所表現出來的熱愛生活積極進取的蓬勃朝氣和豪邁精神,正體現了盛唐氣象,從而成為詩國高潮的重要標誌。
林先生對作為語言藝術的詩歌的藝術語言,尤三致意焉。所謂語言,包括語義和語音,就詩歌語言來說,語義引出詩的語彙,詩化的形象詞語,即詩的原質;語音引出詩的音調音韻和音節,構成詩的格律。所以林先生對於詩歌自身的藝術規律的研究,尤用力於詩的語彙和詩的格律。唐詩語言之完美,林先生以為表現在能夠深入淺出,而又富於新鮮感受,說:“唐詩語言的特點,正在於不僅僅是淺出,而乃是‘深入淺出’”,“不僅是易懂而且是意味深長”(《唐詩的語言》);又說:“這深入淺出的詩歌造詣,又正是唐詩為人們讚賞的一個緣故。”(《從唐詩的特色談起》)深入淺出的關鍵是“悟”,是對於所捕捉的形象有所感悟。他說:“如果‘悟’是對於形象的捕逐,那么,漢魏就是還不曾有意去捕逐,而是聽其自來的,所以說‘不假悟也’;盛唐則是認識到捕逐而且達於深入淺出的造詣,所以是‘透徹之悟’。”(《盛唐氣象》)他以為形象既要深入淺出,又不能陳腐,也不能死板,而要鮮活地去表現,陳陳相因的模仿就沒有生氣,富於生活氣息才能鮮活,說:“新鮮的活力,帶著蓬勃的朝氣,形成為盛唐之音,展現為絢麗壯觀的廣闊天地,使我們感受到飽滿的藝術享受;這就是唐詩使我們百讀不厭的緣故。”又說:“如旦晚才脫筆硯的新鮮,這也就是盛唐時代的性格。”詩歌藝術是富於形象的,所以能否做到深入淺出,就在於“詩歌語言能不能深入形象的領域”,而這又“關係著詩歌能否充分的占領它的藝術領域”(《唐詩的語言》)。深入形象,才能創造出詩歌原質,才能用這種原質表達一種生活理念,才能達到“直覺的感性與明晰的概念之間的反覆辯證交織”,從而取得淺出的效果。漢語有音調之分,因而有平仄聲律;單音詞與多音詞的結合又構成音節;漢語讀音分聲母與韻母,同韻母字詞的搭配於句尾,稱協韻;由音調音節音韻的交織組合,構成了漢語的詩律。於是有五言七言古詩、絕句、律詩等詩歌形式。先生說:“唐詩的主要成就,是古體、絕句和律詩”,“總的說來,律詩富麗,絕句空靈,五古沉著,七古豪放”(《唐詩的格律》)。詩歌語言到了唐代,才趨於成熟,臻於完善,“唐代詩歌不易企及的原因之一,正是這詩歌語言成熟發展的結果”(《唐詩的語言》)。語言的原質和格律的創造,是林先生唐詩研究最為關注的兩個點,實際上也正是他新詩創作中用力最勤的兩個方面。林先生沒有從文學的外部條件,去論證唐詩所受的各種影響,去評價唐詩的歷史地位和價值,而是抓住唐詩的創作主體、方法、流派和語言,從文學本位切入,總結出一些內在規律,為當代創作提供借鑑。這也可以說是詩人論詩的一種特殊品位。
二、詩的演進史觀 林庚先生說:“一切結果都蘊藏在原因之中,而我們卻往往只見到結果;一切發展都包含在一個飛躍的起點上,這便是我們為之凝神的時候。”(《步出城東門》)這話正表明了先生辯證的發展史觀。這種觀點貫穿在他的中國文學史和唐代詩歌研究之中,如果說《中國文學簡史》是縱向的爬梳,那么,他的《唐詩綜論》則是橫向的解剖。但他在解剖唐詩時,也總是放在廣闊的歷史時空之中加以審察,認為:“詩所以是無盡的語言,因為它原是用無盡的歷史為背景的。”(《詩的活力與詩的新原質》)他不是孤立地研究唐詩,而是同社會政治思想聯繫起來研究,也不是靜止地研究唐詩,而是把唐詩作為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來進行研究。無論是巨觀的研究,還是微觀的研究,都體現出他那演進發展的史觀,在他看來,從“百家爭鳴”到“百花齊放”,從寒士文學到市民文學,從詩的原質到詩的格律,都是無盡歷史的演進過程,唐詩不過是這歷史鏈條中的一個環節。
林先生以詩人的敏銳眼光注意到,秦漢與隋唐的驚人相似之處。他說:“秦漢統一之前,春秋戰國的四百年是一個在戰爭歲月中度過的,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過程;而隋唐統一之前,魏晉六朝的四百年也正是一個在戰爭歲月中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過程。”又說:“歷史當然不會完全重演,後者將向更成熟的高潮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略談唐詩高潮中的一些標誌》)社會的分裂,固然給人民造成極大的災難,卻也讓人民打破了禁錮個性的枷鎖,掙脫束縛思想的樊籠,東周的禮樂崩壞了,出現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帶來散文的發展,因而有漢賦的繁榮;東漢禮教瓦解了,出現魏晉六朝的個性解放,帶來詩歌的發展,因而有唐詩的繁榮,從而出現“百花齊放”的局面。文學就是人學,因此思想的活躍,個性的張揚,是文學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唐代詩歌之所以能成為詩國高潮,如果說政治經濟的發達是其基礎,那么社會思想的解放則是其前提。唐代的社會思想是多元的,儒釋道三家並存,在詩人中,一般說來王維近佛,李白近道,杜甫近儒,但就每一位詩人來說,往往也是多元的,李白就很有些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林先生說:“李白的道家思想,是代表了建安以來知識分子的傳統;李白的儒家思想是代表了整個封建社會的基本思想形式。”(《詩人李白》)社會的發展,思想的解放,是經歷了四百年的戰亂才出現的,先生說,“回顧這些歷史的發展和詩歌的發展”,是想說明“唐代這一詩歌高潮的得來不易,它該如何值得我們珍惜”(《略談唐詩高潮中的一些標誌》)。在這裡,林先生正是巨觀地把握了唐詩高潮到來的必然歷史進程,體現了他的發展的史觀。
林先生認為隨著歷史的發展,文學創作主體和文學創作方式也發生變化。在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裡,詩歌創作的主體是寒士,而當工商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這主體便逐漸轉向市民;創作的方式也隨之由寒士的抒情,轉向市民的敘事,於是寒士文學也就向市民文學過渡。他說:“隨著封建社會逐漸走向衰落,正統文學也就日趨老化,這裡正是一個歷史的分界線,這樣,宋元以來,新興的市民文學乃日益興旺起來,而越來越居於創作上的主要地位。這寒士文學與市民文學之間的盛衰交替,也便是中國文學史上最鮮明的一個重大變化。”(《中國文學簡史·導言》)唐代為詩國高潮,也是寒士文學的高峰,李白是站在這個高峰之巔的偉大詩人,而杜甫則是“站在盛唐時代的終點”,在他之後,“詩國的高潮逐漸走向低落”,詩歌也漸次由抒情轉向敘事,“能將身邊瑣事的敘述與關心天下大事的議論渾成地融為一體,構成了他五古的突出特色”,從而“喚起了元白一派,也引導出韓孟一派”,白居易就“相應地表現為向新生的市民文學更為靠攏”,“市民文學的興趣以故事為主,白居易的《長恨歌》那么廣泛流傳,所謂‘一篇長恨有風情’,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他接受市民文學“這一潮流以後,便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輸入了愛情主體和婦女解放的主題”。中唐以後出現的變文、傳奇、曲子詞,都屬於市民文學,都對白居易產生較大的影響,他因此成為“正統文學的趨向終結和市民文學的興起”“這一文學上歷史性轉變的人物”。(《唐代四大詩人》)到了宋明以後,詩文雖然在舊觀念中仍居於正統地位,但實際上已被發展起來的戲曲小說這種市民文學擠到次要的地位上了。林先生說:“宋代詩文是中國封建時代正統文學的尾聲,這時市民文學已經出現,躍躍欲試的將要取正統詩文的地位而代之,這傾向到了元明兩代就全然是市民文學的優勢了。”(《漫談蘇軾及其前赤壁賦水調歌頭念奴嬌》)他正是這樣以演進發展的史觀來看待寒士文學的盛衰和市民文學的興起。
林先生注意到,詩歌是語言的藝術,從詩的原質到詩的格律,不僅有著一定的演進過程,而且各自都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而變化。他說:“在漫長歷史的發展上,這歷史雖然是一條線,其力量最初則只在一點上,……詩所以是一切藝術最高的形式,因為它真正的就是那點的化身。”(《詩的活力與詩的新原質》)這個“點”,就是詩的原質。先生所說的“原質”,或者可稱之為“意象”,是足以表現某種感情或事物的關鍵字,諸如琴、笛、柳、風、木葉、春草,等等,都凝聚著人們的某種感情,猶如被壓縮成一個點的一首詩。詩的原質是從生活中提取創造出來的,因而也有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但是,“詩的新原質的感情是一個較悠久的感情,它將帶我們走一段較長的路”(同上)。大自然的景物往往是詩人捕捉的對象,往往是詩人用典的縮略,從而成為詩的形象,構成詩的原質或意象;這些意象(原質)是由感性和飛躍性交織而成的,“詩人的創造性正是從捕捉新鮮的感受中鍛鍊語言的飛躍能力,從語言的飛躍中提高自己的感受能力,總之,一切都統一在新鮮感受的飛躍交織之中”(《漫談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借鑑》)。正是那充滿飛躍性的感性原質構成了詩歌的基本要素。形象的原質,久而久之,會變得抽象而出現概念化,所以要保持它的新鮮感,就要不斷創新,從生活中提取並創造出新的原質,這是語言詩化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是從語義方面來看語言的詩化過程;從語音方面看,語言音節的變化也有一個詩化過程。林先生髮現,從《詩經》的“二位元組奏”,到楚辭的“三位元組奏”,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過程,四言詩向五言詩、七言詩發展,正是有賴於“三字尾”。節奏的變化,引發句式的變化,又促進音律的完善,從而使詩歌格律日臻完美。所以,先生說:“從建安時代到了這個時期,語言的詩化過程經歷了約四百年才水到渠成。”又說“事實上詩化的過程並不是以五言形式的成熟而達於最高峰,五言詩的成熟帶來了建安時代的高峰,而更高峰則要到七言詩也繼之成熟的唐詩的黃金時代。”(《唐詩的語言》)律體完成於唐代,格律之嚴,音律之美,可謂到了極致。然而物極必反,最完美也就意味著終極,“那就未免呆板”,必須打破。所以林先生說:“唐詩以盛唐時代為代表,這是唐詩發展的最高潮,可是盛唐詩歌的主要成就卻並不在律詩上。”(《唐詩的格律》)在這裡,林先生正是從微觀的發展觀來審察語義和語音的細微變化所引發出來的語言詩化過程。
三、詩的感性筆法 形象化的抽象,藝術化的學術,這是林庚先生論著的一個顯著特點。先生以詩人的悟性去研究唐詩,往往有其獨特的感悟,因而在論述時經常夾進感性的筆法,所以他的論著如同創作一般,讀來新鮮活潑,充滿“理趣”。先生說:“所謂‘理趣’就是說理和發議論又是通過形象的思維表達出來。”(《漫談蘇軾及其前赤壁賦水調歌頭念奴嬌》)他對於唐詩的論述,正是這樣富於理趣。
通過形象來說理,實在是中國文化的悠久傳統。自從《詩經》創造了“比興”,這比興基因便遺傳到整個文化領域,歷代的詩文、戲曲、小說,乃至音樂、美術,無不滲透了比興的因子。《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經》時代結束後,出現了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都是文帶比興,尤其是百家的說理文章,更是把比興發展為寓言,乃至躋身於文學領地。至於把比興運用於詩文評論,也是早已有之。如陸機《文賦》有所謂“精騖八極,心游萬仞”,以形容作文構思,妙趣橫生;全文普遍運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說理,實開後人以詩論詩的先河。唐釋皎然評謝靈運詩之變化,曰“慶雲從風,舒捲萬狀”(《詩式》);敖陶孫評曹植詩之風格,曰“三河少年,風流自賞”(《臞翁詩評》),都是寓抽象於形象之中。這類感性化的說理,在歷來的詩文評中,比比皆是,所以說是一個悠久的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西學東漸,引進西方哲學和邏輯學,學術論著多採用抽象的概念和邏輯的推理,脫離了形象化的抽象和感悟式的說理這一悠久的傳統,以至有人誤以為中國人缺乏推理判斷能力。而林先生堅持採用感性的筆法,反而使人耳目一新,覺得頗富於活潑的感染力。先生說他在廈門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時,在黑板上“寫上‘文壇的夏季’,台下的學生就很興奮”(張鳴訪談錄《林庚先生談文學史研究》)。可見,先生的這種詩性的表述,生面別開,收到很好的效果。
林先生對於一個時代的詩風、詩作乃至詩體的看法,都喜歡用“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形象來加以形容或表述。“盛唐氣象”一詞,幾乎成了舉世皆知的林先生用以說明盛唐詩歌時代風貌的專用語。以“氣象”論詩,並非先生首創,唐釋皎然《詩式》云:“氣象氤氳,由深於體勢。”宋人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又云:“氣象欲其渾厚。”嚴羽《滄浪詩話》也每以“氣象”評詩,諸如“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其《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說:“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都以“氣象”喻指詩的氣質風貌。林先生認為盛唐遠紹建安,而建安有“建安風骨”的定評,於是借“氣象”一詞,標舉“盛唐氣象”,作為盛唐詩歌的總評。所以他說:“盛唐氣象乃是在建安風骨的基礎上又發展了一步,而成為令人難忘的時代”,“盛唐氣象是一個時代的性格形象,是盛唐詩歌普遍的基調”,“盛唐氣象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朝氣蓬勃,如旦晚才脫筆硯的新鮮,這也就是盛唐時代的性格”,“盛唐氣象因此又是一個詩歌時代總的成就,無數優秀的詩人們都為這一氣象憑添了春色。它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造詣的理想,因為它鮮明、開朗、深入淺出;那形象的飛動,想像的豐富,情緒的飽滿,使得思想性與藝術性在這裡統一為豐富無盡的言說。這也就是傳統上譽為‘渾厚’的盛唐氣象的風格”。(《盛唐氣象》)盛唐氣象的核心是時代精神,這精神表現為蓬勃的朝氣,豪邁的激情,猶如生龍活虎的年輕人,所以先生又提出“少年精神”這一形象的比喻,發展了敖陶孫用以評論曹植的“三河少年”一語,借“少年”喻興盛的時代。時代的興盛衰落猶如人的成長衰老,因而以“少年精神”喻指盛唐詩歌是頗為貼切的。與“少年精神”對舉的是“中年心態”,先生在評論北宋文壇時說:“一種中年人潔身自好的要求,一種近於清秋氣象的心情,便成為詩、文、圖畫甚至於哲學(例如理學)的共同基調。這時代的特徵,說明著封建文化的青春創造時代已不再來;但是還力圖在往日的基礎上別開著生面;這在詩文方面,蘇軾就是一個代表人物。”(《漫談蘇軾及其前赤壁賦水調歌頭念奴嬌》)
評論詩人詩作,先生也喜歡使用感性筆法,說:“如果說,王維的詩歌仿佛是新鮮的空氣,清盈而透澈,那么,李白的詩歌則是長風巨浪,波瀾壯闊”;“表現在詩歌上,李白飄逸不群,充滿天真;而杜甫則凝練深沉,波瀾老成”。(《唐代四大詩人》)評論詩體的品格,先生有時也帶進一些形象化的語言,說:“這時南朝的詩歌語言已成熟到萬事皆備只欠東風的階段,北歌便以其從生活語言中來的新鮮活力,仿佛一點催化作用,把它推向高峰。七言詩在這南北文風交流的高潮上,就如一個翻江倒海的弄潮兒,成了天之驕子。”(《唐詩的語言》)
先生不只是在評論詩風、詩作、詩體方面使用這類形象化的語言,採用感性化的筆法,可以說在對整個唐代詩歌方方面面的評析中,那怕是對一首小詩的分析,也是儘可能夾進生動的比興,所以能將學術性論文寫得像文學性散文,讀來有引人入勝之感。
這種感性的筆法,是生動化了,而準確性又如何呢?也許有人以為從抽象到抽象,從概念到概念,那種邏輯推理判斷比較準確。其實不然,每個概念都有一定的外延和內涵,概念的表述,自然只能限制在某一點或面上;而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又是紛繁複雜的,並非說一不二的東西,所以概念的判斷,往往看似準確,卻常常流於片面,反倒不如形象化的表述來得全面,來得準確,是模糊中的準確,猶如模糊數學。我們讀林先生有關唐詩的論著,就深感他那“少年精神”、“盛唐氣象”之類充滿理趣的表述,能讓讀者不斷從中得到新的啟示和新的認識,從而更加全面更加準確地把握唐詩的精神實質和時代風貌。
俗話說,文如其人。這通常是指文學作品,其實,學術著作,也是如此,文品是人品的寫照。在讀完《唐詩綜論》之後,只要追問一下,林先生為什麼要用創作者的視角去觀察唐詩,為什麼要直切唐詩的文學本位,為什麼要從唐詩的演進中去探索規律,為什麼要採用感性的筆法,為什麼特別肯定富於布衣感的寒士,為什麼特別讚揚詩中的自由民主思想,為什麼特別推崇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為什麼特別重視詩歌原質和格律的研究,我們必然會發現,這不就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詩人林庚先生所關心和尋求的一切嗎?他是如同唐代富於朝氣的寒士那樣的知識分子,他是嚮往自由民主的浪漫詩人,他希望在新詩創作中開拓一條新路,唐詩研究是他的寄託,也是他的追求,一切都是為了美麗的明天,所以他說:“讓古典詩歌優秀的成就,豐富我們今天的創作,鼓舞我們塑造出自己時代的更為輝煌的性格形象。”(《盛唐氣象》)林先生就是這樣,把古代的研究與今天的創作結合起來,把理論的研究與創作實踐結合起來;而這又成了最近成立的以林先生為主任的北京大學詩歌研究中心的宗旨。相信在林先生和詩界所有同人的努力下,詩國將會迎來新的高潮。
序言
我為什麼特別喜愛唐詩——代序
我在國小的時候,讀的課文還都是文言的,也就讀了、背了一些古詩,其中有李紳的《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小孩子們吃飯,有時把飯粒撒落在桌子上,大人們見了,就常給我們講應該怎樣愛惜糧食,以及種田不容易等等道理。自己聽了也都明白,可是總覺得不如這首詩給我的印象深。
當時我也還不知道什麼叫唐詩,現在才知道這就是唐詩的好處。它易懂而印象深。易懂也還不算難得,難得的是能給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更難得的是小時候就背熟了的詩,今天再讀時還覺得那么新鮮。這新鮮的並不是那個道理,道理是早就知道的了。新鮮的是對於它的一種說不出來的感受,仿佛每次通過這首詩,自己就又一次感到是在重新認識著世界。這其實就是藝術語言不同於概念的地方。
這種新鮮的認識感,不僅思想性強的作品中才有,一般的好詩中也都有。例如孟浩然的《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一種雨過天青的新鮮感受,把落花的淡淡哀愁沖洗得何等純淨!花總是要落的,而落花也總是有些可惜。春天就是這樣在花開花落中發展著。怎樣認識這樣一個世界呢?這就仿佛是一個新鮮的啟示。
唐詩的可貴處就在於它以最新鮮的感受從生活的各個方面啟發著人們。它的充沛的精神狀態,深入淺出的語言造詣,乃是中國古典詩歌史上最完美的成就。李白的《橫江詞》說:“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在這么驚險壯觀的景色面前,你到底是認為橫江好呢?還是認為橫江惡呢?這就逼得你必須自己去認識世界。
唐詩因此百讀不厭,永遠那么新鮮。也正是這種新鮮的認識感,唐代詩人們才能把祖國河山寫得那么宏偉壯麗。作為大自然的河山,其實千百年來並沒有多大不同,為什麼特別在唐詩中就那么引人入勝呢?這也就是我為什麼特別喜愛唐詩的緣故。
中國被稱為是一個詩的國度,唐詩就是這國度中最絢麗的花果。它的豐富的創造性、新鮮的認識感是祖國古代燦爛文化中永遠值得自豪的藝術成就。我們今天讀唐詩當然不是打算去模仿唐詩,模仿是永遠也不會讓人感到新鮮的。唐詩之後,模仿唐詩的人不知有多少,那些作品都早已被人們遺忘,而唐詩卻還是那么新鮮。我們讀唐詩正是要讓自己的精神狀態新鮮有力,富於生氣,這種精神狀態將有助於我們自己認識我們自己周圍的世界;而世界的認識卻是無限的。唐詩因此正如一切美好的古典藝術創作,它啟發著歷代一切的人們。
作者簡介
林庚,字靜希。詩人,文學史家。1910年2月出生,福建閩侯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1928年考入清華大學,1933年畢業後留校,同時擔任《文學季刊》編委。1934年起存北京大學等校兼課,講授中國文學史。“七七”事變後到廈門大學任教。1947年返京任燕京大學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著有《春夜與窗》、《問路集》、《空間的馳想》等六部詩集及《中國文學史》、《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問論箋》、《詩人李白》、《唐詩綜論》、《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等十一部文集。
目錄
總序 袁行霈
導讀 林東海
我為什麼特別喜愛唐詩——代序 林庚
唐詩高潮
陳子昂與建安風骨——古代詩歌中的浪漫主義傳統
盛唐氣象
略談唐詩高潮中的一些標誌
山水詩是怎樣產生的
唐詩的語言
唐詩的格律
唐代四大詩人
漫談李白詩歌中的誇張
從唐詩的特色談起
唐詩隨筆
“邊塞詩”隨筆
王之渙的《涼州詞》
說涼州
《古風》春種一粒粟——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之一例
詩的活力與詩的新原質
唐詩遠音
漫談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借鑑——詩的國度與詩的語言
屈原與宋玉
說“木葉”——《九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木蘭辭》中的燕山和黑山
青與綠
談詩稿
《野有死麕》
《君子於役》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青青子衿
《易水歌》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青青河畔草》
《步出城東門》
《短歌行》
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春晚綠野秀
寒槐漸如束,秋菊行當把。借問此何時,涼風懷朔馬。
漫談庾信《昭君辭應詔》
秦時明月漢時關
談孟浩然《過故人莊》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漫談蘇軾及其《前赤壁賦》、《水調歌頭》、《念奴嬌》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