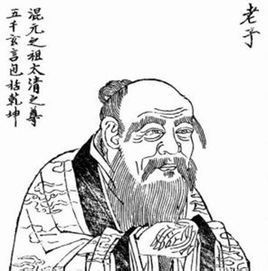歷史記載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並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佛經)雲其國王生浮屠(Buddha)。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Suddhodana),母雲莫邪(Maya)。浮屠身服色黃,發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後漢書襄楷傳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齊書顧歡傳云:‘歡著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畫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老子化胡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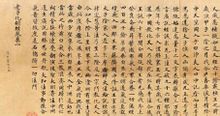 化胡為佛
化胡為佛《老子化胡經》,西晉道士王浮撰一卷。藉以抬高貶低佛教,後人陸續擴增為十卷。《通志·藝文略》即著錄為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六亦錄為十卷,並稱魏明帝為之序。《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著錄十卷,並引裴松之《三國志注》、《新唐書·藝文志》等說明化胡成佛故事的發生及對《化胡經》真偽的爭議。敦煌寫本有此經十卷本殘卷,存一、二、八、十等卷,系唐玄宗時寫本。按王浮所撰一卷本《化胡經》,早佚,後經增纂的十卷本,也僅存殘卷。主要內容是敷衍老子攜關令尹喜西入天竺,化為佛陀,立浮屠教,從此才有佛教產生的故事。現存唐玄宗時寫本之第一卷,記西域八十一國名稱,多與唐代典籍所載相同,當出於初唐。第十卷《老子化胡經玄歌》,則為北魏作品,可見此十卷本非一時一人之作。
化胡由來
1、學者大都以為道教抄襲佛教,其實那是指六朝後的道教,六朝之前則並非如此,相反的,中土的佛教,則自始至終都是在襲取儒道之思想以發展自己,並壯大自己的聲勢。從東晉而後,尤其自梁以後,佛教轉強而道教趨弱,此種情形一直延續至今,遂使人有佛教哲理高於道教這裡的錯覺。
2、學者習慣分道家與道教為二,以為一是哲學,一是宗教;事實上兩者在戰國時期已經融合為一。《老子》一書被道教徒用來做為修仙術,在戰國時候也已經存在。基本上混合老子清淨無為思想及吐故納新術來說真人。文獻見《文子 道原》《莊子 刻意》《莊子 在宥》《楚辭 遠遊》以及漢朝張家山出土漢簡《引書》、《河上公注》《論衡 道虛篇》、王阜《老子聖母碑》《老子想爾注》還有張陵以老子五千言為主要經典等。
3、初期的佛教傳揚不易,所以常依附於黃老道教而行。佛教攀援道教老子大抵可以從東漢明帝時楚王英說起,《後漢書》說其“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黃老、浮屠可以共祠,除佛教初期為了闡教刻意依附老子(老子“我有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和佛教重慈悲、戒貪、謙卑相同,可以比附)外,還和當時流傳老子入胡為浮屠有關。《後漢書》之《襄楷傳》所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老子化西胡品》引《太平經》云:“老子往西越80餘年,生殷周之際也”(《太平經》撰成在襄揩前)。並且,這種說法,未必出自道教徒,極為可能是佛教初傳,為求在中土流行,而刻意攀附。佛教攀附道教,混老子浮屠為一,自佛教傳入伊始就是如此,似乎一直沿襲到漢末,漢獻帝時牟融《牟子理惑論》中依然混佛老為一。到了三國魏末,魚豢《魏略 西戎傳》沿成其意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二十有九。”到了西晉惠帝世,道士王浮根據漢魏流傳下來的傳說撰寫了《老子化胡經》。上述老子化胡的說法,從漢至西晉,少有佛徒提異議,然而自東晉中葉後,佛教的勢力漸盛,不再須要攀附道教,於是開始反過來攻擊老子化胡之說。《老子化胡經》成為佛教徒去之而後快的首要經典,而王浮也成了泄憤的對象。
4、佛教東傳,有系統的譯經大抵從漢末桓帝時的安世高及靈帝時的支婁迦讖開始算起。關於世傳的《四十二章經》,呂征《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以為出自後人偽撰。安所譯經以禪法聞名,支則以般若聞名。二人譯經都假借了不少中土名相及思想。安《佛說大安般若守意經》中所言“清淨”“無為”出自老子,而“守意”“數息”則與漢時道教的“守一”和吐納導引有關。支則沿襲漢人嚴遵《老子指歸》之說,以“本無”來說明般若的“空性”,引老莊“有”“無”之論入般若學中。經過西晉到東晉初的名僧名士交流後,不僅名僧的地位提高了,佛教的理論也因為得到玄學的彌縫,轉而更為強大。原始佛教原本體論,經由支道林、竺法汰、道安等人,將玄學中老莊所言的道物、有無、本末、體用等本體論的探討,引入佛教中,形成了中土佛教特有的佛教思想,而有別於印度佛教。到了劉宋時,佛教勢力大盛,不僅可以和中國本土宗教道教抗衡,同時開始轉而攻擊道教,爭奪宗教的主導權,《弘明集》中所見夷夏論、白黑論等佛道及佛儒等攻防,即在此時展開的。佛徒多諳熟中土文化,而當時人皆昧於印度風習文化,因而佛教徒可以大言不慚地說中土道經是偽造的,佛經翻譯過來,是佛說的,是有根據的,不知道佛經第一次結集已遠在佛死後100年至數百年之久,釋迦牟尼本人並無撰經,佛經也是偽撰的。而時人對印度暗昧無知,因而每有論戰,總是佛徒得利,其勢力亦隨之而漸大,慧安時竟然可以倡導沙門不拜王者。
5、道教的哲理在先秦原本已有很好的發展,到了魏晉之世,也還能興起玄學熱潮,但是,自佛教勢力大盛後,才智之士轉而投入佛教陣營者甚多,入道教者漸少;遂使道教哲理方面的論述日漸式微,只能以術法見長,逐漸形成了術多而學少。相反的,佛教的哲理受中土哲理影響甚深,也因吸取中土文化而強大。格義和玄學化的結果,是采道家之珠玉來裝飾平凡之佛理,使化腐朽為神奇;這也是朱熹所說:“道家(道教)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卻去效釋氏經義之屬。譬如巨家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人家的破瓮破釜。”佛教吸收中土文化,初期是為了傳教所需,但到了六朝末期,甚至唐宋世,佛教已由站穩腳跟而到達極盛,卻依舊襲用中土名相及道教法術,甚至抄襲道經的情形產生。
中國的道教對待印度的佛教可能是另外一種民族神容忍別的民族神但決不能讓他們高居在自己之上的形式。在印度佛教傳入後不久,中國本民族的宗教道教就建立了。道教的建立雖說是受到了佛教傳入的影響,但它卻是由我國這個民族自身文化傳統中產生的一種宗教。道教的建立和發展,必然會和佛教發生矛盾和衝突。矛盾和衝突當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就表現為“佛道先後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發生,是由於道教提出了“老子化胡說”的故事引起的。所謂“老子化胡說”是說,道教的祖師爺老子曾到西方天竺國進行教化,而後天竺才有佛教產生。這個“老子化胡”的故事開始比較簡單,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記載老子至西方教化而有浮屠之教的材料是《後漢書·蘇楊郎襄列傳第二十》:“延熹九年(166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前上琅琊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這段記載只是說明當時有“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傳說,這種傳說的引起很可能是由於當時把老子和浮屠作為神加以禮拜之故。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道教尚未建立之前,已經有把老子和浮屠並列者,如(後漢書·楚王英傳)中說:“楚王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65)……詔報曰: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看來在東漢時帝王常把老子和佛看成同類的神,而後道教又把老子神化作為他們的祖師爺。據《史記》上說,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看到了周朝的衰微,於是西出關(據說是函谷關),這時函谷關的長官尹喜請老子為他著書,於是老子就作了道德上下篇五千言,而後西去,莫知其所終。由於原來就有老子西去的傳說,於是道教徒們就附會說老子西去入夷狄為浮屠。道教是中國所自出,佛教乃外來文化,中國素來持“華”、“夷”之見,把自己看成是華夏的文明地區,而把其他民族都看成是沒有開化的夷狄之邦,尊華夏而賤夷狄。從道教的觀點看,它自己是華夏民族的宗教,而佛教是外來的夷狄宗教,這兩種宗教怎么能並列呢?於是創造了“老子化胡說”,把道教抬高到佛教之上。但《襄楷傳》所載,僅僅說“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並沒有明確講到老子到天竺教化胡人:雖然我們可以分析說襄楷所說的話包含“老子化胡”的意思。到三國時,不僅出現了老子到西方教化胡人的說法,甚至有了老子是佛的老師的說法。據《三國志·魏志》裴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中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老子弟子,別號合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按:魚豢魏明帝(227—239)時為郎中,卒於晉武帝太康(280—289)之後。《魏略》大概作於曹魏之末。“《浮屠》”指佛教的經典《當為當時的某一經典》,此處所說的“《老子》經,”很可能就是指《老子化胡經》之類的“經”,當然不是指的《老子道德經》,因唐道宣《歸正篇·佛為老師章》的注說“出《老子》、《符子》”,或此處《老子》指《老子西升經》。與魚豢大約同時有杜摯作《笳賦》,在其序中說:“昔李伯陽避亂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造斯樂。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後漢書·竇章傳贊》章懷太子注說:“茄,胡樂也,老子作之。”《魏略》述老子化胡之說,杜摯《笳賦序》說老子入西戎作笳樂,可見三國時老子教化胡人的故事甚為流行。在漢末至曹魏這一時期,雖已有“老子化胡”之說,但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佛教徒方面對這種說法提出的反駁。推究其因,或因為佛教這種外來宗教在當時仍依附於中國原有的道術,而老子不僅是兩漢以來黃老之學推崇的對象,而且也是魏晉玄學所推崇者,其在人們心目中之地位當在佛之上,所以還沒有對“老子化胡”這一說法提出異議。至西晉初年,“老子化胡說”仍很流行,如作《高士傳》的皇甫謐嘗說:“老子出關,入天竺國,教胡王為浮屠。”皇甫謐大約生於漢末建安年間(215前後),死在晉武帝太康三年(282),《晉書》有傳。皇甫謐的這段話較之襄楷的話就明確多了。更為重要的是,在西晉時出現了一本據說是由道士王浮所造的《老子化胡經》。《老子化胡經》早已散失,後於敦煌石室得《老子化胡經》殘卷,據大忍淵爾《敦煌道經目錄》所載,有《老子化胡經》序,第一卷、第二卷、第八卷、第十卷等殘卷。但敦煌之《老子化胡經》殘卷據考證已不是西晉時的原本,而是經過後人加工擴大而成的。關於記載王浮造《化胡經》以及他和僧人法祖關於佛道二教正邪的爭論的材料,在此一時期有東晉末竺道祖撰的《晉世雜錄》、劉宋時劉義慶的《幽明錄》、梁裴子野的《眾僧傳》等。記載“老子化胡”故事的書也不少,如葛洪的《神仙傳》、東晉孫盛的《老聃非大賢論》、《老子疑問反訊》等。但最重要的材料應是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法祖法師傳》中的記載,其文說“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後更蘇,雲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又見祭酒王浮,一雲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爭正邪。浮屢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慧皎《高僧傳·帛遠傳》也有同樣的記載。帛遠字法祖,是晉惠帝時(290—306)的人,這時已是西晉中期了。從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到兩個問題:一是,在西晉時道教不僅有“老子化胡之說”,而且創造出了《老子化胡經》這樣的書,用以證明佛教是出於道教;第二是,西晉中葉後,佛教勢力漸盛,不再能容忍道教關於“老子化胡”的說法,因而與之爭辯。但是王浮與法祖爭論的內容不得其詳,大體上是爭論哪一種宗教是“正道”,哪一種宗教是“邪道”,似乎也還不是直接爭論佛道先後問題。《弘明集》卷一有未詳作者的一篇《正誣論》,在這篇文章一開頭就提出了佛道先後的問題,,其文說:“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講道德之經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眾聖之元始也。”這裡所說的“經”是《老子西升經》,在《廣弘明集》卷一中也引有這句話,即說出自《老子西升經》。《正誣論》這篇文章雖作者不可考,但文中說“晉言無為”云云,大體可斷定為西晉或東晉的作品。由此可知,在晉時佛教徒已可以把佛提高到老子之上,來為佛教爭取地位。但是這裡發生了一個問題,難道道教的著作《老子西升經》會自己說他們的祖師爺老子是佛的弟子?顯然是不可能的。其實我們仔細讀所引《西升經》的文字根本得不出老於是佛的弟子這樣的結論來。因為書中“古先生”是指誰並未明言,何以見得是指佛呢?據史料內容看,《老子西升經》大概也是西晉時的作品,而今存《西升經》有多種版本,據《道藏》中所收宋徽宗注本《西升經·西升章第一》說:“老子西升,開道竺乾,號古先生,善入無為,不終不始,永存綿綿。”同本末章《戒文章》第二十九說:“老君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將返神,還手無名,絕身滅有,綿綿常存。吾今逝矣……忽然不見……喜出庭中……即仰睹懸身坐空中,其狀如金人。”這段文字大概也不會是晉時原本的文字,但《西升經》既為道家著作,決無以“古先生”為佛是老子之師的道理,因此大義應是不差的。前面引的一段《西升經》所說的“古先生”自然只能是指老子,並說他去天竺開導其地。後一段更說明老子懸身空中,狀如金人,即變化為佛。晉時的佛教徒改《西升經》只改了個別字,加了一句“善為泥洹”,使文意不清,而解釋說“古先生”是佛,是老子之師。到唐初道宣的《歸正篇·佛為老師章》就改為:“老君曰: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云云,成為老子自己說他的老師佛“化游天竺”了。原來道教徒偽造“老子化胡說”,作《老子化胡經》,後來佛教徒又纂改道教經典,把本來是“老子化胡”的意思改為佛是老子師“化游天竺”。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宗教為了信仰的目的,要把自己的宗教派別抬高到其他宗教派別之上,不惜造假,用以騙人,也騙自己,這種事在宗教史上是屢見不鮮的。這一“老子化胡”問題的爭論越演越烈,佛道二教雙方都大量偽造歷史,把自己祖師爺的生年越提越早,越來越神化。東晉著名的和尚支遁作《釋加文佛像贊》其《序》中說:“昔周姬之末,有大聖號佛……呈百使以為粹,導庶物以歸宗,撥堯孔之外犍,……絡聃周以曾玄……”這樣一來,佛不僅是老子的老師,而且是他的祖師,老子和莊周只是佛的曾孫和玄孫輩了,連作佛的弟子的資格也沒有了。還是這個支遁又作《月光童子贊》,文中說:“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英姿秀乾竺,名播赤縣鄉。”月光童子是佛弟子,支遁說是月光童子來中國教化了中國,而不是佛自己來教化。不僅中國僧人的作品中說“月光童子教化中國”,而且這時翻譯的經典中也出現了所謂“月光童子教化中國”的說法,如《佛說申日經》中說:“申日有子,名旃羅法《原注云:漢言光明童子》……佛告阿難:我般涅槃千歲以後,經法且欲斷絕。月光童子當出泰國,作聖君,受我經法,興隆道化。”這部經收在日本《大正大藏》中,題為西晉竺法獲譯,但據唐智升《開元錄》卷二,在法獲譯《月光童子經》下注說:“初出,名《月光童子經》,或名《申日經》。”然查今存法獲的《月光童子經》,其中根本沒有上面引的一段,因此上引今本《申日經》中的一段顯然是後來的人加進去的。還有一種《灌頂經》也說佛派遣了所謂“三聖化導中華”,文說:“佛語阿難:……閻浮界內有震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所謂“震旦”,是當時印度人稱中國之名,或譯為“真丹”。“三聖化導”指佛派遣三個弟子化導中國。上引文顯然也不會是原來經文所有的,而為翻譯的人對抗“老子化胡說”而增加的。佛教在南北朝有很大發展,帝王、大族信奉者日眾,此時道教雖同樣也有很大發展,但畢竟趕不上佛教的發展。因此,到劉宋以後道教本身也逐漸受到佛教的影響。如前所言劉宋道士陸修靜已在一些問題上接受了佛教的影響,於是在道教中開始出現了一種向佛教讓步,調和佛道的趨勢。宋齊之際有道士顧歡作《夷夏論》,仍持中國傳統的“華夷之分”的觀點,以華夏為禮義之邦,而佛教為外族之教,“下棄妻子,上廢宗祀”,是夷狄之法。但在《夷夏論》中有下面一段反映了道教一定程度上向佛教的讓步,文中說:“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標二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割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無方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這段話中所引用的道經《玄妙內篇》仍持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傳說,但所引佛經又似言佛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不過這些並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顧歡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照他看,從國師道士方面說,最高莫過於老莊;從儒林之宗方面說,最高莫過於周公孔子,所以老、莊、周、孔的地位就相當於佛的地位。上述二部經典的說法無非是說:老子可以是佛,佛也可以是老子。意思是一樣的。所以顧歡得出一個折衷的結論“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佛和道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表現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和光同塵以明近,或者是靈光照耀以示遠。佛道的真理都是為的拯救天下,所以在任何地方都應適用。佛道的大聖人的智慧普及萬物,對任何事物都是一視同仁的。可見顧歡所強調的是佛道二教同有教化濟世的功用,老子和佛對世人說有同樣高的地位,他不再強調老子是佛的老師了。但是,此時佛教方面並不因為顧歡的讓步而妥協,他們還繼續堅持要在佛道中分一高下,有和尚慧通者作《駁夷夏論》,其文說:“論云:‘老孔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此外駁顧歡之《夷夏論》者尚有謝鎮之、朱昭之、朱廣之、袁粲、僧愍、明僧紹等。其中除袁粲托為道士通公作駁之文見《南齊書》者外,他文均見《弘明集》中。如宋釋僧愍作《戎華論》以折顧歡《夷夏論》,其文說:“……是以如來使普賢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既盡,回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這裡僧愍不僅肯定地說老子是釋迦的弟子,而且說明為什麼會有老子西出關之說。他說,先是佛派老子教化中華;在老子對中華進行了一番教化作了“五千言”之後,他的任務算完成了,於是西出關回天竺。於是有人就造出所謂“化胡經”的問題。僧愍的這些說法當然也是毫無根據的,不過他總算為“老子西出關”問題找到一種有利於佛教的解釋。在道教在這個問題上節節退讓時,當時的佛教徒卻毫不退讓。可見當時佛教的勢力是大於道教的。上述幾篇佛教文章除論佛道先後問題外,更主要的是說佛教的教理高於道教,這就不是本題所要討論的了。不僅南朝有“老子化胡”問題之爭論,同期北朝也在佛道兩教中存在著這一問題的爭論。北魏道士寇廉之集道教方術之大成,假託神人,依傍佛典,製作偽經,造浮屠為三十二天延真宮主之說,以抬高道教,據《魏書·釋老志》言:“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為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這裡所謂“經雲”當然是指某種道教經典。道教的寺院多稱“宮”或“觀”,“宮主”指某一“宮觀”的主持者,這裡說“佛”是“延真宮主”自然不會是指道教中最高級的神仙。按:《道教義樞》認為“仙人”的位業有三等:一三清位、二九宮位、三十轉位。所以“宮主”之位在“三清位”之下。寇謙之把佛排在“宮主”之位,也就是把佛教排在道教之下。魏太武帝信奉道教,以至於有毀滅佛法之行動。至孝明帝時,有佛道爭論於朝延之事,而所爭論之焦點仍為佛道先後問題。據《續高僧傳》載,正光元年(520),孝明帝請佛道二教上殿議論。有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人曇謨最對論。此事《廣弘明集》卷一亦載,其文尤詳: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教:“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綱。”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按《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元前605)……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敬王元年(元前519)……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元前1029)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元前949)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幾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昔佛生周昭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這一段記載雖說明至北魏孝明帝時“老子化胡”之爭仍在繼續,所謂《老子開天經》,乃上接寇謙之謂浮屠為三十二延真宮主之說,而佛教徒偽造《周書異記》及《漢法本內傳》以駁道教,亦當作於北魏中葉。至北周時,武帝曾於建德二年(573)又集群臣沙門道士辯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儒教為先者,乃帝歷來之宗旨。而先道後佛很可能是由於武帝受到衛元嵩的影響所致。於是佛道之爭又盛。有僧?著《十八條難道章》,又作《釋老子化胡傳》一卷,駁斥“化胡之說”。茲不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