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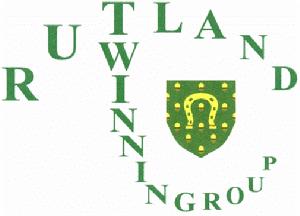
舉世矚目的哥本哈根會議於2009年12月7日召開,根據《巴厘行動計畫》,必須在本次會議上就2012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後的國際氣候制定達成新的協定。國際氣候談判已經形成兩大陣營、三股力量、多個主體、多重博弈的利益格局,各方角力左右著國際氣候制度走向。氣候變化終究是一個發展問題,它因發展而生,其應對措施也與發展階段有關。
美國作為最大的已開發國家,出於其國內利益需要和國際戰略考慮,沒有歐盟積極主動高調,但也不願意放棄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話語權。歐巴馬新政府上台之後,美國展示出積極姿態,但其中期減排目標甚至遠低於其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減排幅度,且以發展中大國參與作為自身行動的先決條件。其它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在政治立場上追隨美國,形成“傘形集團”,因為這些國家名稱的首字母組合類似英語單詞“傘(umbrella)”而得名。
立場
傘形集團主要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家。這些國家認為,強制減排不應該只是已開發國家所承擔的義務,開發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也應參與其中。傘形集團的中期減排目標低,且以一些開發中國家參與減排為前提條件。
2001年,美國政府宣布退出對已開發國家碳排放具有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2011年,難以完成減排任務的加拿大政府為避免支付巨額罰款,也正式宣布退出這一具法律效力的協定。
在《京都議定書》談判中,以美國為首組成的“傘形”國家集團,包含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俄羅斯等多個國家,曾經力量非常強盛。隨著日本、加拿大和俄羅斯先後批准議定書,“傘形”國家集團形式上瓦解,力量也大大削弱。
鑒於傘形集團主要成員都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因此該集團在國際氣候談判中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構建後京都氣候機制的談判中,傘形集團國家出於不同國家利益的驅動和影響因素的制約,表現出了一定的協調性,但是在一些具體的談判議程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從總體看,傘形集團在氣候談判中的立場與承諾同其應該承擔的氣候變化責任相去甚遠。
與其他陣營
歐盟
歐盟將自己視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領導者,在節能減排立法、政策、行動和技術方面一直處於領先地位。與傘形集團國家相比,歐盟在氣候談判中表現相對積極,支持《京都議定書》實施第二承諾期。
然而,歐盟僅僅視第二承諾期為一個過渡階段,極力主張在2015年前建立一個“涵蓋全球主要經濟體並具法律效力”的新減排協定,並在2020年後生效。在相關談判中,歐盟試圖拋棄既有成果,無視“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遭到開發中國家強烈反對。
77國集團+中國
該集團由廣大開發中國家組成,以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組成的“基礎四國”為龍頭,主張《京都議定書》“非附屬檔案一國家”(即開發中國家)落實自願減排行動,倡導南南合作;而“附屬檔案一國家”(即已開發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需作出進一步減排承諾並對開發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支持。
改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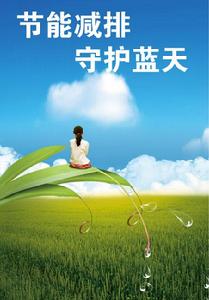 節能減排守護藍天
節能減排守護藍天國際氣候談判,涉及具體議題眾多,每一個議題都涉及各自利益,圍繞巴厘路線圖所明確的共同願景、中期減緩目標、適應、技術和資金五大要素。
共同願景
共同願景是《巴厘行動計畫》在公約長期合作行動中列出的要素之一,目的是為實現公約的最終目標確定一個到2050年的長期目標。但目前對達成長期目標的可行性、相關要素和法律地位等一系列問題存在意見分歧。歐盟認為共同願景需要全面、綜合、具體,並給出了具體的目標值:2050年2度溫升上限,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比1990年水平減少60%—80%;美國表示到2050年減排80%左右,但同時要包含發展中大國的指標,特別是要考慮當前排放和未來趨勢;日本表示長期非約束性目標是共同願景的核心,已開發國家要率先減排;俄羅斯、澳大利亞和韓國都表示共同願景就是一種意願,不具法律約束力;“77國集團+中國”則強調共同願景不應該只有減排目標,還應包括適應、可持續發展內容,應關注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的實施。2009年的八國峰會上已就2050年2度溫升目標和全球減排至少50%的目標達成一致,但這一目標的科學性和現實可行性尚未得到廣泛認同,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減緩問題
減緩問題,尤其是已開發國家2020年的減排目標,一直是應對氣候變化談判最受關注和最為困難的領域,主要涉及已開發國家的減排目標及相關的領域、機制和手段。目前關於減緩的談判議題有已開發國家2020年的減排目標、開發中國家適當的減緩行動、靈活機制、行業方法、國際航空航海燃料排放問題,等等。儘管每個議題都非常重要,但焦點集中在已開發國家2020年的減排目標上。根據美國眾議院已經通過的法案,美國到2020年將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排17%,也就是說,與1990年相比,美國幾乎沒有減排。日本、澳大利亞等其它已開發國家也提出了從5%到25%的目標。因而,目前有關已開發國家減排目標和開發中國家減排行動是氣候談判鬥爭最激烈的領域。
適應
適應問題在巴厘會議之後得到進一步重視,成為國際氣候制度關鍵要素。其原因是氣候變化已經給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造成影響,需要國際機制協調和共同應對。《巴厘行動計畫》達成了一些基本共識,即:依照公約框架儘快採取減緩氣候變化的緊迫行動;推動建立和實施國家適應計畫,以增強開發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意識和能力;建立適應基金機制,以協助最不已開發國家和最貧困群體加強適應行動的實施。
技術
技術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一直是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談判的重點和難點。長期以來,國際氣候談判在技術議題上進展非常緩慢,各方分歧很大。開發中國家強調技術轉讓的界定,不能將技術轉讓與技術貿易混為一談,主張建立全球技術基金,依靠非市場的多邊公共資金推動技術開發與轉讓。已開發國家一方面強調利用現有的資金,強調發揮私營部門和市場的作用,從而淡化政府的責任和提供新資金的義務,另一方面強調開發中國家也有責任改善國內不利於技術轉讓的制度環境,去除阻礙環境友好型技術吸收、消化、利用的主要障礙,包括加強專業人員的能力建設和相關制度建設等。
資金
資金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減緩、適應和技術需要穩定持續的資金來源。滿足資金需求,一方面依靠市場促進資金流動,另一方面需要籌集非市場的公共資金。為了在公約框架內繼續推進資金議題,各國就建立專門用途的新的資金機制提出了許多新的建議。就有關資金機制的管理問題,涉及資金的來源及分配方式,向締約方會議進行匯報的義務,成員國之間的均衡,透明度和易於使用等,也受到各方的關注。鑒於不同機制之間可能引起的資金分散問題,一些國家建議可以考慮建立傘形資金機制框架,在締約方會議的指導下統一協調和管理。除公約框架外的談判,在公約框架外新出現的資金機製備受關注。由英國、日本和美國三方出資、世界銀行具體運作的信託基金,包括三個特定的基金,即:清潔技術基金、森林投資基金和適應氣候彈性示範基金,另外還有戰略氣候基金,主要通過與地區發展銀行合作用於支持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項目。
與中國關係
中國已然於風口浪尖。按照國際能源署的能源統計,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在2007年已成為全球第一,人均排放也超過世界平均水平5%,而且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約有一半源自中國。中國“樹大招風”,由此可見一斑。這也使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面臨空前的壓力。
然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預期並沒有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需要近期承諾定量減排義務。根據一些著名的報告,如斯特恩《國際氣候協定中的關鍵要素》,以及已開發國家官方言論,他們希望中國在2020年前後承諾減排義務,在這之前並沒有要求中國做出絕對量的減排承諾。只希望中國做出國家適當的減緩行動。
中國政府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前宣布,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中國的減排承諾將是“一石擊三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能源安全和能源基礎設施,同時把自己提升到“綠色產業”領軍者地位。
坎昆失態
以主辦國身份孕育了《京都議定書》的日本,在坎昆會議上表態,要親手“掐死”《京都議定書》:“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日本都絕對不會在《京都議定書》的第二階段承諾任何減排目標。”
日本的強硬出人意料,但回顧歷屆國際氣候談判,比日本還“給力”的表演並不鮮見。德國總理默克爾曾經頭一天用眼淚征服所有談判代表同意在減排問題上加強合作,第二天就以保護本國汽車工業為名拒絕在合作協定上籤字。美國前任總統小布希,曾經公開用自己蹩腳的氣候知識,否認已開發國家的工業化與溫室效應間存在“科學”關係。
日本在各項國際問題上向來不願充當“帶頭大哥”的角色,總是習慣於望風而動。此次這么決絕,是因為它背後站著一個強大的傘形集團,包括美、俄等強國。它們大抵上本國環境保護做得不錯,優越感強烈,因此把環境惡化、溫室效應全都歸咎於開發中國家的不自覺上,“受人牽累”的受害者意識強烈。
它們總希望站在道德高地上對開發中國家施以大棒,迫使其為人類命運負責。日本從1990年—2008年的減排數據慘不忍睹,卻把退出《京都議定書》的責任,歸咎於開發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國家承擔責任不夠,歸根結底,還是那種“鄙人再不行也比你強”的心理作怪。
與傘形集團相比,歐盟倒是一直以減排領袖自居。此次坎昆會議,歐盟就表態,願意單方面到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0%。但歐盟的承諾與落實之間差距太大,並不能讓開發中國家心服口服。
傘形集團和歐盟要么自掃門前雪,要么口惠而實不至,但是很多開發中國家也不能因此完全規避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中國把節能減排納入“十二五”規劃的舉措,就代表了新興國家在環保意識與決心方面的巨大進步。但是,也應看到,一方面,許多國家的國力和治理能力根本不足以承擔國際減排這樣的義務;另一方面,許多開發中國家把國際援助當作本國行動的前提,拒絕重新審視本國失當的經濟與環境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惡化了談判的外部環境,也給了已開發國家更多口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