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基本信息
作 者:《新周刊》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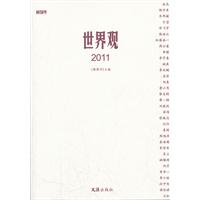
出 版 社:文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1-1
版 次:1頁 數:267字 數:160000
印刷時間:2012-1-1開 本:32開紙 張:膠版紙
印 次:1I S B N:9787549604074包 裝:平裝
編輯推薦
一度,我們總覺得外面的世界比內心的世界重要,物質的東西比精神的東西重要;我們總以為快比慢好,高比低好,多比少好,大比小好……但結果呢,好像不是這樣!
好在明白人越來越多了!雖然人與人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大,觀點也越來越紛雜,但大家還是有一個共識:如果你丟掉了自己內心,就算擁有了整個世界,你其實還是一無所有!
內容簡介 三年前,《新周刊》創辦“世界觀”這個欄目,其目的,就是想讓大家回過頭來,看看自己內心的這個世界,並努力在其中找回那個一度迷失的自我。
收在書里的這些訪談,都是些明白人的心得,你或許不一定同意他們的觀點,但他們朝向自我內心深處的注視和探索,相信會對大家有啟發。
作者簡介 《新周刊》,一本觸覺敏銳、視角獨特、觀點犀利的新銳雜誌。
目錄
序
北島:你得跟自己較勁,你得跟自己過不去
陳丹青:我不知道怎么會變成這個樣子
齊邦媛:我的人生無大怒也無大樂
于堅:我們像灰塵一樣被趕到了大地上
畢飛宇:外部不停地在建,內心不停地在拆遷
熊培云:這個世界不是我搞壞的
加藤嘉一:一個堅持不了原則的男人,別指望有女人
周雲蓬:人應該像螞蟻一樣專注地解決問題
李健:我要和生活平起平坐
李宇春:今年是我出道第六年
姚晨:生活給我什麼,我就接著
李亞鵬:40歲,我找到了我的事業
孟非:生活從下班開始
劉春:超越欲望的方式就是實現欲望
黃小茂:有勇氣面對以前,你就是成熟的
張發財:活著就是尷尬
廖一梅:偽善是對愛最大的戕害
劉慈欣:只有在科幻里,我才是個理想主義者
梁鴻:每個住在城市的人都應該有原罪感
張鐵志:我信仰愛情,我還有激情
瀋陽:宅在家裡也能改變社會
春樹:村上春樹是我最大的競爭對手
周鴻禕:不要把我描繪成一個鬥士
秦海璐:我們只是走在尋找愛情的道路上
朱哲琴:我連一雙翅膀都沒有,我對自己很不滿意
袁立:我不崇拜什麼演員
姚錫娟:我只是一個朗讀者
向京:在現實中,我是一個逃避者
李華一:心中有淨土,才會畫出淨土
李小牧:不像漫畫那樣順順利利的,才是人生
孫中倫:我不是你們想的壞小孩
梁詠琪:嫁個好人好過嫁個有錢人
王虹:如果有三天光明,我想看看我的紫砂壺
線上試讀部分章節
畢飛宇:外部不停地在建,內心不停地在拆遷
生於1964 年,江蘇興化人,作家。畢業於揚州師範學院。2011 年3 月以長篇小說《玉
米》獲得第四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8 月,長篇小說《推拿》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我第一天拿起筆來就伴隨著莫名的壓抑感。其實我天性並不壓抑,相反,是個很樂觀的人。但是,當我寫小說時,那種壓抑感就會跳出來了。寫完《青衣》之後,我發現壓抑和痛感
正是寫作的動力。
二十多歲時,就是想用一句話把世界放倒。非常瞧不起小說,只想做一個詩人。我是1983 年讀的大學,那時候人們心目中的英雄是顧城、舒婷。不過,我很快就知道自己愛詩歌,但能力不在這裡,我還是擅長敘事。大學畢業之後,當了教師,突然發現時間太多了,詩歌十分鐘就寫完了,需要找個能夠“殺”時間的事情來做,於是開始寫小說。表達欲一直伴隨著我,這個很重要。跟語言的親近感也是天然的。
我脾氣急躁,從來都以為自己沒有耐性。開始寫小說之後,才知道原來那么急躁是因為沒有找到適合自己做的事情。我常常一寫小說就是十五六個小時,停下來之後,需要想一下,今天到底有沒有吃晚飯啊?
從鄉村、小鎮到縣城、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這樣的成長經歷讓我一進入文學這個行當就有比較寬的“戲路”。35 歲之後,我才敢走寫實道路。45 歲之後,如何面對急速變
化的中國都市以及不停改頭換面的文化形態,倒是一個新的問題。進入都市後,我們的生活範圍是很小的,視野受限。拓寬生活半徑是當務之急,我常常需要通過朋友的關係到處去
看,觀察各色人等的生活。
以前,我的自信心有點不可思議。1994 年,給張藝謀寫《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劇本時,我都沒去過上海,就是張藝謀拿了一本《上海灘秘史》給我,五六百頁,我翻完就開始動
筆。寫《青衣》的時候就看了一本《京劇知識一百問》。小說出版後,有人以為我是一個老大爺,還有人認為我與某個京劇女演員有徹骨的痛。所以,新聞的本質是真實,而小說的本
質則是虛構,小說家需要虛構的能力。前幾年,我運動受傷,去做理療,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樣子,跟推拿師幾乎每天見面、聊天,有些還成了好朋友。後來我寫了關於盲人推拿師的小說《推拿》,但是跟推拿師們聊天的內容沒有寫進去。某些事情會觸發我的想像,變個樣把
故事的模樣換了,因為我不希望我的盲人朋友對號入座,那樣會傷害他們。其實一旦了解規律性的東西,有些故事可以通過想像完成。虛構是小說家的基本功。那種非得將事實本
身寫出來的誘惑是沒有的,這就是作家與記者的分別。《推拿》出版後,通過有聲讀物,我的盲人朋友很快聽到了,他們很高興,又有點意猶未盡,覺得有許多故事比小說更精彩,還經常打電話給我講各種故事。他們特別渴望對號入座,猜測小說中的人物到底是哪個。但是,與他們聊起來,他們只會說,你寫得好啊。我當然知道這其中有某些客套的成分。很多人認為我擅長寫女性角色,我倒並不這么認為,只要我對某個人物感興趣,就能將他(她)寫好。有時大家覺得某個人物特別出彩,很可能是我寫這部作品的創作狀態比較好,讓人物有了光彩。
作為小說家,一定會有偏好的人物,一種是情感上的,一種是美學上的。比如,從小說美學上講,《玉米》的主角玉米在各方面更飽滿,但是,從情感上我更關注有慶家的。這個人
一出現我就格外小心。我年輕時做老師,一直提醒自己要對學生一視同仁,但我也知道只要是一群人,就難免有親疏。小說家對作品中人物的親疏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人之常情。
有慶家的善良、美麗,又是被損害的,自然我會站在她的一邊。但小說家又不能被人之常情牽著走,小說有自己的邏輯,需要自己平衡。所以,福樓拜寫到包法利夫人自殺後會大哭。
在礦業大學的那個假期,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說。當時寫小說的那支筆裂開了,纏了一層又一層的膠帶,上面是一個假期的汗水和塵垢。當時覺得有種悲壯感,後來想,有什麼好悲壯的呢?寫完一個作品跟計程車司機拉完一天客也沒有什麼區別。
每一部作品的寫作過程都是痛苦的,那些神來之筆對寫作的人都是坎,是對作者的一次次折磨。我是一個宿命的人,很相信運氣。33 歲時,《哺乳期的女人》獲得了魯迅文學獎。
得獎早對我來說是一個好事,因為很早就能看清這一點:有些作品自己寫得很滿意,但是發表之後默默無聞;有些作品寫的時候沒費什麼勁,卻能獲得滿堂彩。我得學會習以為常,
無論什麼結果都隨它去吧。宿命感與天性中的悲觀情緒有關,但我本身是個樂觀的人。悲觀的是巨觀的生命,很早就知道人總要死的。所以,無論瞬間有多么輝煌、快樂,最後都是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不需要有多深的哲學素養,而是某個神經類型決定的。我愛運動,每天都在健身房與鋼鐵器械打交道,最後都是一個失敗的形象回家。因為弄不動了才會停止,而當你停下來,就是精疲力竭、被那些器械打敗的時候。我每天都在面對這樣失敗,對於失敗就很坦然,這是所有狀態的最終歸宿。
我們的文化是一個壓抑的文化,我們的現狀也是壓抑的,在權力和資本面前,人們會覺得渺小。我在《推拿》和《玉米》中都寫到了性壓抑。性壓抑其實是一個修辭手法,對寫小說的人來說,性是一個公器,能夠說明很多問題,有很好得時代特徵。《玉米》中的性壓抑是“文革”時代集權政治的壓抑,而《推拿》中的性壓抑是商品時代的壓抑。對於中國人來說,能夠壓迫他們的也就是權力和資本這兩座大山。時代發展太快了,中國處於快速的上升期,又遇上這個快速的時代,就是一個加速度。五年前的手機和iPhone4 放在一起,感覺一個時代過去了。所以,有人戲言,90 後是懷舊的一代。當然,時間是恆定的,快與慢更是人心理的映照。處於高速發展的時代與遇上一場戰亂沒有區別,每天都在和和美美地妻離子散。這對於小說家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時代,有很好的素材。我們看到外部世界如此繁榮、強大,其實內心破爛不堪,外部不停地在建,內部不停地在拆遷。兵荒馬亂,如何收場?我也不知道。大家都無法節制,今年收入3億,明年一定要4 億,能力已經達到3 億了,內心的欲望告訴
你沒有4 億不行,只有得到4 億之後才能存活。但是不發展又怎樣呢?好像誰也不知道。未來像宇宙一樣,無邊無際,沒有盡頭。沒有一個人會告訴你,到哪一點可以停止了。所以,我渴望的時代性就是尊重局限、尊重節制。但問題是沒有人會選擇克制。在外在的價值評判上,也與無節制發展有呼應。身價2 億的人得到的關注和肯定比2000萬的多。人人都為著更高更強拼殺,文明社會便成了一個叢林。這幾年,網路中最時髦的詞都是表達負面的,糾結、悲催成為全民使用率最高的詞。這是時代的問題,人的幸福指數很低,一旦有一個表達負面的東西,就會廣泛傳播。
作為一個宿命的人,只有一個辦法應對這個不斷膨脹的世界,那就是更加開心地活著,更加踏實地幹活,用內心與外部世界周鏇。否則,一個蘋果手機就可以把你的人生毀了。一會兒iPhone4,一會兒iPhone4s,不停地換,不停地追。所以,我覺得我兒子挺了不起的,我給他iPhone 時,他說,不要,我為什麼要和別人一樣。
(採訪/ 金雯)__
採訪手記
坊間有一種說法,畢飛宇能在三分鐘內讓女人對他產生好感。但是,畢飛宇應該是個傳統的爺們。比如,當我讚揚他是最帥的中國男作家之一時,他便有些生硬地說,外貌對我來說沒有什麼作用,既不能讓我寫出好作品,也不能讓我的書賣得更好。其實我只是想說他長得不錯,像讚揚女人的外貌一樣,這樣的開場白有時不過是寒暄。當然,很多爺們會不太習慣。
他是個極具雄性氣質的人,卻能描摹女人最豐富細膩的內心和情感。對於這一點,他並不完全認同。他說,只要我喜歡某個角色,就能寫好,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老人還是小孩。我相信這是實話。
孟非:生活從下班開始
1971 年生於重慶。1991-1992 年,在江蘇廣播電視報印刷廠做印刷工。1992-1996年,在江蘇電視台文藝部體育組擔任攝像,開始新聞工作生涯。2002 年起至今,先後擔任《南京零距離》、《絕對唱響》、《名師高徒》、《非誠勿擾》等節目主持人。我從前就說過:生活從下班開始。
其實這句話並不意味著我下班後的生活多么豐富多彩,只是我覺得現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精力和生活都是圍繞著工作,莫名其妙地公私不分,下了班還要去應酬,還要去吃那些不想吃的飯,去見那些不想見的人——這是我特別不喜歡的。有次我在從上海回南京的火車上,旁邊坐了一個女人,從上火車開始,她就沒閒著。一個多小時,她始終在打手機,先就家裡的垃圾該怎么處理跟人吵架,然後說公司的業務,給這個說完給那個說,說得沒完沒了。我心想:你至於嗎?你那點破事兒,遲點打會死啊!但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你看那些成功人士,成天都不知道在忙些什麼,打不完的電話,見不完的人,我特別討厭這種生活。
我現在算不算成功人士?從一般社會大眾的感受來說,應該還算可以吧,我要覺得自己還怎么不行,就太矯情了。但人總是還有更多奢望,總是追求自己目前還沒有的那些東西,只要你還有沒能實現的東西,你就總覺得還有目標。現在我所追求的是——可以對我不想做的事情說“不”。聽起來很簡單,其實大多數人都做不到,現在的我也做不到。原因……可能是混得不好吧。(笑)
我沒想過什麼叫好的生活,借用我們節目男嘉賓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要實現財務自由和時間自由。財務自由這話聽上去特別裝,你說你想多掙錢不就完了?但我想時間自由是大多數人都追求的,包括我。我覺得我應該知足了,但又總是希望能更多地支配自己的時間。
如果真有所謂“娛樂圈”,其實我沒什麼圈裡的朋友,就連熟人也沒幾個。我跟這個圈的人沒什麼交往,不是說我不想,而是我不知道該從哪兒開始,我不清楚別人是什麼情況,但我真不知道該從哪裡交朋友。我的朋友大多是過去的,小時候的朋友,或是在工廠里的時候認識的。我想這和年齡有關,和性格也有關,歲數大了一點之後,那種結交別人的願望會大大降低。應酬上的朋友有一些,其中也有比較談得來的,但是這種情況不太多,好玩的人太少了。
我看自己的節目不多,除非家裡人看,我才會跟著看。我的家人也沒那種“非看不可”的心態。其實主持人這個職業既沒有某些人說的那么風光、那么陶醉,也不至於像某些人所說的那么令人沮喪,或者那么不堪。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在舞台上呈現給觀眾的那些東西,一定跟在生活中的自己有重疊的地方,但不完全和生活中的你是一樣的——比如愛情、婚姻和家庭之類的話題,你覺得生活中的我會是一個有興趣討論這些的人嗎?
以前做新聞節目的時候,晚上八點鐘下班,差不多八點半到家我就會關掉手機。現在習慣不同了,我有時候不得不很晚才關機,有時候又根本不開機。做《非誠勿擾》這一年半,對我改變得比較大的是作息時間,我是那種只要生活習慣被打破就會煩躁的人,這是一種不太有出息的性格。現在不是都說要學會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嗎?我就特別怕面對挑戰,所有的挑戰我都害怕面對。
我從來沒有思考過自己的定位和風格是什麼,我並不是那種有很多風格可供挑選的人,我只有一種風格,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一種。你別問我這種風格叫什麼,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回歸新聞領域?那得看電視台需不需要。我絕對不是一個會積極策劃自己方向的人,很多次接受媒體採訪,我都有說到這件事——我在電視台的每一項工作,都是服從安排的結果,沒有哪件事是我主動爭取的。我從來不敢看百度百科“孟非”詞條下的那篇文章,每一次看到,我都會震驚。其實我做工人的那段經歷挺普通的,做工人不是挺正常嗎?中國有多少人在當工人吶!也不見得當了工人就怎么曲折坎坷,沒那么誇張,它確實是我生活當中的一個部分,僅此而已。我那時候沒覺得自己要成就一番事業什麼的,也從來沒有過“我不是一個凡人,我終有一天會風雲上九重”這樣的想法。我只是覺得,能有一份比當時工資高一點的事兒乾乾,也特別好。
我沒想過到底什麼算是人生中的低潮時期。在《非誠勿擾》之前,我做死過很多檔節目,那對我來說也不算是低潮,因為做死過更多節目的主持人也活得好好的,我憑什麼就活不下去了呢?這可能牽涉到每個人的評估標準不同。就像失戀這件事,擱在有些人那兒就不算個什麼事,鬱悶兩天,找朋友說一說,喝個悶酒,弄個什麼事兒打打岔也就過去了,生活再重新開始嘛。但換個人他就有可能去尋死,他就活不下去了。同樣這樣一件事,我們有多大的反應,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評估。
每個人的每一段經歷都會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起碼我的人生中經歷過的事情,會讓我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時候,天然地持有某種傾向性,或者說立場。和那些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相比,我更有可能會站到某一個群體中去想問題。微博上的我確實有一點憤青,我現在儘量不讓自己有憤怒感。但在當下的中國社會,不管你把自己叫知識分子還是知道分子,作為一個社會工作者,如果最後那一點點東西都全部泯滅了的話,我也真的挺難想像的。
2011 年我出版了一本《非說不可》,之前編輯給寫了個作者簡介:“孟非,生於山城,長於金陵。自由之擁躉,藩籬之逆子。隨心所欲不逾矩,遊戲于山水間,縱情於金陵城。安守
恬淡之秉性,不拒聞達之奇遇。行走於人世間,點點雲,淡淡風,且行且吟。”我實在接受不了,就自己給改了:“孟非,不惑之年,還常有困惑;不意聞達,還是俗人一個;不喜爭辯,有話還是非說不可!”
書這個東西,它會跟你一輩子,我不希望過幾年再看到這個東西,自己都覺得自己很丟臉,我沒人家說的那么好。包括現在出版社要出的一本書也是,我把所有自戀的宣傳詞都給刪了,什麼“非常經歷”,什麼“難忘”、“坎坷”、“艱辛”……這一類的修飾詞,統統都不要,回顧過去的經歷就可以了。我是那種隨遇而安的人,我的下一本書,名字就叫《隨遇而安》。
台上的小姑娘喜歡叫我“孟爺爺”,那就叫唄!我不怕她們把我叫老了,叫我孟奶奶我也不介意。我馬上就要40 歲了,老實說感覺有點沮喪。想想自己剛工作的時候,看到一個40
歲的男人,當時覺得他多老吶!而現在我就是那樣的年齡。
(採訪/ 丁曉潔)
採訪手記
不止一次,有《非誠勿擾》的編導跟我說:我敢保證,任何一個記者看到的孟非都不是真的孟非,至少不是我們看到的那個孟非。真正的孟非究竟是什麼樣?他說自己是個隨遇而安的人。跟他聊天的過程中,他說得最多的三個字是:無所謂。做娛樂還是做新聞?無所謂。出
版的書滿不滿意?無所謂。別人都叫你“孟爺爺”?無所謂。意外的是他居然喜歡看東野圭吾的小說,我說這不像是一個40 歲男人看的書,他的回答還是——幼稚就幼稚唄,無所謂。
總是說著“無所謂”的孟非,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他才是活得真正清醒的那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