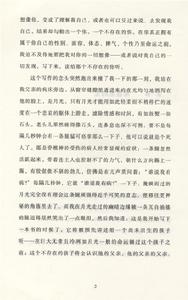基本信息
 《聆聽父親》
《聆聽父親》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1-1
字數:155000
版次:1
頁數:243
印刷時間:2008/01/01
紙張:膠版紙
ISBN:9787208076426
包裝:平裝
內容簡介
全書以與未出生的孩子對話的方式,從祖上五代開始,說到父輩,說到自己所處的時代。 除了父親的講述外,更貫穿了六大爺所寫的“家史漫談”,另有友人的回憶與敘述。大春祖家——山東濟南張家“懋德堂”,是一個有著五大院落、幾百口人丁的顯赫家族。祖規家訓“詩書繼世,忠厚傳家”在世事變化中,悄悄改換成兩副與“福”、“貴”相關的楹聯,張家祖業便也從詩書功名轉為經商富貴。當中國進入20世紀中期抗戰期間,全家更是在顛沛流離而充滿傳奇色彩的經歷中見證了時代的動盪和變遷。作者在追憶中不斷講述家族故事,溯源中國文化,表達了憂鬱而深沉的中國文化鄉愁。
這是一部在時代變遷中觸摸個人血脈的故事,讓我們見到有血有肉的“歷史”,也是“‘小說工匠’張大春的性情之作”,更是張大春小說創作的精神源泉。而作者以個人的家族史來搶救家族記憶,以文化溯源的方式拯救文化凋敝的意圖,也在書中表現得很明顯。
作者簡介
張大春,當代最優秀的華語小說家,1957年生,山東人。好故事,會說書,擅書法,愛賦詩。台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曾任教於輔仁大學、文化大學,現任電台主持人。作品無數,曾以“大頭春”的名字出版系列小說《少年大頭春的生活周記》、《我妹妹》、《野孩子》,另著有小說《雞翎圖》、《公寓導遊》、《四喜憂圍》、《大說謊家》、《歡喜賊》、《夸幫暴力團》、《聆聽父親》、《春燈公子》、《戰夏陽》等,京劇劇本《水滸108》,文學理論《張大春的文學意見》、《小說稗類》等。曾獲聯合報小說獎、時報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等。
目錄
第一章 角落裡的光
第二章 預言
第三章 我從哪裡來?
第四章 傳家之寶
第五章 書寫的人
第六章 我往何處去?
第七章 土地測量員
第八章 日夕望君報琴至
第九章 聆聽父親
媒體評論
第一次,他如此之老實,甘心放棄他風系星座的聰明輕盈,有聞必錄老實透了地向他未出世的兒子訴說自己的父親,父親的父親。
第一次他收起玩心不折不扣比誰都更像一位負責的父親。
第一次他不再操演他一向的主題——真實/虛構。
第一次,他暴露了弱點。
——朱天文
書摘
第一章 角落裡的光
我不認識你,不知道你的面容、體態、脾氣、個性,甚至你的性別,尤其是你的命運,它最為神秘,也最常引起我的想像。當我也還只是個孩子的時候,就不時會幻想:我有一個和我差不多、也許一模一樣的孩子,就站在我的旁邊、對面或者某個我伸手可及的角落。當某一種光輕輕穿越時間與空間,揭去披覆在你周圍的那一層幽暗,我仿佛看見了另一個我——去想像你,變成了理解我自己,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說,去發現我自己,結果卻勾勒出一個你。一個不存在的你。在你真正擁有屬於你自己的性別、面容、體態、脾氣、個性乃至命運之前,我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對你的一切想像——或者說對我自己的一切發現,寫下來,讀給那個不存在的你聽。
這個寫作的念頭突然跑出來撞了我一下的那一刻,我站在我父親的病床旁邊。從窗簾縫隙里透進來的夜光均勻地灑瀉在他的臉上,是月光。只有月光才能用如此輕柔而不稍停佇的速度在一個悲哀的軀體上遊走,濾除情感和時間,有如撫熨一塊石頭。老頭兒果然睡得像石頭,連鼻息也深不可測。要不是每隔幾秒鐘會有一條腿猛可痙攣那么一下子,他可以說就是個死人了。那是脊椎神經受傷的病人經常顯現的症狀:一條腿忽然活躍起來,帶著連主人也控制不了的力氣,朝什麼方向踢上一踢,有股倨傲不馴的勁兒,仿佛是在亢聲質問著:“誰說我有病?”每隔幾秒鐘,它就“誰說我有病?”一下子。掩映而過的月光完全沒有理會這條腿頑強得近乎可笑的意志,便移往更神秘的角落裡去了。而我在月光走過的幽暗邊緣被一條兀自抽搐的腿逗得居然笑出了一點眼淚,然後我知道:這是我開始寫下一本書的時候了,它將被預先講述給一個尚未出生的孩子聽——在巨大無常且冷冽如月光一般的命運輾過這個孩子之前;這個不存在的孩子將會認識他的父親、他的父親的父親,以及他父親的父親的父親。他將認識他們。
命運和浴缸
我還認識另一個小孩,他的名字叫陸寬。那是一個很大氣也很響亮的名字,和我想為你起的名字——張容,幾乎一樣好。就在陸寬即將念國小的前幾天,我坐在他家客廳的一角,讀一本雜誌或什麼的。我忽然聽見他說了一句話(或者是讀出一個句子):
“住進一個沒有命運也沒有浴缸的房子。”緊接著,他很高興地又重複了一遍。
“什麼意思?”我扔下手上的雜誌,仿佛看見了一個多么新奇的、發出光亮的玩具。
“住進一個沒有命運也沒有浴缸的房子。”
“這是哪裡來的話?你想出來的嗎?”
陸寬指了指電視機,熒幕上是華特·迪斯尼的卡通片:“卡通說的。”
我不相信華特·迪斯尼本人或者他手下任何一個會把大力士海格力斯描寫成純良英雄的笨蛋畫工能編出這樣驚人的荒謬語句,於是我再問了一次,他依樣再答了一次,而且又高聲把那句子給念誦了一遍,在念到“浴缸”的時候特別咧開嘴笑起來。
這裡面一定有誤會。也許為卡通作翻譯的傢伙搞錯了,也許配音的說錯了,也許陸寬聽錯了。可是——這也是我想告訴你的,那個句子說對了:住進一個沒有命運也沒有浴缸的房子。
“好逃避人生的巨大與繁瑣。”這是我補充的註腳。
陸寬的媽媽是個名叫皮的好女人。這時她正坐在電視機旁邊的電腦桌前努力修改一個天曉得能不能拍得出來的電影劇本。她在聽見兒子大叫“浴缸”的時候也笑了,從老花鏡的框沿上方瞅一眼兒子,對我說:“他明明很喜歡洗澡的。”
“可是這個句子裡的浴缸的確很好笑。”我說。因為命運太大而浴缸太小的緣故。
皮的外公有這樣一段小小的故事。當這個老人即將度過平生第九十個生日的某一天,他打電話給幾十個散居在外地的兒子、女兒、侄兒、侄女、外甥、外甥女……務期一網打盡。在電話里,他故意用非常低弱的音量告訴每一個孩子:今年不要大張旗鼓地為他慶生做壽。“生日那一天偷偷過去就算了,不要讓老天爺知道。”老人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他還想趁老天爺沒注意的當兒多活些日子。
可是活著——一樁你即將面對的事,是一個多么複雜的工程。它包括太多無論是苦是樂是悲是喜的小零件,太過繁瑣。其中自然包括浴缸這種東西,還有洗澡這種活動。
冼澡
我想先從洗澡說起。
應該不獨中國人是這樣的。每個降生到世上來的孩子所接受的第一個儀式就是洗澡。一盆溫熱的水,浸濕一方潔淨的布,將嬰兒頭上、臉上、軀幹和四肢上屬於母親的血水和體液清除盡去,出落一個全新的人。這全新的人睡眼惺忪,意識蒙嚨,還察覺不到已然碾壓迫至的命運。中國人在這樁事體上特別用心思,新生兒落地的第三天還要擇一吉時,將洗澡之禮再操演一遍,謂之“洗三兒”。講究的人家自然隆而重之,他們會請教精通醫道的人士,調理出一種能強健體質的草藥香油,塗抹在新生兒的身上。“洗三兒”是非常務實的,如果有任何一丁點兒深層的隱喻在裡面,不過就是希望這孩子常保煥然一新的氣質。中國人也從不認為洗的儀式有什麼清滌罪惡、浸潤聖靈的作用。
我在一個天主教會辦的國小念一年級的時候,一度對那個宗教所有的儀式非常著迷,因為聖詩唱起來莊嚴優美,而每個星期五的下午,被稱為“教友”的同學還可以少上一堂課,他們都到教室後方庭園深處的教堂里去望彌撒領聖體——一塊薄薄的、據說沒什麼滋味的小麵餅。我非常希望能嘗嘗那種小麵餅。
“好吃嗎?”我問我的教友同學。
“像紙一樣。”教友同學說。
後來我吃了幾張剪成小圓片的紙。然而那樣並不能滿足我成為一個教友、張嘴接住神父指尖夾過來的聖體以及逃掉一堂課的渴望。想當教友很簡單,教友同學們都這么說:去受洗就可以了。據說受洗一點兒也不疼,神父會在你的額頭上抹些油,教你禱告禱告,大概就是這樣。我跟我父親說我要受洗。他想都不想就說:“你在家好好洗洗就可以了。”
的確。我不該忘記:當我初入學的時候,我父親在我的學籍資料卡的宗教欄里填寫了“儒”這個字。他也解釋過:儒教就是孔夫子的道理;明白了孔夫子的道理就不需要什麼洋教了。我成為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自以為除了衣服和皮膚之外沒什麼可以清洗的。我最熱切的宗教渴望恐怕也就在吞下那幾張紙的時候噎住了。
偶爾,父親願意從病床上下來,勉強拄著助行器到浴室里洗個澡。“連洗個澡也要求人。”他低聲嘆著氣,任我用蓮蓬頭沖洗他那發出陣陣酸氣的身體,然後總是這樣說:“老天爺罰我。”
“老天爺幹嗎罰你?”有一次我故意這么問。
“它就是罰我。”
在那一刻,一個句子朝我衝撞過來:“這老人垮了。”
我繼續拿蓮蓬頭沖洗他身體的各個部位。幾近全禿的頂門、多皺褶且布滿壽斑的脖頸和臉頰、長了顆腺瘤的肩膀、松皮垂軟的胸部和腹部、殘留著棗紅色神經性皰疹斑痕的背脊。我伸手搓搓他的屁眼,又俯身向前托起他的睪丸和雞雞——那裡就是當初我的源起之地,起碼有一半的我是從那么狹小又侷促的所在冒出來的。我輕輕揉了揉它們。顯然,它們也早就垮了。
這老人還沒垮的時候(要講得準確些應該是:他摔那一跤之前的幾十年里)幾乎沒在家洗過澡。他的澡都是在球場裡洗的。差不多也就是從我出生那一年起,他開始打網球。我第一次看見他的身體就是在球場的浴室里。那是一具你知道再怎么樣你也比不上的身體。大。什麼都大的一個身體。吧嗒吧嗒打肥皂、嘩啦嘩啦沖水、呼啊呼啊吆喝著的身體。
對我來說:洗澡必然和這最初的視象融接合一。其意義似乎就是:你得眼睜睜地凝視一種比你巨大的東西,那是非常原始的恐懼。日後我在希區柯克和狄帕瑪的驚慄電影中體會到:人在洗澡的時候,在赤裸著接受水的沖洗澆注的時候,其實無比渺小脆弱。持刀步步逼近的凶狂歹徒只是一個巨大的隱喻;人類無所遁逃,它輾壓迫至,必然得逞。
懲罰
你尚未赤裸裸地到來,而我已著實驚慄著了。因為在身體的最核心,我有重大的欠缺;那是從我父親、甚至我父親的父親……就已然承襲的一種欠缺。簡單地說:我們這個家族的男子的恐懼都太淺薄,我們最多只能在命運面前顫抖、惶惑、喪失意志;再深進去,則空無一物。我們都不知道,也沒有能力探究命運的背後還有些什麼。於是,一具健康偉岸了七十六年的軀體在摔了一跤、損傷了一束比牙籤還細的神經之後,就和整個世界斷離。作為一個人,父親只願意做三件事:睡眠、飲食和排泄。這將是他對生命這個課題的總結論。如果你再追問下去:“為什麼?”他會說:“老天爺罰我。”如果我央求他試著起床站一站、動一動、走一走,他會說:“你不要跟著老天爺一起罰我。”我若不作聲、靜靜坐在他眄視不著的床尾,就會發現他緩緩合上眼皮,微張著嘴,在每一次呼吸吐氣的時候輕誦道:“罰我喔——罰我喔——”
遠甚於被囚禁在僵硬的肢體裡動彈不得的懲罰是:我父親將從此以為他的一生充滿罪孽。我的懲罰則是永遠無法將他從罪孽中解脫出來。
失落自由
據說,受孕三個月之內的胚胎在子宮裡還無法附著,處於一種漂浮、游移的狀態。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你正處於這種狀態。我們都曾經於一無知覺中體驗過這種自由——不徒無知於當下漫遊的邊界,亦且無覺於口後記憶的庫藏,無視於自己的極限、又無羈於緬懷的韁索。這個自由是純物質性的,終人之一生所能渴望的自由最多不過如此。
此刻你還在那樣的自由狀態之中。我只能以拙劣的想像力摹擬你的形體,可能猶如我曾經在顯微鏡里見過的、氣泡般的變形蟲,在一個潮濕、溫潤甚至有點悶熱的子宮裡向你的母親任意下達各種欲望的指令:我想吃那種沾了一點鮮摘辣椒加蒜末的醬料的蚵仔煎、像番茄一般大小帶點中空膨鬆嚼勁的波士頓櫻桃,我想喝沙漠鼠尾草茶、冰鎮酸梅湯,不過我想還是先睡個覺好了——最好,最好在熟睡之前能聽到舒伯特的《鱒魚》,但是我可能在十六個小節之後就聽煩了,那時最好來一段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或者周璇的《夜上海》,我不確定。不過,我不想聞煙味兒。
不錯,抽菸的是我。我正在回憶那個關於自由的啟蒙。在我上國中的時候,有一門課程叫做“公民與道德”。教這門課的老師有一副調門兒極高的嗓子和一雙白皙纖細的腳踝。她的辦公桌在化學實驗室的角落裡,每當我們在電解水分子或還原硫酸銅的時候,她都會尖聲唱一句:“不要吵——”C大調高音部的355313。我們都叫她咪嗦嗦。咪嗦嗦給我們上的第一個關於自由的課程是從這個問題開始的:“自由的定義是什麼?”在點名詢問過全班至少半數的同學這個問題之後,她提出了早先準備好的答案:“自由就是在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的限制之下的行為。懂嗎?”“懂——”C大調高音部的13,哆咪。
我必須移身到戶外離你和你的母親稍遠一些的地方把煙抽完。這時我四十歲,幾乎忘了咪嗦嗦的面孔,不過我必須坦白告訴你:當時我們所懂得的不是自由的定義,而是限制的定義,或者自由的限制。
我不能確知是否世人皆如此,抑或中國人皆如此,但是起碼我這一代乃至於我父親那一代的中國人在提到自由這個詞的時候,總緊緊懷抱著一種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情感——其中後者的成分恐怕還要多些。自由,一個所謂“現代意義”的生命不超過一百年的詞,為不只兩代的中國人帶來的粗廓印象是一種具有威脅性和破壞性而不得不加以限制的力量;即使在傾心嚮往這個字的人們那裡,這個詞也常只是一個孤懸的理想、空洞的口號甚至狡猾的藉口。
而我想告訴你的是,大約就在你逐漸發展了知覺、長出胎盤、開始附著在你母親子宮內的某個角落——一個小小的原鄉——的時候已經失去了自由。關於這種失落,我有兩個故事。一個是你爺爺的,一個是國王的。
追花落河
我八歲那年的初夏五月,在剛灑了水、恢復平整、發出陣陣泥腥味的紅土球場邊的浴室里得到一個允諾:正在吧嗒吧嗒打肥皂的父親說他今年要帶我去游泳。去哪裡?我問。游泳池啊。他說,隨即嘆了口氣,在個池子裡撲蹬撲蹬算什麼游泳?然後他告訴我那個到河裡游泳的故事。一個關於自由及其懲罰的故事。
“我父親很不喜歡我的,你知道罷。”我父親說。我當然知道,我出生之前他大概就告訴我不知道多少次了。他是我爺爺的第七個兒子。在千盼萬盼要個女兒的我爺爺眼裡,這個又黑、又大,鼻子又扁的醜兒子簡直是多餘的,他疼的是老大,沒轍的是老二,欣賞的是老五,討厭的是我父親。我父親被一個抽鴉片、搞鹽務而且脾氣壞透了的老頭子討厭了十年,終於在一個夏天的正午(當然是在挨了一頓痛打之後)得著了神悟——他蹲在濟南市朝陽街老家南屋的一條小水溝邊,看見一朵石榴花從樹梢落下來,一落落進水溝里。石榴花端端正正落在水面上,仿佛遲疑了一下,轉了個圈兒,好像回頭看一眼石榴樹和樹後掛著“有容德乃大,無欺心自安”油漆木刻聯匾的懋德堂,打個顫,便順著清澈的溝水流下去。那溝里流的是泉水,從北屋我奶奶房後不知道哪塊石板底下冒出來.取徑於青石磚的縫隙,繞過西廂房後檐下的兩棵梧桐樹,便往地里鑿成了一條天然的小溝。老祖宗們建懋德堂時刻意留了這溝,取其源頭活水、源遠流長的意思。這溝得了縱容,自西徂東、穿越三進的院落,甚至還在會合了另兩個泉眼之後爬上高坡、潺潺折向南流,在二進的東廂房下,它筆直地朝地面刻出磚石和泥土的楚河漢界。這一如刀斧般銳利、決絕的線條可能是地球上惟一一條自然天成的直線。老祖宗們不敢違逆天意,只得順溝建築屋基。傳說住這排廂房的子孫與族人不會十分親睦。我四大爺是個現成的例子,他叫張萃京,死時身長不滿一尺,從沒見過他下面的三弟二妹。我四大爺在二進的東廂房裡出生又夭亡之後,這排屋子就算是廢了。據說到打日本鬼子的時候充當過點校新兵員額的臨時司令部,我二大爺還在那裡撿著兩把缺把子手槍和兩千多發子彈。日本人進城前半天,我二大爺試著扔了一發子彈在小泉溝里,看沖不沖得走它。那發子彈(用我父親的話說)“像一顆魚雷一樣就給泉水沖跑了”。我二大爺索性把所有的子彈全傾進溝里。半個時辰之後,子彈一發不剩。它們有如挨號排隊的一般、一發接一發沿溝斜斜滾入一進花廳的地底下,流向西屋,再從石榴樹後頭冒出來,大致上仍是一列縱隊,一路流出院牆之外,順著整整七年以前我父親追趕石榴花的路徑,一口氣注入小清河。
插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