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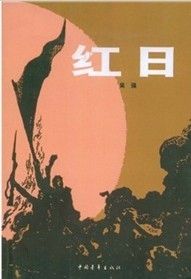 封面
封面![《紅日》[小說] 《紅日》[小說]](/img/6/6dc/nBnauM3X0AjNyYjN1YTO4QTN0QTM4ATO3ITNzQTNwAzMwIzL2kzLyM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紅日》是原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當代作家吳強的作品。《紅日》開了塑造我軍高級指揮員形象的先例,並使這一先例完全暴露在日常性生活陽光中,不帶任何英雄式的神秘氣息。《紅日》大膽地塑造了反面人物形象,並使之性格化,顯示了藝術開創的又一成就。在作品裡,作者一反當時把反面人物類型化、臉譜化的文學時尚,深入地挖掘了反面人物的靈魂,把藝術之筆探入這些人物形象的內心世界,給他們在作品結構中以獨立自律的形象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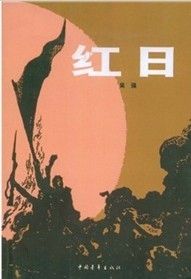 封面
封面《紅日》,吳強所著紅色經典小說,描寫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在山東殲滅國民黨部隊整編74師的故事。故事以軍長沈振新、政委丁元善所率領的一...
內容梗概 作者簡介 創作歷程 點評鑑賞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於1963年,根據吳強所著同名小說改編,著名導演湯曉丹執導的戰爭片。主要劇情為:1946年冬,我軍在蘇北漣水城與敵軍“王牌”整編74師...
基本簡介 劇情介紹 影視誕生 影視藝術沈振新是吳強(1910—1990)創作的長篇小說《紅日》中的人物形象,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高級指揮員。
《柯山紅日》是六幕八場歌劇,將解放西藏的史實予以再現。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均給進藏的人民解放軍帶來重重困難,正是在這種特定環境中,使幾位軍人的...
簡介 故事梗概 藝術評價 演唱者 張越男回憶這是一部“講史”小說。至於“史實”……讀者諸君不用費勁去挑這部小說的史實紕漏,說不定有一天俺會自己把改編的部分、忠實史實的部分分別寫出來,那樣也挺有趣,...
簡介 目錄 相關介紹 評論《飲血紅日》是劉玉州寫的網路小說連載於晉江文學城。作品狀態連載中。
簡介:《紅日之王》是一部連載於起點中文網的虛擬網遊小說,作者是揭結界。
1927年“八一”南昌暴動打響了中共領導的武裝革命第一槍,暴動失敗後,朱德、陳毅率起義失敗的少數人馬轉戰到湘南,舉行了湘南暴動,爾後,向井岡山轉移。這時...
內容簡介 目錄介紹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