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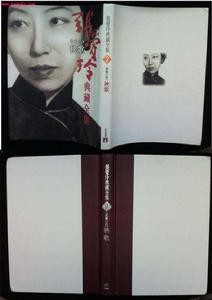 張愛玲 《秧歌》
張愛玲 《秧歌》張愛玲的《秧歌》1953年寫於香港。這部長篇小說是張愛玲到香港後以Eileen chang為筆名發表的,最初是寫給英語圈的讀者看的,後來翻譯成中文。
1952年張愛玲離開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國駐港新聞處,《秧歌》正是她寫的第一個長篇-一個有著明顯“綠背”(即美元)色彩的長篇。新中國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並非像《秧歌》所寫的在“飢餓”的火山口上,顯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秧歌》有一段與內容天關的“妙論”,此“妙論”出現在其前夫胡蘭成於1958年在日本寫的《今生今世》一書中。從時序上說,似乎胡蘭成抄襲了《秧歌》,實則是《秧歌》保留的胡蘭成的漢奸陰影。
創作背景
二十世紀早已落幕,對於世界文學來說,“流亡”絕對是一個描述那個世紀文學最痛心的關鍵字,東西方許多作家都曾生活在這個令人惆悵的詞語裡。那些本可以流亡海外,但留下來觀察、期待美好改變的知識分子無一例外的在1958年後被整肅,打成右派的有55萬之多,其中大多數人都沒有活下來,因為後來的運動劫難實在太多了,根本無法全部躲過。而在這些暴風雨將要發生的6年前,寫出《傾城之戀》 、《金鎖記》等小說的上海著名女作家張愛玲已經黯然退場,離開中國大陸,她的作派是悄無聲息的走,不告訴任何一個人,連她的唯一的弟弟張子靜都沒有告訴。這就是張愛玲的弔詭作派,對於世事演變,她世故而又具有天生的預感,同她外曾祖父李鴻章一樣通融而達練。
1952年7月,她以完成抗日戰爭中斷的港大學業為由,於深圳羅湖橋出境前往香港:“自從羅湖,她覺得是個陰陽界,走陰間回到陽間”(《浮花浪蕊》),這是她離開中國大陸後借小說女主人公洛貞的想像。事實上,她出境去香港出奇的平常、順利。但在小說里,她極盡虛構申請出境之難,申請者日夜焦慮,惟恐得不到批准,可見張愛玲是如何惶恐的日日面對出走前的日子和焦慮心態。她甚至寫自己護照上的名字是自己的筆名,因此出境時緊張萬分,生怕被攔截在“陰界”這邊,而民兵居然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說家張愛玲,她戰戰兢兢的回答後,就放她過去了。小說女主人公洛貞目睹了其他離開“陰間”的人,在過海關後,還不放心的在“陽間”奔跑,洛貞受感染也緊隨其後,走出許多路時才停下歇腳,說:“好了!這下不要緊了。”
1949年後,“中國”是“陰界”的概念,牢牢的攫住了她的意識,使她在小說敘事上被這種恐懼感的意念籠罩著,得不到半點輕鬆。這在她後來的兩部長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里,還有情緒性的意念蔓延。
作品內容
《秧歌》側重講的還是女人的故事,敘事也是用女性視角來敘述的,這是張愛玲的強項。小說一開始,兩個女人就要“歸來/離去”,在上海城裡幫傭三年的月香在“鼓勵勞工回鄉生產”的號召下告別城市,回到山鄉,暫時的被“鄉下跟從前不同了,窮人翻身了。現在的政府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豪言壯語激動著,憧憬回到山鄉過上幸福的家庭生活,她的丈夫是“新社會”的勞模老實人譚金根,一個只看到地契上寫有自己名字而忽略其它主張,忍氣吞聲的青年農民。在嫂子歸來的時候,金根的妹妹金花要出嫁到鄰村的周村去了。
香在回來的當夜就發現回鄉完全是錯誤的決定,是被宣傳鼓動的盲目回鄉:“現在我才曉得,上了當了!”,因為她看見山村到處蔓延著無邊無際的“飢餓”,儘管長輩譚老大、譚大娘還小心翼翼的竭力掩飾,並說一些口號和標語式的話,但月香已經看破玄機了,她開始後悔。現在連金根最疼愛的女兒阿招都在嚷著肚子餓,因為,但凡有一口吃食,金根會毫不猶豫的給阿招,這個時間出嫁相依為命的妹妹金花,也是因為貧困與飢餓逼迫的。
很快,月香就被借債的鄉親們包圍住了,連她親娘和親戚譚老大也來借錢,顯然,月香微薄的錢很難讓所有人滿意,儘管他們開借的僅僅是城裡一副油條早點的數字。現在,比飢餓更難堪的,就是讓村幹部王霖偶然看見中午吃稠粥,這是一種極大的罪惡和恐懼,因為在目睹過“土改”的金根看來,所有人都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稠粥”意味著“三反之一”(地、富、右)的“富農”行徑。王霖是某種黨機器教化的化身,他是失意的青年老幹部,在各種權利運動傾軋中求得縫隙生存,他是一個沒有多少感情的冷漠的人。像他這樣的人在鄉間不在少數,第四章里描述的收麻的合作社幹部惡魔行徑就是冷漠的註腳。
儘管,飢餓與恐懼攫住了所有人的內心,但大家見面還都笑哈哈的,並時不時講一些時髦的標語口號,這以積極分子譚大娘最為拿手。但她指使媳婦金有嫂第一個來借錢時,就已道出實情:“收成雖然好,交了公糧就去了一大半。現在那些苛捐雜稅倒是沒有了,只剩一樣公糧,可是重的嚇死人。蠶絲也是政府收買,茶葉也得賣給政府,出的價特別低。”。
飢餓籠罩著山鄉,但似乎大家有化解的“精神勝利法”,甚至“風裡飄來咚咚的鑼鼓聲……•這兩天村子上天天押著秧歌隊在那裡演習。”。小說的主軸意象“秧歌”,這時是以這樣的情境出現的,張的“荒涼”和“倩笑”意味也明朗清晰起來。
飢餓的現實如此逼仄,已經使月香只有無奈的順從,因為她已經沒有退路了。但這時還有人到哀鴻遍野的飢餓里來尋覓所謂的“鄉村神話”,以便到更大的空間去宣示、布道這裡的優越性,一個城裡文聯的電影編導顧岡,來此收集資料體驗生活,小說又多了一些穿插,也多了另一重視角來觀察飢餓世界裡的“人造神話”。他被安排住在積極分子譚大娘家,顧岡也看穿了房東大娘是王霖“最得意的展覽品”。王霖雖憤憤不平鄙視接待這些“‘解放後’才加入他們陣營的投機分子”,但覺得可以借他們“體驗”出的“神話”來換取政績,以使自己離開這窮鄉僻壤。而顧岡也覺得王霖如此資深的資歷卻在山鄉當一個村乾,肯定是一個被“清”掉的危險分子,接近他對自己不利,也疏遠他。張愛玲讓兩個各自來自基層的小人物都從政治角度來考量、鄙視、猜疑對方,將時代特徵烙在他們冷漠而麻木、萎瑣的內心上。
顧岡面對“這裡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鍋稀薄的米湯,裡面浮著切成一寸來長的一段段的草。”的飢餓世界,“報紙上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的任何地方——發生了饑饉。他有一種奇異的虛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時間與空間,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的地方。”。他知道城裡派他下來是要編造一個“鄉村神話”,而不是來寫寫飢餓真相場面的,這一點,顧很清楚。所以,顧想臆造一個不存在的水壩故事。張愛玲刻意要讓顧在飢餓現實面前,還編造假故事、假劇本,顯然是要藉此諷刺當時文學讀物的“神話性”來源。
年關到了,飢餓已經到了懸崖邊沿了,山村籠罩著一股死亡的氣息,卻還要承擔軍屬的年禮:“每家攤派半隻豬,四十斤年糕,上面掛著紅綠彩稠,由秧歌隊帶領,吹吹打打送上門去。”。或折成現金,限一個日子交齊。王霖帶領人上門索取,金根怒不可遏,拒絕捐獻,面對王霖強硬的姿態和不顧死活的盤剝,悲憤的說:“等不到秋天,我們都不知道死到哪裡去了!”,月香為了息事寧人,就將自己僅有的一點錢拿給狂暴的王霖,請他去置辦爆仗竹,半隻豬,但王還要他們置辦四十斤年糕,金根被月香的妥協激怒了,他隱隱覺得那個貪婪的盤剝黑洞永遠不會填滿的,為此,他對自己深愛的月香大打出手。
金根還是在滿腔憤怒中蒸了自己都沒有嘗過的年糕以作捐獻,並在第二天去村公所繳納捐獻。終於,金根在王霖的言語激釁下,忍無可忍的帶頭反擊了,暴動終於發生了,村民衝擊糧倉準備搶糧食,與守衛的民兵發生衝突,亂槍之下,阿招被踐踏至死。金根身受重傷,但藉助月香之力得以逃脫,由譚村去往周村。月香只有求助於金花,但金花權衡兄妹、夫妻利弊,最後也放棄了收留這個“反革命”兄長,金根也不忍連累月香,自己找一個隱秘的地方悄然死去。月香發現時,金根已杳無蹤跡了。最後,她悲憤的回到譚村,用滿腔怒火將自己當作火種,燒掉了屯著金根繳納糧食和蠶絲的糧倉,自己也隨之化為灰燼。
最後,張愛玲還不忘揶揄那個滿腦子拼湊“時代典型神話”的顧岡,他甚至想:“一個強壯的驚心動魄的景象,作為我那張影片的高潮。只要把這故事搬回去幾年,就沒有問題了,追敘從前在反動政府的統治下,農民怎樣為飢餓所逼迫,暴動起來,搶糧燒倉。”。當然,在那個顧岡白日夢似的影片裡,細節、原由、結局都被演繹篡改,月香成了剝削階級的漂亮地主姨太太,因不滿政府縱火而縱火焚燒糧倉。——總之,謊言就是這樣出籠的,張愛玲結合自己兩年多在上海觀察、聽聞的事例,看出了蹊蹺的正面宣傳影片大約就是這樣被製造/編造出來的。而王霖認為:農民暴動是“間諜”在作祟。同前者一樣,這都是張愛玲深刻的諷刺手法。小說結局是第二天一早,村民扭著秧歌簇擁著年禮照常拜年去了。
作品特色
張愛玲是寫過電影劇本《未了情》 、 《太太萬歲》的,她深知電影鏡頭語言的一幕幕拼接,她在《秧歌》里用電影鏡頭一一掃過村落小鎮街道,以確定和預設她要描述故事的悲劇性基調前奏,讓“秧歌”的喜慶喧囂成為一種張愛玲式的冷冷嘲笑。
《秧歌》寫的是土改後的江南農村社會,時間在1950年到1952年之間,故事發生在一個典型的上海周邊村落,有水道和鐵路連線著上海,與繁華的上海灘相比,這裡簡直就是人間地獄,一腳踏進小鎮就聞到露天茅廁發散的臭氣,“走過這一排茅廁,就是店鋪”,兩者相連著,不分彼此,街市肅殺之餘,連髒水也似乎要“潑出天涯海角,世界的盡頭。”,“每一爿店裡都有一個殺氣騰騰的老闆娘坐鎮著……使過往行人看了很感到不安。”、還有“李麗華、周曼華、周璇,一個個都對著那空空的街道倩笑著。……更增加了那荒涼之感。”、“太陽像一隻黃狗攔街躺著。太陽在這裡老了。”。小說敘事就在這樣一種末日般哀頹、淒傷場景中上演了,氣氛極具陰魅感,人還沒有出現,但“倩笑”與“荒涼”的陰界感覺已經氤氳出來。
書題“秧歌”的喜慶意象則完全找不到蹤跡。在《秧歌》里,這種鄉村集會的自發民間舞蹈,現在已被賦予政治勝利/階級狂歡的遞進式外化儀式,是強制群體演出和張看的流動道具。這在小說的後面會有深刻的隱喻和無奈的暗諷。
無疑,“《秧歌》是一部人的身體和靈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殘的記錄”。《秧歌》也證明張愛玲是一個留意觀察變革中亂世社會,並把握其本質,用人道關懷的“大我”境界直面人生的殘酷悲劇,將渺小如金根、月香最後被投入絞肉機過程作了回訪式的展露,對秧歌原生意象的剝離,苦笑的淋漓盡致的呈現另一種“死亡之舞”,有著入木三分的玩味。
《秧歌》整部小說都在一種夢魘式的可怕的鬼域裡展開,特別對王霖戰前、戰後幾次住在陰間式大古廟(關帝廟)里進行渲染,“黨在戰爭期間是比較肯妥協的,所以他們駐紮在這座廟裡,並沒有破壞那些偶像,也容許女尼繼續居留。”,而一旦打下江山,就“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現在,王霖曾經居住的廟裡,神像早已經被全部砸毀。這只是一個預兆,張愛玲先見性的借廟宇的變遷來洞穿這個政權的殘忍、騙局實質,後來的1958——1976年的近廿年間,當局還發動了砸爛舊世界的一系列運動,幾乎將中國千年文化遺產毀壞殆盡。
小說甚至還安排王霖新婚及此後都是晚上與妻子沙明同宿,“她永遠是晚上來,天亮就走。”,兩人因為戰亂走散後,還在一個城市看見鬼魅一樣飄忽的昔日妻子,這些,都是張有意為之的隱喻。另外,《秧歌》的敘事結構也是饒有意味的,一條敘事線是 “餓鬼” 金根們的掙扎、消身,受到殘害、肢解的人生,寫實性較強;一條敘事線是虛無縹緲的,用心理活動和回憶來呈現王霖、顧岡這兩類被“僱傭”靈魂,說謊、下意識、慣性化的思維和行動,特別是顧岡這類無恥的小文人對月香縱火的嫁接式構思。張愛玲是全知視角和高懸審視他們靈魂的審判員,一如她在《半生緣》里對結局構設的那樣冷峻。
作品評價
1952年下半年到1955年11月,離開香港流亡美國紐約這三年時間裡,張愛玲最有成就的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先後在《今日世界》連載和在紐約用英文出版,這兩部小說至今為止都是被文學史家攻擊的對象,特別是在中國大陸這端,集團式的謾罵之聲從未停止。那是因為張愛玲被破天荒的寫進了《中國現代小說史》,作者夏志清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談論她,大大超過魯迅的篇幅,並稱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超前成就”、“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五四時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國以前的小說家,除了曹雪芹外,也還有幾人在藝術成就上可同張愛玲相比?”。台灣1956年就已經開始神化和介紹她,這與夏志清的讚譽是分不開的,張在台灣得到的傳承也遠遠大於和早於大陸,大陸八十年代始認識張的價值。
張愛玲在《秧歌》前寫的小說很少直接干預當下,對現世進行赤裸裸的批判,大多是寫一個特定階級和特定人群的無奈、蒼涼、錯位、變態、陰森、淒哀的境遇,有時也瞄準灰色、世故的小人物,掙扎在現世權力與金錢、世俗的羅網中,承受著時代的負荷,實現她參差對照的陰性荒涼美學、陰性書寫。狀寫亂世年代的人的流離和疏離狀,還有一種陌生性的美感,現實主義的歌功頌德和批判干預、道德批評,絕少在她的小說中直接出現,但在流亡途中,《秧歌》和《赤地之戀》表明了她的干預當下和揭櫫謊言的勇氣。
中國小說史上不朽之作
《秧歌》已被稱為“在中國小說史上已經是本不朽之作。”。一代中國自由主義宗師胡適1955年就對此評價:“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緻,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讀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夏志清和胡適當然不是信口開河的只以“反共”為職志而臧否作品,他們這兩代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作的開創性工作,是誰都無法迴避的。今天看來,張愛玲的《秧歌》,無論從現實主義角度和公共知識分子良知的維度,都是一部傑出的小說,並不遜色於她的《金鎖記》、《傾城之戀》等代表作,它們是對中國兩個領域的關懷,《秧歌》、《赤地之戀》的出現,反而顯現張在關注民生痛苦和被凌辱的大多數群體方面有了出色的並列。
揭露和預言中國極權社會的偉大的政治小說
《秧歌》是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這部小說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國極權制度對是怎樣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根基,毀滅了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根本關係,描繪了中國農民以及普通人民在這個制度中的無權無勢的地位。這部小說,也許比中國迄今為止發表的任何小說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的中國極權統治的本質。這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令人震驚的。因為這本書出版於1955年,在餓死3800萬人的人類史最大的饑荒還沒有開始,在毀滅了中國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還沒有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十多年之前。這部書是不久就成為現實的中國社會巨大悲劇的讖語。一部小說成為一個時代的預言,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除了《紅樓夢》之外,還沒有一部書可以做到這點。
《秧歌》這本書證實了藝術的穿透力和偉大的政治小說的力量。把這本書放在人類的政治小說歷史上看,這部書是中國作家張愛玲對人類政治小說的偉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