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背景
 相關圖片
相關圖片一九四八年冬,西北野戰軍在陝東澄城、邰陽、蒲城地區發動的、殲敵五萬九千餘人的三次攻勢已勝利結束,東北野戰軍全殲東北之敵,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聯合進行的淮海戰役正在順利發展,全國形勢對我十分有利。在此情況下,平津之敵已成驚弓之鳥。因此,能否穩住平津之敵,使其無法從海上南逃和向綏遠西竄,是我軍實現就地殲滅該敵的關鍵。為此,毛主席令淮海前線我軍暫時留下杜聿明指揮之邱清泉、李彌、孫元良諸兵團之餘部,兩星期內不作最後殲滅之部署,令太原前線我軍緩攻太原,以麻痹平、津之敵;令華北楊羅耿兵團暫時不打新保全之敵三十五軍,以便吸引平、津之敵不好定下從海上逃走的決心;令東北野戰軍提前秘密入關,並對入關的時間、路線以及入關後的行動方針問題,都作了詳細的布置,以求穩住平、津之敵。此外,並令山東軍區集中一部分兵力控制濟南附近一段黃河,防平、津之敵沿津浦線南下向青島逃跑
(一)關於東北野戰軍的入關時間問題。毛主席早在遼瀋戰役結束前,即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和十一月一日就已電示林彪,叫他督促先遣部隊“四縱、十一縱等部向北平附近速進。”)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四時又電示林彪:“你們主力早日入關,包圍津、沽、唐山,在包圍姿態下進行休整,則敵無從從海上逃跑。”軍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再次指示林彪:“東北野戰軍提前於本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關內開動。”但林彪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給軍委的電報中卻說:“東北主力提早入關很困難。”並且還為他的所謂“困難”找了兩個藉口:一是說“東北解放後,部隊思想發生很大波動,東北籍戰士怕離開家鄉,怕走路太遠,甚至某些幹部已開始生長享受情緒。”“同時新兵與俘虜戰士的補充還未就緒,爭取工作也要有相當時間,否則逃亡減員會更為嚴重”,對東北籍的廣大指戰員入關解放全中國的革命積極性作了完全顛倒的反映。二是說“部隊冬大衣、棉帽,棉鞋尚未發下。”而實際情況則是部隊冬裝一部已經發下,不足者在我軍已控制了入關鐵路幹線的情況下,完全可以隨後趕運。
毛主席針對林彪的上述藉口,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嚴令林彪:“你們立即令各縱以一、二天時間完成出發準備,於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軍或至少八個縱隊取捷徑以最快速度行進,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使逃跑,並爭取使中央軍不戰投降(此種可能很大)。”
林彪經過毛主席和中央軍委的三令五申,才勉強同意部署東北主力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開始入關。
(二)關於東北野戰軍的入關行軍路線問題。毛主席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電示林彪說:“傅、蔣在山海關的一個軍尚未撤退,其目的是估計你們主力入關必走該地,讓該部先擋一擋,爭取主力逃跑或固守之餘裕時間。因此,你們主力入關應取四縱、十一縱所走道路,不要走山海關。”又說:“部隊行動須十分蔭蔽。”
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電示林彪:“你們可以位於錦州、打(大)虎山、營口等地之五個縱隊於二十三日出發,取捷徑夜行曉宿蔭蔽迅速行進。”“各部均走熱河境內出冀東,不走山海關。瀋陽地區各部及總部大行李則應緩若干天出發,走山海關附近出唐山。如林(彪)、羅(榮桓),劉(亞樓)決定先走,則攜帶輕便指揮機構先行,並於走後一星期左右在瀋陽報上登出一條表示林尚在沈的新聞,並經新華社廣播。各部隊均應注意蔭蔽。”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電示林彪:“你們後尾部隊及總部亦不要走山海關。”
林彪卻拒不執行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給軍委的電報中說:“由於山海關以北山地及平泉到遵化的路上人煙稀少,所過部隊太多,同時我們大量軍隊經長途行軍南下,敵每日夜均有飛機偵炸,已無秘密可言。昨已令我最後尾之三個軍(三十九軍、四十九軍、四十四軍)經興城、綏中、山海關前進。”
(三)關於東北野戰軍入關後的行動問題。毛主席明確規定第一階段應首先包圍天津、塘沽、蘆台、唐山,斷敵海上退路,與向張家口、新保全急進的華北部隊一道完成對平、津、張之敵的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然後各個殲滅該敵。
林彪卻提出要用第三、第五兩個縱隊先打南口敵十六軍的錯誤主張。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二十一時三十分給軍委的電報說:“為保證確實殲滅傅作義全部及南口之十六軍,我們意見以先到之第三、第五兩個縱隊立即經平谷與順義附近,以五、六天行程插到南口附近,參加戰。屆時如平張間戰役結束,則我之先頭兩個縱隊即轉至北平、通縣以南,防平敵南退。”
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七時電示林彪:“你們想以第三、第五兩縱去打十六軍,在全盤計畫上是不妥的。現傅作義有十四個師、一個騎兵師集中北平、涿縣、通縣、順義、南口區域(下花園、懷來之五個師未計在內),你們的首要任務是不使這些敵人逃至天津。其方法是以四個縱隊占領廊坊、香河之線,隔斷平津聯繫。”又說:“在平津未隔斷的條件下,如果你們除程(子華)、黃(克誠)外再使用兩個縱隊去打南口的十六軍,並把十六軍消滅了,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敵早日逃至天津、塘沽的危險。”最後毛主席還明確指示林彪:“因此,你們仍應靜候後續兵力到達,準備實行隔斷平津、包圍唐山、殲擊蘆塘之計畫。”
林彪卻繼續堅持他以三、五兩縱隊使用於南口方面的錯誤主張。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十八時給軍委的電報說:“已令三、五兩縱全力向南口前進,抓住南口之敵和防止平敵繼續北援,並在南口以南尋機殲敵。該兩縱統歸肖(華)、陳(伯鈞)指揮。五縱本晚以強行軍出發,估計十二號早晨即可到南口附近。”
毛主席針對林彪上述錯誤,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九時急電林彪,嚴令“三縱不應去南口”,並告“理由詳另電”,才制止了林彪先打南口的錯誤行動。
全文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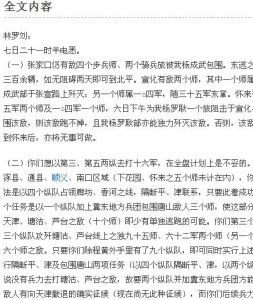 : 準備隔斷平津,包圍唐山,殲擊蘆台塘沽之敵
: 準備隔斷平津,包圍唐山,殲擊蘆台塘沽之敵林羅劉:
七日二十一時半電悉。
(一)張家口仍有敵四個步兵師、兩個騎兵旅被我楊成武包圍。東逃之敵系三十五軍軍部及該軍兩個師,該敵乘汽車三百餘輛,如無阻礙兩天即可到北平。宣化有敵兩個師,其中一個師屬一○一軍,擬向張家口集中,昨(七)日被我楊成武部於張宣路上殲滅;另一個師屬一○四軍,隨三十五軍東竄。懷來有一○四軍兩個師,南口有十六軍三個師。三十五軍兩個師及一○四軍一個師,六日下午為我楊羅耿一個旅阻擊於宣化、懷來之間,如楊羅耿主力昨(七)日能趕上包圍該敵,則該敵跑不掉,且我楊羅耿部亦能獨力殲滅該敵。否則,該敵將於昨日或今日會合懷來之敵逃至北平,程黃到懷來後,亦將無事可做。
(二)你們想以第三、第五兩縱去打十六軍,在全盤計畫上是不妥的。現傅作義有十四個師、一個騎兵師集中北平、涿縣、通縣、順義、南口區域(下花園、懷來之五個師未計在內),你們的首要任務是不使這些敵人逃至天津,其方法是以四個縱隊占領廊坊、香河之線,隔斷平、津聯繫,只要此著成功,北平區敵人十四個師即無法逃脫。你們第二個任務是以一個縱隊加上冀東地方兵團包圍唐山敵人三個師,使這部分敵跑不掉。只要北平、唐山兩區敵人跑不掉,天津、塘沽、蘆台之敵(十個師)即少有單獨逃跑的可能。你們第三個任務是以一個縱隊隔斷天津、塘沽間聯繫,以三個縱隊攻殲塘沽、蘆台線上之獨九十五師、六十二軍兩個師(另一個在天津)及從秦皇島撤回的八十六軍三個師共六個師之敵。只要你們除程黃外手裡有了九個縱隊,即可同時實行上述三項任務。只要你們手裡有六個縱隊,即可實行隔斷平、津及包圍唐山兩項任務(以四個縱隊隔斷平、津,以兩個縱隊包圍唐山。這裡說包圍唐山要兩個縱隊,是說沒有兵力去打塘沽、蘆台之敵,故要兩個縱隊並加冀東地方兵團方能完成包圍唐山之任務)。如果情況緊急,北平敵人有向天津撤退的確實徵候(現在尚無此種徵候),而你們後續兵力未能趕上,手裡只有四個縱隊時,那就只有首先使用於隔斷平、津,使北平敵無法逃脫,以待後續兵力之到達。
(三)在平、津未隔斷的條件下,如果你們除程黃外再使用兩個縱隊去打南口的十六軍,並把十六軍消滅了,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敵早日逃至天津、塘沽的危險。
(四)平、津之敵沒有向西安、鄭州、徐州逃跑的危險,因為我有徐周、彭張兩軍可以阻止其向西安,有劉鄧、陳粟兩軍可以阻止其向鄭州、徐州(我殲黃維、邱清泉、李彌、孫元良等四個兵團三十四個師之作戰可於十天內外解決,然後我軍在隴海、淮河之間須有一時期休息)。
(五)平、津之敵沒有向綏遠[10]逃跑的危險,因為我有八個縱隊在平綏路。
(六)平、津之敵有向青島逃跑的某種危險,因為我在天津、濟南、青島之間沒有兵力。但此種危險不大,因為敵人由天津經濟南到青島,比較我軍由徐州附近到青島之路程要長些,我軍可以由徐州到膠濟線去截擊它。
(七)敵人逃跑的主要危險是海路,但一則津、塘港口快要封凍,二則船隻不足,三則傅作義此時尚無此種準備。他的方針現在還是固守平、津、唐。張垣有敵二萬餘被圍(圍而不打),亦使傅作義難下棄之不顧、單獨逃跑的決心。
(八)因此,你們仍應靜候後續兵力到達,準備實行隔斷平、津,包圍唐山,殲擊蘆、塘之計畫。
(九)如果我能包圍下花園、懷來之敵,那就是最好的形勢。
軍委
八日七時
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
相關資料
林羅劉,指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當時分別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政治委員和參謀長。指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二十一時三十分給中共中央軍委的電報。電報說:為確保殲滅傅作義全部及南口之十六軍,擬以先頭部隊之第三、第五兩個縱隊立即經平谷與順義附近,以五六天行程插到南口附近,參加作戰。屆時如北平、張家口間戰役結束,則我之先頭兩個縱隊即轉至北平、通縣以南,防止平敵南逃。我後到之各縱的行動,擬依爾後北平敵情決定。如平敵繼續退天津,則我各先到縱隊均插至北平東南堵擊敵人。如屆時已判明敵守北平,則以我後到部隊包圍唐山和切斷平津聯繫。
楊成武,當時任華北軍區第三兵團司令員。
指楊得志、羅瑞卿、耿飈分別任司令員、政治委員和參謀長的華北軍區第二兵團。指程子華、黃志勇分別任司令員和參謀長的東北野戰軍第二兵團。
傅作義,當時任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
徐周軍,指徐向前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周士第任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的華北軍區第一兵團。彭張軍,指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張宗遜任副司令員的西北野戰軍。
劉鄧軍,指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的中原野戰軍。陳粟軍,指陳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粟裕任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的華東野戰軍。
黃維、邱清泉、李彌、孫元良,當時分別任國民黨軍第十二兵團、第二兵團、第十三兵團和第十六兵團司令官。
綏遠,即綏遠省。見本卷第82頁注。
平綏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綏遠(今屬內蒙古自治區)包頭的鐵路,即今京包鐵路。
張垣,即今張家口市。
出處: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